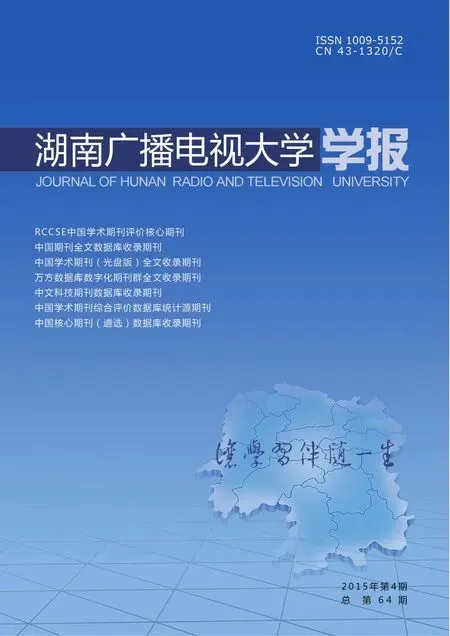理想与现实的流转
——从《边城》到《长河》看沈从文的“蜕变”
吴伟
(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青海西宁 810008)
理想与现实的流转
——从《边城》到《长河》看沈从文的“蜕变”
吴伟
(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青海西宁 810008)
沈从文最引人注目的两部作品,从《边城》到《长河》,一直被认为是从理想到现实的转变,这两部作品甚至会被认为是作者风格转变的标志。但从这两部作品的创作背景和灵魂人物分析来看,并非是如此简单的从理想向现实的转变。无论是浪漫中带着哀婉的边城牧歌,还是充满生活气息现实关照的智慧长河,本质上始终闪耀着沈从文对自然人性执着的追求。而沈从文的这种重建传统自然文明的执着追求,不仅仅是中国现代文学一份独特的贡献,也是当下“城里人”反思自身行为状态的一面镜子。
执着;冲突;自然人性;现代文明
沈从文,从一开始被忽略在文学史编订的范围之外,到七八十年代日渐受到重视,直到现在已被推到极其崇高的地位。毋庸置疑,沈从文的文字乃至他本身的存在,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都是一个特别的贡献。而他最受关注的两部著作《边城》和《长河》,长时间被当做研究他思想转变的切入点。对于这两部作品,哪部更可代表沈从文的创作成就,也引发了长时间的争议。特别是关于这两部作品的理想与现实的相关定义,更是引发了众多读者和学者的种种解读和思考,形成研究领域别样的风貌。在这里,笔者将深入两部作品本身,并结合当下已有的观点加以阐述和延伸,以期探究沈从文从《边城》到《长河》带给他自己以及我们当代人的独特意义。
一、创作时间、背景的异同
要分析《边城》和《长河》的创作背景,不能绕过沈从文的另一部作品,即在1932年沈三十多岁时完成的《从文自传》。在三十几岁的年纪写自传自然是显得太早了些,然而,随着《边城》和《长河》这两部带给他巨大声誉的作品的出版,人们就不敢再轻视这本三十几岁就写出的自传了。《从文自传》以散文的形式描述了自己正式“从文”之前的生活经历,无论是风景还是人事总能被联想起沈后来的作品。这部作品与其说是“自传”,倒不如说是沈寻找自我的一个契点。分析沈后来的作品,《从文自传》无疑是沈从文真正认识自己的湘西世界的起点,自此沈找到了自己所擅长的写作特色。这对《边城》和《长河》的完成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铺垫。
《边城》完成于1934年4月19日,是沈从文第一次返乡以后极大感触的结晶。这时候的故乡已经和他在《从文自传》中描写的湘西世界有了很大的不同,那些他曾以为一辈子都会烂熟于心的人情和风物已然变得陌生起来。加之少年时见到屠杀苗人、拷打乡下人等野蛮残忍的行径在心底悄悄衍生的愿望,与现在失落的心境一拍即合,使作者看到当下扭曲的人性和混乱的局面,他希冀重建美好的自然人性与和谐的人际关系。正是这样一种强烈愿望下的奋笔写作,使得《边城》凝聚着作者许多痛苦回忆的同时也最大程度地闪耀着作者美好理想的灿烂光芒。这也是为何在读《边城》时既读出了浪漫轻快的田园牧歌情调,也读出了挥之不去淡淡哀伤的挽歌情调的原因。
在沈从文创作《边城》时还提出过,他将会在另外一部作品中来描述边城世界拥有保存完整自然人性的乡下人在面对内战与新文明时会变成怎样的模样。这可以说是《长河》创作的酝酿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沈从文南下途中又一次返乡,这次返乡的短暂居住经历伴着“现代”的雷声,于硝烟战火中他心情异常复杂地再一次写出了熟悉又陌生的故乡。这部沈曾计划展现战争时代下的湘西如何被扭曲、被拯救的宏伟巨著最终并没有如他预期的那样顺利完成,由于历史原因,《长河》只完成了一卷,并且直至1945年才第一次正式出版,由于多次审查与删改,稿子从最初的14万字变成11万字,最终流传下来的《长河》不得不说是少了许多原有的深刻和睿智。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否认《长河》的艺术成就,即使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长河中与其他巨著相比亦不会黯然失色。
虽然沈的《边城》和《长河》创作相隔四年,可是不难看出这两部作品的内在本质是一脉相承的,都是意在希望给人以勇气和鼓励,并且沈也切身实际地践行了,先把理想的轮廓描绘出(即《边城》中描绘的纯净和谐的世外桃源),给人以无限期待,而后再给出困境和阻碍(即《长河》中出现不再秉承平等友爱的处世格言的保安队长、师爷等人物),一面担忧一面又明白地指出有希望、勇于追求理想的人即使遇到困难也绝对不会轻易放弃。
二、灵魂人物的性格、命运的异同
《边城》被誉为“诗一般的小说”,《长河》最初发表时更是以散文形式单章发行,靠的本就不是人物和故事情节出彩,因而实际上也谈不上什么主要人物。可是这两部作品却也实实在在存在着所谓的“灵魂人物”——让人过目不忘的拥有独立生命的人物。
《边城》尤以翠翠最为出色。这个生长在一个叫“茶垌”的小山城里的“小兽物”,“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沈从文在这里并没有正面描写翠翠容貌如何美,而是从自己的“乡下人”角度将翠翠融入大自然,突出其乡下姑娘特有的自然美。纵观整部作品,其实开头这段对翠翠的描写也是对其性格和命运相对非常完整的概括。纯洁、美好、健康、自然、聪慧、乖巧又隐隐预示着“黄麂”似的命运。黄麂,一种随时可举步逃入深山的动物,如翠翠一样,最终还是属于这美丽的小山城,自由而又忧伤地奔走于山水间无尽地甜蜜地等待着。这样的小兽物在《长河》中就变成了夭夭,她们相似又相异。
翠翠因着只有一个祖父的原因,天真中带着几分忧郁,轻灵美好犹如在画中。而夭夭则不同,她有父亲母亲和强壮的哥哥,还有老水手这样充满生活智慧的喜爱着她处处护着她的“满满”,相对于翠翠的傩送,夭夭也有着一个还未正式登场的未婚夫,这样美满和热闹自然是不寂寞的,所以,夭夭有着更明媚的爽朗和坦率,似乎从不知忧愁为何物。在“摘橘子”这一章节中尤其将大自然式的活泼和“野气”表现的淋漓尽致。夭夭身上展现出的是迥然不同于翠翠的生命力和自由泼辣的性格。这样的对比隐约透露出这样的信息:翠翠是完全属于大自然,是完整地融于神秘的古老的原始性文明的;而夭夭因为家庭的缘故或许还掺杂着时代的影响,带上了更多的生活气息,也就是俗世中的烟火气息,是经过现代文明浸染以后的“小兽物”,似乎不再如翠翠般拥有如此强烈的空灵的自然气息。这样的对比也似乎更加证明了《长河》是现实性作品,《边城》才是真正的理想性作品。但是继续细品《长河》中夭夭对父亲的撒娇、面对保安队长的带着恶意的调戏甚至挑逗始终保持着“为两个外乡人的言行可笑”的态度,和哥哥三黑子说到这些当官的欺负人时信心满满认为美好的事物都要长存的样子,完全是沉浸在自己天真的纯善世界里。这种是非分明、明快阳光却又已然经过了现实生活的浸养的小精灵,显然更像是对原始自然文明的升华,更显真实而没有距离感。然而越是这样平静自然的生活调子,越让人觉得像是披着现实外衣的理想的翠翠。
再来看作品中另外两个着墨最多的人物。《边城》中的祖父五十年如一日撑船摆渡,坐船人要额外馈赠东西,老人家总是拒绝,实在拒绝不了便用这些银钱添置些烟叶、茶叶供来往行人享用,是个甘守贫穷又尽职尽守的老船夫。对待乡亲甚至过路人都憨厚质朴、古道热肠,对自己唯一的亲人翠翠更是异常疼爱,竭尽全力地护她幸福。老船夫一辈子守在渡口,似乎过着最平淡无味的生活,但从镇上人对他的尊敬态度和他女儿女婿双双殉情后平静抚养小小孤女来看,又隐隐透露出些许不平凡。这一点很容易和《长河》中与其年纪相仿的老水手联系起来。老水手如老船夫一样实际上是着墨最多、贯穿于整部作品的一个重要人物形象,老水手的身世遭遇比老船夫还要坎坷,就如文中所说“身世如同一个故事,简单而不平凡”,年轻时靠水上吃饭,事业刚顺却又突遭横祸,妻儿遭霍乱全部死掉单单只留下他一人,偏又“气运”极差,船货又出事,再不能翻身。直到两鬓斑斑一无所有才回到家乡吕家坪最终以守祠堂打发余生。然而这两个饱经苦难的老人并没有被坎坷的命运压垮,依然爽朗乐观、勤劳善良、热情质朴,面对惨淡的人生不过是交给了他们自己也弄不清的“气运”来排解,这也是边城世界里上了年纪的人特有的智慧。然而这两个孤苦的老人显然是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的。先不比这两个老人的命运谁的更凄苦些,单单只说他们在垂暮之年对生活的态度,老船夫身边只有一个孙女,因而几乎将自己全部的爱倾注在自己的孙女身上,因而当孙女婚事意外因自己的犹豫出现问题时,又是心焦又是后悔居然连老命都搭了进去。老水手呢,老年时孑然一身,无牵无挂,反而是无事不操心无事不挂念,更显其生命力旺盛,更能承担更能面对意外与“变”。这似乎是在预示着,无论是幼女还是老人,都比沉浸在边城世界不谙世事的人要更坚强更有力更充满生活气息更能应对时代的转变。这是现实发展的规律,更是作者的一种理想状态。
不过也不尽然都是完美的人物,作为《边城》的姊妹篇,《长河》中的商会会长、橘子园主人滕长顺是和船总顺顺同属一个类型的人物形象。他们都是小镇上家道殷实、生活美满且因豪爽仗义、为人公道诚实深为乡民尊敬信赖。但是,他们又因着两部作品不同的时代背景的描写有着很明显的不同。船总顺顺因着面对的几乎全是和他一样的质朴勤劳、简单憨厚的乡民,因而其表现的是更为理想的传统道德的楷模,而滕长顺、商会会长因遇到乘着新文明风而来的保安队长、师爷一流而滋生消极应对与妥协无奈的心理,不知不觉间倒是给传统自然人性蒙上了一层闷闷的灰色。
不过这样的缺憾在年青人身上得到了补偿。《长河》中的三黑子很显然要胜《边城》中的天保傩送一筹。三黑子身上隐隐开始张扬的反抗意识是《边城》中由一个少女的懵懂爱情引发塑造起来的青年男子形象所缺乏的。爱情受挫,天保伤心外出,即是逃避也是排解;傩送因着哥哥的意外事故也怀着愧疚与无措选择离开,留下无辜的翠翠惆怅的等待。或许是一时或许是一世,可无论是田园还是都市,一言不发的离开都不能说成是正面面对的解决方式。这样,相对鲜明的对比就出现了。面对恶势力日益旺盛的火焰,三黑子的一句笑言“我当了主席,一定要枪毙好多好多人!做官的不好,也得枪毙”,正是对应了夭夭那好的东西都应该长久存在的愿望,可见,这群年轻人内心深处存在着可能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有多强烈的保卫美好的决心。从这点来看,《长河》倒更像是《边城》的如何捍卫自己宝贵的自然文明的续曲。
三、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边城》侧重于描述传统道德的标准,意在呼唤逐渐逝去的美好,着重突出沈的理想;而《长河》则是将传统道德和现代文明放在同一个舞台上,令其碰撞,引发冲突,在自然平淡的陈述中更显触目惊心,更易促进读者结合现实深入地思考理想的可实现性。这种冲突因为《长河》中出现的新的人物类型——保安队长,而体现的尤为明显。《边城》中出现的是船总顺顺、老船夫、杨马兵之类的淳朴良善的乡下人,他们所生活的世界或者说正是因为有他们才形成的与世隔绝般的只存在于想象中的世外桃源。没有勾心斗角、强抢欺弱,乡民平等友爱、朴素安宁,你接济我我帮助你,倒也其乐融融、安定祥和。而《长河》中正是出现了保安队长、师爷这样的人物,才让读者嗅到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息。官员腐败、苛捐杂税繁重、民间对政府原始性的畏惧与恐慌,保安队长对橘园主人滕长顺、商会会长半是恐吓半是诱骗的贪占其钱财利益,对美丽无邪的乡间小女儿夭夭的无耻垂涎,以及他和师爷已见端倪的丑恶盘算,对比我们所熟悉的至朴至简的边城世界,无疑充满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躁动与压抑。这里原本是远离所谓“城市文明”的恬静田园开始充溢着防备、算计、贪婪、虚伪、蛮横、争利甚至摧残毁坏。大到最受尊重的商会会长莫名被无赖似的保安队长讹去一大笔钱,小到一个无名村妇单单只是听说所谓“新生活”即将到来而引发的无限恐慌和计量,这里的萝卜溪——本该是另外一座边城的萝卜溪变得不一样了。
最显著的原因便是,从前的边城世界只存在一种处世哲学,一种俊秀山水哺育出来的朴素自然文明,而《长河》中的萝卜溪已经被正日益流行更是得到当局肯定并且正大肆推行的现代都市文明入侵。一介武夫保安队长,风流自赏的最主要原因便是自诩是“省里中学念过书的人,见过场面,和烫了头发手指甲涂红胶的交际花谈恋爱时,写情书必用‘红叶笺’,‘爬客’自来水笔。凡事浸透了时髦精神,所以对乡下女子便有点瞧不上眼”。而这自认为跟这些乡下人不一样的保安队长,不想不仅仅在乡下人橘子园主人滕长顺那里碰了钉子、沟通障碍,在对这存了轻视之心的乡下姑娘面前也是大大跌了面子。他自以为是和这乡下姑娘发生了“爱情”,自说自话,讲些长沙女学生的事,意在“调戏夭夭,点到夭夭小心子上,引起她对于都市的歆羡憧憬,和对于个人的崇拜”,可夭夭自始至终都是觉得这是个可笑的外乡人,觉得他说话不中听,倒是觉得受了侮辱,不愿多理睬这位自以为一表人才、颇具身份的人物。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与行为,反映的是现代都市文明与接近原始的自然乡土文明之间的冲突,更是在本质上折射了沈从文面对现实与理想不得统一的痛苦。他一面痛苦于理想与现实碰撞后显示的不堪一击,一面又不愿放弃理想的美好与天真,他在《长河》中一面厌恶保安队长的丑恶嘴脸,一面又不忍将其作为他一贯的城市题材的角色那样加以辛辣讽刺,企图用温柔的笔触加以嘲讽批判以期读者以及他自己可以看到一个相对还没有被大肆破坏的美丽乡村。他在对现实妥协的同时,也没有放弃他的理想,对于《长河》这部未完成的作品,我们还是怀着很大的期待的,不知到最后,这是一部《边城》的延续,还是一部迥然不同于《边城》淡漠哀愁的大悲剧呢?
四、从未言弃的理想追求
很多人认为《边城》是沈从文对满目疮痍的现实的逃避,而《长河》则是作者智慧沉淀后的勇敢面对与理性分析,因而尽管笔下尽显对理想的温情,却也难逃对无法改变现实的无奈与沉痛。诚然,《长河》是作者人生经验的结晶,是作者揉进理想与现实的心血,是经历过边城的幻想后的清醒与睿智,似乎正合一些已深入人心的结论:《边城》是沈从文理想的极致,而《长河》则是一曲对现实无奈叹息的挽歌。也就是说,《边城》是沈从文浪漫的执着追求,而《长河》则是沈回归无力无奈的写实。可真的深剖两部作品,理想与现实真的就如此泾渭分明吗?
前面分析过《边城》的创作背景,沈是怀着对现实的失望与无助,并且希望借此可为改良人性略尽微薄之力,单单是这一层创作动机,就可猜测到一曲田园牧歌即使是再悠扬动听,却也不会尽是乌托邦的幻想。《边城》里无论风景还是人物的原型都是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不仅存在更是沈烂熟于心的过往。因此,沈靠的不只是他天才的想象,更多的反而是靠实实在在的回忆来描绘那一方向往的。翠翠无可预知的等待,老船夫无法抵御的命运,船总顺顺痛失爱子的伤痛,傩送感情复杂离开不知归期的茫然,虽然清淡浮出,仿佛沉醉于烟雾缭绕的山水草房就可心安,可细细品来,似乎比《长河》那充满世俗气息的调子更显悲伤与无力。是的,聪慧的夭夭在未完成的那部分长河里,大概不会像孤单的翠翠那样只身在渡口撑着永远不会停下的小船,无望而又甜蜜地等待,夭夭是纯净美好翠翠的翻版,却又远比内向略带忧郁的翠翠更有主意,更何况,夭夭还有她强壮结实的哥哥三黑子,沧桑平凡却又不寻常充满别样智慧的满满,她的明天,看似凶险,却一定不是交给命运的被动等待。再看我们前面对人物的分析,夭夭很显然是对翠翠形象的更进一步的丰满,她因为浓浓的生活气息更显真实、饱满,也更易打动人心。若说对比温柔的浪漫与冷冰冰的写实,沈从文偏要在浪漫的尾巴上添上一个浓浓的悲剧,祖父在忧虑中死去,天保在失落中意外身亡,傩送在内疚中茫然离开,翠翠在甜蜜与忧伤中开始无言的等待。而不再如歌如画的充满生活气息的写实中,《长河》却在夭夭处在无形的危险与就要发生大变革的喧嚣气氛中留下夭夭清脆而坚定的“美好的都要长存”的愿望和三黑子老水手总要除掉邪恶的信念。具体描绘出理想蓝图却无法圆满的悲伤,面对艰难现实却永不言弃的坚守,哪个更像是浪漫的理想,哪个又是清醒的现实写照?
答案其实已经呼之欲出,《边城》如梦,梦的操控是那双无形的命运的手;而《长河》是梦醒时努力去追梦的执着,尽管现代文明已经大张旗鼓地侵入乡村,尽管原本宁静简单的小镇或者村头出现了越来越多保安队长和师爷这样的人物,尽管越来越多乡下人选择像商会会长和橘子园主人滕长顺般多些消息多些智慧多些圆滑以求自保,可夭夭、三黑子都还在,边城也就会继续存在。即使并不都如夭夭、三黑子这样保留着完整的自然人性,萝卜溪也始终会以它特别的方式抗衡着城市文明的吞噬。也就是说《边城》更像是沈从文理想的“常”态,《长河》则更像是理想的“变”态。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提到过“农民对于政府的原始恐惧”,略过沈从文本人的道家情怀和人生智慧不谈,我们单来谈谈萝卜溪的村民们对这一恐惧的应对。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愚昧与茫然无措,他们甚至是以一种接近于“天真和欢愉”的态度来应对的。《长河》中第二章《秋(动中有静)》描述了乡下人对“新生活”的理解与反映。尽管这一新名词源于对政府的惧怕而引起乡民的恐慌,但乡下人心思单纯,紧张如那打听个不停的农妇也不过是异常惦记家中埋藏的二十几块现洋钱,而饱经风霜的老水手更是洒脱,横竖家里空空,无论是什么“都并不怎么使光棍穷人害怕”,与其把他后来对“新生活”的一连串猜测和打听说成“恐慌”,倒不如说是他在为自己闲适的生活找些事来做。这是乡下人的生活态度,面对形形色色的“变”,他们坚信只要他们依然坚守他们最朴素最实际的努力和勇气,不害别人,保护好自己的同时也希冀联合同类人一同抗争就能保护本应有的生活状态,这也是宁静世外桃源一片祥和繁碌的必要条件。沈从文小心翼翼地描述“新生活”之类的新式文明带给乡村的“变”时,依然坚定地告诉他的读者“常”还在,乡下人的习性都还在,不会因为“变”轻易地就将其“质”扔掉,无论是恐慌还是无措,他祖辈留下的那些细微的反应与心态还是原来的样子。乡下人接触再多新事物,那渗入骨髓里的“旧”还时时在不经意间显露。这种深刻,若非真的融入了生活是无法描绘出来的。而作为“乡下人”的沈从文,他对理想的追求究竟随着现实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也可想而知。
五、结论
从《边城》到《长河》,是沈从文的一场“蜕变”,把读者从梦境带入现实,并不是美梦醒来时的不甘心,更多的反而是一种透彻的恍悟。有着这样美的一场梦,自然是更加强了对这梦的渴望,而由理想之梦过渡到真切现实上来,认清现实自然是必由之路。探析沈从文的意图,唯有给人以鼓励和勇气,永远执着于对理想的追求,我们当下在面对比《长河》中更严重的喧嚣与破坏时,在面对城市文明几乎将我们原始的自然文明逼入绝境,所谓乡下人越来越少,农业户口几乎要成为稀有资源时,才可以怀抱着无尽的希望更从容地应对。这或许是沈从文这特别的乡下人带给我们当下越来越多的“城里人”更特别的启示和贡献吧。
[1]沈从文.从文自传[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6:14.
[2]沈从文.边城·长河[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77.
[3]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22.
[4]甘翠.《边城》评说70年[D].中央民族大学,2005:05.
[5]吴世勇.论影响沈从文创作的六个因素[D].华东师范大学,2005:04.
[6]陶宏.《边城》《长河》中的“常”与“变”[J].时代文学(下半月),2008,(10).
[7]温泉.近十年沈从文《边城》研究述评[J].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6,(07).
[8]李佳慧.传统与现代的矛盾——读《长河》有感[J].当代小说(下),2010,(06).
[9]张永禄.《长河》未竟的中国式“战争与和平”[J].社会科学,2009,(05).
The Transfer from Ideal to Reality:On Shen Congwen's “Metamorphosis”from his Border Town and Long River
WUWei
Border Town and Long River,Shen Congwen'smost notable works,has long been regarded as the symbol of transition from the ideal into reality.But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creation background and the soul of the two works,it is not so easy to shift from ideal to reality.Whether romantic with pathos in the border town pastoral,still full of life breath long wisdom of practical attention,nature always shines in persistentpursuitofhuman nature.And the persistentpursuit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and natural civilization is notonly a special contribution to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ut also amirror for the“oppidan”to rethink their behavior.
persistence;conflict;natural humanity;modern civilization
I206.6
A
1009-5152(2015)04-0026-05
2015—07—08
吴伟(1992— ),男,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根据课文《乡下人家》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