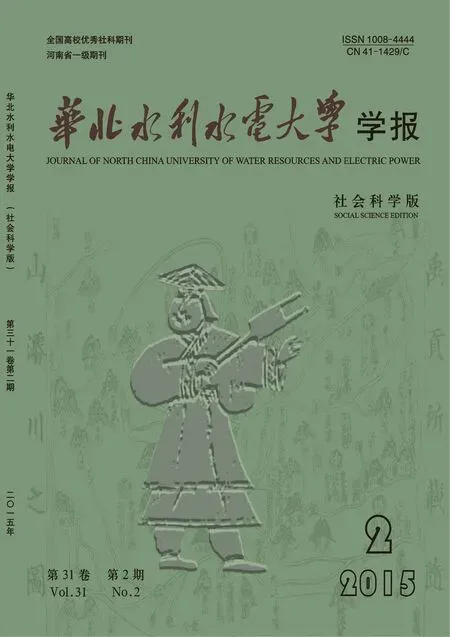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综述
温松峰
(郑州轻工业学院外国语学院,河南郑州450002)
莎士比亚最早进入中国始于1904年林纾的《吟边燕语》,译自兰姆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而非完整的莎剧。因此,此后一段时间,中国莎学并没有发展起来,中国文人缺乏对莎士比亚作品的整体把握,也没有针对单个剧本进行的文学研究。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进步知识分子为救国家于危亡,发起新文化运动,学习西方科技文化,以求摆脱蒙昧,破除封建思想的束缚。因此,莎士比亚也成为这一时期文人的关注对象。1922年田汉翻译的《哈孟雷特》全译本出版。自此,中国的莎评开始发展,开始有众多评介莎士比亚的论文和报刊文章对其剧作的内容、形式和艺术成就进行概括分析。但由于中国文人对于莎士比亚的作品仍然比较陌生,他们对莎士比亚的接受态度是矛盾的,中国的莎学研究也明显落后于西方。因此,这一时期的莎学研究主要依赖西方丰富的莎学研究成果。
一、中国文人对莎士比亚矛盾的接受态度
如西方学术界一样,中国文人对莎士比亚也有比较矛盾的态度,推崇者穷尽溢美之词称颂他,反对者也毫不掩饰对他的轻视。以鲁迅为首的文人出于政治和社会改良需要,十分推崇莎士比亚,借此来表达社会政治主张。鲁迅在作品中数次提到莎士比亚,视他为“作为诗人的英雄”,认为像莎剧一样的文学作品“为国民之首义”,能使国家“自振其精神而绍介其伟美于世界”[1](P64-65)。他还认为,莎士比亚与牛顿同样重要,强国之道不仅靠先进科技,也需要人文学科的成就,“人群所当希冀要求者,不惟奈端(牛顿)已也,亦希诗人如狭斯丕尔(莎士比亚)”[1](P35)。中国也有反对莎士比亚的声音,《文艺月刊》曾刊发过“托尔斯泰论莎士比亚”一文,向中国读者介绍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批判,认为莎剧是抄袭的粗制滥造之作,剧中人物、语言千篇一律。《新青年》发表的“近代文学上戏剧之位置”一文也认为莎剧的思想性不强,最多是能给人带来“极强的刺激”。
中国文人在讨论译介什么样的外国作品促进社会变革时,对莎士比亚也有矛盾的态度。茅盾、郑振铎等人认为翻译外国文学作品要满足译者的爱好,更要基于现实需求,能“足救时弊”。在1922年8月11日的《文学旬刊》中,郑振铎强调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作用:“(一)能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二)能引导中国人到现代的人生问题,与现代的思想相接触”。莎剧无法满足现实需要,所以翻译它们不够经济实用。而支持翻译莎剧的郭沫若则在1922年7月27日的《学灯》中反对郑振铎的观点。“为什么说要翻译《神曲》《哈孟雷德》《浮士德》等书,便能预断其不经济,不切要呢?”认为文学杰作必有超时代的影响力,值得译介到中国。
还有一些文人对莎士比亚的态度前后矛盾,前期是大肆批判,后期是极力推崇,如茅盾、郑振铎、胡适等。茅盾早期认为,莎士比亚是宫廷御用文人,靠“女士的喜欢,贵族的趋奉”才能名噪一时[2](P451),中国需要的是“社会的工具,平民的文学”,“人道正义的呼声”,不是莎士比亚的作品[2](P450)。到了后期,他对莎士比亚又无比推崇。郑振铎后期也给予莎士比亚很高的褒奖,认为其所塑造的人物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莎剧“无有可与并肩的”[3](P212)。胡适早期也贬低莎士比亚:“萧士比亚实远不如近代的戏剧家……他那几本‘最大’的哀剧,其实只当得近世的平常‘刺激剧’。如Othello,近代的大家决不做这样的丑戏!”[4](P392)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胡适抛弃了对莎士比亚的偏见,尽管没有深入研究,但是已经意识到莎士比亚的重要意义,利用庚子赔款积极推动莎剧翻译工作,促成了梁实秋的翻译与研究。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人对莎士比亚的矛盾态度与当时的文化主张密不可分,新文化运动主张学习西方,使中国文人认识到莎士比亚的价值。然而,当时的文坛强调文学的政治实用性,认为莎士比亚有悖于现实需要而反对。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林纾用文言文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分不开。林纾的故事集让中国人对莎士比亚有了一定了解,但文言文有悖于五四运动反传统、反文言文的要求。此外,他还将故事题目变为如《肉券》《鬼诏》等,如此以来,莎剧故事看上去像中国旧式小说,在弘扬文学的革命性的环境下,很容易将莎士比亚的作品看作毫无革命性的消遣文学,将其边缘化。
二、以茅盾为首的政治实用主义莎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腐败软弱的国民政府无力抵抗日本的侵略,东北三省沦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这种政治背景和中国文以载道的传统使这一时期文人的文学创作与研究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他们主动担负起改造社会、革新政治的使命。中国的莎学研究也同样带有深刻的政治烙印,被赋予了较多的政治化思维。茅盾的莎学思想正是基于特定的政治立场,服务政治需要,目的在于服务革命文学创作,服务中国的革命。茅盾最有影响力的莎学评论主要集中在《西洋文学通论》(1930年)、《莎士比亚与现实主义》(1934年)、《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1935年)、《莎士比亚出生三七五周年纪念》(1939年)等论著中。《莎士比亚与现实主义》是中国人首次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莎士比亚的评论,同时也对其剧作的内容和思想进行深刻分析。在文中,茅盾沿袭马克思恩格斯的评论,对莎士比亚是现实主义作家进行了论证。他认为,莎士比亚在剧作中刻画的世界“是现实的世界,而不是空想出来的世界”[5](P316)。这是马克思主义莎评直接服务于中国的现实和文学创作的开端,也确定了中国的莎学研究基调,对当时及后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的莎学批评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莎士比亚出生三七五周年纪念》中,茅盾赞扬了苏联人民大规模传播研究莎士比亚的做法,高度评价了苏联文人的莎学研究立场和贡献,认为苏联人民“真正估定了莎士比亚的价值,把他的伟大和优点发扬了出来”[5](P469)。茅盾沿袭了苏联的莎评者观点。他认为,作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物大都是在与人性中的残暴、伪善和奸诈做斗争,其中所展现的为真理和正义不惜牺牲个人的精神能唤起人们对光明的向往,是值得我们推崇的。他更明确指出莎士比亚作品对于中国现实的指导意义,“在今日,法西斯的群魔比起莎士比亚所写的那些‘恶棍’,更其野蛮,更其没有人性……学习莎士比亚以加强我们的反法西斯的文化斗争的力量”[5](P469-470)。
很明显,茅盾对莎士比亚的现实主义意义进行解读,是受政治实用主义的影响,其政治意义远大于其文学意义。但他的莎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国莎学研究都十分强调莎士比亚的现实主义意义和人民性。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是片面的,也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文学研究的宗旨。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种做法强化了文学在促进社会改良、推动民族解放方面的意义,为中国其他文人提供了一个模范,使文学创作和批评也为救亡图存、变革社会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梁实秋:人性论与无阶级性
梁实秋是中国第一位独立完成莎士比亚全部作品翻译的学者。他还撰写了大量的莎评文章,在1932年到1939年间,发表了莎评文章二十多篇。梁实秋的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为莎剧写的译序和众多莎评文章中,既有对西方莎评成果的综述,也有对特定剧目的研究。曾经留学美国、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梁实秋认为,西方的莎学研究已经硕果累累,中国人应先学习西方学者的成就。因此,他沿袭了西方的莎评传统,译介了诸多西方学者的观点,这使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坛显得比较独特,因为借鉴的西方观点与当时文学政治化的思想不同。梁实秋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反对文学的阶级性和政治实用性,认为将作者划分阶级、断言作家和作品代表某一阶级与对立阶级对抗的做法是狭隘的。在他的莎学思想中,莎士比亚不属于某个阶级,他的作品也不是政治工具,作品中的讽刺和同情都不具有阶级性,任何阶级的弱点都是“文学家的讽刺的对象”,所有伟大的作家对人间疾苦怀有的同情也是“超阶级的”[6](P644)。
在众多西方莎学思想中,约翰逊的人性论对梁实秋的莎学观点影响最大。约翰逊在《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中指出,莎士比亚的剧本“忠于普遍的人性……给具有普遍性的事物以正确的表现”[7](P41)。梁实秋同样认为,文学是人性的产物,莎士比亚的作品之所以得以传承至今,是因为他的作品“有一点普遍的质素”,以“普遍的人性”为基础[8](P125)。四大悲剧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描绘的都是具有普遍性的基本的人性。梁实秋还写过梳理西方莎学研究成果的莎评文章。1933年发表的《莎士比亚在十八世纪》是对英国学者斯密士的《莎士比亚在十八世纪》(1928年)的翻译介绍,让中国莎学研究者了解18世纪西方莎学研究的总体情况,也让文人认识到18世纪和约翰逊在西方莎学研究中的意义,即:十八世纪是旧派古典主义莎学批评到新派浪漫主义批评的过渡;约翰逊既是旧派的终结者,也是新派的开创者,见证了从概括到分析的转变。同年发表的《哈姆雷特问题之研究》介绍了几个十九世纪莎学研究者对哈姆雷特研究有代表性的学术思想,讲述歌德、柯尔律治、哈兹里特、施莱格尔等西方学者对哈姆雷特“拖延”等问题的分析。
梁实秋的莎学思想基于学术层面的探究,对西方莎学研究中的观点和问题都有较好的把握。这种批评实践完全是非政治的、与主流文学批评相悖的,因此,梁实秋遭到了进步文人的抨击,如鲁迅就对其人性论进行了批判。尽管当时基于政治需求所进行的文学批评是主旋律,政治层面的研究压倒了学术层面的研究,但梁实秋依然能坚持不以满足政治需要为文学研究目的,让当时的中国文人全面领略莎士比亚的魅力,开阔了中国读者的阅读视野,在早期的中国莎学研究中起到了很大的引导、启蒙作用,推动了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对中国莎学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总之,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接受莎士比亚的主流的价值标准是满足社会政治诉求,文学创作、译介、研究等领域都表现出了强烈的社会政治功用性。鲁迅和茅盾等人的主张反映了当时迫切的政治需求,让文学发挥了其干预推动社会变革的作用。然而,赋予文学创作和批评过多的政治实用性必然会破坏文学的艺术价值,妨碍人们去感受文学的美。由于这种特定的文化环境,学术层面的莎学研究则比较弱,致使其他层面的莎学研究的价值被忽略,如梁实秋的莎评在当时就没有得到重视。但是,梁实秋所坚持的学术研究思想及其众多莎评文章,也是中国莎学研究的丰富遗产,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莎学研究的发展。
[1]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茅盾.茅盾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3]郑振铎.文学全集(第11卷)[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
[4]胡适.胡适全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5]茅盾.茅盾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6]梁实秋.梁实秋文集(第8卷)[M].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7]塞缪尔·约翰逊.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C]∥莎士比亚评论汇编.李赋宁,潘家洵,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8]梁实秋.梁实秋文集(第1卷)[M].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