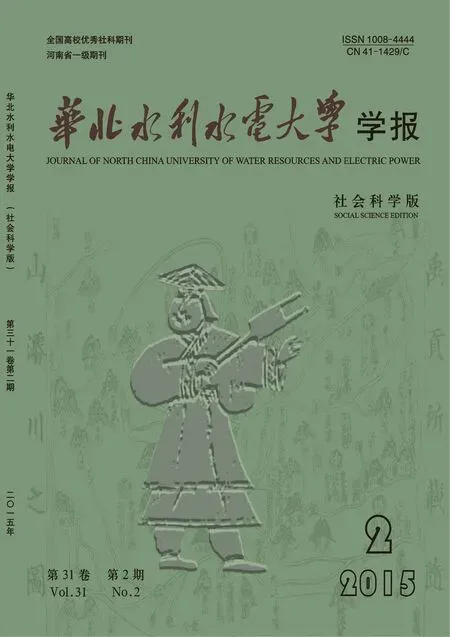河患、迁城与地方社会——以明代孟津县城迁移为中心
张乐锋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200433)
城市作为人类社会活动最为集中的地区,其兴衰、迁移不但是区域环境变迁的反映,同时也对区域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目前针对黄河中下游地区水患和城市迁移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既有从宏观角度对区域城市分布变迁的研究,也有对单个城市的迁移与衰落的研究,两者主要侧重于河患导致城市迁移的频次与历次城址的分布,对于单次城址迁移的过程和城市迁移对当地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则较少注意。
孟津位于黄河中、下游的过渡地区,历史上一直是重要的黄河津济处。相对于下游频繁的决溢而言,孟津段的河患更多表现为黄河侧蚀造成的河岸消长。明代孟津县地狭民贫、差役负担繁重,嘉靖年间黄河水患导致的县城迁移改变了原有的驿道格局,使得孟津当地负担加剧,地方官绅联合行动,取消协济,展现了自然环境、国家制度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明代孟津县环境状况
孟津县设于金代,后世因之。明代孟津县属河南府,南临邙山,北滨黄河,山河表里,“邙山与河越崤、函谷东下,相并而走于津,弥望皆山,河从山口流出,固无所谓原野也”[1](P117),县境整体呈东西向带状沿黄河南岸延伸。境内地形以山地为主,平地稀少,“孟津为郡之北鄙,半阜半洼,形如引弓。论壤地者,无取也”[1](P117)。全县耕地面积共计三千五百余顷,其中黄河坍塌、山石以及三、四等地又占去半数。黄河经山陕峡谷出三门峡后,至孟津“河谷到这里骤然开阔,河流南北摆动的幅度也更为广大,因而对两岸的侧蚀也较以上各河段为显著”[2](P139)。黄河河身南北摆动造成“水涨则横绝民田,水落则泥沙壅岸”的情况[1](P120)。耕地面积狭小,从而形成“地狭土瘠,耕百亩者十无一二家,山角水涯犹力争垦”的景象[1](P162)。
明初,经过元末战乱,孟津县民户稀少,“洪武中编户三千七百九十二,口二万三千六百九十六”[1](P147),至嘉靖年间,户口增长缓慢,仅“户四千六百五十五,口六万九千三十四”[1](P147),由明初二十五里,至嘉靖间归并为十八里[1](P146)。土地狭窄、贫瘠,民户稀少,使得孟津县经济萧条,以至于形成了“民性多梗,告讦繁滋”的风气[3](P20)。
孟津作为黄河中游重要的津济处,“东连巩洛,西据谷城,邙山面其南,黄河枕其北。陕蜀之通衢,蕃夷之贡道”[4](P1100)。县内分布有诸多黄河渡口,“西有硖石津,又西有委粟津,又有高渚、马渚、陶渚,皆为大河津济处”[5](P938)。交通地位的重要使得孟津民众差役负担沉重,“大渡之船,岁时办二十余只,舟师弓兵额办百名,驿使旁午交驰于道”,再加之徭役、田赋等,“民已不堪其劳瘁矣”[1](P290)。明代孟津县“地狭民贫,户口仅足以当临邑之半”[1](P290),而且“山僻,粮重”,以至于民众“多逋”[4](P1100-1101)。万历年间,王士性游历中州时,有“孟津在邙山外,止辖河坡一带,纵不过五里,横十之,与新安二县为洛中最下而疲”评价[6](P227)。
二、黄河水患与新城营建
金代设孟津县治“于古渡口桃花店西一里柳林”[1](P115),利用唐代修筑的永安石堤,以资屏障[4](P1100)。元初因袭金代旧址,后“以潴水浸城,徙治于柳林之西二里永安里,北枕黄河,南临渐池,无城郭”[1](P116),仍旧注重永安堤的防护作用。明初沿用元代城址,县城“南距山,北滨河,即以垣屋为堤岸”,虽然已是“势甚阽危”,但由于明代前期黄河以北岸侵蚀为主,“初河趋北,岸南之势缓”[7](P232),孟津县城得以保全,而且于城外修筑夏公堤以期稳固[1](P126)。
明代中期以后黄河逐渐南侵,孟津县城所受的威胁随时间推移而愈加严重,以至于“每暴雨愁霖,汹涛迅沛,或上流滔天,昏夜骤至,目不及瞬首在前,百姓奔呼荡析,莫知其极”[7](P232),永安、夏公等堤终未能阻挡黄河南侵。嘉靖十一年(1532年),“壬辰(1532 年)夏六月夜,大水溢,坏襄县郭”[7](P232),尽管之前已有迁城之议,但“识者已谓当迁而横议于心,乘舟臭载”,直至此时“民始震恐,咸黜乃心而图迁之议决矣”[7](P233)。
壬辰水患后,从时任知县易诏“当河决之患,因湿成庳,知府怜之,辞官而去”的经历知孟津县城环境之恶劣[3](P23)。三年后,“嘉靖乙未(1535 年)之春,予(王邦瑞)驻孟津舍北署,河水齿厅事殆尽,波声震撼,几席间令人食不下咽,回视向之民居,栉比鳞次者,皆荡荡然水中”[7](P233)。而数年间未有迁城之举,一方面由于知县易诏虽“犹力疾请迁县治”,但“檄未下”,因病“乞归”[8](P535)。知县更替,迁城事务缺乏主持者,而且孟津地狭民贫,缺乏迁建新城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在于明代中央对于地方的严格控制。按《明会典》:“凡军民官司,有所营造,应申上而不申上,应待报而不待报,而擅起差人工者,各记所役人雇工钱,坐赃论。若非法营造,及非时起差人工营造者,罪亦如之”,虽有“其城垣坍倒,仓库公廨损坏,一时起差丁夫军人修理者,不在此限”的规定[9](P825),但从后面迁城的整个过程看,依然严格遵守此规定,申报程序繁琐,行政效率低下。此外,县城作为地方社会的中心,其迁移涉及多方利益,因此“时县令曾君钊陈利害,上之巡抚都御史简公,巡按御史蔡公,又谋及藩臬,谋及守长,谋及父老,谋乃卜噬,乃具疏以闻,遂蒙谕命”[7](P236)。
在得到迁城许可之后,河南知府黄玠“度地得旧城西二十里,名圣贤庄者,去河远而土壤良,乃用牲焉”[7](P237),兼顾城市安全和地形条件,《明世宗实录》则明确道出其城址选择的意图,“迁河南孟津县治于圣贤庄,避河患也”[10](P3812)。
新城营建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经始于丙辰(1536 年)春二月,讫工于夏五月”[7](P236),由“时分守少参任公,既而张公为之经营规制、劳来群黎,太守张公实综理之,乃委别驾韩君溉往督其役”[7](P236),四个月左右的时间完成了新城的主体建造,“坛、城郭、县治、学校、公署、民舍一切民社之务,秩秩具举”[7](P237)。新城营建费用通过土地买卖等方式筹集,“酌街衢之地以授民,取直以充用”[7](P238),并以此种方式吸引民众,但新城迁建之初,“比屋未集”,人口稀少。第二阶段,则主要针对新城“比屋未集,润色未遑”的问题,“继以分守少参李公、大参冯公、分巡佥宪翟公、吕公属之郡守钟公复申命增饰之”[7](P238),具体事务则由时任孟津知县王尧弼主持。“陋者崇之,隘者拓之,缺略者补之,若祠前哲以导化,树仁爱以表坊,遏捷径以周行,合市廛以致众”[7](P238),从而使新城成为所谓“四民悦聚,毂击肩摩”的“弦歌之区”。但“吏兹土者非一人,视其民之胥沉,议及十余年,始克迁者,岂非任重者有待然乎。抑安土重迁,古以为难”[7](P238),表明新城对于当地民众而言非为首选,更多地表现为政治权力干预的结果。
从河南知府黄玠的选址原则“去河远”可知,官方试图通过迁城来彻底改变孟津饱经河患威胁的状况,而由新城的开发情形看,这一措施尽管使得作为行政中心的县城远离河患,却与更多从经济角度考虑的地方民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背离。新城的选址忽略了交通等其他重要因素,最终对孟津当地社会产生了始料未及的影响。
三、驿递负担与地方应对
从孟津全境的形势来看,“邙盖如弓,河界如弧,中铺一带平壤”的地势[1](P117),仅中部地带平坦适宜建城。虽然新城较于旧城而言,无河患之忧,却远离黄河渡口,旧城因其重要的交通地位而设有孟津巡检司。孟津新城位置与驿道格局的背离,在当时的驿传制度下给当地社会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明代“因地理要冲偏僻,量宜设置”驿站,“以便公差人员往来”[9](P735),而孟津县城“设当孔道,使车往来者相辄于途”,却“素无驿递”[1](P296)。其实,“素无驿递”当就洪武初年以后而言,因为“洪武元年革水军府复为孟津县,置官……递运所……旋移递运所于孟县”[8](P126),说明洪武初年孟津应当设有递运所,同时也反映出孟县与洛阳之间往来便利,“盖敝县东北有河阳县,西南有周南驿,相隔七十里。嘉靖十三年(1534年)以前,县治在黄河渡口,与河阳只隔一水,故从北来者,驻河阳;从南来者,驻洛阳,各自应付,与敝县无干也”[1](P277)。因孟津旧城位置适中,河阳至洛阳间路程可一日走完,故孟津县只有佥夫摆渡之责,无承担食宿、马匹之役。
明代驿递差役的佥派原则是“其佥点人户,先尽各驿附近去处佥点,如果不敷,许于相邻府县点差”[9](P736)。正因孟津未设驿站,而位于东西驿道的渑池硖石、陕州义昌、新安函谷、洛阳周南四驿差使往来不断,负担沉重,如明代陕州设有甘棠、硖石二马驿,硖石、七里店、横渠、张茅四递运所,“所以以供往来支运输也,因地当要冲,而交通阻塞,而天下有事,陕民更日不暇给”,两驿四所费用,“每岁达万两以上,以供应之役”,若无他处协济,只能“卖儿贴女为之赔累者”。在此情况下,孟津“以故本县站银编出外县协济千余金,事势固然”[11](P369)。孟津县“先年编驿马五匹入硖石、义昌走递,后改前□入周南驿四匹,函关驿一匹”[1](P297),而且“每马仍帮三马、三夫,岁费千金”[1](P297),对于地狭民贫的孟津县而言已十分沉重,“供亿益繁,卒使劳□□□宁岁,馁婿者无停积。故民纷纷塞道控诉,此实利害切身,亦不得已而鸣也”。尽管“戊午年(1558年)巡按杨公右河观风孟津,深念邑小差重,心甚怜之,词批恳至”,但“事竟不行”[1](P298)。
县城西迁之后,孟津的驿递负担陡增,究其原因为“县治改于旧治之西二十五里,夹在两驿适中处所。故从北来者,必渡河而止宿孟津,便于次日过府。南来者多越本府,亦止于孟津,便于日间渡河”[1](P277)。往来差使由原本仅穿县而过,因路途里程增加,而变为至孟津留宿,“往来过客,无日不临,无日不宿”,客使停留期间所需费用皆有孟津本县承担,“倒换皂快,支应饭食,其费可较两驿更倍”[1](P277)。孟津本为小邑,之前虽无直接驿递负担,却因“且阻大河,审敛舟师,造渡船二十有奇”,加之协济负担,已“民乏困之若倒悬”。迁城之后,“驿传一节尤为重累”,协济负担使得“民愈不堪其命”[1](P297)。
由于孟津新城与洛阳、孟县二地间路途增加,差役负担剧增,为本县所不能支撑,故时人意识到了协济的不合理性,认为“夫应付,苦在本县,而站银,协济在外县,是剥腹充人,不均不情,莫此为甚”[1](P277)。然而,协济的取消在当时的制度环境下并非易事,尽管尚无有关裁撤驿站或协济的具体规定,但添设驿站的繁琐程序已能反映其大致情况:“凡新开地方堪设驿,分递运所,或旧设驿所相离为远,往复不便,可以添设。差人踏勘明白,取勘彼处乡村市镇,画图贴说回报,验其里路,远近相同,应设驿所车船马驴数目俱奏,移咨工部盖造衙门,吏部诠官,礼部铸印,合用人夫。行移有司照例佥点”[9](P736)。
明中前期驿传夫役的佥点根据民户税粮数额征收,但也规定“如一户粮数不及百石者,许众户凑数共当一夫”[9](P736),由上文“耕百亩者十无一二家”可知,孟津县绝少有纳粮数十石者,因而协济夫役则有诸多民户拼凑支应,涉及面广。民众取消协济的意愿强烈,并逐渐由以梁桥、杨金等人为首的地方士绅发起。“梁桥,字世资,号裕轩,以例贡任宜兴县丞,恤民隐,除陋规,宜民思之。归里日,里中旧出马五匹协济周南、函关两驿,大为民病,桥力请于令,详请掣回以供本邑走递。里人感其义,勒石墓门志之”[1](P232)。至嘉靖三十七年(1558 年),知县冯嘉乾上任伊始,“首询民瘼,得其实”。在获知地方实情后,冯嘉乾“恳请巡抚石屏胡公、分守凤阿姜公,欲将前马掣回协济里甲”且“二公深嘉其请”,却因“非编造之期,姑令解银二驿,以示存恤,以待编造,通融拨付”[1](P291)。尽管上级承认此等请求的正当性,却碍于“非编造之期”这一制度规定,仍令协济。因此,此次申请虽得到上级首肯,却未获准,随着胡、姜二人相继去职,希望变得更加渺茫。
此后,尽管冯嘉乾在嘉靖四十至四十四年(1561—1565年)间,“力恳大宪详牒凡数十上”[1](P182),却毫无收获,原因之一即碍于有关驿递夫役的编造周期。虽然“天顺间奏准天下驿递夫役每十年一次磨勘重编”,至“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以后,改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所属驿递五年一编”[9](P757),驿递的编造时间缩短,但仍有明确的期限规定。直至嘉靖四十四年,其时“甲子(1565年)适审编之年,冯君复举而申之,署府事贰守蒲阪史君少山即呈白高阳刘公得庵,会太府同州李公临郊至,后先同心极赞,阙成刘公以少参分守本道批准,转详未举而去之。分守吾道惠庵耿公……遂极力移文驿传道安陆杨公,次泉亦□然思以拯之,即于甲子岁,呈请巡抚迟公朐冈,按台颜公冲宇二公,咸剔隐蠹以振废,卹民穷以□□俱蒙批准,周南、函关二驿马缺,以编剩银两□□。孟津县原马五匹遂令尽数掣回走递,至于驴、牛头只,仍令应役”,持续数年之久的申请虽几经波折,其目的已基本达到。
从《司台守令善政祠碑记》末尾所载之人,“惟时乡官县丞梁桥、监丞杨金、知县陈邦瑞……国学生员陈馨……及乡民张隆……蒋仲芳等思诸公之德不忘,乃备书事之始末,属余为文建祠立碑永垂不朽”[1](P291),结合上文所述梁桥“力请于令,详请掣回以供本邑走递”,可推断当时孟津县的士绅阶层在取消协济负担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陈惟芝对于取消协济负担的作用亦十分重要,因此“以请除驿递□□德之公,建惠里祠,春秋享祀”[3](P31)。陈惟芝的《与驿传道郑公书》,表达了作者取消协济负担之恳请,“生孟津鄙人也,过蒙至受,敢以本县疾苦敬陈台下”[1](P277),其有关孟津驿负担之状况上文已多引用。陈惟芝恳请“试一查之,必有恻然动心者”,并且通过多方游说以扩大影响,“昨生已与司院公祖言其情,皆以鄙邑站银应掣回本县”[1](P277),试图增强其说服力,并增加驿传道之压力。由“生即达于本县,申请而处置则在台下。倘若申到,乞批允查豁,或未申到,亦乞据禀一查”[1](P277)可知,陈惟芝之信当写于孟津县申请协济的关键时期,并且起到重要的作用,“为其邑豁传金七百余两,请粟活饥,里人祝于社”[12](P9355)。
孟津县城的迁移改变了原有的驿道格局,导致驿递负担的增加,对于本已疲敝的地方社会而言,不堪忍受,进而力图取消之前的协济差役。地方士绅与官员在遵照明代驿递制度的情况下,多方运作,使得免除协济负担的申请得以批准,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展现了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
四、余论
黄河水患导致的孟津县城迁移,改变了当地原有的驿道格局,使得本已疲敝的孟津社会负担剧增,协济差役经地方各界努力而取消,展现了自然环境变动下,城市迁移对地方社会造成的影响,反映出环境、制度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相对于城市选址的研究,对城市迁移与地方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薄弱。中国古代,尤其是明清时期作为传统社会的总结时代,各项制度十分完备,中央对于地方社会的控制力度空前。同样,此时期也是所谓“明清小宇宙期”,自然灾害频繁,交织了自然、制度与地方的问题,现象繁多。黄河中下游地区尤甚,河患频发,沿黄城市屡受水灾。诸多城市,尤其县城多次迁移以躲避水患。县级政区作为国家统治的基础,管辖着区域内的赋税、差役等各项事务,与民众关系也最为密切。伴随基层政区行政中心迁移的是因政府制度规定与地方实际背离而产生的地方社会的一系列变化。因此,从环境与制度的视角,对灾害多发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聚落、社会变迁进行研究,努力探究其发展演变的内在机理与规律,对理解此地区今日之自然和社会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1]赵擢彤.孟津县志[M].清嘉庆二十一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
[2]史念海.河山集(二)[M].北京:三联书店,1981.
[3]徐元灿.孟津县志[M].清康熙四十八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
[4]顾炎武.肇域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5]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王士性.广志绎[M].北京:中华书局,2012.
[7]王邦瑞.王襄毅公集[M].明隆庆五年刻本,上海图书馆藏善本.
[8]施诚.河南府志[M].清乾隆四十四年刻本,国家图书馆数字方志.
[9]申时行,等.明会典[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0]张居正,等.明世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1962.
[11]欧阳珍.陕县志[M].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12]顾秉谦,等.明神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