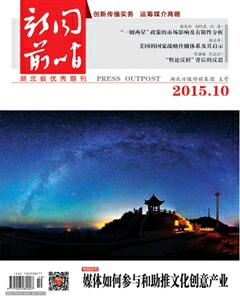网络视频狂欢研究
◎余存哲 郭蔓
网络视频狂欢研究
◎余存哲 郭蔓
2015年是网络视频在我国发展的第十年,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和网络技术的不断提升,以及网络视频行业的日渐成熟,网络视频用户规模以及用户使用率的不断提高,用户的媒介使用习惯逐渐由单向传播的传统电视转向了注重互动与分享的网络视频。[1]与此同时,“媒介形式的多元化和新媒体所具有的海量、交互、超时空等特性使新的传播范式中‘人’本身成为传播的主体,个人表达得到充分的体现”。[2]雷军印度发布会被众多网友重新剪辑制作的《Are you ok?》系列音乐在网络上迅速传播,由此可见,网络视频作为新媒体的重要组成形式之一,网民在视频语言上也实现了话语权上的觉醒。本文将以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为视角来关照网络视频的狂欢现象,在填补研究空缺的基础上探讨网络视频空间的对话特点,以期为网络视频的快速传播提供参考。
狂欢理论网络视频大众文化
一、狂欢理论与网络空间
(一)巴赫金的狂欢理论
对话理论和狂欢理论是前苏联思想家巴赫金的核心思想。民主平等的对话方式、反对命令和服从命令的交流形式构成了他理想的对话世界,全民参与、不分等级、荒诞戏谑、充满粗鄙成为巴赫金狂欢世界的逻辑规则,这也同时形成了他对于狂欢节感受的四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随便而又亲昵的接触”,即无序性,任何人之间的任何距离都不复存在,原本不可逾越的等级秩序被打破,人们成为平等的参与者;第二个维度是“插科打诨”,即颠覆性,这同亲昵接触紧密相连,颠覆了人与人之间原本的联系;第三个维度是“俯就”,即解构性,用狂欢化的思维范式来审视和建构世界,神圣同粗俗、崇高同卑下、伟大同渺小、明智同愚蠢等混合联姻,结成一体;第四个维度是“粗鄙”,即民俗性,充斥着冒渎不敬和对神圣文字和箴言的摹仿讥讽。在狂欢节上,小丑“加冕”为国王,又通过“脱冕”被打倒。[3]如此,小丑与国王的颠倒,最高权力象征物的被玩弄,使得“加冕”和“脱冕”的演出,自然浸透着狂欢式的诸范畴。[4]
(二)狂欢理论与网络空间存在合理关联
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开放性、交互性与虚拟性为网民在互联网平台上的狂欢准备了必要前提,在此基础上,网络空间中博客、微博、音乐网站、视频网站等新媒体平台的不断涌现不仅为网民狂欢行为的实施搭建了“狂欢广场”,同时也为网民的狂欢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狂欢语言:文字、图片、音频与视频等多种形式。狂欢理论的乌托邦式诉求与现实品格的辩证统一毫无疑问映射着理想而又现实的网络新媒体传播。
二、网络视频狂欢的突出要件
(一)狂欢广场:作为“自由空间”的视频平台
巴赫金对于狂欢广场的论述出现在他对拉伯雷的“民间广场”文学的分析中,在此基础上,他拓展了“广场”的空间概念:由具象到抽象。在他眼中,“广场”不仅是一个大众聚会的具象场所,更是大众享受感官刺激与理性交流的抽象自由空间。
视频网站平台不仅是一个承载视频电子资源的具象空间,更是一个用户消费与分享视频内容进而获取感官刺激、交流理性思想的虚拟自由空间。大众在现实中获取信息,通过网络视频传播信息,进而使得现实生活再次受到影响。这个过程充分显示了网络视频第二世界与第一世界的关系,同时体现了网络视频平台是一个现实而又理想的狂欢广场。
(二)狂欢语言:“插科打诨”式的视频语言
在巴赫金眼中,“生活就其本质来说是对话的:提问、聆听、应答、赞同等等。网络视频,作为集文字、图片、声音与影像于一体的视频符号,在巴赫金对话理论视域下毫无疑问是绝佳的对话语言,实践中的最近的一个案例更是证明了这一点。
今年上半年,一段关于小米公司总裁雷军在印度的产品发布会的视频在网上疯传,网友经过精心的剪辑配上无厘头的音乐生产出了风靡一时的《Are you ok?》—所谓的雷军个人单曲。笔者在各大视频网站上对包含“Are you ok”、“雷军印度发布会”等信息视频内容进行了搜索,最终得到了数量总和超过两千个的相关网络视频(截至2015年5月17日数据),而这些网络视频几乎都是“插科打诨”式对雷军英语水平的调侃。笔者选取了优酷视频平台中涉及《Are you ok?》内容的前三个视频,对其视频语言进行了简单分析。
从表1中可以明显看出,雷军在印度的发布会本应该是严肃的,然而网友却从中抓住了雷军英语的“重点”,将原视频剪辑成充满重复性、快节奏、搞笑与插科打诨的网络视频,并在网上进行了大范围的传播且引起了超过两千个同类视频的诞生。由此可见,网络视频作为一种视频语言能够承担巴赫金狂欢理论中的狂欢语言的功能角色。
(三)狂欢参与者:“随便而又亲昵的接触”
大众通过网络视频语言的交流是“随便而又亲昵的接触”。根据CNNIC发布的《2014年中国网民搜索行为研究报告》数据显示,视频网站的搜索引擎渗透率已经达到75.2%,可见我国网络视频用户主动搜索视频的习惯已经基本形成,他们收看视频的主要关注点在于所搜索的视频是否满足他们的需要,而并非视频的上传作者,尤其在网络视频狂欢时期,用户对于狂欢内容的需求是第一位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观看视频的消费者与生产视频的创作者之间的对话通过网络视频得以完成。
当筷子兄弟的《小苹果》爆红网络时,网民也发挥自己的想象制作了属于自己的“小苹果”MV。以优酷土豆视频客户端为例,以“小苹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既有爷爷奶奶辈分的广场舞蹈,也有在校大学生晚会的表演视频,还有幼儿园小朋友的可爱舞步。无论视频的主体是谁,网络视频的浏览量都是巨大的。由此可见,这一过程既不会因为视频创作者的身份而有所变化,也不会因为消费者与创作者之间的关系而减弱,因而狂欢参与者之间是“随便而又亲昵的接触”。
(四)狂欢仪式:狂欢参与者的“加冕”与“脱冕”
“网络突发事件如同日常生活中的仪式,发挥着微调的作用。”[5]在网络视频平台上,狂欢参与者可以对任何自己认同的对象进行“加冕”,也可以将任何自己反对或者嘲弄的对象进行“脱冕”,这种身份上的“加冕”与“脱冕”调和着平凡人内心对于第一世界与第二世界的思考。用户在生产网络视频过程中,往往在自己的主观意志的指导下剪辑视频,例如前文中提到的“Are you ok”视频狂欢,用户上传的网络视频将小米总裁雷军“脱冕”为一个英语水平较低的中国大公司总裁,将自己“加冕”为一个英语水平较高的人以调侃雷军的英语。而小苹果舞蹈MV也将音乐“脱冕”为全民化的娱乐产物。狂欢参与者对于网络视频对象的“加冕”与“脱冕”的过程,正是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关照下网络视频狂欢的狂欢仪式。
三、网络视频狂欢的技术动力、社会诱因及文化思考
(一)网络视频狂欢的媒介技术动力
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曾说过:“视觉为人们看见和希望看见事物的欲望提供了许多方便,视觉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一变化的根源与其说是电影电视这类大众传播媒介本身,莫如说人类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地域性和社会性流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孕育了这种新文化的传播形式。”[6]随着Premiere、After Effects等视频剪辑软件在我国的不断发展,更加友好的界面、更加齐全的功能、更加完美的效果使得大众能够轻松将视频剪辑到自己心中理想的效果。打破了传统媒介把关人重重限制的“赛博空间”成为草根们狂欢的秀场。
(二)网络视频狂欢背后的社会诱因
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充满民俗性与趣味性的大众文化也迅速发展,使得过去居于中心地位的正统文化成为大众调侃的对象,形成了独特的后现代大众文化。这种文化中所体现的零散化、去中心化与近距离化等特征凸显出当今社会多元的价值取向。而网络视频在一定程度上缩减了精英文化与民俗文化的隔阂,“通俗艺术的目的是安抚,使人们从痛苦之中解脱出来而获得自我满足,而不是催人奋进,使人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7]同时商业力量也推动了网络视频的视觉狂欢,当今娱乐化消费趋势的凸显,文化成为人们消费的主要对象。
四、结语
(一)话语空间的拓展增强信息传播力
就受众而言,网络视频成为大众表达情感以及娱乐的话语形式,进一步拓展了大众的话语空间;就传者而言,在受众所关注的话题上利用网络视频这种新兴的话语表达形式,结合创意的剪辑形式,进一步精确了传播对象,提高了信息的传播力。
(二)理性面对网络视频狂欢现象
面对网络视频领域的狂欢,我们既要承认它的合理存在,注意到网民狂欢背后的真正需求,同时也应进一步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净化狂欢中“搭车”的不良文化,始终保持开放包容而又文明理性的心态来面对这一文化热潮,网络视频的狂欢才能在保持自身精神内涵的同时健康持续发展。
注释:
[1]吴平:《视频的社会化分享》,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王琦予:《从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看“自媒体时代》,《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3]刘晓伟:《狂欢理论视阈下的微博狂欢研究—以新浪微博“春晚吐槽”现象为例》,《新闻大学》2014年第2期
[4]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5]毛新青:《虚拟世界的仪式狂欢——网络突发事件中的个体自由与社会控制》,《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8期
[6]孟建:《论影像文化传播——兼议后影像文化传播的兴起》,第七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2001
[7]阿诺德·蒙泽尔:《艺术社会学》,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湖北大学楚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