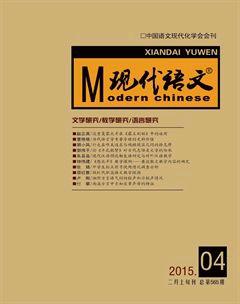鲁迅对标点符号运用的自觉
说到鲁迅先生的作品,我们往往会想到其思想内涵的深刻、人物形象的典型、语言的老道犀利,但我们若再留心文本细部,就会发现鲁迅作品中标点符号的运用也堪称经典和艺术。就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内的作家作品很难找出能在标点符号运用方面可以和鲁迅先生相媲美的。
要说鲁迅先生对标点符号运用的自觉,就要了解一下现代新式标点符号运用的大体进程。我们知道现代新式标点并非我们传统文化所固有,而是经过五四时期一批新文化先驱苦心研究经营,在综合中国传统与西方标点符号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胡适于“1916年6月为《科学》作了一篇《论句读及文字符号》的长文,约一万字,凡规定了十余种符号。”(胡适《逼上梁山》)并宣言他以后的所有文章都采用自己制定的标点符号的格式。《论句读及文字符号》一文可说是我国新式标点符号第一篇系统完整的科学论文。1919年11月胡适首倡并联名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等北大教授向教育部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这份议案是由胡适拟稿,也是与他积极提倡白话文教育相关联的配套方案。1920年2月经教育部批准,这份议案成为我国第一部政府颁行的标点符号方案,这项改革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无疑有着巨大的积极意义。
但标点符号在社会上的推广和运用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这一过程中,鲁迅是积极的践行者。我们提到鲁迅和标点符号的问题,肯定会想到鲁迅为标点符号索要稿费这段典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出版界对标点符号不太重视,在支付稿费时,往往把它从字数中扣除,不给稿费。一次,鲁迅应约为某书局撰写一书稿,由于事先探知该书局不支付标点符号的稿费,因此鲁迅以他的“鲁迅式”的行为方式将他书稿中的标点符号一律省略,通篇没有一个标点符号。编辑看了书稿后,以“难以断句”为由,请求鲁迅加上标点。鲁迅认为:“既要作者加标点符号分出段落、章节,可见标点还是必不可少的。既然如此,标点也得算字数。”书局无奈,只好采纳鲁迅的意见,将标点符号也折算字数支付了鲁迅稿费。从这个小故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鲁迅对标点符号的重视。当然鲁迅对标点符号的重视不只体现在为标点符号争取同文字一样的地位,更体现在对标点符号运用的一种自觉。
他多次著文举例说明古文虽语言精炼典雅,但没有标点符号,不注重语法的精密,往往会语义难明,歧义迭出,给读者造成很大的阅读障碍。大声疾呼“须用新式标点”。在《域外小说集》(1909年)的略例中曾专门列出一条:“!表大声,?表问难,近已习见,不俟诠释。此他有虚线以表语不尽,或语中辍。有直线以表略停顿,或在句之上下,则为用同于括弧。如‘名门之儿僮——年十四五耳——”1919年4月,他通过钱玄同将小说《药》投给《新青年》杂志,并致信钱玄同说:“请您鉴定改正了那些外国圈点之类,交与编辑人;因为我于外国圈点之类,没有心得,恐怕要错。还有人名旁的线,也要请看一看。譬如里面提起一个花白胡子的人,后来便称他花白胡子,恐怕就该加直线了,我却没有加。”这里当然体现了鲁迅的谦虚,但更多的是一种严谨,是一种对标点符号运用的自觉。
在《域外小说集》中,鲁迅还只是用几种符号,到了写《呐喊》《徬徨》时,标点符号的运用已是相当的规范且经典了,可谓是将标点符号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们不妨就鲁迅先生的小说举几个例子来看一看,看看鲁迅是怎样使用标点符号的。
首先看《故乡》,闰土在文章中直接出现过两次,一次是“我”回忆中的童年闰土,一次是“我”回故乡看到的中年闰土。写少年闰土这一部分,作者多用短句,逗号和句号用得最多。特别是句号。闰土说的第一句话是在“我”要他去捕鸟时,“他说:‘这不能。”;当“我”问他看瓜是“管贼么?”他回答:“不是。”;当“我”问到猹是否咬人时,“有胡叉呢。”我们从这些句号的运用,可以看出少年的闰土是多么的神气、多么的自信,多么的自由!闰土心中是毫无牵绊的,闰土是一个阳光、自信、内心自由的小男孩!当闰土第二次出现时,已是二十余年以后了。闰土说了短短的六段话,每段话都不长,最短的只有一句,最长的也不过三句。但这六段话竟用了十个省略号。我们不读文字,只从这十个“……”的密集排列中,也可看到一个欲言又止、吞吞吐吐、窝窝囊囊、痛苦不堪、饱经风霜已失去了少年自信、自由和灵气的令人心酸的闰土。这真可说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笔者认为鲁迅先生并不是无意为之的,而是有意为之。从前面的多个“。”,到后面的十个“……”给读者构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这也许正应了“有意味的形式”吧,可谓耐人寻味。你可见过有这样将普普通通的两种标点符号运用到如此境界的文学作品吗?写这篇作品时是一九二一年一月,新式标点符号颁布运用只有十一个月。真是难以想象!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看当时的情况,那是“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鲁迅《忆半农君》)。当时白话文还处在守旧派的围堵夹攻之中,就在一九一九年的二三月间林纾还在所写的小说《荆生》《妖梦》中欲置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于死地而后快呢。鲁迅对标点符号运用得如此规范、娴熟、艺术,我们不能不说这是因为他的一种文化自觉和艺术敏感。
再看《祝福》:
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
直到十几天之后,这才陆续的知道她家里还有严厉的婆婆;小叔子,十多岁,能打柴了;她是春天没了丈夫的;他本来也打柴为生,比她小十岁:大家所知道的就只是这一点。
《祝福》这两段行文中对分号和冒号的运用可说是规范极了,可以当作讲授分号、冒号用法的范例。
“我问你:你那时怎么后来竟依了呢?”
“我么?……”,
“你呀。我想:这总是你自己愿意了,不然……”
“阿阿,你不知道他力气多么大呀。”
“我不信。我不信你这么大的力气,真会拗他不过。你后来一定是自己肯了,倒推说他力气大。”
“阿阿,你……你倒自己试试看。”她笑了。
柳妈和祥林嫂的这段对话中省略号的运用岂止是规范,简直可称得上艺术了,它可以让读者咀嚼出多少意味来呢:柳妈的诡谲、猎奇、无聊至极和俗不可耐,祥林嫂的有口难言、欲言又止、万般辛酸和一生中难得的一丝娇羞都在这“……”之中了!
这“……”可不是鲁迅信手而来的,鲁迅是很重视这六个小点的。鲁迅先生曾在《“……”“□□□□”论补》一文中嘲讽过那些新文学家在使用省略号时的随意,当时有人任意延伸,有的竟长达大半页,全是小点点,“在洋书上,普通用六点,吝啬的却只用三点,然而中国是地大物博的,同化之际,就渐渐的长起来,九点,十二点,以至几十点。有一种大作家,则简直至少点上三四行,以见其中的奥义,无穷无尽,实在不可以言语形容。”可见当时就是那些愿意接受并积极使用标点符号这种新生事物的新文学家在运用时也是不甚规范的,更遑论那些欲置新文化于死地的保守派了。
鲁迅对标点符号的自觉,不仅体现在自己作品的行文中。1935年11月,鲁迅帮助审阅萧红《生死场》的最后一次校稿,15日在致萧军的信中说:“校稿除改正了几个错字之外,又改正了一点格式,例如每行的第一格,就是一个圈或一个点,很不好看,现在都已改正。”鲁迅这里所说的是标点符号的一条规则,即一行之首不应出现逗号、句号之类。就标点符号的这一条运用规则,现在又有多少人了解且重视呢?我们不也是时常会在报纸、杂志、电视屏幕的字幕上看到那种不规范的用法吗?
鲁迅对标点符号的自觉其实和他对推行白话文的新文化运动的自觉是一致的,像胡适、陈独秀、蔡元培、鲁迅这一批文化先驱毕其一生的努力,就是想将中国文化导向现代化,将古老中国导向现代中国。我们无法想象言文不一、文无标点的中国文化面对当今这个开放的、日新月异的世界将会是何种境地!笔者认为那一代人努力的方向是不容动摇的吧。
参与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胡适.胡适文集[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胡明.胡适传论[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王岱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10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