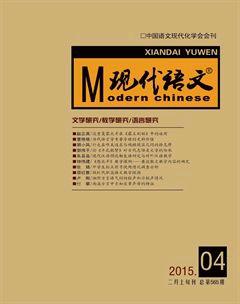坚守在雪域高原上的格桑花
摘 要:祖籍四川南江县的70后作家卢一萍的作品在新疆的各民族作家中是比较有特色的,他一直在先锋写作的道路上摸索、坚守,一直在求新求变,追求试验性、超越当下经验的叙事。他希望在自己的灵魂中重建文学的真理,从世俗世界逐步向精神领域靠近。所以,他一直坚守在对文学创作的探索和试验的路上。他追求生命存在的诗性意义,渴望走向一种能让灵魂憩息的、精神的家园,所以他跋涉、旅行,在出走与回归之间往复。先锋性的书写、生命存在的思考以及浓烈的悲情色彩构成了卢一萍作品的基调。
关键词:卢一萍 先锋性 生命存在 悲情色彩
卢一萍作为一位新疆的新生代军旅作家,他的作品与笔者接触过大多数新疆作家的作品存在不同,体现出一些与众不同之处。这其中有民族性、地域性的内容在里面,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写作淡出主流话语之外,体现了更多先锋性与对生命存在的思考。在题材上,多数以西北,尤其是以祖国边疆为背景来摹写新疆大地上那些令人难以揣测的传奇与故事。卢一萍坚守在求新求变的先锋探索道路上,试图去寻找一种更加纯粹的、适合自己的写作方式。笔者力图从先锋性、生命存在与悲情色彩这三个方面来分析其文学创作。
一、坚守纯粹的先锋
何为先锋呢?20世界80年代之后的华夏大地,伴随着一系列新政策的推行,人们在面临现实市场经济潮流的挑战时,也遭受着外来文化的冲击,人们一直以来信奉的理想与价值观念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质疑。中国的先锋文学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先锋文学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一些自我意识十分强烈的艺术家和作家,本着“不断创新”的原则,试图打破传统规范。先锋派作家们(艺术家)所标榜的这种姿态,实际上是用行动来论证只有颠覆旧的传统,才能开辟新的领域,才能在社会体制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情况下找到一种内在的精神给养。“先锋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这种趋势在东部文坛日渐消歇,然而,中国西部的边地先锋小说潮却意外的兴起”[1]。卢一萍,就是这众多作家中一直背离文坛主流,默默坚守探寻纯粹先锋的一位。
卢一萍作品的先锋性从其执笔写作时就体现了出来。他在军校读书期间发表的长篇小说《黑白》(后更名为《激情王国》)以及之后的中短篇小说《寻找回家的路》就有了一种极为明确的先锋叙事特征,在若干年之后,他的这两本书被选入了丁帆主编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他一直求新求变,力图自我突破。不断进行试验性的形式探索是他的追求,这种形式探索几乎覆盖了他的所有作品。相较于其上述两部作品中荒诞、怪异的叙事手法,在其之后的作品中,卢一萍似乎不注重叙事手法,“叙述不温不火,但其实这是他给读者设置的一个圈套”[2],在这些读起来有种匀速前进的作品故事背后却蕴含着大智若愚的境界与对时代、历史等的思考。其中还蕴含了反讽、象征意味。
他的短篇小说《北京吉普》,写的是生活在帕米尔高原上一个牧人的传奇。在一个时期以前,生活在那片高原上的人都是以骑马代步,纵然之后机动车的出现打破了这一传统,大多数的人依然如此。也许是命运的偶然,身份卑微的牧人“我”用马鞭把自己的情敌马伊尔江的吉普车(其实车是政府配发给贵为县长的马伊尔江的父亲的)抽成了所谓的癞皮狗。理所当然,“我”被抓进了那所从未关押过人的监狱,就因为此事,“我”被当地的人们开始传唱起来,俨然成了英雄一般的人物,这当然是不符实情的。出狱之后,“我”迫于马伊尔江的威胁成为了开吉普车的司机,直到退休。“我”入狱时,美丽的娜依姑娘在等待“我”,出狱之后,娜依理所当然地嫁给了“我”。故事叙述清晰简单,却有着极强的寓言性。卢一萍设置了这样一个带有乌托邦色彩的虚幻之地,人们生活富足,相处和谐,有那么一个长期没有犯人的监狱。然而后来有了吉普车,有了新的意识形态下的县长,监狱里却迎来了它的第一个犯人,这前后的逻辑关系与其中的旨趣值得反思。这让人可以联想到很多当下严肃、沉重的问题。县长能拘押一个冒犯北京吉普车的牧人,也能在其出狱之后让他学习驾驶北京吉普,进而成为自己的专属司机,这里面当然蕴含着更多有关人性的思考。“北京吉普”成为了一个丰富的象征体,在大多数人以骑马代步的时代,“北京吉普”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只有尊贵如马伊尔江的县长父亲才能拥有。文中有这么几处描述,“但每个见到北京吉普的人都会向坐在里面的县长致敬——有时也搞不清他们致敬的对象究竟是县长,还是吉普。”[3]是的,人们致敬的不管是谁,那都是权力的象征。卑微如“我”这样的牧人在做出鞭抽吉普的行为后只能面临牢狱之灾。鞭抽吉普这件事,难道不是普通人对权力压迫的反抗和控诉吗?显然,卢一萍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在新的体制与意识形态下,这种以鞭抽吉普来反抗的行为是那样的苍白与无能为力,到最后只能是徒劳。
在其另一篇带有寓言色彩的中篇小说《索狼荒原》中,卢一萍对一直信奉的理想、历史、价值观念以及人性提出了质疑和思考。小说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新中国成立初期,整个国家百废待兴,新疆也处在屯垦初期,名叫柳岚的年轻女兵,怀揣着报效祖国的理想,奔赴新疆,来到了索狼荒原,然而等待她的却是“分配婚姻”。组织上给她介绍了屡立战功的营长王阎罗,她自然抗命不遵。之后,索狼荒原迎来了发配至此的一些遣犯,其中包括女犯薛晓琼。后来,薛晓琼与营长之间有了感情。虽然柳岚坚持不肯与营长结婚,后来还是在组织的再三坚持下宣布与营长结婚。一段时间之后,柳岚与薛晓琼同时怀上了营长的孩子,然而在双双临产之际,柳岚怀的“革命后代”难产而死,为了爱情,为了不牵连营长而自称怀的是“杂种”的薛晓琼却生下了这索狼荒原上的第一个孩子,之后,薛晓琼赴死。故事至此,相信多数读者与笔者有相同的悲伤与压抑之感。与上述《北京吉普》的叙述方式不同,“应当说,卢一萍的这篇小说让我见识了他另一种小说创造能力,也就是说,他不是不可以做故事性极强的小说写作,而在于他有追求,不愿意以机巧来达成某种个人要求,他是真正的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艺术创造。”这篇小说,包含了作者对历史、人性的思考和认识,体现了他的一种精神向度。小说旨在表现一种历史事实以及人的诡异命运,引导读者去联想、去思考。这篇小说颠覆了传统的历史观念,给读者展示了那段灰色的、鲜为人知的历史。卢一萍在此解构了传统的历史本质、历史规律,放弃了宏大叙事。简简单单的叙述中,以个体生命、灾难人生、存在的荒谬构成历史文本中的主要内容,复活了感觉、欲念等被传统历史理性原则禁锢或忽略的人的非理性因素。与之相关联的历史形态就以偶然性、模糊性、荒谬性、悲剧性等面目呈示,并且充满了一种历史的颓败和荒凉。卢一萍在这里反复书写偶然、颓败、荒凉,使历史在他的“修辞想象”中迷失合目的性的发展方向,原因就在于世界的变幻莫测和人类理想的脆弱。卢一萍自己也说过:“阐释理想的脆弱性成了我写作的主旨。”当代生活的喧嚣和混乱,使他对“此在”产生了一种荒谬的感觉,反常的历史叙事正是他内心积蓄着的这种历史荒谬感的文体展现。
在中短篇小说集《帕米尔情歌》中,卢一萍还收录了许多极赋象征与反讽意味的作品。中篇小说《二傻》中的二傻,《杨烈中尉之死》中的杨烈中尉,这两个形象富于象征意味,同时也是卢一萍自身的写照——对文学的傻劲与追求。卢一萍在阐述自己的写作姿态时这么说过:“其实,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们的小说内在的锋芒就已不复存在。一些在八十年代那种特定的文学环境中博得了声明的、一度才华飞扬的先锋小说作家,为了适应市场化写作的需求,纷纷转换了写作方式,叛离了自己的写作方向,使具有探索、试验特质的先锋写作很快沉入水下,开始了艰难的潜行。”因此,在不断变换的喧嚣和热闹的时代下,卢一萍选择了远离主流,默默地追寻属于自己的创作风格,坚守着纯粹的先锋探索。
二、追求生命存在的诗性意义
卢一萍先生说:“我命如一萍,而路是负载它的河水。我一旦停下来,必然水竭河枯,浮萍萎黄。”他是一直行走在路上的,行走在这被时代污染的大地上,愈行愈远,只为去寻找那生命存在的本质。卢一萍的游记散文集《世界屋脊之书》,讲述了他漫步帕米尔高原、慕士塔格雪山、昆仑山脉、藏北高原以及阿里之后的生命反思。他目睹了塔吉克这个游牧民族的生活状态,领略了慕士塔格雪峰的威严与峭拔,感受了帕米尔高原给他带来的震撼性的压力与高原反应的胁迫,最后沉浸在藏北文化的历史悠久与阿里的神秘之中。这种与大地的亲近,使他感知了世界,领悟了生命的真谛。作为被抛在世的个体存在,他看到了来自生活的伤害与来自时代的污染。在这个市场经济泛滥、人们普遍丧失信仰的时代,卢一萍敏锐地感受到了人内心的孤独。这里,我们不妨来说说魏晋时期的陶渊明,时逢社会黑暗,时局动乱,大多数的文人成了政治漩涡的牺牲品,而他却选择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意生活。陶渊明就是用这样亲近自然、回归自然的方式,完成了对生命悲剧意识的消解,最终达到了一种对生命存在的诗性意义的追求。同样,卢一萍在对现实重新解悟之后,试图在其作品中通过上述先锋叙事来实现对生命存在的诗性意义的理想追求。“《寻找回家的路》中的我、惟、盲人、音乐师都在追寻着一种生命存在的诗性,而现实总是灰暗的,现实的具象图景往往遮蔽或抹煞了生命存在的诗性意义,这使乞丐、流浪汉兼诗人的我在对生命诗性存在的探索中受挫,从而坠入梦幻。于是我就在现实与梦幻之间穿行,时间和空间由此消弭了清晰的界限,时间被撕碎,空间被切割。我就在这样破碎的时空中,孤独地寻找回家之路,辨识自己的恋人、情人和妻子惟。而惟是否存在与惟的真实身份都无法确定,但不论是哪一个惟都既是我的诗性精神追求的拯救者、献身者,又是我的诗性追求中的神性化身。我却因失忆而无法实现自己的寻找和辨识。因此,在我与家和惟之间留下了无法填补的空缺。显然,这里存在着多重隐喻:首先,家是诗意栖居之所,是精神家园;惟是引路人,是家之诗意精神的神性化身,我寻找回家之路的过程也就是人类永难实现而又永不放弃的寻找精神家园的隐喻。其次,空缺与故事呈现的生活史构成隐喻关系,即对不完整生活的不完整讲述。因此,当空缺与空缺造成的荒诞在卢一萍的小说中出现时,并不是作为一个结果,而是作为一个原因。”卢一萍没有陶渊明那么幸运,陶渊明最后达到了那种诗意存在的追求,而卢一萍却无法从宿命中突围,无法找到“回家的路”[4]。但是,他没有放弃“精神新生”与“精神回家”的希望,这也是他一直在远行,一直在路上的原因。
三、挥之不去的悲情色彩
提起悲情色彩,这是中国文学自古至今挥不去的话题,尤其对中国西部文学而言,更是如此。从盛唐边塞诗到五代十国的北朝民歌,再到后来的小说、散文等,悲情色彩永远是西部文学中那颗最灿烂的明珠。卢一萍的作品题材,更多的是与表现中国西部尤其是新疆这块土地有关。他的作品,主要体现了个体生命的悲情意识、爱情与婚姻的悲情意识以及自然环境所呈现的悲情意识。
卢一萍从个体生命与时代的对立出发,反思时代对个体命运的影响,深刻地表现个体生命的悲情意识,从而展现个体在面对现实时的无奈与悲哀。在他的长篇报告文学《八千湘女上天山》中,作者以湘女口述的方式讲述了共和国史上那段悲壮但又被大众抹杀的历史。书中,作者向读者展示了一段段发生在那个年代的悲惨故事:共和国成立初期,大批怀揣屯疆戍边理想的湘女来到新疆这个“西边的西边的地方”,然而入疆之后,她们却大都成了“组织”上发放给大龄官兵的妻子。由此,人生命运急剧变化,她们成为了这大漠荒原上的第一代母亲。从此,远离家乡,远离亲人,为了“革命的需要”,扎根于此。从文本中读者不难发现,作品中所提到的湘女们,她们都多多少少存在遗憾,她们想念湖南的亲人,想念湖南的水,想念湖南那香喷喷的大米,她们对自身的遭遇多表无奈,从她们的口述中,读者能感受到她们的悲哀感。在书的结尾,卢一萍引用了这么一首诗“左公筹边未肯还,引得春风度玉关。王陶屯垦开新史,直叫塞北变江南。御敌湘军称十万,征西湘女过八千;代代湘人戍边来,丰碑座座满天山。”[5]这首诗不仅赞扬了湘女在边疆建设中的巨大贡献,同时也给整部作品着上了浓郁的悲情色彩。在这本书中,湘女们的个体生命悲情与历史悲情得到了完美的契合。
爱情与婚姻的悲情色彩同样弥漫在卢一萍的作品中。还是以笔者在第一部分中提到的《索狼荒原》为例,作品主要以女兵柳岚、连长王阎罗、女囚犯薛晓琼三人之间的爱情为线索来叙述,组织上让柳岚与营长结合,柳岚不从;营长与女犯薛晓琼两情相悦,组织上肯定不许,最后柳岚迫于压力与营长结婚,薛晓琼在为营长生完孩子后选择自杀。柳岚在“被结婚”后,“他颓然地站在那里,觉得自己的整个生命都在崩塌。突然,她不顾一切地冲出了那个地窝子,向着无边的旷野,向着寒冷的黑夜深处没命地跑去。”的确,女兵柳岚心中美好的爱情理想破灭了,从这段叙述中,她心中的悲凉、哀伤体现得淋漓尽致。薛晓琼,这个极具悲剧命运的女人,生下与营长的孩子后,怀着对营长的爱、对爱情的追求,吊死在了一棵树上。这篇小说,作者极赋深情地向读者展示了那个年代中的爱情婚姻悲剧。
卢一萍的作品多写西部题材,涉及了许多西部的自然环境,而这种自然环境呈现的悲情意识实际上就是酷烈的自然物象与人生际遇相结合所产生的孤独感和悲怆感的集中体现,是人在天涯的忧伤:“上路者已没有故乡——哪怕这故乡仅仅是象征性的。”[6]是彻入骨髓的荒凉和孤独:“过了八十里兰干,人烟渐渐稀少,又行50公里,到了普沙。普沙是进入昆仑山前的最后一个村庄。在大山的怀抱里,这个小村庄像一粒尘沙,随时有可能被一阵风刮得无影无踪。”是生的悲怆:“兴干也许为了维护一匹战马的尊严,保持一匹良马的晚节,隐遁到了荒原的深处,隐遁到了雪线之上圣洁的冰峰雪岭之间,隐遁到了充溢着苦难的尘世之外,重新化作了石头。”这样的悲情色彩贯穿在作家的作品中,不仅构成了作品内涵的基本要素,而且也形成了卢一萍叙述模式的重要元色。
卢一萍从未停止行走,就如他自己所说:“我逃避那种喧嚣的方式就是去旅行,用旅行这块石头来磨自己的文学之剑。”他在坚守,并不断地实践和抵达,就像那生命力顽强的格桑花一样,绽放在帕米尔高原、昆仑山脉、藏北高原以及皑皑雪山之间。
注释:
[1]李兴阳:《走出超验世界的边地先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西部先锋小说论》,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2]杨献平:《卢一萍:寓言的边疆——以<北京吉普>和<索狼荒原>为例》,文学与人生,2011年,第9期。
[3]卢一萍:《帕米尔情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4]丁帆:《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5]卢一萍:《八千湘女上天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6]卢一萍:《世界屋脊之书》,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张国涛 新疆伊宁 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83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