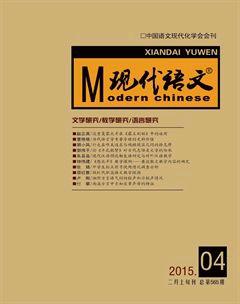梁启超的“新民说”与晚清“政治小说”
摘 要:梁启超的“新民说”动摇了中国传统政治观赖以存在的价值基础,为灾难中挣扎的中国人注入了新鲜血液。“政治小说”,作为“新民观”的传播媒介,也因此大放光彩。梁启超从新民思想出发,对政治小说大力倡导,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古典小说观的进步,为小说地位的提高和文人参与小说创作扫清了障碍;另一方面作为晚清“小说界革命”兴起的一大动因,促成了中国小说的近代转型。
关键词:梁启超 新民说 政治小说 小说近代转型
关于晚清“小说界革命”的缘起,历来众多著述者都认为其产生于生死存亡的历史背景下,既有中国小说自身的原因,也受西方小说外部的影响。关于外力方面,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陈平原在《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中就旗帜鲜明地指出:“域外小说的输入,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文学结构内部的变迁是二十世纪小说的原动力”[1]。然而,内因方面,前贤时哲虽有论著,综其要义,大多围绕晚清社会危机展开,具体到思想根源,却鲜有论著。因此,笔者拟从以下方面对梁启超的“新民说”与“政治小说”的关系略作梳理。
一
戊戌维新失败后,小说成了我国学界最受关注的艺术门类,在时代风气的驱使下,出现了“经世不如八股盛,八股不如小说何”的创作局面。短短十余年,成册的小说译著接连诞生,从梁启超最早创办《新小说》,到1918年徐枕亚创办《小说季报》,先后发行的小说期刊在五十种以上。这种小说势力的单方面膨胀除了与西方小说的移植渗透、印刷业的蓬勃发展有密切联系之外,还不得不归功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其新民思想对文学领域的大力开拓。
近代中国,鸦片战争以一种灾难性的形式叩启了中国的政治大门,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帷幕。之后就出现了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批值得纪念的启蒙思想先驱。然而,这一时期,启蒙思想只是萌芽初现,尚难形成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潮。直到七八十年代,郑观应等人提出“育才于学校”的文化主张,提出在中国开办学堂以学习“西学”。但和前人一样,其思想根源中同样视“西学”为“器”,认为“器”是不能代替封建社会所言的“圣人之道”,学习“西学”只是为了“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因此,这些较早时期的思想家很难使启蒙主义风靡于世,深入人心。
而后经历了大约半世纪之久,直到戊戌维新前后,中国才真正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第一次启蒙运动高潮。谈论第一次启蒙思潮的出现,甲午中日战争自然是一件绕不过去的大事件。而从实际情况看,中国此前也不断在和西方交手,且败多胜少。即便如此,中国在亚洲国家面前,仍抱有一丝优越感和自信心。然而,甲午一战,一向以天朝自居的清王朝败给了同样沐浴东方文明的弹丸岛国日本,朝野上下极为震惊。梁启超叹言“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役割台湾,偿二百兆始”[2]。一时间,从“公车上书”,到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变法维新,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将其全部精力投放到救国大任中,但变法仍以失败而告终。1900年,唐才常等在国内组织“自立起义军”也宣告失败。至此,改良派试图“武力勤王”的计划也相继宣告破产。
经此一系列重大打击,梁启超潜心思索失败原因。于是,通过自下而上以开启民智为核心的“新民理论”应时而生。
二
戊戌维新失败,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亡命东瀛。在日本避居的日子里,梁启超爱国救亡热情丝毫未减,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继续鼓吹改良维新。梁启超“新民”思想主要蕴含在其1902年到1906年以单篇形式发表的一系列政论文中。之后,二十篇文章汇编成册,取名《新民说》。
在《新民说》中,梁启超以洋洋洒洒十数万言全面探讨了对国民性改造的一系列问题。全书开篇,作者就从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谈起,着重论述了“新民”的重要性。由此,他认为提高和改造国民的素质迫在眉睫、刻不容缓,而“新民”的呼唤就成了《新民说》最根本的目的。接着,梁启超又从世界各民族竞争的大趋势,探讨了中国国民性改造的重要意义,提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的论断。在文中,作者言之凿凿地断言:“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3]
在梁启超看来,只有一个有尊严的新民才能够活得堂堂正正。但尊严不是谁想要就有的,也不是任何人都能保住自己的尊严不被他人侵犯的。一个人要活的有尊严,要活的堂堂正正,就需要有权利来保障。若权利丢了,人皆可以欺,何谈尊严二字?何谈堂堂正正做人?然而,权者生于智,所以,要兴民权,就要先开民智。而民智的关键又在德的养成,于是兴民德就成了必经之路。正如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刊词中谈到:“本报取《大学》新民主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能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至此,梁启超以其独到的眼光,完整地提出了“三民思想”,即民智、民权、民德。然而,三者中梁启超尤以民德为最重。他说:“夫言群治者,必曰德,曰智,曰力,然智与力之成就甚易,惟德最难”[4]。
由“公德”概念又间接引出了“群”。“群”之于梁启超着实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早在1896年,他就提出了“以群为体”的民主观,并指出“以群术治群,群乃成;以独术治群,群乃败”。在《论公德》的结尾处,梁启超再次申明了“利群”的崇高地位,“公德之大目的,即在利群,而万千条理即由是生焉。本论以后各子目,殆皆可以“利群”二字有纲,以一贯之也。”纵观《新民说》一书,在《论公德》发表后的十三节皆是对“公德”的阐释和“实行此公德之方法”。由此不难看出,书中谈及新民应具有的国家思想与政治能力,权利与义务思想,自由观念与自治能力,进取冒险和尚武精神,自尊和毅力,无不与“群”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而是否“利群”则成为梁启超评判道德善恶的唯一标准。
今天,从哲学意义上严格来讲,梁启超毋庸置疑是一位极端的主观唯心论者。他最基本的哲学命题就是“境者心造”。梁启超曾说:“全世界者,全世界人类心理所造成。一社会者,一社会人之心理所造成。”[5]而这样的哲学形式表现在认识论领域,势必就要颠倒意识和存在的关系。结合20世纪初的中国情势看,国势岌岌,国人麻木,梁启超的意志决定论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思想言论也,即为其事、其物之母”等一类言论,并不罕见。然而,梁启超这种片面夸大意识能动性,忽视物质的论调;天真地以为只要凝聚某一思想,就可以形成某一类事实的想法。因此,从这样的认识论出发,梁启超等一大批维新人士只能困在文化思想领域转圈子,其关注点也只能是思想文化观念的变革。然而,这一做法却阴差阳错地促成了晚晴文学领域异乎寻常的繁荣和辉煌。
三
因“新民救国”的需要而引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这一论断,正是梁启超基于“新民”思想而得出的全新观点。也因此,小说成了梁启超开启民智最有力的武器。
为了让人们重视小说,梁启超形象地把小说比作空气和菽麦,即“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与呼吸之餐嚼之矣”。进一步,梁启超批驳充斥着“状元宰相”“才子佳人”“江湖盗贼”“妖巫狐鬼”思想的传统小说为中国群治腐败的总根源。而要改变这种腐朽现状,唯有政治小说可以担此重任。于是,梁启超为社会改良开出的第二剂药方就是“政治小说”。
“政治小说”,顾名思义,就是以政治思想取胜的小说。梁启超在《<新小说>第一号》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盖今日提倡小说之目的,务以震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非前此诲盗诲淫诸作可比。”之后,在《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中还给出明确的定义:“政治小说者,昔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其立论皆以中国为主,事实全由于幻想。”从主题方面看,作者强调最多的就是作品的思想艺术,即“小说要有所寄托”。而没有政治寄托,不能启迪民众的政治觉悟,恰是梁启超对旧小说最不满意的地方。也正因如此,梁启超从最初对小说的关注就带有强烈的现实目的和功利色彩。诚如日本中野美代子言:“梁启超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只是在亡命日本时热衷于提高小说的地位。他所说的小说与政治小说几乎是同义词,回到政界后连小说的‘小字也从未提起过。” 这些话虽然带有些夸张的成分,但也基本符合事实。
“政治小说”的大旗一经打出,立刻在当时知识界掀起了轩然大波。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的惊人之语:“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虽然倒因为果,却从社会效应的角度强调了小说的重要性和小说为社会服务的社会功用。如果说,《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是晚清第一篇受西方小说理论影响的小说论著,那么,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则是第一篇以西方小说理论为指导,在前人基础上进行了创新的纲领性文件。文章刊载后,其影响遍及全国,在很长时期内,小说界都以此文为坐标。夏曾佑、狄葆贤、梁启勋、陶佑曾等人纷纷就此发表文章,一方面同声附和“政治小说”的观点,另一方面沿着“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思路,继续鼓吹“新小说”。举人出身的邱炜萲就在《小说与民智之关系》中谈到:“谋开凡民智慧……其要领在多译浅白读本,以资各州县城乡小馆塾,一在多译政治小说,以引彼农工商贩新思想。”[6]更有甚者,燕南尚生著《新评水浒传》,封面副题就是“祖国第一政治小说”。正因为如此,清末“政治小说”被提到至上的地位,“小说界革命”也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得到蓬勃发展。中国小说摆脱传统小说才子、佳人、公案类型的束缚,直接作用于社会的政治小说大量涌现,具有了经邦济世的强大功效。一言以蔽之,从翻译之初起,目的旨在作政治宣传,故所谓‘政治小说之风甚盛。
政治小说在晚清流行不过十几年,但其对之后的小说创作可谓影响深远。梁启超的“新民说”动摇了中国传统观念赖以存在的价值基础,使建立在这一思想之上的传统小说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由梁启超开启的重视“新民”的人性观,到五四时期“为人生”主题的开创,隐隐约约都可见政治小说的影子。从这点讲,梁启超的“新民说”的确为中国小说创作的现代转型打开了先驱之路。
注释:
[1]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
[3][4]梁启超:《新民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
[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余之生死观》,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
[6]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李智婷 山西太原 山西大学 03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