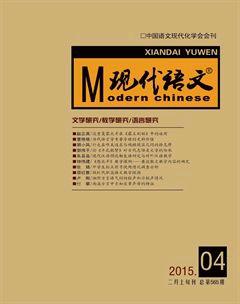论《老残游记》中逸云形象及其悲剧色彩
摘 要:特殊的寺庙生活把逸云铸炼成了一个充满魅力的风尘尼姑,但残酷的现实让她美好的爱情理想终归破灭,她以尼姑而兼妓女的身份混迹于人世的火坑,只好以宗教来自救超脱,但逍遥背后的无奈显示出深沉的悲剧色彩。
关键词:《老残游记》 逸云 悲剧色彩
清代刘鹗(1857年—1909年)所著《老残游记》是著名的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以江湖医生老残的口吻讲述游历中的所见所闻所为,文笔生动,备受好评。作为针砭时弊的谴责小说,《老残游记》虽以社会谴责和景物描写取胜,但其突出的艺术成就也体现在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从第二回“明湖湖边美人绝调”开始,刘鹗以老残之审美视角展现了他对女性形象的深刻理解。而逸云,正是其续集的九回中最具独特生命色彩和性格特质的一位女性形象。
一、逸云整体形象
逸云六七岁便进入了斗姥宫,斗姥宫是一个尼姑庵,“里边全是姑子”。佛教的尼姑,说来均为出家修行,一旦受戒之后,就不得不过上一种心如枯井、身如槁木的非人性、不人道的生活,成了所谓的“方外之人”。不过现实中,她们进入佛门有着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这泰山脚下的斗姥宫便不是寻常意义上的佛门寺庙。它同时还是一座高档宾馆,承担着送迎上山的达官贵人的接待任务,“但凡上等客官,上山都是在这庙里吃饭”。庙里的尼姑也不是寻常意义上的佛门尼姑,她们的生活另有一番景象,她们在精神上被规定了向佛教经典教义学习,追求跳出轮回的大劫,与一般的佛教徒是一致的。而在实际生活中,她们又被赋予了招待员、陪酒女郎和歌女的角色,甚至陪客人睡觉,与世俗风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逸云,便是在如此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位充满魅力的风尘尼姑。尼姑中的风尘女子,风尘中的年轻尼姑,这种兼而有之的双重身份,赋予了逸云特别的性格和独具的神韵。
逸云在斗姥宫一众年轻的尼姑里面算不得特别好看,只是“团团面孔,淡施脂粉,却一脸的秀气,眼睛也还有神”[1],“笑起来一双眼又秀又媚,却是不笑起来又冷若冰霜”[2]。但从这六回的描写中,不管是书中老残一行人还是书外的读者,恐怕都会被逸云的言行举止和眼界思想所震撼。用她自己的话说,皆因“从小全得读书,读到半通就念经典、做功课,有官绅来陪着讲讲话,不讨人嫌。”[3]因此受过教育的她不仅勤快、麻利、细致、周到,而且有见识有修养:她询问扬州隋堤杨柳的下落,关注“扬州八怪”的现状,对每一处泰山景致“到了一个古迹,说一个古迹”,又风雅又泼辣,实在是洋溢着青春的活力与朝气,让人又爱又敬。尤为难得的是,她身为尼姑,却秉持洒脱卓越的爱情观,更使其形象熠熠放光。
二、自由进步的女性爱情观
逸云身为尼姑,却颇具人文情怀,她从自然的人性出发,看重人的爱情,勇于反对宗教的禁欲主义。早在初见德夫人等人时就说:“男女相爱,本是人情之正,被情丝所缚,也是有的。”[4]可见其对情爱的开放。她肯定人性情感的合理,更肯定女性在情感世界中应有的地位,表现出相对自由进步的女性观。
第三回中,逸云在德夫人的询问下坦率畅谈自己的恋爱历程:一开始她便敢于梦想爱情,从第一眼对任三爷的投缘,到渐渐明白自己的女儿心思,她对自己的爱情提前进行了一番疯狂的心理建构。她想象着自己和任三爷恩爱的画面,她想要的衣裳、帷幔子之类的任三爷都买给她,在这个过程中,她获得了心理和精神层面的满足。当然,这得益于师父不干预她的选择从而使她有足够的自由和权力去追求自己的爱人。其后她一反女子的内敛与被动,大胆向任三爷表白爱情。生活在斗姥宫的自然山水中,泰山巍峨广阔、自在洒脱的空间为逸云带来了内心的自由与不羁。“见了标致的爷们,哪有不爱的呢!”她没有想过隐藏自己的感情,而是极为直接、开放、大胆和主动,毫无虚伪和做作,喜欢就是喜欢,爱就是爱。这种思想和行为与《红楼梦》中的妙玉有着天壤之别。当爱情来时,逸云热烈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但就在她将要开始夫唱妇随的平静美好时,她却做出了谁也想不到的决定。因为她不仅想象了嫁给任三爷之后的幸福,同样也考虑到嫁给任三爷之后的悲惨,“再把那有姨太太的人盘算盘算:十成里有三成是正太太把姨太太折磨死的;十成里也有两成是姨太太把正太太憋闷死了的;十成里有五成是唧唧咕咕,不是斗口就是淘气;一百里也没有一个太太平平的。”[5]在比较了现在的处境和以后可能的结局之后,她没有盲目,而是理智地权衡利弊,并最终决定放弃,甚至从此对情爱之事顿悟:回到自己的生活,回归自我。
王国维说:“欲达解脱之域者,故不可不尝人世之忧患。”轻描淡写的果断冷静背后,正是逸云经历种种情劫的历练之后,洞彻人生,达到超脱的境界,以至最后说出“我辈种种烦恼,无穷痛苦,都从自己知道自己是女人这一念上生出来的,若看明白了男女本无分别,这就入了西方净土极乐世界了”[6]这样的佛法。
三、逍遥背后的无奈
在逸云从追求爱情到放弃爱情的过程中,她好像处于主动地位,处处主宰爱情命运,并且在刻骨铭心的故事里终于摆脱烦恼而悟道心净。然而在人人都惊叹于逸云的佛理通达生花妙舌之时,却往往忽略了她的悟禅和“出淤泥而不染”带有很重的悲剧色彩。
首先,从生活环境来看。很小被送到庙里做尼姑的逸云没有家;没有丈夫的养活和庇护也无法生存;所以事实上她根本离不开斗姥宫。而斗姥宫这个“半清不浑”的庙宇,是社会的折射:清代晚期,上层社会奢靡堕落,下层百姓度日维艰,贪官横行嚣张跋扈,读者从靓云被迫下乡的事件里可见一斑:“今儿晚上如果靓云不来陪我睡觉,明天一定来封庙门。”经德慧生这样的“京官”再三威慑,此事才算了结。可见生活在如此环境下的斗姥宫众人,欲求得一生安稳,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只能乖乖顺从,任人摆布。
其次,从社会地位来看。生活在封建末世的大环境和斗姥宫这样一个特殊的小环境中,逸云以尼姑之名倚门卖笑。清净庙堂成了人欲横流的青楼,精神的超越中夹杂着最原始的肉体出卖。事实上,逸云的身份地位是极其低贱的。她与德夫人、环翠谈到自己为人处世的态度与方式时说:“近来我的主意把我自己分做两个人:一个叫做住世的逸云,既做了斗姥宫的姑子凡我应做的事都做,不管什么人,要我说话就说话,要我陪酒就陪酒,要搂就搂,要抱就抱,都无不可,只是陪他睡觉做不到;又一个我呢,叫做出世的逸云,终日里但凡闲暇的时候,就去同那儒释道三教的圣人玩耍,或者看看天地日月变的把戏,很够开心的了。”[7]她仿佛达到了佛教那“忘身忘相”的境界,但这种精神境界只是对不公正命运的一种消极反抗,她的人格是分裂的,精神与肉体是分离的。这种分离,使得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觉苦,反而可以在闲暇中找到精神上的快乐和寄托。这种快乐是黄莲树下弹琵琶的快乐,是哭干眼泪之后的狠心微笑。
最后,从爱情结局来看。封建社会中女性地位一直很低,爱情命运也往往以悲剧为多,但是逸云的爱情结局不同于以往爱情小说的悲剧模式。在广泛流传的古代爱情小说中,女子所遭遇的爱情悲剧主要源自男子的负心,如唐人传奇《莺莺传》《霍小玉传》,或者是源于无力抵抗外界压力,如《红楼梦》中宝、黛之悲剧。但是这两大类产生悲剧的原因在逸云身上都不具备,她之所以勇于斩断情丝,固然有宗教因素的影响,但最重要的原因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是从自身实际利益考虑。离开斗姥宫,她得不到名分,得不到一个完整的爱和人生依靠,处境更不如现在,于是一觉醒来她从“迷”而“悟”,从“华云”变成了“逸云”。“华云”,是对浮华人世功名利禄的追求和留恋;“逸云”,则是对人世功名利禄的忘却和超越。她借助庄子的心斋和佛教的禅定,来分裂自己的人格,解脱恼人的苦痛。
从这个结局看,也许人们都会觉得逸云就此摆脱了世间诸多烦恼纷扰,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是很好的。但其实没有现实的出路,就没有人格和心理的出路。逸云不是解脱了痛苦,而只是将痛苦深深地压在心底。她身处风尘俗世间,肉身在浊世中遭污染受痛苦,要在畸形的斗姥宫这样一个姑子庙里活下去,她只有在心灵上“忘身忘相”醒悟超脱,用佛教构筑的精神空间以自救,给自己一片自由。但显然,这种精神上的自由与透悟,是一种深层的逃避和妥协。
四、结语
东汉末年,佛教传入,随着佛教中国化,儒、释、道文化在相异冲突中又相融互补,不断渗透调和,合力成为对知识分子进行精神塑造和提供灵魂安顿的一整套哲学体系。逸云本身是一名佛家弟子,她从小读书习字、接受传统儒学教育,具有很高的文化知识,加之长期接触中上层官僚和知识分子,其心中早已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融合儒释道的思想意念方式。
在新旧时代的交替之际,面对尴尬而低贱的处境,逸云以尼姑而兼妓女的身份混迹于人世的火坑,她的留发修行,她的吃肉喝酒,她的涂脂抹粉,她的潇洒风流,掩盖不住的是逍遥背后对人世的无奈。她无力改变现实,只好改变自己,游走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在时代的矛盾,国家的危难中,她的“出淤泥而不染”令人心生钦佩,但她就像一个戴着镣铐的舞者,舞姿虽优美脱俗,然而铁链碰撞的声响却如命运和时代的叹息,笼罩了一层悲剧色彩。
注释:
[1][2][3][4][5][6][7]刘鹗:《老残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16页,第224页,第218页,第240—242页,第244页。
参考文献:
[1]刘鹗.老残游记[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世纪出版社,2005.
[3]王学钧.老残游记的禅智慧——逸云释论[J].明清小说研究,1994,(2).
(张婉霜 河南大学文学院 475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