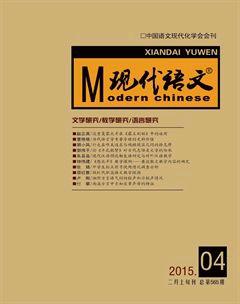论传奇《娇红记》的艺术魅力
摘 要:明末传奇作家孟称舜的戏剧作品《娇红记》在艺术手法、人物塑造等各方面都别具特色,其中《娇红记》的传奇性、人物心理描写以及升仙结局更是与同时代的传奇作品有很大的不同。因此,笔者将从《娇红记》的传奇性以及其剧场性几个方面入手,对传奇的特色进行分析,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关键词:孟称舜 《娇红记》 特色
晚明传奇剧作家孟称舜的剧作《娇红记》描写了主人公申纯与王娇娘因为门第之见而双双殉情的爱情悲剧。王业浩曾盛赞此剧“据事而不幻,沁心而不淫,织巧而不露,酸鼻而不佻,以至临川让粹,宛陵让才,松陵让律,而吴苑玉峰输其浓至淡荡。”[1]概括而言,孟称舜《娇红记》的特色主要在于传奇作品本身的“奇”和传奇的剧场性。
一、非奇不传的《娇红记》
明清文学一向以小说戏曲见长,它不似恢弘壮阔的王朝背景下“铺陈摛文,体物写志”的汉大赋,也不似高深莫测的玄言诗体,更没有驰马纵横的大漠边疆情怀,它所拥有的是对于人性的体察、对于市民阶层的着力描绘。它为迎合大众的口味必然设置了相当的趣味性,这种趣味性正是“非奇不传”的特色。
李渔《闲情偶寄》尝云:“古人呼剧本为传奇者,因其事甚奇特,未经人见而传之,是以得名,可见非奇不传。”[2]传奇性是传奇作品的本质特征也是其生命力所在,而《娇红记》就是具有传奇性的代表作。在这部宏篇巨制中,作者孟称舜着意在细节上精心雕琢,为读者奉献了一出“奇”剧。首先,申娇至死不渝的爱恋就是极具传奇性的,其爱恋不掺杂功利的因素,不带入门第的偏见。王娇娘一介女流的爱情观不让须眉:“奴家每想,古来才子佳人共谐姻眷,人生大幸,无过于斯。若乃红颜失配,抱恨难言。所以聪俊女子,宁为卓文君之自求良偶,无学李易安之终托匪材。至或两情既惬,虽若吴紫玉赵素馨,身葬荒丘,情种来世,亦所不恨。”[1]佳人才子共谐是人生一大乐事,如果不能实现,宁愿为情而死也不愿像李易安一样托身匪材,王季思评点道:“自求良偶,虽死不恨,这是全剧宗旨。”[3]将一介女流的爱情观念作为一部传奇的宗旨来着力描绘,当是传奇的之“奇”所在了。王娇娘的爱情观是纯粹而理想的,她不慕泼天价的富贵,对于司马相如此类聪明而不专情者也持批判态度,只为能与生同舍死同穴的同心子白首不分离,“视富贵子弟如粪土,风格高绝。”[5]
此外,传奇一改从来才子佳人戏曲大团圆的喜剧结局,人为设置申娇双双殒命的悲剧结局也是这部戏曲的“新奇”所在。朱光潜先生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中国剧作家最爱写的是名誉和爱情……戏剧情境当然常常穿插不幸事件,但结尾总是大团圆,不管主人公处于多么悲惨的境地,你尽可放心,结尾一定是皆大欢喜。”[4]诚如其所言,中国古典戏曲走进了才子高中、佳人封诰的“大团圆”怪圈,但是这种大团圆的结局麻痹了人心,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传奇的艺术性。传奇《娇红记》一改之前戏曲的大团圆结局,将申娇双双殒命化为鸳鸯的故事情节作为传奇的高潮加以铺叙:“这一对鸳鸯,飞翔上下,自初时到今,捕之不得,逐之不去,活是小姐和申官人相亲相依的景象。这敢是两人精魂所化也?……呀!如今一堆鸳鸯,忽然不见了,这分明是两人精魂出现。前云死后即归仙道,以此看来,果不虚了。正是:世间只有情难化,地上无如情久长。”[1]申娇二人死后双双化为鸳鸯,一改才子佳人奉旨完婚的传统设置,也摒弃了为爱情死而还魂的一幕,而将男女双方的精魂化为鸳鸯,将上古时代韩凭与妻生死相随的缠绵化为了传奇中的一缕诗意。
二、场上之曲《娇红记》
歌德曾云:“为舞台上演而写作是一种特殊的工作……写在纸上使我们着迷的东西搬上舞台就可能枯燥无味……一个人为舞台上演写剧本,既要懂行,又要有才能,这两条都是难能罕见的。如果不结合在一起,就很难收到好的效果。”[5]作为戏曲表演的底本,传奇剧本除了要具有便于供案头阅读的文学性外,还需要具有可供演出的剧场性。孟称舜的《娇红记》就是一部将戏剧文学可读可演的特点表现得十分出色的作品。在传奇《娇红记》中,除了大量华丽的词藻之外,还有大量用于表示动作的提示词,如在《絮鞋》一出中,就先后运用“生上”“觑介”“翻床介”“见鞋介”“取鞋行介”,以表现申生偷鞋的一连串动作。戏剧作品贵在意深词显,适当的通俗之词以及个性化的人物形象在作品中是十分重要的,而在人物的塑造中,作者还加入了许多类似于马小三、戈小十以及帅公子这类小丑人物,似有意以之作为申娇恋情之外的另一条线索,使苦乐交错、悲喜递迁,不致一方走向极端。而这种双线结构是戏曲的传统结构,合乎戏曲场上搬演的特点与规律。在第五出《访丽》中,马小三、戈小十描述王娇娘“生的菩萨样,是件儿都停当。再端详,体似凝酥,脸似芙蓉,一见神魂荡。头儿梳的光,衣儿熏的香。大爷,你若见了呵,不由你不摊倒在销金帐。”帅公子即做倒介,说了句“咦,我死哩!”[1]其好色的本性,庸俗的模样立刻跃然纸上,生动传神。
又有对侍女飞红的生动描写,孟称舜对于侍女飞红的描写具有兼本色与文采,可读可演颇具意趣的特色。本色者如第四出飞红打趣娇娘反被小姐恼了,俏皮的她回小姐道:“飞红在此久了,看奶奶去。你五分心事我已三分晓,何须抵口遮藏了?我且闭门不管月黄昏,一任梅花落尽多多少。”此句风格俏皮可爱,“我且闭门不管月黄昏”使得整句话欲说还休,“闭门不管月黄昏”中一个“闭”字惟妙惟肖,用闭门这一动作暗喻飞红热心的关闭,生动地描写出飞红赌咒今后不管申娇二人的赌气神态。 “一任梅花落尽”中,梅花既指娇娘又喻指申娇的爱情,用“梅花落尽”比喻娇娘对申生欲迎还羞的心理,巧妙含蓄,意味无穷。此处飞红通过一句简单俏皮的唱词把小姐的一点春闺心绪看在眼里而嘴里又占尽风头,唱词的风格表现出一个侍女应有的风度,以平常之词和几句俏皮的话儿就使得她的娇俏形象跃然纸上。
雅致者有第二十八出,飞红见春色正好便去瞧申纯,看着眼前美丽的风光便有唱词【风入松】道:“看年年花柳冷烟迷,恁韶光把人轻掷。千愁万恨在眉尖逼,待抛下甚时抛得。长伴着春风翠帏,肠断也燕双栖。” 此唱词平仄得当极为雅致,以“花”“柳”“冷烟”“春风”“翠帏”等意象表现韶光易逝、青春难返的惆怅与无奈。唱词中“燕双飞”的意象借自然界现象表达出飞红对于双宿双栖的爱情的向往。整段唱词使用多种意象,真切地表现了侍女的动人情思。
元代戏剧家胡祗遹提出“九美之说”:“一、姿质浓粹,光彩动人;二、举止闲雅,无尘俗态;三、心思聪慧,涧达事物之情状;四、语言辩利,字句真明;五、歌喉清和圆转,累累然如贯珠;六、分付顾盼,使人解悟;七、一唱一说,轻重疾徐中节合度,虽记诵闲熟,非如老僧之诵经;八、发明古人喜怒哀乐、忧悲愉佚、言行功业,使观听者如在目前,谛听忘倦,惟恐不得闻;九、温故知新,关键词藻,时出新奇,使人不能测度为之限量。九美既备,当独步同流。”[6]九美所针对的主要是戏剧的表演方式,但是它同时也对剧作家的创作活动作出了限定,其中四美和五美针对语言和歌喉的要求实际上就是要求作家在创作时就注意到语言必须符合主人公的性格,而字词句间的承接必须连贯,不能为追求声律之美而导致晦涩。作为最终面向市民的大众艺术,戏剧的创作不仅要讲求以上的方面,更要关注其舞台实效,即要使戏曲成为场上之曲。而孟称舜的《娇红记》在人物的设置、唱词的讲究上都做足了功夫,使得整部传奇兼有可读可演的特色,成就了《娇红记》在传奇史上的重要地位。
注释:
[1]孟称舜:《娇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69页,第260页,第18页。
[2]李渔:《李渔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页。
[3]王季思:《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358页。
[4]朱光潜:《悲剧心理学》,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页。
[5]爱克曼:《歌德谈话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59页,第181页。
[6]叶长海:《中国戏剧史稿》,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
(曹仪婕 云南昆明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 650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