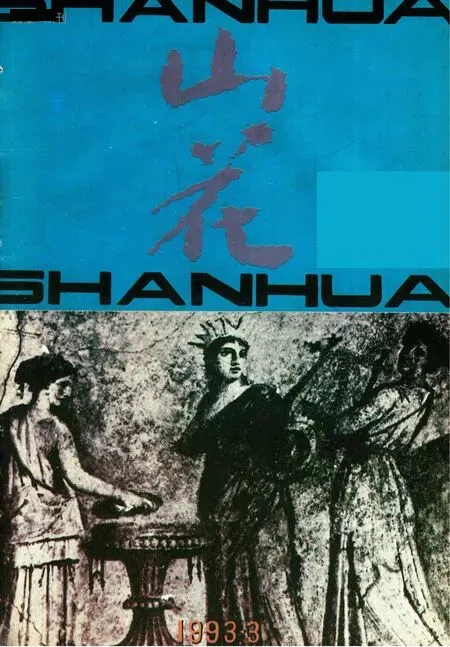探析历史叙事中的女性经验
邹 璐
探析历史叙事中的女性经验
邹 璐
尽管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有一些西方的女权主义理论被引介到中国,但关于性别身份的观念直到90年代上半期才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被重视,理论与创作的互动则一直若即若离,只是在某些作家那里形成比较鲜明的呼应。但女性写作的历史却在现代以来的文学史中就存在清晰的脉络。就新时期的女性写作而言,也可以看到女性作家一直处在时代的前列,以她们特殊的敏感表达了这个时期最迫切的历史愿望。在当代思想和情感解放的历程中,女性也以其敏感提供了崭新的意义。“新时期的历史叙事以人性论为美学出发点,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走出极左路线的历史阴影,急切抚平精神创伤,肯定人的存在价值。对人的肯定推演出一系列命题:人性、人道主义、个性解放、主体论、自我实现等等。女性作家则在这一历史实践展开过程中与男性作家并行不悖,而且时有惊人之举。”①
残雪的写作始终以她独特的语言和独特的对世界的感知方式来区别于主流的文学叙事。对于残雪来说,文学叙述永远是语言接近世界的一种方式,或者说,语言本身构成了它自己的世界,那是他者的世界,不能被现实化,永远拒绝现实化,也就是詹姆逊所说的“永远的历史化”。2006年,残雪出版的小说集《暗夜》,那里面收入她2003—2006年的作品,按照残雪自己的说法,她总是一个阶段“上一个台阶”,“这些近作应该是已相当成熟的作品了”②。如果认为残雪这样说有自夸炫耀之嫌的话,那就错了。事实上,她有足够的底气。这本书的封底就有几位外国的作家对残雪作出很高的评价。苏珊·桑塔格说:“如果要我说出谁是中国最好的作家,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残雪’。”美国小说家乔恩·所罗门说:“我无法相信一位这样的作家——直率地说,她无可匹敌——在英语文学世界里还未获得她赢得声誉。她的近期作品更是从手法上和情感上大大超越了她的早期作品。”
残雪构建起一种女性的话语和她们想象世界的方法,那种童话世界一般的永远孩子气的荒诞感,混合着女性自我认同的困扰,残雪所展示的女性话语的空间极狭窄,又无比宽广,这是一种另类文学,一种永远的先锋派以及女性叙事混合在一起的话语洪流。
王安忆的小说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她似乎总是在触及历史本质性问题的那一刻回避而去。1993年第2期的《收获》刊载了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这无疑是王安忆极其重要的作品,却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部长篇小说像是王安忆要写的一部自传,作为叙述人的“我”是一个城市女性,小说的第1、3、5、7、9章从横向上讲述作家个人的成长经历,第2、4、6、8、10章从纵向上追溯家族历史,纵横交错,“我”的现在的城市生活与对“我”的祖先前辈的想象交叉展开。前辈的历史主要是母亲的家族的历史,使得叙事看上去像是要建立一个母系家族的历史。小说不断地检视自我的心灵,对自我的反思一直绵延深入到家族历史的谱系的建构中,“我”的历史如此被虚构和重建。母系的历史中依然充满了父系的雄伟,历史叙事的中心还是矗立起一个男性形象。《纪实与虚构》对历史有一种独特的反思角度,那个叙述人“我”的女性形象不断把女性的命运引入父权制的强大历史,这也是一种特殊的女性视角。
王安忆曾表示她所理解的历史是一种日常的生活史。③《长恨歌》中的王琦瑶虽然通过偶然的机会戴上了“上海小姐”的桂冠,但这并没有给她带来好运,而是把她的生活推向了曲折。旧时代结束了,她的上海浮华梦想也终结了,回到了弄堂,重新开始她的上海小女人的生活。浮华的历史给王琦瑶带来的是进入普通生活的特殊方式,王安忆选择这个角度来审视一个女人的日常生活以及她最后的归宿,确实是颇具匠心。在这里透示出王安忆对女性命运的关切,但不是那种政治性很强的女权主义,而是一个写作者的女性的视角对另一个女人的那种刻画,这种女性的意识,以及对女性的意识,笔者以为有时它的意义要大于那种空泛的政治化的女性意识。王琦瑶对政治无知,但政治似乎就在她的旁边,随时都可打碎她的生活。最终她还是被一双男人的手掐死,而这双手,象征着男性的历史鼓动起来的欲望,对金钱财富的贪婪是男性历史的本质,也是一切暴力的根源。这个历史还诱惑着女人,瓦解女人的日常生活。女人终究无法回避膨胀起来的历史。说到底王安忆这些小说中都隐藏着一个很深的主题,那就是关于女性欲望的表达与压抑的主题,女性的欲望的表达如此严重地影响到女性的一生,而压抑则构成了女性生活史的规则,这个规则无法打破,这就是女性的深刻悲剧。在这一意义上,王安忆看似平和的叙述,实则书写出女性的悲愤史。王安忆过去的作品都显得大气,与张爱玲相比,王安忆确实“大气”得多,然而,对于她来说,成也“大气”,败也“大气”,“大气”使王安忆过于迷恋历史化的叙事,有时“小气”反倒使王安忆的作品有一种更纯粹的味道,就如《长恨歌》一般。
铁凝一直被各种研究描述为女性主义写作的典范,但铁凝自己并不认同这种说法,她更乐于把自己看成一种性别身份色彩并不浓厚的作家。她甚至声称“我不是女性主义者”。铁凝如此声称,并不是要与女性主义划清界线,实在是因为女性主义有被滥用之嫌,铁凝不希望她被打上这种标签,她希望她的文学具有更为广泛和纯粹的意义,而不只是身份政治的诉求。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就不从女性主义写作的角度去阐释铁凝。在铁凝的许多作品中,女性形象一直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铁凝的短篇小说《哦,香雪》,描写了一个淳朴农村少女对现代文明的向往,表现乡村女性的生活变化的痕迹,那不是激进的现代主义意识,但表达了一个乡村女性自然流露出的现代性意识,和对现代生活的向往。这种女性视角不是概念化的,而是回到朴素的乡土。铁凝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在当时引起强烈的反响,在个性解放和人性论的意义上受到肯定。在中国现代性还依然处于建构的历史中时,与时代同步前进的人格精神塑造成为作家关注的主题,而女性的人格精神的建构也是现代性建构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样的时期,铁凝作品表达的女性意识,当然不可能是什么与社会疏离的怪戾的女性,而是女性在对时代的敏感领悟中所获得的那种独立的自我。
《玫瑰门》中的司漪纹早年渴望得到传统大家庭的接纳,旧家庭的迅速崩溃,让她卷入了革命暴力的历史,外部世界对她再度构成巨大的压迫。作为一个女人,她无论如何也不能获得革命的宽恕,她不只是反动没落家庭的后裔,同时也身为女人,因此具有原罪般的本性。但她身上却顽固地保持着中国传统父权家长制的作风,她以父权制的家庭专制的方式来对付家庭成员,一方面是无保留地把自己奉献给这个父权制的家庭,另一方面,“父亲”的缺席,让她承担起家庭父权建构的任务。特别是在“文革”的残酷岁月中,司漪纹领导着她的家庭与这个时代的浩劫展开了无望的搏斗,而与此同时,这个家庭内部也在进行着一场无声无息却同样残酷的“玫瑰战争”。然而,她们无法找到女性的方式,女性除了仿效父权制的方式,没有她们自己对待家/国的方式,特别是面对历史暴力,她们只有充当殉葬品。
铁凝的《孕妇和牛》以淡雅的笔法,却意指着一个谜一样的思维向度。如果考虑到这篇小说写于整个社会陷于彷徨的90年代初,那对这篇小说所能读解出的微妙的寓言意义,当不会感到意外。贺绍俊认为:“《孕妇和牛》是一个标志,标志着铁凝思想上的成熟。孕妇和那头唤作‘黑’的牛悠悠地行走在乡间的路上,‘她和它各自怀着一个小生命仿佛有点儿同病相怜,又有点儿共同的自豪感’,这多少有些像铁凝对社会人生有了新的体认,这些新的体认孕育在她的内心,就像是孕育着新的生命。”④
铁凝的小说《永远有多远》讲述了北京胡同里年轻女性白大省的生活经历。白大省七八岁时就被胡同里的老人赞誉为“仁义”,长大后她依然保持着自己纯朴善良的天性。她总是乐于助人,天真地相信别人,结果却总是被别人利用,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心灵的创痛。她幼时的伙伴,也在利用她的善良。但始终不动摇的是她对爱的理解,那就是“选择一个爱他比他爱你更厉害”的爱人。白大省的内心总是一种“爱他人”的倾向,这可能是当代社会难得的美德。而白大省总是屡屡受到伤害,这一方面表明这种美德的可贵,另一方面也传达出作者对其能否生存在下去的隐忧。在商业社会来临的时期,铁凝的这些关于老北京的记忆,实则是对商业主义时代人伦道德的一种警醒。白大省是典型的北京女孩,也是老北京的遗产。
张抗抗则更倾向于首先表达关于人的问题,“当人的尊严都没有的时候,哪儿还有女性尊严啊!”⑤张抗抗更乐于在人性的深度上去表现两性的关系,或者说在两性的心灵撞击中去探求人性的困感和深度,以此来书写女性的内心世界,这也是张抗抗小说持续表现的主题。
张抗抗的长篇小说《情爱画廊》,试图以爱的乌托邦来建构一种的情感理想,这与张抗抗在80年代对人性理想的追寻是如出一辙的。只是这一次张抗抗更加强调理想性,明显地她想与时代拉开距离,可见她认为由此才会有情感世界的真正的纯粹性。实际上,《情爱画廊》是个典型的三角爱情关系,又加入了伦理的维度:母女两个人同时爱上一个画家——周由,身为母亲的水虹与女儿就此展开了各自对爱和人性的理解。多种维度的设置,让爱的冲突不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内心的矛盾纠结展开的。实际上,这个故事的抒情味极浓,而且跌宕着一种诗意的气息。张抗抗在两性关系中,所要表达的不是对抗性的冲突感,而是试图寻求一种理想式的相互融合。也许张抗抗的这种构想很不“女性主义”,但在中国的90年代的语境存在中,她所要表达的对女性心理世界的关注,实际上也是一种更为内在的真实性的存在。
但在2002年,张抗抗的《作女》则明显地表现出比较激进的女性主义意味,实际上这与《作女》中的人物性格有直接的关系。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卓尔,是个35岁的成熟女性,“卓尔”是“卓尔不群”的意思,张抗抗试图写出一群“卓尔不群”的城市白领丽人的群像,以此能看出当代文学的城市经验的丰富和深化。卓尔周围有一群和她一样的年轻女性,这些女性有着高学历、高智商,不依附于任何男人,有着自己的独立个性,她们完全凭借自己的内心感受去享受生活,她们喜欢幻想,追求精神价值。这些新新人类式的白领丽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当今的女性独立,真的很难说清楚。与其说她们是作为一种实际的挑战,不如说是作为一种幻想,形成了一道当代消费社会的风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侧面。而张抗抗的叙述始终散发着一种反讽的意味,也是对“卓尔们”在中国的生存状态及其效果保持着一种相当警惕的态度。
注释:
①陈晓明:《壮怀激烈:中国当代文学60年》,《文艺争鸣》,2009年第4期。
②残雪:《暗夜·后记》,华文出版社,2006年版。
③参见《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与王安忆谈〈长恨歌〉》,《文学报》,2000年10月26日。
④贺绍俊:《作家铁凝》,昆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3页。
⑤张抗抗、李小江:《女性身份与女性视角》,原载《钟山》2002年第3期,参见张清华编《女性文学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69页。
邹 璐(1978— ),女,大连人,大连外国语大学文化传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小说研究。
作者简介:
基金项目:2013年度大连外国语大学科研基金青年项目: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意识源流与创作主题研究(项目编号:2013XJQN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