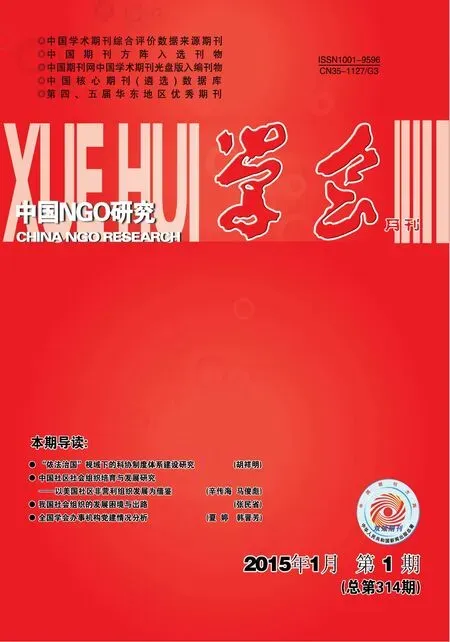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困境与出路
张民省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困境与出路
张民省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社会组织是协同政府提升社会自治能力、完善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当前,中国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着观念落后、制度僵化和人力不足的多重困境,如何“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本文提出应逐步弱化政府主导的“一元化”治理格局,为源自民间力量的社会组织腾出作为空间的基本思路。建议从加快培育公民社会以促进公民权利意识觉醒、加快制度建设以法治精神构筑社会组织发展的理性秩序和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以壮大中产阶层的社会构成,多方合力推动我国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
社会组织 困境 活力
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而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离不开社会组织的现代化。只有使大量的社会组织参与到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活动之中,才能有效地弥补经济运行的“市场失灵”和公共服务的“政府缺位”,形成政府与民间“共同治理”的社会治理格局。
一、社会转型期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
社会组织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从广义上讲,社会组织指人们在共同的社会活动中结成的关系较亲密的人群,包括家庭、家族、政府、军队、企业、学校、医院、教会等有一定内部同质性的团体,由一定数量的社会成员,按照一定规范并围绕一定目标聚合而成。而本文指称的社会组织,主要是从狭义而言,特别指的是那些区别于政府,出于维护自身权利或以为社会提供特定服务为目的组建的稳定群体,如中介组织、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行业协会、兴趣小组、非营利机构等组织。
美国管理学家彼得·F·德鲁克认为,社会组织是“社会领域中基于志愿者并且能够发挥人的精神力量的组织,同时提供了社会所需要的社会服务和政治体制所需要的领导力量开发”[2]的重要力量。我国学者郑杭生认为,“社会组织具有完善市场机制、保障改善民生、繁荣发展文化、促进公众参与等诸多功能。基本功能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协调功能;二是道德建设功能”[3]]。因为对于一个健康的社会来说,在政府与个人之间确实需要一些具有协调性、媒介性的中间组织来润滑和黏合,这样的组织不仅能协调政府与个人的关系,而且可以在国家经济增长、社会道德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古今中外都曾广泛存在的行业协会、宗教团体等组织,一方面,可以通过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来遏制个体的自私自利;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社会组织的活动来扩大弘扬利他主义行为和价值。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快速转型和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如果有适当数量和规模的社会组织作为沟通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桥梁,那么必然可以成为社会矛盾的“减震器”、政府治理的“变速箱”、社会公平的“平衡仪”,对和谐社会的建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七大提出“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4]的任务后,我国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已经开始逐步由原来的约束管控转向了培育鼓励为主。在2011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也首次提出“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坚持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发挥其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5]的重大命题。2012年十八大又提出了“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4]的新任务。可以说,伴随着这些观念上的转变,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空间已经大大增加。据民政部发布的《2011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1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6.2万个,比上年增长3.7%。其中,全国共有社会团体25.5万个,比上年增长4.0%”。“我国共有基金会2614个,比上年增加414个,增长18.8%”[6]。目前,这些组织几乎覆盖了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劳动、民政、体育、环保、法律、慈善等公益领域及中介、工商服务的社会组织,已经初步形成体系。
作为公民社会的基础,包括政治组织、经济组织(企业)、文化组织、军事组织、宗教组织等在内的各种类型的社会群体,已经在我国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经济生活方面,社会组织正在推动国际、行业、企业之间的不同合作,一方面使各组织成员的活动由无序变为有序;另一方面又把分散的个体粘合成一个新的强大集体,把有限的个体力量变成了强大的集体合力。社会组织还通过提供和分享就业信息,扩大了就业渠道,增加了就业机会。通过积极参与各类经济活动,各类社会组织中的从业人员迅速增加,据统计,到2011年为止,全国各类社会组织共“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599.3万人,形成固定资产1885亿元”[7]。同时,许多经济类社会组织和行业组织,在规范行业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中同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政治参与方面,各种社会组织对各级政府的公共决策正在产生着日益重要的影响,有力地推动着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这些社会组织不仅成为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重要渠道和推进基层群众自治的重要动力,而且成为了沟通政府与公民的桥梁,有利于增强官民之间的互信;在公益事业方面,各类社会组织一直承担着扶贫济困,促进慈善事业做强、做大的重任。据民政部2012年公布的资料,“从捐赠总额来看,从2006年的127亿元到2011年的845亿元,6年间我国年均捐赠收入超过668亿元,平均年增长率达62.71%”[7]。除此之外,社会组织的公益作用还特别体现在保护生态、改善环境、维护社会治安、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在文化建设方面,社会组织通过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包括有形的、无形的)对组织成员的约束,从而使组织成员的活动互相配合、步调一致,有效地发挥了调动组织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组织的凝聚力,增强组织成员向心力的作用。如各地社区组织广泛开展的文化体育活动,几乎都是由社区居民社团自发组织的,对改善人际关系,形成文明风气做出了重要贡献。
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民间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大量产生,使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开始产生,国家与社会组织出现适度分离。2011年国庆节前夕,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对《南方日报》东莞观察《坤叔公益团队“转正”受挫背后》一文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有关部门要转变观念,努力成为社会公益和社会慈善发展的助推者,而不是障碍”[8]。社会组织的相关制度环境也开始得到改善,特别是一些地方性法规有了实质性改进,如广东东莞、浙江宁波等地都面向社区社会组织和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实行登记和备案双轨制,率先为这两类社会组织“松绑”。这样,中国的社会组织不仅在民间发展起来,而且走向了国际社会。2011年5月,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在《中国公民社会的现状与未来》中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结构分化大体定型为:以政府官员为代表、以政府组织为基础的国家系统;以企业主为代表、以企业组织为基础的市场系统;以公民为代表,以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为基础的公民社会系统”。“到目前为止,全国性社团已经在122个国际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在92个国际组织中担任理事”[9]。2012年10月8日,国内的5个民间环保组织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开了49家中外企业在华供应链存在的环境问题报告。之后尽管有19家企业未对“涉污”进行回应,但其中大部分企业仍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改变污染现状。有评论认为,“民间组织此番获得有效话语权的原因并不在于揭黑产生的威慑力,更根本的原因是来自于本身的专业性操作,以及对所工作领域的宏观视野”[10]。但不可否认,对社会组织在中国应该大发展或作用发挥到什么程度?国内仍有一些人存在一定的偏见,主要表现为长期的“宏观鼓励”与具体的“微观约束”,把社会组织看作是政府治理潜在的“对手”。而从公民社会建设的制度环境来看,对社会组织的制约仍然大于鼓励,重要的法律法规还不太完备。如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教授在2012年4月接受“财新网”采访时说,“与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一样,长期以来,社会组织特别是民间发起的组织被视为政府的对手,有关方面生怕其得到社会支持从而形成对抗政府的力量”[11]。他认为,这样的心态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的时候也许有一定道理,但是当生产力充分发展,解决了人们的基本生存问题后,像老年护理、儿童照料、残疾人的社会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就会日益突出,这种眼光就不合时宜了。因为过去完全依赖家庭的社会照料服务结构已经解体,绝大多数的中国家庭日益丧失赡养老年人的社会功能。于是,60多年前由发达国家提出的护理照料型的社会服务问题,今天也终于成了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护理照料型的社会服务产品,政府不可能完全直接承担起生产的责任,只有社会组织才是生产此类服务产品的主导力量。中国社会需要大量的护理照料型社会服务产品,这是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以后所必然产生的问题。
二、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深层困境
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社会需求的多元化呈现、体制改革的“深水区”探索,均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在中国社会组织应有功能的实际作用层面与公众期待层面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此,近年来我国学界对社会组织的研究不断增多,特别是对社会组织发展困境的研究就成为关注的焦点。笔者以为,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困境,一不是外部的“资金不足”[12],二不是内部的“缺乏自律”[13],而主要还是观念落后、体制局限、能力不足三方面的困扰:
(一)观念落后
“社会组织的发展必须倚重于现代公民的权利意识和自为意识的觉醒,进而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体系”[14],这是社会组织成长和生命力的思想基础。因为社会组织成长和发展的根基在“民间”,即一个个作为公民的具体的人们身上。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强有力的现代公民意识的支撑,特别是权利意识和自为意识的树立。首先,公民要有权利意识,即公民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能意识到自身具有受法律保护的、不受侵犯的基本公民权利。当政府部门、社会团体或其他公民的行为损害到自己及其所在组织的合法利益时,懂得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及其所在组织的正当权利。按照美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的观点,“权利观念明确的人,可以独立地表现自己的意志而不傲慢,正直地表示服从而不奴颜婢膝。屈服于暴力的人,只能自侮和自卑”[15]。受我国曾经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影响,行政权力长期支配社会的局面造成的后果是公民权利的长期被剥夺和公共精神的缺失。虽然今天中国的封建社会形式已成历史烟云,但是不等于具有封建社会管理思想的官僚个体就已销声匿迹,同时公民普遍的自我权利意识羸弱和对权力崇拜的惯性思维依然在延续。这是社会组织深入发展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其次,公民要有自为意识。即作为公民,能够摆脱在行使权利时“等、靠、要”的思想,能经常意识到自己可以通过自身的力量或个体联合起来维护和增进自身利益的思想自觉。从历史上看,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农业社会,造成了这种社会形态下“培养”出来的人缺乏自为意识,即使偶尔联合起来也经常是暂时的、松散的、无力量的。正如马克思把农业经济形态下的无组织的“劳动者—农民”的联合比喻成“一袋马铃薯”[16],以这一表述形容中国的公民社会结构恐怕也是比较贴切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建立了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为特征的政治体制,由国家和政府对社会实施全面干预、对公民个体实施全面管理,使公民可以自为的空间被大大挤压,自为意识由此大大减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逐渐得到重塑,但是符合现代政治学原理所主张的权力委托的关系依然没有形成,公民个体的自为空间也没有真正释放出来。
(二)体制局限
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表明,社会组织每前进一步都受到制度环境的直接影响。适当的制度环境能够促进其健康发展;而不适当的制度环境则可能会使其走上歧途。在我国,阻碍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性缺陷有三个方面:一是不合理的管理束缚。我国的社会组织体系和管理体制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具有“单位制”的许多特点,还不能完全适应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形势,不能在社会转型中充分发挥功能作用。在我国现行社会管理体制中,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分工不够明确,政府对社会组织管理过多,社会组织对政府依赖过多,自治能力较为低下。主要表现为:社会组织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行政化”倾向,这在基层社会组织(社区)中尤为明显,如社区大都成了“政府的腿”,而没有成为“居民的头”,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政府的从属机构和延伸物”更合适[3]。二是不合理的准入机制。目前,我国对社会组织在“准入制度”的限定比较僵化,于是大量的社会组织在出生认可时就陷入了合法性危机。如1998年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条对申请成立社会组织者的条件在第一、四、五款都有规定,如“社团必须有50个人以上的个人会员或者30个人以上的单位会员,个人会员、单位会员混合组成的会员总数不得少于50个人”、“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社团必须有合法的资产和经费来源,全国性的社会团体有10万元以上的活动资金,地方性的社会团体有3万元以上的活动资金”等[17],这些入口登记的门槛偏高,这样就使许多实际长期存在并深受群众欢迎的社会组织很难进入合法的管理体系,而只好以非法的方式“半活跃”于社会中,更奢谈享受政府在财政和税收上对它们的支持和优惠。三是支持性政策缺失。社会组织虽然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但并不等于在政策、资金方面就不需要政府的支持,而事实恰恰相反,政府的制度性资助是社会组织发展壮大的重要资金保障。在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的社会管理中,特别是基层社区管理的起步和运行阶段,仍特别需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来助力推动。如果那些与民生密切相关的社会事务由政府广泛地向社会组织开放,积极引导和鼓励有意愿、有能力、合乎规范的社会组织参与进来,那时能够向群众提供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就会增多,社会服务效率才会不断提高。
(三)能力不足
当前,我国的社会结构和分配方式从整体上看尚难满足社会组织发展的需要,这一问题又导致了社会组织的薄弱和服务力量的不足。关于社会结构不合理,表现在国家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结果,应形成公正、合理的现代化社会结构——“橄榄型”形态(即从“富少穷多”的“洋葱头型”演变为“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结构)。从社会学上说,“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因为中间阶层的人数最多,使得对立的贫富两极成为一个连续性的排列,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看到拾级而上的希望,从而有助于舒缓贫富差距蓄积的对立情绪以及由此衍生的社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显著的提高,但是目前我国中产阶层在经济方面的整体力量还不够强大,没有形成理想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如在我国领土广袤的农村地区,收入偏低的农民是最主要的社会阶层。2010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13.39亿的总人口中,农村人口为6.74亿人,占人口总量的50. 32%[18]。在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的8个阶层30多个群体中,收入较低的农民、工人、社会底部阶层和其他弱势群体是社会的大多数。由于历史、文化、教育等多重原因的影响,他们不仅权利意识、自治意识、结社意识等相对落后,而且作为现代社会公民所需要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也十分不足。关于收入分配不合理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所有制单位之间以及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和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呈现出非理性拉大的趋势,这使广大的低收入人群在想参与社会组织开展的公益活动时也显得“力不从心”或“不想出力”。而之所以有人“不想出力”,与我国目前收入差距拉大的不正常因素有关:一是初次分配秩序不公平。一些行业有名目繁多的工资外收入,接近或超过了工资表内的收入。二是收入分配不公开。一些单位有比较隐性化、多元化的额外收入。加之,当前社会以权谋私、坑蒙拐骗的现象不绝于耳,对社会组织赖以壮大所需要的善心、爱心、公心带来了极大的伤害。据相关统计数据表明,“近年来,全国平均每年流失的各类税收为5700亿~6800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6%~9.1%。另外,中国的地下经济十分严重,由此产生的灰色收入偷漏税流失额在700亿~800亿元之间。国家税收的严重流失,一方面使一部分人的财富迅速加大;另一方面又使国家缺乏必要的再分配能力,难以有效地援助弱势群体,最终加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19]。如此以来,中国社会阶层较为明显的“洋葱头型”结构和经济收入的“分配不公”,就使得谁是参与社会组织的后备力量,并持之以恒地促进社会组织不断发展成为一大难题。
三、对我国社会组织全面、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1]要求。当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我们必须站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高度,充分提升社会组织建设水平,发挥社会组织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中的协同作用,积极探索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新途径,着力从观念培育、机制完善、人才保障三个方面寻求突破,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发展保障。
(一)提高公民意识
要有效地破解社会组织发展的观念性困局。当前,最紧迫、最根本的问题是解决传统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风俗习惯和价值准则的束缚,培育人们树立“民主意识与法律意识在国家活动领域为主的宏观范围内交融整合而成的特殊社会意识”——公民意识,建设“公民对自身权利的认识和觉醒,对法律权威性的承认和尊崇,对法治理想的崇敬和追求”[20]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现代含义意味着崇尚基于“包容”精神的多元主义、基于“法治”原则的权益主义和基于“参与”意识的自治精神。可以说,多元主义、权益主义和自治精神也是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壮大的重要思想基础。当然,做好这件事情,绝非一日之功,我们必须为此付出艰巨的努力。而建立起公民社会的目标,就是要让公民认识到“社会是自己的社会”,而公民社会的建立,是以权利意识和自为意识为内核的公民意识不断增强为条件的。如果一个现代社会成员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公民社会就不可能建成。一度,一些人认为公民社会的形成需要等待公民意识的提高和成熟,但殊不知“公民意识的真正孕育、产生和发展是在人们参加各种日常社会生活实践中实现的,参加公民社会组织的实践活动就是塑造现代公民意识的主要方式之一”[21]。如在现代社会,“自由结社”是公民社会组织的重要实践活动,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而结社的形式就是为了保护文明可能受到威胁的一种社会自组织尝试,这些结社的团体就“像是一个个不能随意限制或暗中加以迫害的既有知识又有力量的公民,他们在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反对政府的无理要求的时候,也保护公民全体的自由”[22]。所以,今天我们有必要通过组织化的路径,培育公民社会的建立,推动公民权利意识和自为意识的觉醒,进而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体系。
(二)完善制度建设
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良好的法治环境。当前,我国在社会组织领域尚无基本法方面的规范,其地位、功能都缺乏基本定位,现行的法规也偏于程序法而缺少实体法,对一些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出现的新型社会组织的治理甚至无法可依。因此,加强制度建设,以法治精神构筑理性的社会组织规则极为迫切。在国家层面,我们应在社会组织领域加强立法工作,“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1]。构建更加合理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组织自我管理、自我运行的能力和提供服务的质量。健全社会组织负责人管理、资金管理、年度检查、查处退出等制度,做好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为促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奠定坚实的法治基础;在政府层面,应以“政社分开”为原则,推进社会组织的“去行政化”,努力使“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1]。加强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构建设,强化登记管理机关权威性,增强社会组织执法和涉外社会组织监管力量,成立国家层面的社会组织建设工作协调领导机构,负责统筹、指导、规划社会组织工作,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在中国大力发展行业、商会、公益慈善、社会服务、经济、科技、体育、文化等类型的社会组织;在政策层面,做到“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这些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加强对社会组织和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引导它们依法开展活动”[1]。引导社会组织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加强自律,提高透明度和公信力。同时,应该明确规定现职国家公务人员不得在行业协会商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中兼职,至于离退休后确需在社会组织中兼任某些职务的也应当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
(三)扩大人力资源
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仍偏于“洋葱头”形状,为数众多的社会人群收入不高、权利意识淡漠,话语权弱小,成为社会组织发展和公民社会构建的硬伤。因此,有学者提出了中国公民社会发展道路的三种精英主导模式:即政治精英主导的“威权诱导型”路径、知识精英主导的“民主倡导型”路径、经济精英主导的“财富推进型”路径[23]。但笔者以为,中国要走向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更需要切实依靠由其自身迸发的内在力量,因为“受过较高程度的教育、收入较高和职业地位较高的人更倾向于参加组织”[24]才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自觉性。只有社会中产阶层的人数增加了,才有意识和能力去组建或参加各种公益性的民间社团组织,也只有当社会上的大多数人进入到中产阶层,才能保证社会结构的稳定。目前,我国社会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等收入阶层的代际更替呈现迅速变化的趋势,但在我国老的中产阶层已经退出,新的中产阶层主要在大城市中出现的情况下,中产阶层的总体力量还比较弱小。因此,对执政者来说,当下有必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培育和壮大社会中产阶层,促进社会的各阶层结构人数变成“橄榄型”的特征。另外,还可以在个人收入调节税上对中产阶层予以优惠,在融资方面给予一定的让利,激励更多的社会成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致富,从而加入社会中等收入的阶层。同时,政府还应站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高度推进社会组织专业人才建设,加强社会组织的人才资源开发,解决当前社会组织人才的“短板”问题。如可以通过对社会组织工作人员的培训,使其具有良好的业务能力、专业素质和奉献精神。加大引进社会管理人才,特别是加大对高素质、专业化、创新性人才的引进力度,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生活待遇,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从精神上、情感上留住人才。
总之,在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时期,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系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时代课题。十八大之后,我国社会组织已经迎来了大发展的“春天”,为此我们要尽快选择一个合适的角度,努力破解社会组织在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使中国的社会组织在促进公民政治参与、协助政府职能转变、强化公共权力监督、提高社会服务水平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美)彼得·F·德鲁克.社会的管理[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3]郑杭生,陆益龙.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的功能[N].北京:人民日报,2012-4-25.
[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EB/OL].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11 -03/16/content_22156007_4.htm.
[6]民政部.2011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EB/OL]. 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mzyw/201206/201 20600324725.shtm l.
[7]民政部.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6.2万个,固定资产1885亿元[EB/OL].http://new s.xinhuanet.com/fortune/2012-12/13/c_114016270.htm.
[8]胡键,岳宗.汪洋为社会公益组织“正名”,强调重监管而非拒人门外[N].广州日报,2011-10-09.
[9]俞可平.走向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N].南方都市报,2011-05-08.
[10]黄英男.民间公益组织走向国际舞台[N].京华时报,2012-10-15.
[11]王振耀.社会组织立法必须透明[EB/OL].http: //special.caixin.com/2012-04-19/100381296.htm l
[12]何增科.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要素分析[A].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3]周澜.“第三部门”在中国发展的困境分析[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54-55.
[14]包雅钧.当前中国社会与治理[J].科学决策,2011 (7):60-63.
[15]托克维尔,董果良.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7.
[16]中共中央文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Z].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0号),1998-10-25.
[18]文静,马文婷.中国内地总人口已达13.39亿,城乡人口接近持平[N].京华时报,2011-04-29.
[19]刘书艳.高收入阶层缴个税较少[N].证券日报,2010-09-11.
[20]张民省.公民意识与中国现代化[J].山西大学学报,2005(2):120-123.
[21]李永杰.公民社会组织与现代公民意识的塑造[J].长白学刊,2008(3):41-45.
[22]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8.
[23]王名.走向公民社会—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历史及趋势[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5):7-14+161.
[24]杨光斌.政治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Puzzles and Wayout: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al Organizations
ZHANG M in-sheng
(College of Politics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ShanxiUniversity,Taiyuan 030006,China)
The socialorganization isan important carrier in cooperating w ith the government to enhance the ability of socialautonomy and improve the social governance.At present,multiple difficultiesexis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al organizations,such asold-fashioned ideas,stiff system and inadequatemanpower,how to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s a problem.In this paper,we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weaken gradually the unified governance structure to provide action space for social organizations,and advice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al organizations from accelerating the cultivation of civil society to enhance the awaking of civil rights consciousness,accelerating system building to build the rational order of social organizations’development by the rule of law,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to strengthen the social composition of them iddle class.
socialorganizations;dilemma;dynam 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