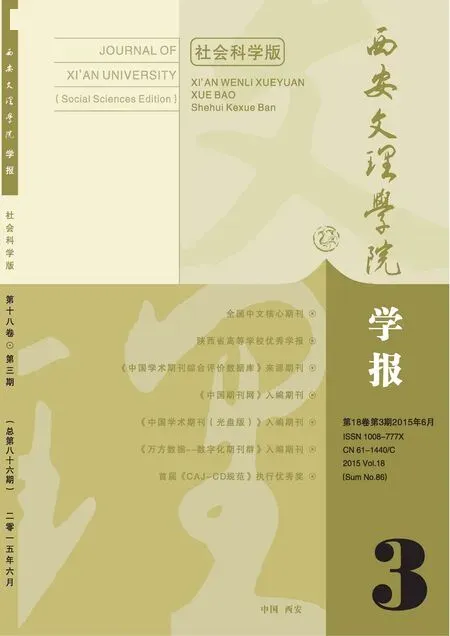民国时期西安的戏曲班社与城市文化
【历史文化研究】
民国时期西安的戏曲班社与城市文化
张妍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兰州730107)
摘要:在清末民初“戏曲改良”背景下,一批秦腔改良班社兴起于西安城内,这些戏曲班社大都实行室内剧场的经营方式。与此同时,随着西安城内商业的繁荣,逐渐形成了以秦腔剧场为主体的公共娱乐场所,导致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更形塑着城市文化。这些戏曲班社体现出秦腔戏曲文化所包含的传统特性、戏曲杂志与电气化舞台美术所展现的现代特性。通过探析民国时期西安秦腔班社,可窥得城市文化新旧交叠的特性。
关键词:民国时期;戏曲班社;秦腔;城市文化
收稿日期:2015-01-05
作者简介:张妍(1992—),女,陕西泾阳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近代中国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思想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J809.2
文章编号:1008-777X(2015)03-0051-04
文献标志码:A
秦腔作为一种民间戏曲,至少从明清以来便一直流行于关中地区。清末民初政权鼎革之际,一些地方知识分子有感于民众智识上的落后,欲以改良戏曲的实践活动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由此催生出一批活跃于民国时期舞台的秦腔班社。有学者指出,近代戏曲“已经成为了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沟通传统生活方式与时代主题的桥梁”。[1]民国时期的秦腔班社多集中在省城西安,带动了西安城市文化的勃兴,通过研究这些班社的发展与城市社会生活的变迁,可窥得民国时期西安城市文化的特殊性。
一、近代西安戏曲改良运动的演变
清末民初以来,一些受到改良和革命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便致力于启发下层民众,达到变革社会的目的。其中一些人将眼光聚焦到戏曲和戏剧上来,他们将变革传统戏曲作为启发民智、塑造新国民的手段。如上海的“新舞台”剧院,引进了西方的戏剧思想,通过推行一些文明戏来达到启蒙大众的目的。
与此同时,地处一隅的陕西由于相对封闭的地理位置,一方面,在近代新式话剧的普及进程中显得迟滞;另一方面,传统的地方戏曲秦腔则长久地流传下来。根据明万历年间的传奇抄本《钵中莲》的记载,秦腔至少兴起于明代中期。清代乾隆时期秦腔艺人魏长生在北京曾名噪一时。到了嘉庆时期先后形成了西秦腔、同州梆子、西安乱弹、汉调桄桄等不同唱腔的秦腔。道光至光绪年间,西安乱弹得到了突出发展,民国时期更是中路秦腔重要的发展转折阶段,西安易俗社的改革使得中路秦腔的面貌为之一变,被称为“改良新声”,由此东路、西路、南路秦腔开始衰落,后来即以“乱弹”通称秦腔。[2]37-44
早在1900年,来到西安作为观察记者的美国人尼克尔斯就曾惊叹于秦地人民爱看戏的传统,[3]可以想见乡民们除了日常的饮食起居和在田间辛勤劳作以外,并没有太多的消遣方式,也因为秦腔 “演唱者之表情足以感动愚民,使阅者欣赏,凡风雅之大夫,高贵之眷属,幼稚之民众,愚鲁之贩走,无不点首称许”。[4]
1912年,身为陕西同盟会员的李桐轩、孙仁玉在西安兴办了近代陕西第一个地方秦腔剧社——易俗伶学社(后改名为易俗社),其社名表达了“移风易俗”、“补助社会教育”的寄托。[5]易俗社作为民国创立以来第一个秦腔改良班社,其背后的支持力量、培养体制、剧本作家群、演出活动的范围就在陕西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呈现出特性。如创作剧目的作家群体包括李桐轩、孙仁玉、高培支、范紫东、封至模在内的一大批地方知识分子,而很多人都是从新式学堂肄业,具有传统理学兼新学背景的读书人。据统计,民国时期易俗社先后招收了13期学生,培养了600名优秀的戏曲演艺人才,共有约50人为易俗社撰写过剧本,创作了600个剧本。[6]
与此同时,西安城内还兴起一股创社热潮,先后成立了十余个带有戏曲改良色彩的戏曲班社,其中较知名者有:三意社,1915年由苏长泰创办,以编演传统戏为主,保留较多传统戏目,同时也编演新剧,同时在唱腔表演上有重大改革;正俗社,成立于1918年,多上演传统戏剧,在民国时期一度与易俗社、三意社成鼎立之势;榛苓社,1914年成立,由地方知识分子惠春波主办,仿易俗社招收学生设文化课,聘著名艺人出任教练。
易俗社、三意社、正俗社等剧社是在近代戏曲改良背景下由地方精英推动形成的秦腔班社,旨在通过新编剧目启发民智,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时人曾评价易俗社:“服装皆购自上海,武术则多为北平人所教。但观众听戏甚静,虽遇雨亦不避。且谈话,吵闹,咳嗽,吐痰之事极少,次数点与北平之听戏者不同……该社实为一最难得最努力之剧界新建儿。盖沪汉等处之旧剧团,多为经营性质,虽偶尔亦编演新剧,然其内容均只能为资产阶级谋娱乐,绝不肯为民众知识作宣传也。”[7]
二、戏曲班社剧场的出现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
传统秦腔戏曲演出常常是在一个土台子上,仅仅挂两个“出将”“入相”的帘子,以及舞台中央的一桌两椅,后来这些戏台逐渐演变为坐落于戏楼上的专门戏场。清末民初时期,单纯的庙会戏已不能适应群众的文化需求,逐渐出现售签(票)的营业演出,向室内营业剧场转变,此时陕西各县城镇开始有专门的戏场、戏园。[8]192-1991906年,蒲城张少云在西安关岳庙街建立宜春园剧场,开城市营业剧场的先河。1916年陆建章购得此园,又转卖给易俗社。此剧场建有舞台和观众厅,中间池座设有靠背木椅坐席,两边栏杆外增施站席,站席楼上建有包厢,采用售票对号入座形式作营业演出,成为民国时期陕西城市戏曲演出场所的基本形制。[9]245全盛时期的易俗社,“60亩的占地面积几乎占据了西安市中心钟楼广场的整个东北区域,场地内部包括露天剧场、舞台和栈桥、演出皮影和马戏的席棚,周围还有贩卖手工艺品和小吃的商铺,后来在西南方向还设立了电影院。”[10]这表明民国时期西安城内已形成了商业和文娱活动结合的功能区域。
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剧社和行会建造了以铅板盖顶,以芦席裹体的室内演出剧场。主要分布在钟楼地区和南院门地区:钟楼地区有西安三意社剧场(1914年创建于西安城内骡马市药材会馆的戏楼);还有1938年建立的西安集义社剧场(位于骡马市惠家巷南侧三皇庙内),它由观众厅、舞台、化妆室组成,设座468位,两侧站票可容纳观众1 000余人。[11]与此同时,南院门成为兼有文化娱乐和商业经济中心的功能区,南院门的福建会馆最初是正俗社(创建于1914年)的演出场地。彼时城内还有西安集义社剧场、夏声剧院、长安大舞台、民乐园戏院、国民戏院、山西会馆与银匠会馆舞台等戏院和剧场。[9]除此以外,还有一些知名票友李游鹤、阎甘园、封至模、李逸僧合办的“广益娱乐社”。[2]56
事实上,自从1934年陇海铁路修建以后,便带来了西安经济贸易的短暂兴盛:[12]物资可直接由铁路过潼关直抵省城,渭河流域的农产品也可以借此外运。外来货物的价格“正在被日渐发达的交通敉平”。[13]不仅东部发达地区的物资与人流纷纷涌入西安城内,带动了城内商业贸易的迅速发展,而且给城内的文化娱乐带来了新的气息。张恨水在《西游小记》中介绍了20世纪30年代西安的饭店、酒楼、电影院等营业场所,更是专门介绍了易俗社与正俗社的演出活动。[14]在20世纪40年代的一份名为《西京要览》的调查统计中,在“文化娱乐”一项里,标注出西安有两家电影院和八家戏剧剧社。[15]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西安城市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商业的繁荣,城市内部出现了洋行、住宿饭店、照相馆、电影院、剧场、图书馆等生活服务和文化娱乐场所,城市空间结构发生了变化,城市内部产生了固定的文化娱乐区域。[9]367
三、民国时期西安戏曲班社体现的城市文化特点
1.与政治力量的紧密结合
民国时期西安城内涌现的戏曲演出场所构成了城市内部的“公共空间”,[16]而在这些新形成的公共空间中,大众文化与地方政治在其中又如何交互影响?[17]以易俗社为例,我们可从中分析大众娱乐场所与地方政治的关系。一方面,易俗社在创社初期便集结了部分陕西同盟会员和军政要员,创社成员普遍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从成立起便一直是西安城内的“文化地标”,许多社会名流政要均观赏过演出。1924年鲁迅来西安讲学期间至易俗社观看演出后,曾赠予“古调独弹”的匾额一副,并把来陕讲学的酬金悉数捐给剧社,以鼓励这种民间曲艺团体的发展。[18]30西安事变期间,张学良、杨虎城通过安排蒋介石和南京来的一些高级官员至易俗社听戏,借机在背后周密部署安排,达成逼蒋联共抗日的历史壮举。[19]1946年,由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委派的“台湾光复致敬团”至西安时被安排在易俗社欣赏秦腔。[20]可以看到易俗社在创办初期和其后发展过程中始终充斥着政治和军事的底色。作为一个民间剧团,有如此特殊的背景,确属十分罕见。在西安这样相对较孤立的内地城市里,政客和军人的政治势力居于支配地位。对当权者而言,易俗社是地方文化的象征,所以班社长期依附于政治势力,并借此获得社会地位与经济援助。[21]195-211
2.秦腔剧种包含的传统性
易俗社创社初期,主办人就将“历史戏曲”作为编演曲目中的主要内容,引用“历史上政治之优缺点及个人善恶之行为作为后人鉴戒”。[22]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易俗社受到时任冀察政务委员、抗日名将宋哲元的邀请,赴北平演出,为华北抗日将士打气,将古代守家卫国的传统融进了时代的“民族主义”中。剧社的封至模准备了反映民族英雄抗敌救国的《山河破碎》《还我河山》《淝水之战》《韩世忠》等新编历史戏曲。封至模还在《京报》阐述了其创作意图:“现在的中国,现在的中华民族,现在国人的民族意识是否与南北宋相若?”[23]150-160
尽管在新文化运动的20世纪20年代,胡适、傅斯年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张要彻底废弃传统戏曲、引进西方的话剧与歌剧,认为这种反映传统的君臣、忠孝与贞洁等道德伦理内容的戏曲无益于激发现代的国民性,但是民国时期的西安却呈现出传统戏曲与现代话剧并驾齐驱的现象,且戏曲的发展经久不衰,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易俗社两赴北平演出,并借此与齐如山、程砚秋、尚小云、欧阳予倩等剧界名流的交往,更是获得了平津剧界的关注。作为城市文化一部分,戏曲更多地呈现出了传统的坚韧。[24]
3.报刊与舞台美术体现的现代性
民国时期已有专门的戏曲杂志、报纸(及副刊)刊载戏评。以易俗社为例,在1922年赴汉口演出时,多家报纸对其演出均做了报道,且受到了在汉口的黄炎培、康有为等社会名流的褒扬,梁启超更是题赠“化风成俗”的匾额送至剧社。又如在1937年,剧社曾赴北平、天津演出,《北洋画报》刊登广告介绍其上演剧目,以“陕西梅兰芳”的称号盛赞了剧社演员王天民“其扮相与声音俱能销魂动魄”。[25]《国剧画报》《民治报》《大公报》都对其演出做了报道,[18]30《京报》《十日戏剧》等报纸杂志刊载了演出剧照和演员定妆照,《全民报》刊载短评:“然易俗社之戏剧内容,涵义深远,极合时代之要求,有相当之价值,则诚然也。”[23]150-160由此可知此时报刊的传播,对于戏曲班社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除了演出场所的固定化,民国时期秦腔的舞台美术也不断推陈出新。20世纪30年代初,西方的洋货进入中国广大农村,美孚牌石油(即煤油,旧称洋油)逐渐为舞台照明所利用,照明设备由灯碗变成了火蛋,“棉花内包上石盐绑在铁丝上,然后浸泡在盛满煤油的脸盆内,晚上演出时点上,光照四方,也算文明了一时。”[8]192-199从20世纪20年代初赴汉口演出后,易俗社便开始改良化妆和布景,女演员戴在头上的装饰从土气纸花改为玻璃管串。[26]20世纪30年代,在两次赴北平演出期间还借鉴了京剧的布景效果,将一些新的舞台灯光、布景模式带回了陕西,在舞美上追求“声、光、电、色”的现代化。[27]这种剧场设施、舞台美术的电气化正反映了民国时期城市生活中广泛的物质文化变迁。
通过梳理民国时期西安城内秦腔班社的发展过程,我们会发现由梁启超、陈独秀等知识分子倡导的戏曲改良理念,如何被一群“行事较低调的地方知识分子持之以恒地付诸实践”。[21]195-211这种开启民智、改良社会风气的实践因时因地而不同,有选择地将西式话剧引进的上海“新舞台”,又将传统秦腔进行改造的陕西“易俗社”。在以易俗社为代表的戏曲舞台上,可看到《三滴血》《柜中缘》这样批判封建道德伦理的题材,更可观赏《鸦片战争》《颐和园》这样反映爱国主义的时代主题剧目。在民国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与动荡的政局之下,这些戏曲班社对社会的影响十分深远:他们成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赋予了秦腔这种传统艺术新的发展空间,在演员培养、剧目创作、舞台美术上均推陈出新,关于秦腔艺术的理论研究文章也频繁地刊载于报刊上;弘扬了陕西地域文化并将其传播开来,剧目“从劝剪发辫、戒缠足、戒包办婚姻、戒迷信到提倡文化科学、警示国家存亡与民族兴废的危机”上均有涉猎,社会风气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这些戏曲班社成为城内的“文化地标”,政客名流与平民百姓都可以欣赏演出。通过研究民国时期西安城内的戏曲班社,我们不仅能看到此时呈现新旧交叠特性的城市文化,也能感受到其与政治局势和时代背景相互交织的复杂面向。
[参考文献]
[1]陈平原.中国戏剧研究的三种路向[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1-27.
[2]苏育生.中国秦腔[M].上海:上海百家出版社,2009.
[3][美]弗朗西斯·亨利·尼科尔斯.穿越神秘的陕西[M].史红帅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 120-125.
[4]侯鸿鉴.考察西北教育及调查陕甘秦腔戏剧述略[J].江苏教育,1935,(9):137-140.
[5]陕西易俗社.易俗伶学社缘起[G].西安:公益印刷局,1912:20-25.
[6]陕西省西安市文化局文艺研究室.西安易俗社五十年[N].戏剧报,1962,(9):22-27.
[7]陈光垚.最近西安之戏剧[C]//易俗社七十年资料汇编编辑组.易俗社七十年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82:40-45.
[8]刘俊凤.民国关中社会生活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9]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文化艺术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10]雷茅宇.古调独弹——西安易俗社剧场剖析[J].建筑学报,1983,(1):37-37.
[11]任云英.近代西安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研究:1840—1949[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5.
[12]侯鸿鉴.西北漫游记·青海考察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2002:14.
[13]杨早.西望长安不见家——近代游记中的西安叙事[J].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0,(1):137-144.
[14]张恨水.西游小记·西行杂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2003:47-49.
[15]曹弃.西京要览[G].西安:扫荡报办事处,1945:10-15.
[16]李长莉.清末民初城市的“公共休闲”与“公共时间”[J].史学月刊,2007,(11):83-89.
[17]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4.
[18]易俗社七十年资料[C]//易俗社七十年资料汇编编辑组.易俗社七十年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82.
[19]葛鲜挺.革命军兴易俗社——“双十二”和“七·七事变”中的易俗社[J].当代戏剧,1992,(5):27-38.
[20]许雪姬.台湾光复团的任务及其影响[J].台湾史研究,2011,(2):97-145.
[21]李孝悌.西安易俗社与中国近代的戏曲改良运动[C]//陈平原.西安: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2]易俗社章程[C]//易俗社七十年资料汇编编辑组.易俗社七十年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82:55.
[23]何桑.百年易俗社[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0.
[24]李孝悌.民初的戏剧改良论[J].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3,(22):281-307.
[25]逸飞. 陕西易俗社将来津[N]. 北洋画报, 1937. (1568).
[26]肖润华.三十年来之秦腔[C]//易俗社七十年资料汇编编辑组.易俗社七十年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82:50-52.
[27]甄亮.易俗社文化谈[J].当代戏剧,2008,(6):36-45.
[责任编辑张敏]
Opera Troupes and City Culture of Xi’an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ZHANG Yan
(SchoolofHistoryandCulture,LanzhouUniversity,Lanzhou730107,China)
Abstract:Opera troupes thrived in Xi’an city in the background of Opera Reforming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Most of the opera troupes operated in indoor theaters. The commercial prosperity in the city gave rise to the popularity of public recreation places with Qing Opera Theater as its main component part, which l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yout of the c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shaped the city culture. These Opera troupes display a combin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and the modern. The rising and developing of Qing Opera Troupe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hows an overlapping of the new culture and the old in city.
Key words: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pera troupes; Qing Opera; city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