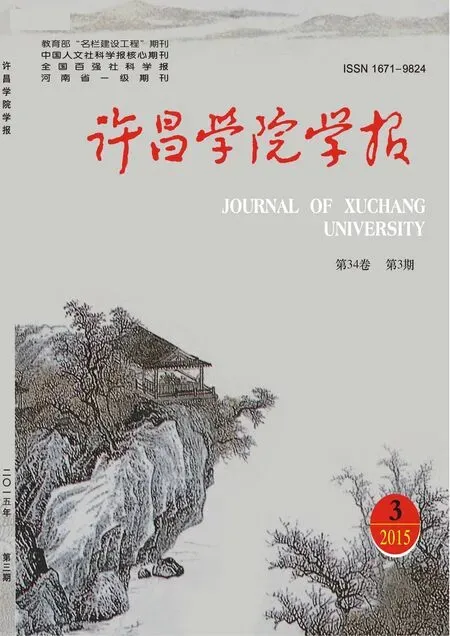谶纬与钟嵘诗论
王 承 斌
(许昌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0)
谶纬与钟嵘诗论
王 承 斌
(许昌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0)
谶纬在东汉盛行一时,魏晋南北朝时仍有相当的势力。纬书中包含的奇特的想象、丰富的辞藻等,对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如此,谶纬还对后世文学理论影响甚大,钟嵘的诗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谶纬影响:在诗的起源方面,他的“物感说”不同于传统的讽谏教化论,而是在纬书“物感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对诗歌地位、作用的认识上,钟嵘弱化了传统诗论强调的教化作用,将诗与自然万物联系,从诗在天地万物中所处的地位上论其作用,带有一定程度的天人感应色彩;在诗歌抒发情感方面,钟嵘表现出与传统诗论更大的不同,很重视与“志”、教化无关的怨情,这是对纬书“诗含五际六情”、强调诗歌抒发情感的进一步发展。
谶纬;钟嵘;诗学思想
东汉之际,谶纬盛行,汉末此风稍息,但流风余韵绵延不绝。南朝齐梁时,纬书仍有相当势力,《隋书·经籍志》记载:“至宋大明中,始禁图谶,梁天监已后,又重其制。”[1]941可见纬书在当时还甚有影响,但因对统治者不利,才一再被禁。
纬书包含有奇特的想象、丰富的辞藻,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对文学创作有较大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许多文人自觉取其精华,如曹植、曹丕、嵇康、阮籍、左思、沈约、谢灵运等人作品中都有纬书的影子,李善注《文选》时已指出过这一点。西晋文论家挚虞曾说过:“图谶之属,虽非正文之制,然以取其纵横有义,反覆成章。”[2]1906肯定了谶讳对文章的作用。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文之枢纽”部分专列《正纬》一章,讨论纬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对纬书也十分重视。钟嵘诗论思想与谶纬的关系不甚明显,前人研究钟氏诗学思想时,多注意儒家传统诗论和玄学之影响,论其与谶纬关系者甚少。但若深入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钟嵘诗论与谶纬之间有较密切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诗之产生——物感说
物感说是六朝重要的文学观念之一。它认为文学是“心”感于外物的结果,自然外物的变迁,引起主体的心灵波动,情不能已,自然发而为文。如《文心雕龙·明诗》篇中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3]65便是此义。其《物色》篇中进一步探讨了自然景物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认为春夏秋冬的更迭,使作家依次产生“悦豫之情”、“郁陶之心”、“阴沈之志”、“矜肃之虑”等,并提出“情以物迁,辞以情发”[3]693的观点;《诗品》开篇即言“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4]1等,也是强调了人“感物生情”,诗歌自然脱口而出。
关于物感说,学界一般认为源起于《礼记·乐记》,因其中首次提到“心感于物”的观点——“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5]661,它指出了音乐等艺术是心感于物的结果。人们将此作为物感说的起源当没有错,不过它未对“物”作明确界定,也未言明“物”是如何引起创作主体的内心感受,如喜怒哀乐之类情感的变化,并如何以不同艺术形式表现出来,故而还只是模糊的、不成熟的说法。
纬书继承发展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大肆宣扬符瑞、灾异、谴告等天人感应现象,文艺也被其纳入天人感应的神学体系中。这方面黄金鹏先生有过较详细的论述[6]106,可参看。大体上说,纬书认为文艺可以沟通天、地、人,如音乐能“承天心,理礼乐,通上下四时之气,和合人之情,以慎天地者也。”(《乐纬·动声仪》)[7]537诗歌是“天文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也”[8]2123等。在这种背景下,纬书进一步发展了物感说——“诗人感而后思,思而后积,积而后满,满而后作。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7]544这不仅指出了诗是诗人感于外物的产物,还指明了“感物”而生诗的具体过程是“感——思——积——满——作”,这对后世文论产生了巨大影响。如陆机在《文赋》中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9]1即指出了写作过程是睹物感叹而思,悲喜之情积于内,自然发于外的过程。本文前面提到的《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所探讨的自然景物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也与此相关。钟嵘论诗时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斯四侯之感诸诗者也。……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4]47其中“摇荡性情”、“感荡心灵”等,也明显是心感于物后积、满而思,最后发之于外的过程,这无疑是在纬书诗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此外,纬书“物感说”中所感之物还包括“事”,即把“事”这一现实生活引入诗论中,提出诗歌应反映社会现实问题。如《春秋纬·说题辞》中说:“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淡为心,思虑为志,故诗之为言志也。”[8]2123其中的“事”即指现实生活;又“乐者,移风易俗。所谓声俗者,若楚声高,齐声下。所谓事俗者,若齐俗奢,陈俗利巫也。”[7]538其中之“事”指“齐俗奢,陈俗利巫”,也包含了社会现实内容。这里需要一提的是,纬书强调诗歌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与传统诗论中的“美刺说”有所不同。我国很早便有将文学创作与社会政治相联系的观念,如先秦以来就存在的采诗观风,强调“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5]663,便是认为诗歌是社会政治的反映。后来的《诗大序》继承了这一点——“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10]16等,也是强调诗歌对社会政治的反映,很少涉及政教外的其他方面。这方面前人论述已多,此不赘。而纬书中说的诗歌所反映之“事”,无论是“在事为诗”,还是“齐俗奢,陈俗利巫”,虽与“言志”及“移风易俗”的教化相关,但相比于《诗大序》等的说法,却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教化说的影响,更多地是指社会风气,指日常生活中的个人之事。
众所周知,钟嵘的“物感说”中所感之物,除指自然景物外,还包括“楚臣去境”等社会生活内容,他非常重视现实生活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可以说,钟嵘的“物感说”存在一个转向,即由魏晋以来所强调的自然物向社会事物的回归,但又不能说是向传统“感物”的完全回归。李健先生曾专门撰文讨论钟嵘的“感物”思想,认为它“与先秦两汉的文学教化有着根本的不同。其主要表现在:在钟嵘的感物思想中,作家、艺术家与社会现实的感应也像与自然物象的感应一样是自然、自由的,而先秦两汉的文学教化是强行赋予、刻意赋予,没有任何自然与自由可言……”[11]96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先秦两汉时的“感物”说,不重自然物象而重讽谏教化,而钟嵘之“感物”说,除强调“诗是个人生命对自然生命的一种感发和体察”外,还强调对社会生活中“群”“怨”的反映,并且“不像《毛诗序》那样着眼于政教得失,而是立基于个体的哀乐。”[12]55即和政教的关系已不大,有很多是与纯粹的个人情感相关,如男女恋情、个人不幸遭遇引发的怨情等,《诗品》上品中的李陵、班姬,中品的秦嘉、徐淑等均如此。他的“感物”强调的是社会生活对人心的触动,是自由、自觉的,摆脱了刻意附会政治的因素,这更接近纬书的说法。
二、对诗歌地位和作用之认识
先秦儒家诗论给了《诗》很高的地位,但那多是和政治教化相关的。如孔子论诗时提到诗的“兴观群怨”功能,强调美刺教化、有补于世,强调诗歌在疏导人们情感、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主要是就诗之社会政治作用而言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诗》有了极高地位。
《诗》等文艺在纬书中也有极高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教化有关,如纬书中认为《诗》“在于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讽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诗纬·含神雾》)[7]464即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认为音乐具有巨大的感染力——“温润以和,似南风之至,其为音,如寒暑风雨之动物,如物之动人,雷动兽含,风雨动鱼龙,仁义动君子,财色动小人。”[7]540即音乐潜移默化的感染力可以用来移风易俗等。这些都是从教化角度来说的。不过,《诗》在纬书中的崇高地位不全取决于此,纬书已从更高的哲学高度上对《诗》作了全新判断。《诗纬·含神雾》中说:“诗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万物之户也。”[7]464由于目前所见的纬书缺失严重,我们已无法确知这句话的具体语境及语意所指,但有一点很明显,它认为诗在天地之间居于重要地位,能够成为君德、百福、万物的始祖和本源。在这里,诗似乎成了宇宙万物的核心。这实际上把文学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诗纬》对诗之性质的这一认识,与传统诗论强调诗的政治教化功能有所不同,它将诗与自然天地联系起来,是从诗在天地万物中所处的地位上,来认识它所能发挥的作用的。《诗纬》作者之所以能提出这一说法,当是与纬学中的“天人感应”说相联系的。前文已经提到过,在纬学的思想体系中,文学艺术可以使天、地、人沟通联系起来,所以,纬学中的诗论、乐论等,也就是其“天人感应”说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对《诗》之地位、作用的认识也就明显突破了传统教化说。
钟嵘在这方面的认识,非常接近纬书。他对诗歌地位作用的重视,在某些方面是着眼于教化,如认为诗歌能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强调诗歌在宣泄情感,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方面的作用等。但其认识又不限于此,如在论诗歌作用时提到“照烛三才,辉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响,幽微藉之以昭告。”[4]1其中“照烛三才”一说,即隐含了纬书中文艺沟通天、地、人的思想,并认为诗之光彩可辉光、陶冶天地万物,也是从诗在天地万物中的地位上论其作用的。他还认为诗歌能“动天地,感鬼神”[4]1,这明显是取用《诗大序》中“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10]2的说法,却舍去了其中关于诗歌政教作用的“正得失”的论说,故与政教的关系更远,带有了一定的天人感应色彩,这些不能不说是受纬书的影响。
三、诗歌之“言志”与“缘情”
传统儒家诗论强调“诗言志”,强调诗对社会政治的反映,强调诗有补于世,很少涉及到情。现在学界一般认为,“言志”主要是表现人的政治抱负及对政治社会问题的态度和看法,虽然它不完全排除人的情感因素,如《诗大序》中曾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吟咏性情”[10]2等,但对涉及到的“情”,多要求归于雅正,强调“温柔敦厚”,“发乎情,止乎礼仪”,要求诗歌表达的思想感情不能有悖于“礼仪”,不能违背封建伦理纲常,不能有损于统治阶级利益;要求诗歌能从思想感情上感化人和对人进行道德规范。
相比于传统诗论,纬书论诗有明显不同,它十分强调诗歌的抒情性。《春秋纬·演孔图》中说“诗含五际六情。”此条下宋均注为“六情,即六义也,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7]583其实,此“六情”释为《诗经》之“六义”甚不恰当,难以说通。现在一般认为,这“六情”说出自《齐诗》翼奉的“六情”说。翼奉在其上元帝封事中明确说到“六情”为“北方之情,好也;……东方之情,怒也;……南方之情,恶也;……西方之情,喜也;……上方之情,乐也;……下方之情,哀也。”[13]3168即指人之喜、怒、哀、乐、好、恶等情感,这也是汉代对人情分类较普遍的看法。如班固就曾说:“喜怒哀乐爱恶谓六情,所以扶成五性。”[14]382仲长统也说过:“喜怒哀乐好恶谓之六情”[15]957等。翼奉提出“六情”时,特别说到“诗之为学,情性而已”[13]3170,认为诗应该自由、充分地表达人的情感,这实际上是在“言志”说的基础上融合了情感因素,将“言志”说政治方面作用同人之情感因素结合了起来。其中,“止乎礼义”方面被淡化了,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言志”说对情感的束缚。对于《诗经》研究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开启了古代诗论由“言志”到“缘情”的道路,六朝时的“缘情说”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诗缘情”所强调的思想感情的抒发,已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儒家诗教的束缚,强调“发乎情”,看不到多少“止乎礼”的要求。这一点前人论述已多,此不赘。
钟嵘论诗时也非常强调情感,《诗品序》中明确说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4]1认为诗歌和舞蹈都是性情的表现,没有性情的摇荡,便没有诗与舞,从而旗帜鲜明地提出诗歌“吟咏情性”的主张。更重要的是,钟嵘特别重视那种与教化无关的个人情感,如《诗品》极重怨情,其上品十二家诗中,提到“怨情”的达八家之多;被列为中品的一些诗人,如“凄怨”的秦嘉、徐淑诗,“孤怨宜恨”的郭泰机诗,“长于清怨”的沈约诗等,他也都给予了肯定。他所重视的这些怨情,有些与“言志”、教化相关,但也有相当部分与之无关,如班姬诗“词旨清捷,怨深文绮”[4]94,与传统之“志”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无关教化,却被列入上品;又评秦嘉、徐淑“夫妻事既可伤,文亦凄怨。徐淑叙别之作,亚于《团扇》矣。”[4]197夫妻之情也与言志、政教无关,却列为中品之首;张华虽“儿女情多,风云气少”[4]216,也被列入中品,等等。反之,一些教化意图异常明显的诗作,如班固的《咏史》等,钟嵘却只字未提。张伯伟先生论及这一点时也曾说:“(钟嵘)将诗歌反映的内容及效用落实于‘可以群、可以怨’二端,‘嘉会寄诗以亲’即‘可以群’,‘离群托诗以怨’即‘可以怨’。而且,这种‘群’和‘怨’并不像《毛诗序》那样着眼于政教得失,而是立基于个体的哀乐。”[12]56所以说,钟嵘虽未完全摆脱“言志说”的影响,但无疑是沿着纬书强调诗歌抒情性这一路走下来,离传统“言志说”更远了一些。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纬书的诗论与传统诗论之间虽有一些共同之处,但也有着诸多的不同。比较钟嵘诗论与二者的关系,我们不难看出,钟嵘论诗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传统诗论的影响,但在很多方面却更接近纬书。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对钟嵘诗论有更清楚、全面的把握。
[1] 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 严可均.全晋文[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 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4] 钟嵘撰、曹旭集注.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5] 孔颖达.礼记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6] 黄金鹏.纬书与汉魏六朝文论[J].北京大学学报,1999(4):105-110.
[7] 安居香山.纬书集成[M].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8] 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9] 陆机.陆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0]孔颖达.毛诗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1]李健.钟嵘的感物美学[J].文学评论,2004(5):94-101.
[12]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4]班固撰、陈立疏证.白虎通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4.
[15]严可均.全后汉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责任编辑:石长平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etic Theories of ChenWei and Zhong Rong
WANG Cheng-bi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Xuchang University, Xuchang 461000, China)
Chen Wei was prevalent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still popular in Wei and Jin Dynasty. The strange imagination and rich rhetoric in Chen Wei's writings have a tremendous impact on the literary creation. At that time, many literary theorists noticed the fact and pointed it out. Chen Wei also has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literary theory. Zhong Rong's poetic theory was largely affected by it, for example, about the origin of the poem, Zhong Rong's poetic theory, the Wu Gan Shuo, developed from Chen Wei's.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oetic status and role, Zhong Rong weakened its education role; instead he contacted poetry with the natural world and commented on poetic role from its status in the natural world. Zhong Rong also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e resentment irrelevant to traditional moralizing. He further developed Chen Wei's theory emphasizing poetry emotion which is greatly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poetic theory.
Chen Wei; Zhong Rong; Poetic theory
2014-10-26
王承斌(1972—),男,安徽郎溪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汉魏六朝文学与文献学。
I206
A
1671-9824(2015)03-0025-04
——以王嘉《拾遗记》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