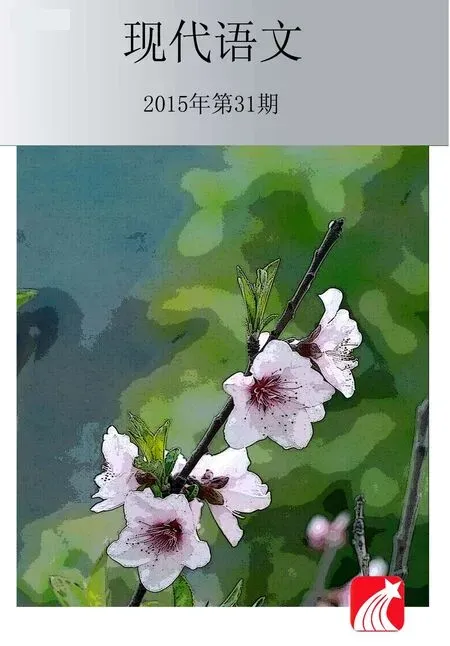论穆旦诗歌的家国情怀
○史红华
论穆旦诗歌的家国情怀
○史红华
摘要:穆旦是一位优秀的爱国诗人,在苦难深重的20世纪40年代,他的心总是紧紧地与祖国和人民连在一起。穆旦的诗歌始终把握时代脉搏,直面人生的复杂性和苦难性,他以拥抱人民、民族的姿态,显示了知识分子的正义与良知。
关键词:穆旦诗歌家国情怀
1937年日寇入侵,中国的土地、生灵遭到残酷的践踏,对于忧患深重的中国来说,抗战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抗战给国人带来流亡、屈辱、受难,同时也带来奋起、热情与抗争。许多诗人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之中,将文学的社会化转换为文学的政治化,主流诗歌以人民、时代为本位,坚持对现实的关注。时代容不得任何有良心的诗人超然世外,诗歌创作亦不可能仅仅向内思考自我、艺术的意义和价值,还必须向外探索自我、艺术和时代的联系。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穆旦进行诗歌创作的时候,首先把目光聚焦到了国家、民族、社会的发展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得他的思考始终指向他们所生活的那片土地。穆旦积极应和着时代风云的呼唤,以知识分子视角透视、感受着现实,将中国知识分子的个人意识主动地融入了人民意识,其诗歌深层的文化意蕴是以家国为本的入世情感和心理,从中人们可以触摸到现代中国人灵魂的骚动不安,感受中华民族在特定时代的痛苦与艰辛。
一、西南联大南迁苦,莘莘学子爱国情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7月29日、30日北平和天津沦陷,战火烧到了平津。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北方最著名的学府决定南迁,在湖南长沙建立国立长沙联合大学,简称“长沙临大”(即后来西南联大的前身)。校园并非世外桃源,动荡的现实生活时时激荡着穆旦的心:
然而,那是一团猛烈的火焰,
是对死亡蕴积的野性的凶残,
在狂暴的原野和荆棘的山谷里,
像一阵怒涛绞着无边的海浪,
它拧起全身的力。
在黑暗中,随着一声凄厉的号叫,
它是以如星的锐利的眼睛,
射出那可怕的复仇的光芒。
——(《野兽》)
写于1937年的这首诗,恰是诗人在战乱离散之际,感受民族的痛苦,在自我灵魂深处挣扎、搏斗的心灵历程。他以野兽的受伤和不屈作为中华民族遭受侵略和反抗意识之觉醒的象征,在诗歌深处回响着民族抗战的有力呼唤。这类关注民族苦难现实的诗作还有《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古墙》《出发》《原野上走路》,等等。
1938年,长沙陷入危机。1938年2月29日,穆旦与西南联大的师生开始了步行迁校的“世界史上艰辛而具有伟大意义的长征”。这次长征全程350华里,历时68天,跨越了湘、黔、滇三个省份,最终到达昆明。诗人的双脚从此真正地踏上了广裹而坚实的中国大地,感受着祖国母亲的苦难,触摸着她累累的伤痕。惨遭铁蹄践踏的祖国,千万个家园被无情地毁灭,到处是战乱,人民已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些个残酷的,为死亡恫吓的人们,/像是蜂拥的昆虫,向我们的洞里挤。”(《防空洞里的抒情诗》)饱尝战乱之痛的中国人民的险恶处境,使穆旦深刻地体会到人的生命“像一只逃奔的鸟,我们的生活/孤单着,永远在恐惧下进行,/如果这里集腋起一点温暖,/一定的,我们会在那里得到憎恨,/然而在漫长的梦魔惊破的地方,/一切的不幸汇合,像汹涌的海浪,/我们的大陆将被残酷来冲洗。”(《不幸的人们》)踏过了处于艰苦岁月的三千国土,如此跋涉回来的诗人,不会是在象牙塔里抒写风花雪月的文学青年,而是让自己贴到泥土里,与社会、与现实相融。
战争使穆旦的心灵和肉体受到双重的考验,其在诗人眼前展开的不仅是烽火连天、山河破碎的现实,更有对民族生存现状的痛苦记忆,这使得穆旦的诗一触及祖国和人民,其笔墨就蕴涵着无限深情,《赞美》就是一部典范之作。“我有太多的话语,太悠久的感情,/我要以荒凉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骡子车,/我要以槽子船,漫山的野花,阴雨的天气,/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赞美》写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作者宛如胜利的预言家在高声欢唱:“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诗人穆旦在痛苦中并没有彷徨,他从人民身上看到了民族潜在的巨大力量,由此发出了反复的咏叹:“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他真诚地赞美生活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人民,赞美他们的坚忍,赞美他们由苦难走向抗争,赞美整个民族的崛起!
二、缅甸远征不归路,一腔热血照汗青
如果说,从1937年到1942年,穆旦还是在局外感受战争带来的苦难,那么参加远征军并经历惨绝人寰的野人山战役,则是真正意义上用生命体察和咀嚼苦难。联大毕业不久的24岁的穆旦投笔从戎,毅然参加中国远征军,任随军翻译,出征缅甸抗日战场。仅仅三个月后,诗人便亲历了一场无比残酷的战斗:“那是一九四二年的缅甸撤退,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被死去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毒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够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和空间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他更不能支撑了,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到八日之久。但是这个二十四岁的年青人,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结果是拖着他的身体到达印度。虽然他从此变了一个人,以后在印度三个月的休养里又几乎因为饥饿之后的过饱而死去,这个瘦长的,外表脆弱的诗人却有着意想不到的坚韧。”整个战斗中,现实一次又一次地把穆旦推向绝望的边缘,无情地把他置于常人难以想象的生命的极限状态,穆旦的这次死亡临界点的体验,这番特殊的经历和深重的苦难,使得其诗歌真实地描写饥饿、灾难、病痛、死亡,表达出非同常人的切身感受和丰富体验。在1945年,穆旦曾写了这么一首诗来追念战争中那些倒下去的伙伴——《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抗日战士“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而捐躯,而他们的归宿则是“原始的自然”——这个人类最初的“故乡”。这是对出国作战的众多野人山胡康河谷的白骨的献祭,是对死者的悲歌与礼赞,也是对众多无名英雄、农民战士的悼歌,更是诗人对残酷战争决绝的反抗。
对战争中个体的复杂感受的关注是这一时期穆旦很多诗歌的主题,《出发》里这样写道:“告诉我们和平又必需杀戮,/而那可厌的我们先得去欢喜。/知道了‘人’不够,我们再学习/蹂躏它的方法,排成机械的阵式,/智力体力蠕动着像一群野兽,”“给我们善感的心灵又要它歌唱/僵硬的声音。个人的哀喜/被大量制造又被蔑视/被否定,被僵化,是人生底意义;/在你的计划里有毒害的一环。”战争服从鲜明的政治目的和政治要求,当个人并不是麻木地服从战争时,个体会用理性审视战争的残酷。战争里也有人性的复杂,有死亡的威胁,战争的过程成了每个个体经历炼狱的一个过程,而战争的意义和结果还是未知的,所以穆旦鼓励个体在残酷的现实中“活下去”:“活下去,在这片危险的土地上,/活在成群死亡的降临中,/当所在的幻象已变狰狞,所有的力量已经/如同暴露的大海/凶残摧毁凶残,/如同你和我都渐渐强壮了却又死去,/那永恒的人。”穆旦的这种现实关怀延续了鲁迅关注个体生命的思考,他告诉我们在战争年代的语境里需要对个体精神的关注,亲历了战争的诗人,其笔下的战争从来不是英雄主义的凯旋之歌,也不止于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式的对侵略者的浮泛谴责。在穆旦看来,战争是“一次人类的错误”,在战争当中,真正的敌人是罪恶的战争“本身”。换言之,穆旦对战争的怀疑与抗拒不仅仅是基于单纯的民族感情,更是基于对人类的博爱。观照战争,穆旦己超越了政治派别的意识,而站在“人”的立场上,以个体之良心见证这血和肉的搏斗。
三、流离辗转生计艰,心忧国难悯苍生
1943年初,穆旦在印度养病,撤回国内后,他没有重新回到联大外文系任教,而是颠沛于昆明、重庆、贵阳、桂林等地,先后在中国航空公司、重庆新闻学院、西南航空公司等处做翻译、学员或雇员,时而失业,生活困顿。一直到1946年,曾经一起在缅甸抗日战场共事的罗又伦将军邀请穆旦去沈阳创办《新报》,穆旦才结束了辗转于大西南各地的生活,到了东北。长期生活于社会底层,穆旦与劳苦大众有了更广泛的接触,也真切地了解到了底层贫民的喜怒哀乐。在这一时期穆旦经常面向时代、现实、人民、民族命运等宽阔的情思地带,为忧患的人生担待,表达出对芸芸众生的终极关怀。像《农民兵》,从普通的生命看到人间的不公,从生命对生命的压迫发掘社会良心:“他们是工人而没有劳资,/他们取得而无权享受,/他们是春天而没有种子,/他们被谋害从未曾控诉。”字里行间充溢着对社会底层人民的感叹牵念。同时,和爱相对应的与生俱来的批判意识被激发得强悍无比,不遗余力地发掘现实的黑暗、丑恶与荒谬。“我们站在这个荒凉的世界上/我们是廿世纪的众生骚动在它的黑暗里,/我们有机器和制度却没有文明/我们有复杂的感情却无处归依/我们有很多的声音而没有真理/我们来自一个良心却各自藏起”(《隐现》)。中国人处于怎样失语和黑暗的环境中?真理还有人坚守么?文明还有人追寻么?良心在变质么?冷静客观不动声色的陈述表达了对现实生存的批判和否定。穆旦这种“拥抱人民”的姿态,这种寻找诗与现实、时代契合的精神立场,注定了他的诗骨子里永远镌刻着典型的中国情感和中国经验。
1945年,是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一年:抗日战争胜利了!穆旦亲身感受了这一伟大时代的气息。亲历了战争,对战争有着深深的恐惧与抗拒的诗人,自然会感到振奋与喜悦,在《轰炸东京》中他深切感怀着抗日战争胜利的欣喜,情不自禁地呐喊着,“我们的思想炽热已不能等待”“一个合理的世界就要投下来”,在诗中穆旦亦有力地谴责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们要把你们长期的罪恶提醒”,显示出其鲜明的反法西斯的立场。
血火交迸、纷乱异常的20世纪40年代,战乱、灾难、死亡,他以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身心,最敏锐地感受着中华民族的痛苦与磨难。在诗歌创作方面,穆旦自始至终坚持着诗歌艺术责任和现实责任的统一,尽管他没有用他全部诗作加入到集体的为民族前进的鼓动呐喊中来,但是穆旦的诗歌是深深地扎根于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的,而且他始终不忘用诗歌来表现民族的苦难和人民水深火热的处境。穆旦身上的这种对于民族国家的责任感,是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所应该具有的;穆旦所葆有的这种对于民族国家的责任感也正是当代知识分子所缺失的,他留给我们的思考至今仍然闪现着智慧的光辉。
参考文献:
[1]温儒敏.中国现代批评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杜运燮,周与良,李方等编.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穆旦逝世20周年纪念文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79.
[3]穆旦.穆旦诗文集(二卷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4]穆旦.穆旦译文集(八卷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辛笛,陈敬容,杜运燮等编.九叶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6]杆运燮,袁可嘉,周与良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
(史红华辽宁大连辽宁对外经贸学院116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