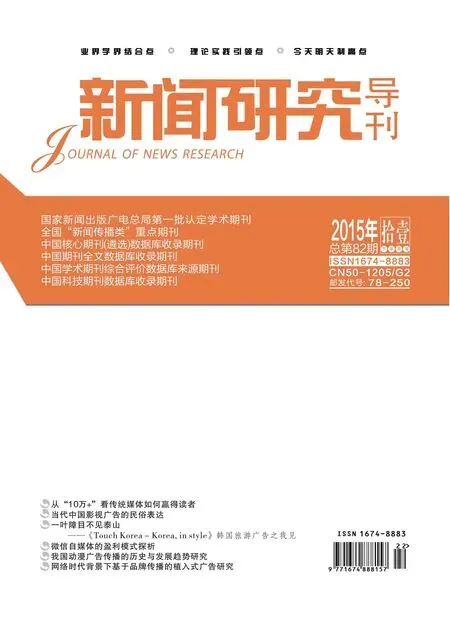网络公共事件研究的符号学路径
——《网络公共事件:符号、对话与社会认同》序
董天策
(重庆大学 新闻学院,重庆 400030)
网络公共事件研究的符号学路径
——《网络公共事件:符号、对话与社会认同》序
董天策
(重庆大学 新闻学院,重庆 400030)
李红博士的专著《网络公共事件:符号、对话与社会认同》即将出版,要笔者作序,深感欣慰,慨然应允。由于这部专著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笔者作为他的导师,自然深知其中甘苦。
进入新世纪以来,网络舆论逐渐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领域。社会与学界对网络舆论的研究,除了对网络舆论做一般的学理性探讨,关注最多的是网络舆情与网络热点事件。一般地说,对网络舆情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当前网络舆情态势的监测、分析、引导、控制,这在社会管理上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而网络热点事件作为网络舆情的波峰,自然是研究的一个重点,迅速成为一个研究热点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究竟应当如何审视网络热点事件,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首先,如何命名“网络热点事件”,不同的论者往往使用不同的概念,诸如“网络事件”、“网络群体性事件”、“新媒体事件”、“网络媒介事件”、“网络公共事件”、“网络舆论事件”、“网络舆情事件”、“网络突发事件”、“网络集群行为”、“网络集体行动”、“网络群体行为”等等,不一而足。其中,使用最普遍的概念无疑是“网络群体性事件”,而论者的研究旨趣主要在于探讨“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监测、防范、应对、引导、管控等问题。这样一种危机管理的研究视域与学术立场,在现代风险社会自然具有其迫切的合理性与现实性。
不过,“网络群体性事件”究竟是不是一种群体性事件?在笔者看来,这至少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学理问题。从研究视域与学术立场看,对所谓“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基本上沿袭了“群体性事件”研究的价值预设,认定其具有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故而强调将其当作一种可能的或现实的危机来加以管理。问题在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真的就是洪水猛兽吗?就在2009年《瞭望》周刊发表《应对“网上群体性事件”新题》一文引起广泛关注之际,社会学家邵道生随即撰写《“网络民主”十三论:“网络民意冲击波”》一文,在光明网-光明观察中大声疾呼:网上“一呼百万应”现象不应该叫“网上群体性事件”,应该叫“网络民意冲击波效应”。遗憾的是,大多数研究者并未理会邵先生的见解,仍然在有关研究中采用“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命名以及危机管理的研究范式。
2010年,钟瑛、余秀才在《新闻与传播研究》第4期发表《1998-2009重大网络舆论事件及其传播特征探析》一文,通过对160个重大网络舆论事件的解析,尤其是通过各种检索工具追踪事件发展过程以及最终解决结果,发现这些重大网络舆论事件所产生的作用大多是正向的:起正向作用的案例106起,比例为66%;起中性作用的案例为39起,比例为24%;起负向作用的案例有15起,比例为10%。两位学者研究的“网络舆论事件”,所指对象与“网络群体性事件”相同,只是名称各异。这促使笔者思考“网络群体性事件”究竟是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2011年7月,笔者在暨南大学传媒领袖讲习班做了一个专题演讲,题目即“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的学理反思”,阐明所谓“网络群体性事件”,在大多数情况下的准确命名,应当是“网络公共事件”。
把“网络热点事件”命名为“网络公共事件”,意味着它是社会公众通过互联网就某种公共事务或公共问题表达意见、展开讨论的公共舆论过程。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网络舆论事件”或“网络舆情事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说,“公共舆论是人民表达他们意志和意见的无机方式”,“在公共舆论中真理和无穷错误直接混杂在一起”。因此,公共舆论是需要加以理性引导的。另一方面,公共舆论又是公民个人“对普遍事务具有他特有的判断、意见和建议,并予以表达”而形成的言论集合,是民心民意的反映,又是值得高度重视的。如果从网络民主、网络公共领域的建构这一学术视域出发,“网络公共事件”或许是具有重要建设意义的论题。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指出,“我们要选择所研究的问题,在这种选择之中,就包含了价值,我们陈述这些问题时,要使用一些核心观念,在这些核心观念之中,也包含了价值,价值影响到它们的解决思路。”李红博士当初选择“网络公共事件”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相对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而言,不仅解决了概念的科学性,更重要的是转换了学术视域,着重探讨当代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建设问题。在此意义上,这样的学术切入角度,与众多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相比,无疑具有十分鲜明的学术创新意义。
回顾起来,李红博士把自己研究的问题纳入传媒公共性或传媒公共领域的研究传统,可以说是找准了理论归依。然而,究竟如何进行研究,即运用什么理论资源来探讨网络公共事件,却是一个颇费踌躇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独立思考,李红博士告诉笔者运用符号学理论来展开研究,笔者觉得很有新意,但同时也感到很有挑战性。
理论上,符号学与传播学具有天然的联系,但由于符号学在不少学人看来既玄妙又高深,难以在研究中加以有效运用。虽然国内学人早在80年代中期就意识到符号学与传播学的联系,却很少运用符号学理论来研究传播问题。直到1997年吴文虎教授出版《广告的符号世界》,运用符号学理论来研究传播问题才成为国内学者比较系统的学术实践。其后,刘智著《新闻文化与符号》1999年出版,算是把符号学引入了新闻学研究。而真正体现运用符号学理论来研究新闻传播实绩的,应推曾庆香2005年出版的《新闻叙事学》。该书把新闻作为话语分析的对象,对新闻话语的结构、生成、事实建构、神话性、意识形态建构以及原型沉淀做了深入论述,为深化新闻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方法论。当然,在此前后,符号学基础理论研究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譬如,李彬教授著《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2003年出版,赵毅衡教授著《符号学:原理与推演》2011年出版,都是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
李红博士运用符号学理论来研究网络公共事件的挑战性表现在哪里呢?我以为,网络公共事件作为一个公共舆论过程,其话语表达虽然相对集中,却也存在空间开放、众声喧哗、话语碎片等显而易见的特点,倘若从某个局部切入进去做一番符号学分析,撰写一篇或数篇几千字的论文,应不是什么难事。而要对网络公共事件研究进行系统的理论建构,则显然是一件十分费力的事情。经过一番潜心静气的研究,李红博士终于建构出网络公共事件研究的逻辑框架,除导论和结语外,分五章写出具有内在学理联系的博士论文,包括:“网络公共事件研究的符号学路径”、“意义框定:网络公共事件中的命名与定义”、“修辞效果:网络公共事件的符号修辞分析”、“网络公共事件的叙事结构与舆论召唤”、“自我与他者:网络公共事件中的主体分析”,堪称符号学视域中网络公共事件研究的重要成果。
那么,李红博士的这部专著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新见解新认识呢?作者认为,“在中国,网络公共事件层出不穷,可以看作是社会共识和对话的缺乏所导致。网络公共事件中的对话涉及到主体与主体之间、文本的不同叙述层次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个体与意识形态之间等等,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共同生活。”作者强调,在“断裂社会”,面对“城乡断裂、阶层断裂、官民断裂、制度断裂、信任断裂、价值观断裂等等”现实,“‘断裂’不但是一个客观的现实,而且是一种认知和预设,在网络公共事件中就总是体现为‘弱势感’或‘相对剥夺感’,从而对权势阶层充满怨恨,造成网络空间的群体极化。而权势者在此过程中又不能很好地认知自己的社会位置,这就导致很容易将不同意见和怨恨理解为是‘对抗’,‘破坏’和‘颠覆’,从而将事件看成‘暴力’而用暴力对待。”面对这种困境,作者主张,“只有通过对话才能实现精神的沟通和认同的形成,人与人之间以及社会中的断裂才能得以修复。”全书结语以“通过对话实现认同”为标题,不仅彰显了作者深沉的人文情怀,而且提供了另一种弥合社会分歧的治理思路,可喜可贺!
是为序。
G206.2
A
1674-8883(2015)22-0200-01
董天策,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