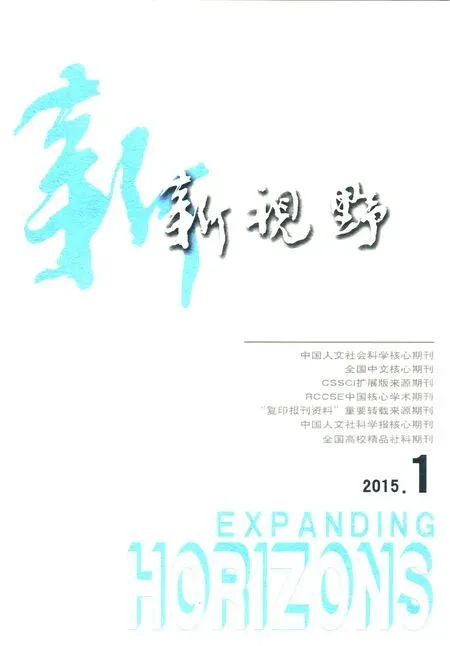京津冀协同发展对“环渤海”地区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文/杨东方
京津冀协同发展对“环渤海”地区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文/杨东方
京津冀是“环渤海”地区具有制高点作用的经济发展“域面”,打造京津冀的区域合力会助推“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梯度空间是“环渤海”地区的重大发展机遇,能否缩短京津冀协同发展产生集聚效应的时间是“环渤海”地区发展面对的挑战。应当设计“环渤海”地区整体空间规划,打造“环渤海”地区若干经济发展“域面”,建设北京与“环渤海沿海经济带”的“点轴系统”以探索京津冀协同发展带动“环渤海”地区发展的路径。
京津冀;“环渤海”地区;协同发展;经济发展梯度
一 京津冀是“环渤海”地区具有制高点作用的“域面”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基础
城市是一个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核心载体。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辅相成的进程看,城市的发展有效地带动了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2013年北京的GDP为19500.6亿元,天津为14370.1亿元,分别占京津冀GDP总和的31.37%和23.11%。河北省的GDP为28301.4亿元,占京津冀GDP总和的45.52%。从我国东部沿海省份的经济发展状况看,2013年河北省的GDP虽然低于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但高于辽宁(27077.7亿元)和福建(21759.6亿元),[1]这与北京、天津高级要素的辐射和产业链的延伸以及服务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所以,京津的经济发展对河北省经济的带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区域的发展要靠城市的带动,同时,城市的发展要有区域的支撑。北京和天津的面积分别是1.64和1.19万平方公里,占京津冀总面积的7.59%和5.51%,是典型的城市形态。河北省的面积为18.77万平方公里,占京津冀总面积的86.90%。目前,北京、天津的环境压力和经济发展转型要求以及发展空间约束,需要河北省提供区域的支撑,当然,这种区域的支撑不是以牺牲河北省利益为代价,而是需要整合目前京津冀各自的发展目标,实现京津冀经济社会协同发展。
京津冀作为一个区域共同体,客观存在协同发展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题汇报时提出的“四个立足”,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装上新引擎:“立足各自比较优势”以打造京津冀新的增长极;“立足现代产业分工要求”以增加京津冀布局合理性;“立足区域优势互补原则”以提升京津冀整体竞争优势;“立足合作共赢理念”以实现京津冀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二)京津冀“域面”的作用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看,京津冀是一个具有制高点作用的“域面”,在“环渤海”地区表现尤为明显。
经济发展“域面”的“制高点”作用一般表现为:因地位高远而能够做到战略宏阔,因位置优越而能够调动和集聚资源,因竞争优势而能够引领发展方向,因水平高度而能够多有制胜把握,因倍受关注而能够赢得发展机遇。京津冀所具有制高点的“域面”作用,在“环渤海”地区表现尤为明显。2013年,“环渤海”地区的辽宁、河北、山东、北京和天津“三省两市”的GDP之和为143934.1亿元,其中京津冀占比为43.19%。在“环渤海”地区中,京津冀因政治、文化、交通等功能,因经济发展的体量和品质,因科技、信息、资本、高素质劳动力的汇聚,是一个具有制高点作用的经济发展“域面”,而且京津冀作为一个区域整体,完全有条件、也有能力发挥制高点的“域面”作用,打造京津冀的区域合力,助推“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同时,打造京津冀的区域合力,也有利于实现我国经济发展南北平衡、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优化资源要素的布局与配置、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竞争优势。
二 京津冀协同发展对“环渤海”地区的机遇与挑战
(一)空间范围过大是“环渤海”地区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一般讲,“环渤海”地区是指环绕着渤海全部及黄海的部分沿岸地区所组成的广大经济区域,以京津冀为核心、以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为两翼的“环渤海”经济区域。然而,现实中“环渤海”地区的空间范围过大:“2+3”区域,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面积51.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3亿;“2+5”区域,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山西和内蒙古中部地区,面积11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6亿。
1.空间范围过大导致合作成本太高。长三角的面积约21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4亿。珠三角的面积约2.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500万。由此可见“环渤海”地区在这样大的范围内进行经济合作,合作的成本很高,必然引发“行政区利益”与“经济区利益”间的冲突。
2.空间范围过大导致行政色彩太浓。长三角虽然由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组成,由于其面积不大,而且在历史上、在民间就存在比较好的分工与合作,特别是宁、沪、杭地区各种渊源交错,具有一定的一体化基础,行政色彩并不强烈。“环渤海”地区进行经济合作,必然借行政之力,由政府推动。然而,每个行政区域本身经济发展就不平衡,有的是相当不平衡,不可能采取不顾本行政区域经济均衡发展而进行“环渤海”地区经济合作的行动。
3.空间范围过大导致内部成分太复杂。从地理区域看,“环渤海”地区由3个相对独立的“港口—腹地”区域构成:以大连为出海口,腹地是东北地区;以青岛、烟台为出海口,腹地是山东全省并兼华东、华中少部分地区;以天津为出海口,腹地是华北地区和西北地区。由于其复杂的内部成分,且各组成部分自成体系,导致“环渤海”地区经济合作在政策制定、信息共享以及要素流动等方面不一致,进而影响其经济合作向纵深发展。
A:力嘉投资建立的潮阳力嘉中学在2012年7月11日举行落成庆典并交付使用。从最初投资的4000万元开始,至今已经投入了7000万元,全校共2600人,每个班平均都在60人以上,且学校的规模还在不断扩大。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对“环渤海”地区发展的机遇大于挑战
1.发展的机遇。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存在“一带”“双核”的核心地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是依托“一带”和“双核”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梯度空间,这对“环渤海”地区是重大的发展机遇。
(1)依托秦皇岛、唐山、天津、沧州,做强“京津冀沿海经济带”,进而做强“环渤海沿海经济带”。目前,秦皇岛、唐山、天津、沧州四个城市的GDP总量为24673.1亿元,占京津冀GDP总量的39.69%。[2]“京津冀沿海经济带”做强,可有效地与大连、烟台、青岛连接,进而做强“环渤海沿海经济带”。“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不能在区域内无重点地全面铺开,必须有重点地回归“环渤海”的属性,否则会因空间范围过大而丧失合作的动力。“环渤海沿海经济带”是一个区域开放系统,临海的地理位置优越,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演进,经济发展中市场的力量不断加强,资源优化配置的效率不断提高,已初步具备为周边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依托的能力,能够有效拉动“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
(2)京津双城联动引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方向,也会带动“环渤海”城市群的健康发展。北京和天津的经济规模大,具有集聚产业的功能,是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也是“环渤海”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城市群是以核心城市向周围辐射所构成的城市集合,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体现了实现区域发展动力、区域发展质量和区域发展公平三者在内涵上的统一,是国民经济发展、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标志之一。促进京津两个核心城市的联动,充分发挥“极点”的作用,决定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方向、力度和质量,也会通过带动“环渤海”城市群的健康发展进而提高“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质量。
2.面临的挑战。能否缩短京津冀协同发展产生集聚效应的时间,是“环渤海”地区发展面对的主要挑战。
京津冀协同发展促成各种生产要素向京津冀聚集,这是经济活动和经济要素在空间上的、客观的极化过程。如果把经济增长分为经济的平衡增长和经济的不平衡增长,那么一个国家或区域要实现经济平衡增长只是一种理想,绝对的经济平衡增长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与“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需要注意解决二者之间的经济增长关系,既要承认区域经济增长的差距,更要解决区域经济增长的差距。因此,能否缩短京津冀协同发展产生集聚效应的时间是对“环渤海”发展的挑战。
(1)尽量降低京津冀协同发展对“环渤海”地区发展的负效果。京津冀协同发展会产生吸引力,使周边地区的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转移到京津冀,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周边区域的发展机会,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对“环渤海”地区产生的负效果。那么尽量降低负效果,在资金、人才、贸易等方面尽量使“环渤海”地区具有一些有利的条件和发展的机会,具有一些现代化产业发展的条件,具有一些获利的基础,为最终实现京津冀与“环渤海”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创造条件和奠定基础。
(2)尽快显现京津冀协同发展产生的扩散效应。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初级阶段,集聚效应是主要的;当京津冀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扩散效应才会开始加强,并通过一系列联动机制不断向周围扩散,从而逐步缩小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在一般条件下,市场的作用通常是倾向扩大而不是缩小区域间的差异,这就需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加强政府正确的、有效的干预,使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扩散效应尽快显现。
三 京津冀协同发展带动“环渤海”地区发展的路径
(一)设计整体空间规划
设计“环渤海”地区发展的整体空间规划,一方面是设计京津冀协同发展带动“环渤海”地区发展的整体空间安排,另一方面是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有效的空间依托,二者相辅相成。如果不认真设计“环渤海”地区发展的整体空间规划,以往京津冀合作桎梏的表现就会在“环渤海”地区重演,各地政府就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以整个区域的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来进行“碎片式”的决策和行动。
设计“环渤海”地区发展的整体空间规划的原则应体现以下内涵:充分发挥出“环渤海”地区利用、整合资源以及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有效发挥出“环渤海”地区通过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促成区域内各经济部门有机结合的能力;全面形成“环渤海”地区整体竞争优势,提高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水平;有效体现出“环渤海”地区保护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的协调局面。“环渤海”地区发展的整体空间规划原则,既有利于形成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生态,也有利于形成环渤海地区全面发展的生态,还有利于形成环渤海地区与周边区域实现依托发展的生态。
(二)打造若干经济发展“域面”
所谓经济发展的梯度,是对经济活动在空间不均匀分布状况的描述,是指经济发展水平在空间上所存在的差异。梯度推移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经济发展在空间上是从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推移,推移的过程缩小了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对均衡。地理空间是影响梯度推移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梯度推移方向的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低梯度地区的接受能力,低梯度地区只有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和发展才能够能动地接受高梯度的产业转移。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打造京津冀高梯度“域面”,但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目前,京津冀自身也需要打造经济发展“域面”,如以北京、天津、唐山为点的“域面”,以北京、天津、保定为点的“域面”,以北京、天津、沧州为点的“域面”,以北京、唐山、秦皇岛为点的“域面”,以北京、秦皇岛、承德为点的“域面”,以石家庄、保定、沧州为点的“域面”,等等。这些“域面”之间是存在一定经济发展梯度的,梯度推移的实现取决于低梯度“域面”的生产力水平。
因此,“环渤海”地区需要积极主动地打造若干经济发展“域面”,使之具有接受、消化京津冀高梯度域面经济活动的能力,能够优先地实现高梯度地区的功能和产业的落地。地理空间并不是决定梯度推移的必然因素,经济发展的内涵和水平才是决定梯度推移的必然因素。打造若干经济发展“域面”以实现梯度推移,意味着要在整个“环渤海”区域内实现跨越地理空间的跳跃式的梯度推移。“环渤海”地区,只要有效提升自身经济发展水平,把握好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周期,优化与其他地区经济互补的品质,不断加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互动性、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双向性,是会实现跨越地理空间的跳跃式的梯度推移,使京津冀梯度推移在整个“环渤海”地区展开。
(三)建设北京与“环渤海沿海经济带”的“点轴系统”
理论上讲,北京与“环渤海沿海经济带”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点轴系统”。点轴开发理论认为,点轴开发是经济增长的能量走向整个区域空间的第一步,也是经济在区域的整个空间成长的第一步。“点轴系统”所形成的经济发展能量不仅会在系统内部得以强化,而且会向系统外部进行经济和社会扩散,在新的地区与新的点之间形成“点轴子系统”,在区域中形成不同等级的极点和轴线,它们相互连接将会构成分布有序的点轴空间结构。
北京与“环渤海沿海经济带”的“点轴系统”,对于“环渤海”地区的生产要素流动和经济活动联系,提供了比单个极点和孤立经济带发展更为优越的空间,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环渤海地区资源和要素的优化配置以及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要从北京形成若干条垂直于“环渤海沿海经济带”的放射性经济合作走廊。目前,北京和天津之间经济合作走廊的优势已初步显现,北京和唐山、沧州、秦皇岛之间经济合作走廊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空间需要继续强化和完善,同时还要建设北京与“环渤海沿海经济带”的辽宁、山东的经济合作走廊。
建设北京与“环渤海沿海经济带”的“点轴系统”,在规划建设之初一般处于基态,所具有的能量不高,辐射力和影响力较弱。当对资源要素进行整合、重新优化配置后,北京与“环渤海沿海经济带”的“点轴系统”吸收了能量,就会跃升到较高能级,处于激发态,具有强劲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既实现了北京对“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有效促进,又实现了北京和“环渤海”地区有机和谐的联系。另外,北京与“环渤海沿海经济带”的点轴开发模式,在“环渤海”空间上就会具有形成经济发展网络的基础,而经济发展网络一经形成,标志着“环渤海”地区发展的空间结构的有机形成,能够产生出单个点和线所不能完成的功能,能够使扩散作用增强,使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在空间上趋于均衡。
注释:
[1]数据来源:2013年北京、天津、河北、辽宁、福建、浙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数据来源:2013年天津、唐山、沧州、秦皇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责任编辑 顾伟伟
F127
A
1006-0138(2015)01-0110-04
杨东方,中共天津市委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天津市,300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