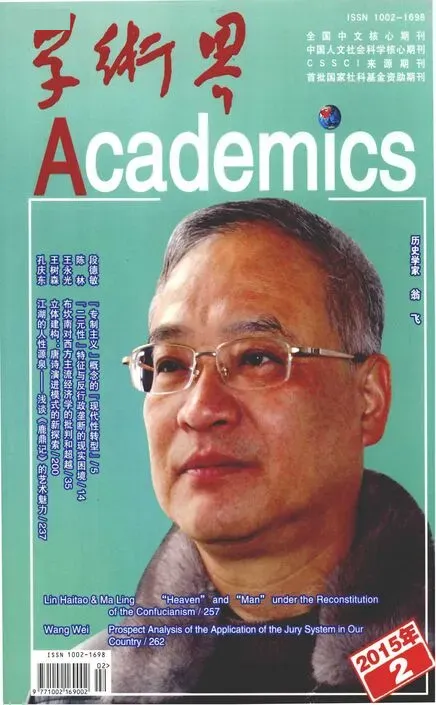立体建构:唐诗演进模式的新探索——谈余恕诚唐诗研究的贡献
○王树森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安徽 合肥 230051)
一、前 言
余恕诚先生(1939-2014),安徽省肥西县人,是我国著名古典文学专家,一生专攻唐诗。他的唐诗研究,在文献和理论两方面,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他与刘学锴先生三十余年亲密无间,合作共事所完成的《李商隐诗歌集解》《李商隐文编年校注》,被誉为新时期唐诗文献整理的“扛鼎之作”。而他本人所独立完成的《唐诗风貌》《唐诗与其他文体之关系》《“诗家三李”论集》〔1〕等论文论著,则显示出他对唐诗理论研究的重视与自觉。他的唐诗理论研究,最重要的贡献,是对立体建构唐诗演进模式进行了新的探索。
二、纵向寻绎诗歌迁变轨迹
早在1978年,傅璇琮先生在反思此前文学史研究的不足之时,就曾敏锐地指出:
我们现在的一些文学史著作的体例,对于叙述复杂情况的文学发展,似乎也有很大局限。我们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包括某些断代文学史,史的叙述是很不够的,而是像一个个作家的评传、作品介绍的汇编。为什么我们不能以某一发展阶段为单元,叙述这一时期的经济和政治,这一时期的群众生活和风俗特色呢?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来叙述,在哪几年中,有哪些作家离开了人世,或离开了文坛,而又有哪些年轻的作家兴起;在哪几年中,这一作家在做什么,那一作家又在做什么,他们有哪些交往,这些交往对当时及后来的文学具有哪些影响;在哪一年或哪几年中,创作的收获特别丰硕,而在另一些年中,文学创作又是那样的枯槁和停滞,这些又都是因为什么?〔2〕
傅先生在这里提出的一连串问题,其实已经包含着唐诗研究需要进行立体多维审视的深入思考。无独有偶,余恕诚先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中文系大学本科生开设“唐诗研究”选修课,开宗明义,也曾以形象的语言阐释了立体建构唐诗演进体系的必要性。他说:
我们原来的唐代文学主要介绍作家作品,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熟悉了一、二流作家和他们的部分作品,但我们作为基础课的唐宋文学,往往局限于一个个作家,一篇篇作品,比较孤立和分散,就像我们夜晚看蓝天上的星星,这颗叫什么,那颗叫什么,是已经知道了一些。但这些星星与星星之间有什么关系,哪些星星组成一个星座,哪些星座又组成星系(比如什么是太阳系,什么是银河系),星系和星系之间又有什么关系。这些纵横联系,我们还不甚了然,而不了解这种纵横联系,我们孤立地想记住这些星星是很难的,对天体更本质的认识也还很不够的。现在,我们就是要把唐代诗国天幕里的群星纵横联系起来,力图构成一个完整的图像,获得一个整体认识。〔3〕
两相对照,可见两位先生都对发明唐代诗歌的纵横联系怀有自觉的意识。与傅先生侧重于从文化背景、社会发展寻求唐诗繁荣成因有所区别,余先生将主要精力放在诗歌内部发展规律的探讨。这种探讨,首先是以对诗歌迁变纵向轨迹的寻绎为发轫。
唐代诗歌高度繁荣,但毕竟持续了三百年的时间,有其自身发展、繁荣、衰落的内在轨迹。这一点,古人即已有所认识,明人高棅提出的“四唐”说可为其代表。〔4〕在《唐诗风貌》一书中,余先生则以初、盛、中、晚为序,结合代表性作品,探讨不同阶段诗歌的内容与艺术,寻绎唐诗演进的纵向轨迹。在其晚年所做的《晚唐诗坛与李商隐诗歌》的学术讲演中,他进一步宏观概括了唐诗发展的“三变”:
唐代诗歌至少有三次大的变化,第一次是陈子昂、李白以及盛唐诗人改变了初唐的面貌,这是一次变化。陈子昂高举诗歌大旗要改革,但是真正的完成是到李白他们的手里,迎来了盛唐的高潮——开元天宝诗歌;第二次高潮是中唐,就是韩愈、白居易这些人在盛唐之后,不愿意跟盛唐亦步亦趋,不愿重复盛唐,他们再开辟、再变化,改变了盛唐诗歌的面貌,出现了中唐。中唐又是一个繁荣的多元化的面貌,这是第二次大变化;第三次大变化,……这个时候,在新的社会土壤上又产生一批人,即晚唐的李商隐、温庭筠、杜牧。这批诗人是真正代表晚唐的,表现晚唐人的心理,展现晚唐的那种风情,这是唐诗的第三次变化。〔5〕
全局式的鸟瞰之外,余先生对具体作家前后影响继承关系的研究,则更显细致深入。如发表于1999年的《诗歌:从韩愈到李商隐——兼谈文学演进中的穿透与移位现象》一文,就是讨论中晚唐文学巨子韩愈与李商隐之间艺术上的内在相通与前后迁变。文章分别论证了李商隐学韩愈的三个层面:一是从对韩文的推崇到对韩诗的追摹;二是以李贺为中介的又一种追摹;三是李商隐主体风格的确立。对于第三个层面,余先生着重探求主观化的渊源,如他认为“李商隐的创作沿韩愈、李贺诗主观性增强的趋势继续向前推进”,又认为李商隐笔下的形象与心灵情感不像前两位诗人那样呈现出表现与被表现的关系,而是“混沌一片,常常把内心景观作为直接描摹与表现对象,展现更为本原的心灵状态。”又说:“在意象的组合上,从韩愈到李商隐,经历了逐步削弱逻辑制约的过程。”〔6〕这些论断,都是对中晚唐诗歌艺术变迁深层线索的重要发现。
余先生考察唐诗艺术迁变,眼界不局限于唐代,而是将视域扩展到整个一部中国诗史。如《“诗家三李”说考论》强调三李对屈原艺术经验的继承;又如杜诗和汉乐府文学传统间的关系,也在他的多篇论文中被提及。当然,与这些前人已有较充分论述的内容相比,余先生更致力于考察甚少为人关注,却又客观存在且十分重要的诗史演进问题。这方面的代表作,首推《从“阮旨遥深”到“玉溪要眇”——中国古代象征性多义性诗歌从主理到主情》一文。〔7〕请看作者在篇首的导论:
中国诗史上风格以幽深奥隐著称的诗人,魏晋之际有阮籍,晚唐有李商隐。阮诗代表作标题为“咏怀”,诗旨在政治和感遇方面,以传统批评眼光看,托体自高;李诗多言男女闺闱,诗旨众说不一,很少有人把它和政治感遇型的《咏怀》诗相提并论。实际上两家诗在魏晋之际和唐代,亦即中国五七言诗发展的两次高潮中,代表着当时象征性、多义性诗歌所达到的高度。两家诗歌的风貌特征和前后变化,可以作为很好的切入点,进而研究中国诗歌比兴象征传统的发展及其艺术经验。〔8〕
文章对阮籍与李商隐两位异代诗人诗歌风貌的异同,有许多具体论述,这里不拟一一征引,但是从他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优秀诗人,十分深入地研究前代文学传统,并且努力根据当下的具体创作实践进行继承革新。这种自觉的文学发展意识,不仅是保证中国文学生生不息的不竭动力,其中所反映出的诗人们的巨大艺术创造力以及在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即便对于今天的文学创作与研究,也有很高的借鉴意义。
三、横向展示异体相生景观
唐代诗歌一盛再盛,高潮迭起,从纵向看,得益于几代诗人不断总结诗学遗产,推陈出新;而从横向看,也与当时诗、词、文、赋诸文体全面繁荣,诗歌主动吸取其他文体艺术经验密不可分。对此,前人在讨论相关具体问题时已有注意,如北宋沈括说“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近人胡小石、任半塘、林庚、钱锺书等人讨论杜甫《北征》“以赋为诗”、唐声诗与曲子词之关系、盛唐诗赋消长、樊南四六与玉溪诗风消息相通等问题,均有所涉及。余先生在1990年代研究唐代诗歌迁变,也已关注。到了上世纪末,则开始对唐代以诗歌为中心的文体关系进行系统思考。之所以要研究这一课题,是因为他注意到:“从创作上看,唐代是我国古代文学全面发展时期,除曲外,各种重要文体,此时都已出现。充分展现了文体生态的丰富性和相互间的促进和依存关系。异体相生,诗文的繁荣乃至传奇与词的产生,都与文体之间的交融和由此带来的文体合成与生发力量有一定关系。”〔9〕而此后十多年间,他先后撰写近二十篇相关论文,重点讨论文体交融及其合成与生发力量,并最终形成四十多万字的专著——《唐诗与其他文体之关系》。在本书开篇,余先生如是阐明他的研究目标:
本书研究唐代诗歌与其他各体文学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推进的关系。从诗与诸文体的交融互动中,展示唐诗广泛吸收众体之长,不断推陈出新、开拓变化、一盛再盛、空前繁荣的景观,发掘其长期保持并发挥文体创新能力的原因;同时,也从诸文体并立与联系这一特定角度,考察唐代诗、赋、文、小说、词在文苑中彼此依存发展的状况:赋与诗在唐代的新一轮互动交流,古文在诗歌启发与带动下的革新,诗歌的影响与传奇与词体的生成。合而观之,则又可见诸体相辅相成、相互生发,对成就一代文学繁荣所起的巨大作用。在对上述几个方面进行描述的基础上,本书还将进一步探讨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及相关文学理论问题。〔10〕
立足于文体关系的横向互动,余先生对唐代一流诗人的诗歌成就所依赖的文体关系背景作了精辟深入的揭示,如李商隐是晚唐近体诗大家,同时又是四六文高手,二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尤其是擅长骈文对李商隐诗歌艺术有何种促进作用?虽有钱锺书先生揭示在前,但其具体情况仍未有详论。余先生则通过对义山大量代表性诗作的细密分析,指出:“李商隐以骈文为诗,把骈文的因素带进诗歌,讲究诗歌的词采、对偶、用典、虚字,以及表达上的委婉含蓄,给诗歌再次带来新的变化。”〔11〕又如李贺诗歌的实际内容,后世阐释分歧很大,余先生的《李贺诗歌的赋体渊源》一文,〔12〕独辟蹊径,拈出李贺诗歌的对赋体艺术经验的吸收这一重要话题,从主要题材、创作精神、艺术手法等多个方面,探讨李贺诗歌的赋体渊源,并将此作为辨识李贺诗歌思想内容和艺术创新的重要切入点,同样,有关李白、杜甫与赋体的关系,韩文与韩诗的关系,唐诗与传奇的互动等,余先生都作了十分深入的探究,通过他的研究,让人们意识到,积极主动吸收其他文体艺术经验,是唐诗发展的重要根源。
文体互动所产生的巨大艺术推动力,在有关诗词文体代兴的讨论中,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展现。余先生不仅梳理了南朝宫体诗经唐代宫词而向五代宋初词体提供艺术养料的轨迹,而且特别深入地探讨了中晚唐诗歌流派对晚唐五代词风的影响。《中晚唐诗歌流派与晚唐五代词风》一文“论述中晚唐诗派在词体初建过程中所起的影响作用,以及其如何导致温庭筠、韦庄二家词风之不同。旨在藉此深化诗词之间关系研究,全面认识词体文类风格的形成,与词家早期疏、密二派肇始之由。”〔13〕对于此文,《文学评论》在当期的编后记中说:
(本文)是一项古典诗词关系覃思精研的优异成果。……余先生在这里,深思熟虑后先凿开一口通“风”的活眼。从“中晚唐诗风”与“晚唐五代词风”的活眼切入,再细辨“风色”,蹑“风”追影,即从两“风”的通贯、重迭、递进及演化关节探寻中晚唐诗派在词体构建过程中的影响,最后夹入“情境意味”与两“风”在审美感知上气格异同的甄别,这样诗与词在文体建构上的质性演化图像就浮现出来了。
既考察外在体制的表层影响,更注重内在词语、意象、情境、风格等多种因素的潜在演化,使诗词两大文体间的前后相递的实际关系有了堪称完美的展示。
考察唐诗与其他文体之间的关系,个案研究之外,理论性的总结更有启示意义。余先生无疑自觉于此,几乎每一个个案研究的最后,总会有高度凝练的理论概括。譬如以李商隐《韩碑》诗为例,余先生创造性地阐释了“破体”为文所体现的唐人文体创新精神;〔14〕讨论李商隐诗歌受小说影响,作者除了考察影响的具体表现,而且根据清人纪昀所提出的诗史“升降大关”的判断,指出传奇小说对于中晚唐诗歌的影响,元白叙事诗的继承是显露的,而“从李贺等滥觞,到李商隐深入推进,大量吸收偏记杂录、志怪小说、神鬼故事、野史、传奇内容,吸收传奇小说的艺术经验与笔趣,其变化是更为深入的”,对于“加深对文体间交融互动和中晚唐诗歌演变的认识,无疑是十分重要的。”〔15〕有关这种总结性的看法,更为集中地体现在《唐诗与其他文体之关系》一书的绪论和结语之中,如:
透过每一种文体的发展,几乎都能看到异质的引入,及其与其他文体相融的交叉性、综合性。多种文体,包括前代和后代之间不同类型之文相互影响、渗透、交流,相互扶持,乃至相互竞争,使其在发展过程中能不断吸收各方面的营养,克服因循守旧的惰性,是文学创新和文体变革的重要动力。〔16〕
再如: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不断肯定和否定、异化和同化的过程。一种文体,本来无所谓形制。开创者文成法立,乃有形制。但此形制,并非僵死不变。它在发展中一方面自律肯定,同时又不断自体否定。前者创之,后者承之因之,更必须广之大之,才能如生命之有生存发展。文体窘于既定之格套,必然要求突破。在越出本界与他体互参时,可能对自体有新的发现,亦可能因得他体的成分与艺术手法之助,生发出新的枝芽,开放出新的花朵。〔17〕
系统总结文体互动、异体相生对促进中国文学演进的积极意义,又指出人为设置文体禁忌可能是宋代以后有关文体失去生机活力的重要缘由。这些看法,对我们深化对中国文学史众多现象或理论问题的认识,有着重要启发。
四、“风骨离不开性情”:发掘唐诗演进的文化土壤
刘学锴先生在为《唐诗风貌》作序时指出:
本书对唐诗总体风貌及各个时期、各个重要诗人与诗派、各种体裁风貌的准确把握与细致辨析,固然很见功力,但著者的主要着眼点和用力处,却不止是对唐诗风貌的描述,而是对风貌成因的深入探讨。书中特别注意在诗歌风貌与社会生活之间,寻找中介,联系特定文化背景、诗人生活与创作心态,探讨某种诗歌风貌形成的基因,而且这种探讨,常能发人之所未发。〔18〕
刘先生所揭示的,确为余先生治学的重要特点,但凡研究一个问题,不仅力求毫发无遗地知其然,同时也要探寻其所以然。通过对唐代诗歌迁变的纵向寻绎,以及对唐诗与其他文体关系的横向展示,余先生已经完成了唐诗演进模式的立体建构,但在余先生看来,若问题只解决到这一步,只能说揭示了唐代文学全面繁荣的内因,而这种立体演进,本质上又是唐代文学全面繁荣的基本表征。假如进一步追问,何以唐代文学能呈现出如此表征?则不能不对作为客体的社会文化土壤,与作为主体的诗人生活与创作心态作出探讨。余先生经过深入研究,在上述两个方面都进行了科学回答。
在《唐诗风貌》一书中,余先生首列两章篇幅,从唐代南北统一、民族融合与时代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三个方面,宏观概括了一代诗歌所共有的“丰神情韵”,而到了其后分阶段唐诗不同时期的艺术风貌迁变时,也时时不忘寻找迁变背后的社会文化土壤。譬如尽管有陈子昂等人高倡风骨兴寄,并且沈宋与四杰也已进行积极的创作实践,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初唐诗歌仍未走出“百年徘徊”(袁行霈语)的困境,若仅从文学内部寻找成因,显然难以回答。余先生则极富眼光地提出:“风骨离不开性情”,他认为初唐诗与盛唐诗之所以相隔不是一层天地,根本上是因为诗人的性情没有得到充分释放。而这种性情,又需要时代大潮的鼓荡。他进而分析了伴随着盛唐的各种社会条件对性情的催发,包括诗人身份地位的变化、思想的解放、精神的昂扬等多个方面。在余先生看来,正是这多重因素叠加,才使得诗歌终于在开元十五年前后,迎来了盛唐的大潮汹涌。
唐诗之走向盛唐高峰,离不开时代社会的有利条件,唐诗之由盛唐而中唐,继而晚唐,也与国家命运、社会氛围的起落变迁息息相关。中唐是一个诗歌大变的时代,涌现出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李贺等多位各具一种面貌却都较为发露直致的重要诗人,特别是韩诗的奇险、白诗的平易,大大不同于盛唐雄壮浑厚、和谐蕴藉的诗歌风貌。这是昌黎等人开辟宇宙的重要贡献。不过这个贡献,本质上也是对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几度谋求中兴而不可得,社会总体氛围渐趋躁动的折射。同样,晚唐社会矛盾多发,特别是朋党之争、藩镇割据与阉寺之祸这三大顽疾,更是造成社会精神状态陷入低迷,进而造成晚唐诗歌走向“沉沦”(袁行霈语)的根源,特别是李商隐诗歌“凄艳浑融”主体艺术风格的社会根源。余先生在辨析中晚唐诗歌风貌时,充分注意并要言不烦地讲清楚时代条件的变化,使他对于诗歌迁变轨迹的准确把握有了根本保证。
研究不同阶段诗歌风貌,需要考察时代条件的变化,而考察某一作家诗歌创作的前后差异,同样不能忽视外部环境的影响。譬如李白的入京与被放逐、韩愈的南贬潮州、白居易的谪居江州、李商隐与令狐綯关系的破裂,是考察几位诗人心境与创作的重要抓手。对于这些,前人时贤均已不同程度作了揭示。余先生在对相关诗人进行研究之时,也十分注意具体人事背景的变动。这方面最为明显的例证,是他对杜甫后期诗歌的探讨。众所周知,以《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三吏”“三别”等为代表的杜甫现实主义诗歌创作,是以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国势的剧烈变动为背景的,但杜甫晚年颠沛陇蜀、流离江湘,至死未归京洛,与中央政治已经相距遥远,也正是这段时间,诗人又有《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等力作,原因何在?如果不深究肃代两朝的政局与时势,恐怕难明就里。在《政治对李杜诗歌创作的正面推动作用——兼论中国诗歌高潮期的时代政治特征》一文中,作者详细分析了肃代之际唐王朝形势的新变化,指出皇位的更替,特别是此前受打击的琯党成员的再获启用,“使杜甫备受鼓舞,改变了蛰居成都草堂,避官且又避世的生活态度”,〔19〕开始重新对政治积极关注,进而迎来其个人诗歌创作的第二次辉煌。特别是为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攻陷长安一事,“从闻讯到忧念、焦虑和事后总结回顾,构成达二十首以上的一个长系列,忧西川的诗,亦达十首之多。”〔20〕十分引人注目。再到后来,余先生在讨论杜甫有关吐蕃诗歌创作时,又进一步指出,杜诗现实主义风格的维系和强化,杜诗西行以后创作所表现出的苍茫雄浑的境界与沉重的悲凉感,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唐蕃交恶的现实基础及其对时代氛围的敏锐感受。〔21〕这些看法,对于我们深刻认识杜诗发展与时代政治之关系,显然有很大帮助。
诗歌的纵向迁变与时代发展的相依相存,尚属易见易察。其实纵然是横向的文体互动,同样也需要合适的文化土壤滋养。譬如诗赋合流主要发生在初盛唐,韩愈的“以文为诗”,突出地表现在中唐,传奇受诗赋影响,在中唐后期与晚唐前期迎来兴盛,而词体的初步成熟则要迟至晚唐五代。之所以呈现出这种阶段性特征,与时代社会环境有着重要关联。在《唐诗与其他文体之关系》一书中,余先生对这种关联进行了细密揭示,如解释中唐诗歌与传奇小说之间何以能相互影响,突出提到中唐尚文、尚奇的时代文化风尚。对于某一具体诗人之吸收其他文体经验,余先生也注意从文化土壤或具体时代背景中寻找中介。譬如李白《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名篇,其汪洋恣肆的艺术风貌,有明显的辞赋身影。余先生联系李白出生于蜀地,而司马相如、杨雄、王褒等汉赋经典作家也是蜀人,认为共同的地域文化传统使得李白诗与汉大赋更易发生联系;〔22〕而李白诗歌偏于“清净明丽”的基调则与其长期往来皖南,近距离体验皖南秀美山水、接受南朝乐府与江南民歌影响,关系甚密。〔23〕李商隐诗歌“好对切事”,得益于他长期的骈体文写作训练,而若进一步追问,何以他能获得这种长期训练,则不能不提及他少从令狐楚学习四六文,而后大半生辗转多地幕府,需要代幕主起草大量今体章奏的特殊人生经历。在《樊南文与玉溪诗》一文中,余先生特别提醒李商隐的这一经历,从而解释了樊南四六何以能与玉溪诗风“消息相通”的原因。
五、“因看重故有借重”:探寻唐诗演进的心理基础
文学,终究是作家精神情感与艺术创造的产物。纵然是身处相似的时空环境,面对大致相同的创作素材,不同作家基于各自处境心境,所创作出的作品往往会大异其趣。同样,唐代诗歌历三百年而不断向前推进,并能在与其他文体的互动中长久保持艺术生命力,既依赖于时代文化土壤,也离不开作家本人的强大主观能动性发挥作用。余先生在讨论李贺诗歌创作吸收汉代辞赋艺术经验时,首先揭示了李贺诗的一个突出现象:
李贺诗中有一个突出现象,凡具有用以自比意味的古人,绝大多数都是赋家或诗赋兼擅的文人。有宋玉、司马相如、杨雄、赵壹、张仲蔚、边让、曹植等。其中,西汉大赋家司马相如被提到的次数尤多,共六见。〔24〕
他进一步指出:
因看重故有借重。尽管李贺所用文体为诗体,但赋源自诗骚,诗与赋关系极近,彼此相互参用吸收,实为普遍而经常的现象。唐代又处在诗赋彼此消长、积极开展交融互动的关节点上,……特别是在文与质、辞与理的关系上,赋偏重在文与辞。《三都赋》称赋“文必极美”、“辞必尽丽”,道出了赋体“唯美”的特征。而李贺,则如钱锺书所云:“长吉穿凿入仄,惨淡经营,都在修辞设色”(《谈艺录》七《李长吉诗》),故而对于李贺这样的诗人,醉心于“极美”、“尽丽”的赋,以赋为借鉴取资的对象,便是很自然的事。〔25〕
余先生在这里提出的“因看重故有借重”的命题,实在是解释文学史中许多现象的依据。以李白为例,李白诗歌的壮美气象,与汉大赋极似,这与他幼时诵司马相如《子虚赋》,“私心慕之”(《秋于敬亭送从侄耑游庐山序》)的经历与感受有密切关联,李白又说:“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可见他对这位蜀地文学先贤怀有何等的敬仰之情,如果不了解这样的学习经历与心理原因,恐怕就很难对李白诗学汉大赋有深入认识。同样,李白发出“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的高呼,足见他对建安文学与谢朓诗歌的推崇,而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也自觉以前贤为鉴,表现出相近的艺术风貌。
不同文体间发生相互作用,离不开作家主体心理的支配,而诗歌内部的前后迁变,同样需要通过作家的主动选择才能实现。李商隐《韩碑》诗追咏韩愈《平淮西碑》文,特别强调“文成破体”,这其中就包含着与韩愈相同的“追怀元和时期君相协谋,扫平叛乱,中兴唐室”功勋的政治共识,正因为有这样一种共识在,尽管“韩诗雄直奇险,表现为阳刚之美,李诗瑰艳朦胧,表现为阴柔之美”,〔26〕但李商隐的《安平公诗》《偶成转韵赠七十二句赠四同舍》《李肱所遗画松》等诗却明显是在追摹韩诗。在余先生看来,设若没有这种心灵共鸣,那么面对义山“斩蛟破璧不无意,平生自许非匆匆”“沥胆祝愿天有眼,君子之泽方滂沱”“樛枝势夭矫,胡欲蟠拏空。又如惊螭走,默与奔云逢”等豪纵奇险,置诸韩集几可乱真的诗句时,难免感到突兀。
作家主体心理在促进诗歌创作,推动文学发展中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在中国文学史那些经典作家身上,有最为鲜明的体现。李白诗歌的豪放、杜甫诗歌的沉郁,与诗人个性气质很有关系。余先生在研究中,特别是当他的研究对象集中在阮籍、李白、韩愈、李贺、李商隐等偏主观化的诗人时,尤为重视个性气质的探究。《变奏与心源——韩愈大变唐诗的若干剖析》一文,作者除了强调时代给韩愈思想心理带来的冲击外,也提到韩愈性格中的“躁劲”“功利”“偏激好斗”,甚至“木强而又善谑”。可以说,假如没有这种个性气质作支撑,韩愈无法主导“以文为诗”的诗歌变革,当不起“大变唐诗”的历史重任。他又多次引用王世贞的判断:“李长吉师心”。认为着意于表现内在的“迷魂”“心曲”,是李贺天生的性格特质与自觉的艺术追求,这些看法,抓住创作者内在精神因素予以深入挖掘,对于考察外在诗歌风貌,无疑是追本溯源之举。
余先生长期研究义山诗,李商隐的诗歌不仅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晚唐时代内容,而且表现了深渺幽微的心灵世界,特别是《无题》等近体律绝所创造的朦胧多义又凄艳浑融的境界,很大程度上确定了其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那么造成李商隐诗歌特色与成就的个体原因在哪?余恕诚先生曾有过一段概括:
党人的成见,加以李商隐个性孤介,他一直沉沦下僚,……时世、家世、身世,从各方面促成了李商隐易于感伤的、内向型的性格与心态。他所秉赋的才情,他的悲剧性和内向型的性格,使他灵心善感,而且感情异常丰富细腻。国事家事、春去秋来、人情物态,以及与朋友、与异性的交往,均能引发他丰富的感情活动。“庾信生多感,杨朱死有情”(《送千牛李将军》),“多感”“有情”,及其所带有的悲剧色彩,在他的创作中表现得十分突出。〔27〕
既强调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也注意到个性气质所决定着的观照世界的基本方式,可以说,正是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相互影响,才最终形成李商隐特有的主体艺术风格。
六、结 语
余恕诚先生1961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至2014年逝世,一直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科研工作,五十三年如一日,焚膏继晷,孜孜以求,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光,仍然在执着思考他为之付出一生的唐诗研究。他的唐诗研究贡献是多方面的。无论是唐诗基础文献整理,还是唐诗演进体系建构,无论是唐诗文化背景探讨,还是唐诗艺术本体分析,都进行了辛勤探索,获得了重要成就。到了晚年,他又将相当精力转到对20世纪唐诗研究的回顾总结上来。在他看来,20世纪的唐诗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但仍有许多可供开拓的领地。关于唐诗研究的未来,他希望要更重视艺术,更重视文本,要将优秀作品的审美意蕴与人文内涵充分发掘出来,要真正使唐诗研究在弘扬传统文化、提升中华民族精神品质上做出应有的贡献。有理由相信,在21世纪的中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愈来愈近于实现的伟大时代里,包括唐诗研究在内的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余先生,以及一切有志于传承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前贤们的深切期待,一定会在新世纪得到更加有力的回应。而他们所进行的开创性研究,以及体现在研究中的情怀与精神,也必将会被后来人永远铭记。
注释:
〔1〕《唐诗风貌》1997年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2010年由中华书局出增订版,此外,1999年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繁体字版,改名为《唐诗风貌及其文化底蕴》;《唐诗与其他文体之关系》201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系与吴怀东教授联合署名;《“诗家三李”论集》2014年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2〕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前言第3页。
〔3〕余恕诚:《唐诗讲演录》(未刊稿)。
〔4〕如明人高棅在《唐诗品汇总序》中即说:“今试以数十百篇之诗,隐其姓名,以示学者,须要识得何者为初唐,何者为盛唐,何者为中唐,为晚唐。”
〔5〕〔6〕〔8〕〔11〕〔15〕〔19〕〔20〕〔23〕〔24〕〔25〕〔27〕《“诗家三李”论集》,中华书局,2014年,第200-201、159-170、147、248、268-269、55、57、38-43、115、117、186页。
〔7〕余恕诚:《从“阮旨遥深”到“玉溪要眇 ”——中国古代象征性多义性诗歌之从主理到主情》,《文学遗产》2002年第1期。
〔9〕〔10〕〔14〕〔16〕〔17〕余恕诚、吴怀东:《唐诗与其他文体之关系》,中华书局,2012年,第1、1、15-16、19、353页。
〔12〕余恕诚:《李贺诗歌的赋体渊源》,《文学遗产》2014年第1期,收入《“诗家三李”论集》。
〔13〕余恕诚:《中晚唐诗歌流派与晚唐五代词风》,《文学评论》2009年第3期。
〔18〕余恕诚:《唐诗风貌》,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序言第2页。
〔21〕王树森、余恕诚:《唐蕃关系视野下的杜甫诗歌》,《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第5期。
〔22〕余恕诚:《李白与长江》,《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
〔26〕余恕诚:《唐诗风貌》,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