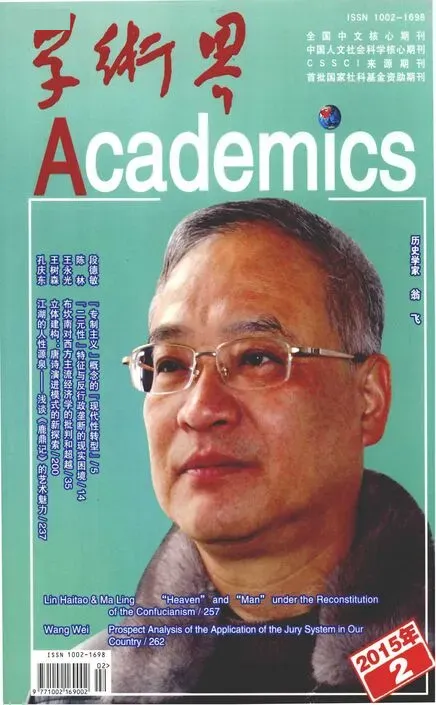马来西亚华文女性小说的创作特征
○ 刘 征
(1.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2.宁夏医科大学,宁夏 银川 750004)
马来西亚华文文学〔2〕(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是世界华文文学(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其女性小说的书写更能体现出华人女性在马来西亚生存、奋斗、扎根的各种人生境况与生命体验。近三十年来,从事马来西亚华文女性小说(Malaysian Chinese Female Novels)创作的女作家们用自己对汉语文学的热爱、对汉语写作的坚持、对异域生活的感悟、对中华文化的固守,以及马来西亚独有的地域色彩、审美特征,为全世界不同层面的学者、读者展示了一幅充满南洋风情与中华特色的海外图景,并为马华文学的总体构建、世界文化的多元并流和文学创作的多重声音提供了丰富、鲜活的文字实证,使我们可以看到愈趋繁荣的世界华文文学更为鲜明的区域特色和更加深刻的本质特征。她们的笔下,从早期反映侨民奋斗史的现实主义文学,到后来较为复杂的生存书写,到当下马华文学“新生代”〔3〕女作家的勇敢尝试,广泛涉猎婚恋、职场、教育、经商、身体写作等各个领域,巧妙地演绎了中外文化的混杂局面给华人族群带来的精神感受,塑造了一大批具有多重文化经验和独特精神品质的女性人物形象,从而丰富了马华文学的文字表达。她们在艺术实践上的努力尝试,使得处于世界华文文学边缘位置的马华女性写作,在保持中华民族文化部分特征的同时,也在异域文化中展示了自己的独特风貌,并逐步开始赢得大陆学界的肯定,逐渐成长出一朵悄悄盛放的南洋之花。
总体看来,马华女性小说的创作呈现出以下三方面特征。
一、马华女性小说主题的演变表现出女作家创作心态由“落叶归根”向“落地生根”的转变
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马华女性小说中的各类传统文学主题就呈现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演绎及传播,这其中有对故乡的思念,有对传统婚恋观的秉承。例如这一阶段“乡愁”主题的小说中,作家心中秉承的还是对故乡的牵挂、对中华文化的坚守。商晚筠的短篇小说《林容伯来晚餐》《南隆·老树·一辈子的事》这些作品均隐喻了对中国大陆的思念、保持着对中华民族血液的继承和对故国家园难离的情愫。《林容伯来晚餐》这篇小说运用儿童视角去审视林容伯这一人物形象,对其性格与文化心理进行了生动的塑造,并将以往熟悉的乡土生活以及华人群体中习以为常的生活场景以一种全新而合理的方式表现在故事中。在小说中,作者细腻而生动地描绘林容伯来家里做客的情景,通过对林容伯这一人物形象的描绘,反映了当时老一辈马来西亚华人的传统价值观与华人社会的生活景象。林容伯等老一辈华人对汉语方言的重视与坚决的捍卫这一细节可以集中表现出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眷恋与深情。“木树,我来了大半天都没听见汝查某囡仔郎讲潮州话,潮州仔满嘴讲的都是福建话,福建仔似的,莫不是笑死人。”〔4〕可以看出林容伯这样的早期移民对母语根深蒂固的不舍情结,他认为能够掌握母语,是一种值得骄傲的事情,相反则是会被人嘲笑的。作家用“方言”这种特殊的方式纪念着自己的故乡,寄托了自己的思乡之情。
然而,马华女作家们不能一味地描写乡愁,也不能一味地表现中国文学的传统主题,为了开垦新的表现领域,她们必须从根本上脱离对故土的怀念,转而将心态调整到更适合在马华文学占有一席之地的状态,从而将自己的写作推向更为广阔的空间。因而,马华女性小说经历了作家创作心态的调整与重新定位,其主要发展脉络为:从落叶归根心结的反复吟唱,到离散心态的悲情书写,到决心落地生根的全情表达,这样一个复杂而又渐行渐明朗的过程。
1957年马来西亚正式建国后,政治制度的变革致使大部分华侨选择了马来西亚国籍。既然永远无法再回到中国大陆,那么转变心态,将马来西亚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便成为最最务实的想法与态度。柏一的《水仙花之约》是一篇能够充分体现华人在马来西亚“落地生根”后以马来西亚当作家园的短篇小说。女主人公何嘉怡留学台湾,学成回国时,已经是三十岁的大姑娘了,她的男朋友坚持移民澳洲。何嘉怡想起从幼年起父母对自己的点滴照顾、想起自己成长的土地,几番挣扎后毅然放弃婚姻。何嘉怡对男友说:“我一向不赞成移民。劳工要走,优秀生要走,大富豪要走,专业人士也要走!谁留下发展国家?”〔5〕这里的“国家”并非神州大地,而是南洋沃土。这样的表白,让读者清晰地看到,小说中的主人公已把马来西亚当作自己的故乡。马华女作家的创作心态由前辈作家的“落叶归根”逐渐转换为“落地生根”,在这里可见一斑。
当作家的创作心态调整以后,马华女性小说涌现出大量描写马来西亚本土特色的作品来。曾沛的微型小说集《行车岁月》、李忆莙的短篇小说《风华正茂花亭亭》、融融的长篇小说《青山依旧在》都成为由落叶归根转向落地生根的马来西亚本土书写的代表作。李忆莙的《风华正茂花亭亭》是一篇涉及华族和印度族通婚的短篇小说。华人小伙周承安的成绩不够优秀,没能考上马来亚大学也没能出国留学,仅在税务局混得一个小职位。而女友印度族姑娘玛妮不仅学业优秀,更出身于北印度贵族世家,家里拥有大量财富。周承安一直生活在经济的重压下,出于中国传统男子的自尊,他拒绝接受玛妮家庭的帮助。然而即便有来自各方的压力,感情还是战胜了种族矛盾,最终他们结合了。玛妮这朵胡姬花〔6〕不再憔悴、萧条,而是在华人眼中绽放出自己美丽的容颜。小说中,周承安和父亲之间的矛盾能够集中体现出华人对异族的认识与评价以及“新老”两代华人在异族通婚问题上所持有的不同立场,这一问题在马来西亚这一多元种族的国家屡见不鲜。
饶芃子说:“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造‘他者’形象,创造出他所理解(心目中)的‘他者’形象,这是两种文化相遇‘对话’而产生的,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诠释,虽然当中不可避免会有‘误会’和‘误解’。”〔7〕所以,华人与异族在婚姻问题上的巨大分歧是民族大融合的一段必经历程,而这种分歧只有全人类共同的释怀与包容才能获得真正落地生根、开枝散叶。李忆莙也通过对异族女子的全新书写完成了马华女性小说的本土化尝试,并为读者呈现了完美的异族形象。
二、女性意识的觉醒体现出作家对第三世界女性生存境遇的关注
女性的生存境况与社会地位始终是全人类探讨的一个共同话题,在东西方各国、在不同人种、族群中,女性始终处于“他者”地位。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华女作家逐渐意识到女性地位的不平等,主动承担起为第三世界女性代言的责任,于是出现了大批“言说女性”的作品。唐珉的《津渡无涯》;李忆莙的《死世界》《怨女》;柏一的《荒唐不是梦》;商晚筠的《七色花水》《痴女阿莲》《未亡人》;以及煜煜的《方曼玉》《错爱》,这些作品共同深刻表现了夫权桎梏下没有尊严、没有地位的女性的凄惨生活。故事中的这些女性把寻求幸福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异性,一旦所投靠的男人无法依靠或逃避责任,她们的一切理想和幸福都化为泡影。黎紫书《某个平常的四月天》《蛆魇》《疾》等作品,塑造了一系列丑父形象。对丑父形象的塑造,体现了生命中父爱的缺席;是对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解构;是女性寻求平等自由的渴望和呼声。纵观这一阶段的马华女性小说,作家开始“言说女性”,借助文字语言来讲述关于女性的故事。
受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马华女性小说中出现了“娜拉出走”和“躯体解放”这两类女性形象。面对来自南洋的父权压迫,马华女作家笔下的“娜拉”同样充满了“出走”的欲望与决心。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构成了马来西亚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她们存在于世界之中,并逐渐开始尝试寻找抵抗父权的途径。她们笔下的人物都具有一种不服软、不认输的顽强性格。代表作有:艾斯的《万水千山》;商晚筠的《疲倦的马》《季妩》;柏一的《烟烧一颗心》;李忆莙的《女人》,这些小说旨在揭示,女性必须由家庭空间走向社会空间,必须实现经济上的独立才能完成由家庭人向社会人的转变。“躯体解放”指的是首先挣脱“被视”的困境,其次“解放”自己的身体。在父权、夫权主导的社会中,女性的身体永远需要透过男性的审视和判断来被物化为男性性欲的对象。女性在被审视的过程中,失去了自我,总是以男性的审视作为自我审视的评价标准,这代表着女性永远只能作为客体的性对象而存在,所以女性一定要率先摆脱“被视”的困境。此方面的代表作有:商晚筠的《未完待续》《卷帘》和柏一的《糖水酸柑汁》。这些作品旨在证明,通常意义上的写作对于想要改变女性的命运而言是无济于事的,如果想要彻底摧毁菲勒斯中心语言体系,女性就必须通过她们的躯体来写作。女性之所以无法发声,是因为身体被长期压制着。历史和文化对女性的钳制以及对女性身体和欲望的钳制过于严苛,女性想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就要从审视女性自身的主体经验开始。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马华女性小说中,我们不难看到那些非常态情爱的书写,它们是对女性存在的反思与反省,也是对女性存在的反抗与放逐。这其中表现忘年恋的如商晚筠的《人间·烟火》和黎紫书的《流年》;表现婚外情的如商晚筠的《卷帘》和黎紫书的《此时此刻》;以及表现同性恋的如商晚筠的《街角》《跳蚤》和扶风的《霓裳曲》。这些作品揭示出:无论选择忘年恋、婚外恋亦或是同性恋,在某种意义上她们都是缺爱的人,她们离经叛道的行为注定要遭到“家”的放逐而成为“家”的弃儿。然而她们依然最渴望家庭的群体,被“家”放逐让她们倍感家的温暖,懂得家的可贵。所以这些勇于追求“解放”的女性形象更应该获得社会、家庭以及异性的包容和关爱。
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华女作家的女性意识被激发,女性主动承担起为女性代言的责任,形成了女性言说的主体,完成了“言说女性”的第一步跨越,这标志着马来西亚的华人女性结束了自身的历史性沉默。伴随时代的发展、思想的进步,马华女作家们又进一步主动选择“用自己的语言方式来言说”,从而完成了“女性言说”的重大突破。从“言说女性”到“女性言说”的主体意识过渡,是马华女性小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创作实践上完成的最大突破与挑战,它丰富了马华女性小说的主题内涵,也为马华文学增添了一抹靓丽的颜色。
三、新世纪以来马华女性小说表现方式的革新展示出作家艺术水准的提升
进入新世纪以来,马华女作家蜕变了作品中刻意体现“中国性”的元素、抛弃了对传统华人生活的描绘,在作品中融入了更多全新的手法与实践,呈现出新的作品风格。她们在创作中渴求与世界对话,努力在作品中呈现出打破马华现实主义传统的格局,追求属于自己的独特个性;她们以自我突破式的创作手法为马华文坛提供了一种多元发展、多元表现的创造力,她们以个性化、多元化的创作实践,彻底颠覆了马华作家惯有的文学传统。新世纪以来马华文学“新生代”女作家们的作品,无论是改写本土故事题材、马共历史题材还是女性主体性突破的题材,都能反映出她们对人生作出的理性判断与独特的哲学思考,以及对人的尊严、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重估与肯定。
黄万华曾对马华文学“新生代”作家有过这样的评价,“在21世纪的最初一二十年中,他们的创作将会引起海外华文文学格局的一些深层次调整。这种调整自然联系着他们各自跟居住国各族群的关系,各自在居住国主流社会所处的地位、社会参与方式等”。〔8〕他又说,“其艺术水准、历史深度不逊于同时代的中国大陆、台湾、港澳作家。其影响超越了中国本土,甚至引起了海外华文文学格局的一些深层次调整。”〔9〕这两段话充分肯定了马华文学“新生代”作家的创作能力、艺术水准和破旧立新的勇气与实践。马华文学“新生代”女作家们的魔幻现实与死亡叙事是最能代表她们集体创作水平的一种艺术尝试,而这其中的代表当属黎紫书、贺淑芳、梁靖芬三人。她们的笔下,不乏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现实生活的变形、夸张、重塑式的魔幻书写,《蛆魇》《浮荒》《别再提起》《五行颠簸》《母墟》,都是突破现实、另觅他径的成功之作。这几部作品通过离奇的现实世界旨在揭示一个核心问题:马来西亚在地华人究竟应该如何定位自己的身份。同时,“新生代”女作家小说中那些具有“南洋特征”的“文学意象”不仅具备鲜明的马来西亚地域特色,同时还具备文学性。雨水、森林、草药、鹦鹉这些意象的选取均来自于马来西亚特有的气候或物种,均能体现南洋色彩,它们不仅蕴含了丰富的小说内涵同时还蕴含了丰富的社会文化知识,它们共同丰富了马华文学“新生代”女作家的魔幻世界的书写。张依苹的《哭泣的雨林》;黎紫书的《国北边陲》《推开阁楼之窗》均为典型代表作。此外,马华文学“新生代”女作家们不仅写到死亡,同时也思考着如何死亡以及与死亡形成二元对立的人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新生代”女作家的死亡叙事所具有的审美价值正是在于它反映了生存和死亡共时共存的对立意义,作家表现了生死对立的在场性,并赋予其巨大的审美价值。在《疾》《死人沼国》这些作品中,作者勇敢地描写生死,意在表达其实生死距离并不遥远但又很遥远的悖论,只有在拥有生命时给予生命更多的关爱才是对逝者最大的尊重。
纵观马华文学“新生代”女作家新世纪以来的小说文本,可以发现,隐匿作家的性别、消失的中华元素、跳跃的时空、颠倒的时序、反复交错出现的叙述者,成为她们全新启动的叙事方式,她们突破了马华文学的传统创作手法,革新了马华文学的话语方式,开辟了题材选择的新路径,真正做到了标新立异,为奠定马华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中的重要地位贡献了巨大力量。
四、结 语
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大放异彩的今天,在华文作家作品辈出的今天,我们能够深切感受到汉语作为全球华人的共同母语的重要与伟大,同时也为汉语写作的成功而感到自豪。身处马来西亚的华文女作家们不甘示弱,静静守候在富饶的南洋沃土,静静蓄积能量、汲取营养、持之以恒地坚持着华文写作。如今她们以不俗的成绩在马华文坛上开出自己异常美丽的花朵,并逐渐引起大陆学者的普遍关注。但不得不说,马华女性小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那就是:微型小说数量过多,却无经典作品,作家几乎同时面临“书写策略重复单一”的明显缺陷。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有关婚恋故事的叙事。很多作家都以婚外情构成传统婚姻故事的主线,然后融入自己对情感、文化和观念的理解,以一种单一的思维模式,传达作家主体对客体文化的个人考量。总览马华女作家的微型小说,集中于对“中年男女的婚外情”、“底层市民的辛苦奋斗”、“老辈华人与第二三代华人的生活观价值观的迥异”、“父母对孩子的教育”等几大主题的叙事,缺乏对人性、人生的更深层的洞悉、拿捏与理解。但无论怎样,近三十年来马华女性小说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值得关注、值得肯定的。这朵南洋之花,会渐渐将自己的芬芳播撒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会将汉语写作的美丽传递到世界各地。
注释:
〔1〕马来西亚华文女性小说,以下简称“马华女性小说”。
〔2〕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简称“马华文学”;马来西亚华文小说简称“马华小说”。
〔3〕马华文学“新生代”作家群是指出生于20世纪60、70年代,90年代初登上马华文坛的青年作家群,包括黄锦树、陈大为、钟怡雯、黎紫书、林幸谦、林春美、辛金顺、潘碧华、贺淑芳、梁靖芬等人。马华文学新生代的崛起成为20世纪90年代马华文坛的最大事件,也为马华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本文所要分析探讨的是马华文学“新生代”女性作家的作品。
〔4〕〔马〕商晚筠:《痴女阿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第90页。
〔5〕〔马〕柏一:《水仙花之约》选自小说集《荒唐不是梦》,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04页。
〔6〕胡姬花:胡姬花是东南亚国度的热带丛林中所生长的一种常见的花,极具地域色彩。胡,本是历史汉人对中国境内的北方少数民族的称呼,后来泛指少数民族或者与汉族相对的其他族群,“胡”泛化,与“番”一样成为异族的标志性称谓,如波斯等,胡姬,也就成了异族女子的代名词。女人如花,因此本文此处用胡姬花这种植物来指称马来西亚境内与华人女子相对的异族女子。
〔7〕饶芃子:面向21世纪的华文文学——在“第十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暨第二届海内外潮人作家作品国际研讨会”上的学术引言,《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71页。
〔8〕黄万华:《在旅行中拒绝旅行》,《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3期。
〔9〕黄万华:《新世纪10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及其趋向》,《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