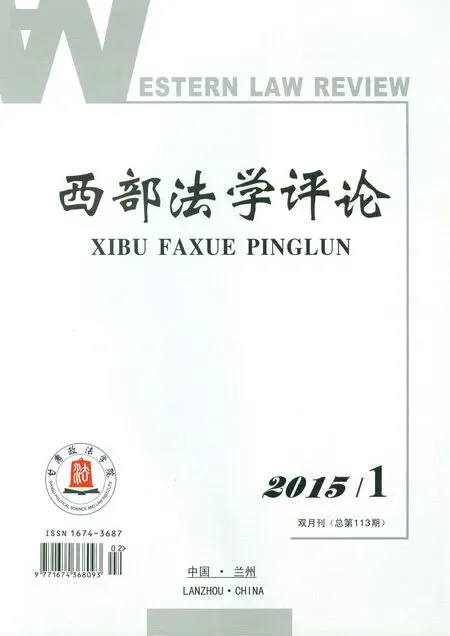法家法治类型的理论诠释——兼及当代中国法治的法家元素
武建敏
法治是一种让无数中国人魂牵梦绕的文化形态,但对多数人而言法治总有一个西方的标准。〔1〕任何法治都具有理想性,即便是在西方法治依然是一个不断追寻的历史过程。Richard H.Fallon,Jr.,The Rule of Law as A Concept in Constitutional Discourse,97Colum.L.Rev.1.这一标准主要在近代西方的启蒙时代开其端,其间由于现实实践活动的催动,西方人创造了一系列被称之为现代性价值的重要范畴,正是这些现代性价值构成了西方法治的思想基石。然而,那毕竟是异域的文化价值,百年中国的法治追求却始终无法在根本上将那些现代性价值转化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当我们深入到传统之中发掘思想资源的时候,自然就会明了中国现代性法治探寻之艰难。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它们已经深刻地融入传统的流动之中,构成了从历史到今日依然控制着我们的思想文化资源。对当代中国法治问题的探讨必须深入到传统当中,去挖掘那颇具智慧但有时却让人感到尴尬的思想资源法家的法治类型无疑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一种传统之流。
一、法治类型的多元化:一种中国的立场
在现代中国对于法治问题的研究中,人们已经习惯了西方的法治理论范式,认为只有西方近代启蒙思想所开创的法治理论及其法治实践,才真正具有法治的价值,而将除此之外的所有的法律实践活动都看作非法治状态。〔2〕我在这里所坚持的是一种法治类型学的理论,这是一种法治多元化的思维方式,其理论内涵展示的是宽容的态度和立场。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是用一种理论范式否定其他理论范式的学术霸权主义。若依据这样的法治主张,就会产生一系列实践上的问题,给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造成无数的 “遮蔽”,难以生成宽容的学术态度,自然也无法获得理论上的创造。
认为古代社会没有法治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是一种流俗,而不是一种真理。真理虽然也具有主观性,但真理既不可能是单纯的主观性,也不能是单纯的客观性,而是一种主客交融的合理性,在主观的信念中表达了客观的合理性。当人们只是站在今天的立场对待古代社会的法治问题的时候,那么其所体现出的主观性就是一种片面性,它不会将人们的主观世界打造为一个合理化的世界,而只能让人们在错误的认识指导之下做一些有损传统价值的分析。流俗作为一种在社会中传播的东西,一旦在人们的观念中转化为习惯,其危害性是很大的。将法治仅仅看作今天才有的现象,虽然未必妨碍人们对于古代社会的研究,但却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与采取别的视角对古代法律研究所可能呈现的面貌迥然有别的状态。
错误观念的产生有着很多复杂的原因,也是学术研究中经常会出现的一种现象。不知道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当代中国人在研究传统社会的时候,首先在自己的头脑中就先验地认为传统是一个过去存在的状态,从现代的立场上是要整体否定的。因为我们现代社会所搞的制度和文化的特质在传统社会里都是不存在的,就认为传统和现代之间有一个决然有别的鸿沟,这个沟壑其实并不是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沟壑,而是人们内心的沟壑。当这种沟壑成为人心中的固定思维结构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可怕的自以为是真理的信念。于是错误观念的产生就是一种必然。然而我们发现在西方人对于西方传统的研究中,他们总是回归到过去,回归到古希腊,无论是思想还是制度,西方人并不对古希腊做一种完全性质上的否定,而是去深入挖掘那些思想的现代价值。这应该是中国现代研究者必须学习的。
在法治问题上,不仅西方社会有法治,而且中国也有法治;不仅中国现代有法治,而且中国古代也有法治;不仅中国古代社会有法治,而且还有多元化的法治类型,理论形态上儒家与法家都有自己的法治类型理论,而在历史的流动中所生成的则是一种融合式的法治类型,其间法家的法治类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特定社会中所存在的法治都是法治的一种类型,而不是那个普遍性的法治,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普遍的法治类型,就像世界上并不存在一批抽象的马是一样的道理,因为任何马都必然要落实到白马、黑马抑或棕马。这里就涉及到普遍和特殊的关系问题,普遍是人类思想的一种抽象,但任何普遍在现实中都必须有一个载体。法治是人们抽象的一个概念,它本身是普遍的,但法治的普遍并不能替代法治的特殊,在人类历史上实际存在的只能是法治的特殊,而不是法治的普遍。中国古代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法治,这种法治对于传统社会而言是维系它的延续和发展的重要保障,如果传统社会不是一个法治社会的话,那么中国传统形态的历史就不会在人类历史上存在那么多年。
这种错误的观念在思维方式上是错误的,但是很有市场。既然这种观念有如此大的市场,那么我们在反思的过程中就难以避免要对这种观念的反思进行再反思,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其实这种错误的观念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表现为它认识到了今天的法治所应该具有的与古代法治不同的特征。如果认识不到这种差异,就很难在现代法治建设中促进法治的发展,将一系列符合现代性价值的法律转化为一种现实的行动,而这种行动的持续发展将造就伟大的现代性法治。我所担心的并不是这种法治论所认识到的现代法治的独特性,而是在对这种独特性进行把握的时候忽略了对于传统法治与西方法治的合理评价。这主要是个思维方式和观念的问题,如果这种观念被持续化和固定化就必然会给实践造成负面的影响。
作为一种反思,法治类型理论主要是要否定现代法治论者的片面性,而希图达到一种真正的具有历史和现实价值的思维理念。法治类型学的理论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理论和现实、历史与逻辑、抽象与具体、普遍与特殊、理性与感性相统一的理论状态,这种理论同时应该是一种最高的实践,以此为基础必然能够在现实的法治行动中真正地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而将中国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的理论形态就是法治类型理论。〔6〕当然法治所包含的诸多元素在这篇简短的文章中难以企及,它应该是整个的法治类型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诸多法治的重要元素在这里都是隐含的,但并未明确地进行探讨,比如作为法治所包含的规则、标准和原则的元素、法治的有效性元素、法治的稳定性元素、法治的权威性元素以及法治的公平正义之程序性元素,都是法治所隐含的重要元素。(Richard H.Fallon,Jr.,The Rule of Law as A Concept in Constitutional Discourse,97Colum.L.Rev.1.)当然这些都是形式性元素,也是本质性的元素;而实质性的元素则会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发生变化,本文所涉及的法治类型的变迁实际上主要是从法治的实质性元素角度而言的,当然实质性元素在根本上不是与形式性元素分割的。
二法家法治类型的特质
法家是战国时期兴起的一个思想流派,它的产生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有着内在的关联,同时也和国家治理的方略选择有着内在的呼应。任何思想都是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法家自然也是战国时代思想精神的表达。战国时代崇尚武功,各个诸侯国相互争斗企图实现华夏民族的统一,而希望达到统一的理想单纯地依靠德治主义的方略实难奏效,乱中取胜必当以法家为先,于是法治的思想理论便具有了历史实践的合理性。但是,在传统中国,法家的法治理论仅仅是法治的一种理想类型,在现实的历史实践中虽然也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对象化,但在思想理论上毕竟无法与儒家相抗衡。法家的法治理论包含着一种深刻的历史哲学思想,它以当时的战国时代为历史条件,认为战国时代不能依靠礼治和德治获得成功,〔7〕当然,法家也不是就那么绝对地反对伦理道德,比如,“韩非那么不容情地指证人性的实质以及人际关系的原则,并不是因为期望教化使人存辞让之心,也并非肯认自私之求的合理性,更不是欲以否定伦理的社会价值。事实上,韩非子与其前辈法家一样主张序定伦理,其对于礼的重视是相当明朗的。其定尊卑、贵贱、君臣、父子之伦,忠孝之德,大体同于儒家,只是弃其亲亲而已。韩非子亦并非不重道德,但他认为,世人所重之德在私德而非公德,以名德自况而否定正德。”陈少峰著:《中国伦理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4页。而必须依靠法治。如果在战国依然依靠先王的治理方略进行统治,那么就只能是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这是一种历史发展论的重要思想,也是从历史哲学为法治主张进行辩护的重要体现。〔8〕提到法治的概念,人们普遍地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没有法治的。这些人的思维完全被西方化的法治理念和现代性的法治观念所束缚,认为提到法治则必然只有现代社会方有法治,古代社会乃是专制社会,怎么可能有法治可言?这是对法治做了片面的理解之后所表现出的一个自然的特征,属于思维方式的问题。于是凡是这样认为的人都要炮制出两个概念,即法治和法制,并且认为在古代社会只有法制,而没有法治。这是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不可能真切地对待历史,也难以从历史中汲取合理的思想影响。法家作为古代中国的法治理论的主张者,有着丰厚的法治思想,且不可戴着现代人的有色镜片去考察古代社会的法治思想。武树臣先生曾经有一个质问:“法家的 ‘法治’原本如此,为何称不得 ‘法治’?”该质问发人深省。参见武树臣:《法家法治思想的再评判》,载 《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98年创刊号。
女娲庙所在山峰向南500米,有座山叫“偏头山”。据当地百姓讲,当时女娲在炼石之成后,奋力举石补天,第一脚踏力过猛,此山踏歪偏向山南一侧,故得名“偏头山”,相传山上曾留下女娲的脚印。
法家的法治包含了一些内在的特质,这些特质不仅在古代中国逐渐融入到了传统之流当中,而且对于现代中国的法治运行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法家法治的一些特点学术界已经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在这里我力图进行一些反思性的阐释,或许对于认真理解和诠释法家法治能有些许帮助。
(一)法家法治类型的特质之一:人性恶抑或功利主义
法家的法治主张与人性论内在相连。“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9〕参见 《管子·禁藏》。这里把人性看作趋利避害,统治者掌握了这个理念也就自然地可以加以利用使得臣民皆服从君王。无论是商鞅还是韩非大体上都体现了 “人性恶”的基本主张。商鞅尝言:“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逸,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论其然也?今夫盗贼上犯君之所禁,而下失臣民之礼,故名辱而身危;犹不上者,利也。其上世之世,衣不暖肤,食不满肠,苦其志意,劳其四肢,伤其五脏,而益裕广耳,非性之常也,而为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凑,则民道之。”〔10〕参见 《商君书·算地》。再看韩非对圣人的人性论评述:“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以为民先,股无,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士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11〕参见 《韩非子·五蠹》。
在很多法学学说中,都有着关于人性论与法治关系问题的研究。人们通常认为,“人性善”就是导向 “礼治”和 “德治”,而 “人性恶”就必然导向 “法治”,在这种认识中有一个前提设定,即道德是自律的,而法律是他律的,因为人性是善的,所以依靠道德就可以达到治理的状态,而如果人性是恶的,那就不能依靠自律性的道德,而必须依靠他律性的法律进行统治。大致这成为了一个基本的思维方式。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如果人性是恶的,那么依靠法律也是很难达到治理的。这大概是现代人的一种想当然的看法,未必具有真理性。兴盛于战国的法家其实并不是这么认为的,法家只是认为因为人性中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所以法律可以加以利用,在这个意义上人性论真正对应的是法家的惩罚理论。〔12〕这就是商鞅所说的 “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的道理,参见 《商君书·错法》。当人们用一种价值判断的思维模式去评价人性中的诸多事实的时候,总是喜欢为这些人性中的特质贴上一个标签,于是人性恶也就成为这其间最为重要的标签。这个标签很容易绝对化,并且总是无法获得中国人的认可,因为虽然法家击中了人性的要害,但在千百年的文化传承中我们并不愿意接受人性恶的判定。其实对人性进行善与恶的二元划分,本身就是一种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法家所揭示的的确是人性中的重要特质,但这种特质似乎将其称之为功利主义更为恰当,〔13〕法家的功利主义实际上也是一种道德,当然是以利益考量为前提的道德,匮乏了 “仁义”的结构内涵。关于法家之道德的功利主义色彩,可参见 [美]本杰明·史华兹著:《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程钢译,刘东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45页。这样免去了两极对立思维方式的学术困境和思想疑难,更能以平和的态度认真对待法家的思想。
对功利之计量乃是人性的事实,在这一点上法家要比儒家更为实际。在一般的意义上去理解儒家的理想要比法家的理想远大得多,但法家的许多思想主张在中国的社会中反而比儒家的更为理想。法家的功利主义考量是很实际的,但在这一点上恰恰背离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而儒家却是与这个结构相契合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法家的功利主义恰恰是一种更为理想的策略。在法家那里,“赏善罚恶”是基于功利主义的一种正义形态,然而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赏善罚恶”必然被等级化,于是 “赏善罚恶”也就失去了其原本的思想价值而成为一种理想的文化形态。其实儒家也是主张 “赏善罚恶”的,只是由于其 “情本体”的等差伦理以及等级化的伦理结构无法促进这一最基本的正义之实现。再加之以中国的社会结构浸染着儒家化的习性,并且已经深入人心与人们的行为方式之中,故此使得 “赏善罚恶”这种最基本的法治主张都不能顺畅的实现。无论是基于功利主义的 “赏善罚恶”还是基于原本的道德理念的 “赏善罚恶”,其基本的思想意向都是很明确的,然后一旦遭遇与其相冲突的传统,这种正义就显得比较脆弱。当然,倘若真地能够以法家的 “厉行法治”去推动社会方方面面的运行,则 “赏善罚恶”的实现也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儒家文化的支配下必然会给 “恶”容留一定的地盘。
(二)法家法治类型的特质之二:专制主义抑或权力主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到底是否存在专制主义的问题颇费思量,就中国古代社会之运行的主导方面讲,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绝对的专制主义的制度,因此所谓的 “封建专制”是一个值得商榷的概念,又或者仅仅是一个标签而已。而当我们从理论形态上对传统中国文化是否具有专制主义进行评判的时候,则可以说儒家并不主张专制,从根本上说儒家讲求的君权是相对的,并且君权是要受到限制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的 “德”实际上就是对君权的最大限制,如果我们将儒家的治理方略从主导方面概括为 “德治主义”的话,那么这个 “德治主义”就具有限制君权的功能,因此可以说儒家在理论上是不存在专制主义的思想主张的。至于对法家的判定,则显得有些困难,〔14〕倘若我们看看齐法家的一些主张就会发现,他们很强调君主对法律的遵守,正所谓 “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管子·法法》)而同时其所主张的谏议机构的设立或可看做是对君权的一种限制,“齐桓公问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为之有道乎?对曰:勿创勿作,时至而随。毋以私好恶害公正,察民所恶,以自为戒。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唉;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为之,其名云何?对曰:名曰啧室之议。曰:法简而易行,刑审而不犯,事约而易从,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过,谓之正士,内于啧室之议。有司执事者咸以厥事奉职,而不忘为。此啧室之事也,请以东郭牙为之。此人能以正事争于君前者也。桓公曰:善。”(《管子·桓公问》)可见,法家也有不同的声音。但从总体上看法家是主张君主的绝对权力论的,也就是说君主在实际上是终极的立法者和最终的裁判者。“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日法,二日信,三日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权制独断于君则威。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惟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故上多惠言而不克其赏,则下不用;数加严令而不致其刑,则民傲死。凡赏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约也。故明主任法。明主不蔽之谓明,不欺之谓察。故赏厚而信,刑重而必;不失疏远,不违亲近,故臣不蔽主,而下不欺上。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议,此国之所以乱也。先王县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释权衡而断轻重,废尺寸而意长短,虽察,商贾不用,为其不必也。故法者,国之权衡也。夫倍法度而任私议,皆不知类者也。不以法论知、能、贤、不肖者,惟尧;而世不尽为尧。是故先王知自议誉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者诛之。赏诛之法,不失其议,故民不争。不以爵禄便近亲,则劳臣不怨;不以刑罚隐疏远,则下亲上。”〔15〕参见 《商君书·修权》。无论是法、信,还是权,其所隐含的都是君主的权力的运用问题。
在法家的思想代表中,慎到是非常重视权势的,当然这权势就是君主的权势。“立天子者,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者;不使大夫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嬖妾疑焉;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则动,两则争,杂则相伤,害在有与,不在独也。故臣有两位者,国必乱;臣两位而国不乱者,君在也,恃君而不乱矣,失君必乱。子有两位者,家必乱,子两位而家不乱者,父在也。恃父而不乱矣,失父必乱。臣疑其君,无不危之国;孽疑其宗,无不危之家。”〔16〕参见 《慎子·德立》但慎到也认为君主并不是万能的,“治乱、存亡、荣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17〕参见 《慎子·知忠》并进而主张对君王也要进行一定的限制,正所谓 “非立天下以为天子”和 “非立国以为君”。〔18〕参见 《慎子·威德》商鞅在太子犯法之后,惩罚了太子的师傅,并未对太子进行惩罚。但似乎从这些都不能必然地得出法家所主张的乃是专制主义,需要明确的是专制主义充满着任意性,在一个专制主义的理论设计中不可能有法的显赫地位,而法家的思想代表无疑都非常重视法在治理事业中的卓越价值。
因此法家真正崇拜的实际上乃是一种权力主义,“君子操权一正以立术,立官贵爵以称之,论荣举功以任之,则是上下之称平。上下之称平,则臣得尽其力,而主得专其柄。”〔19〕参见 《商君书·算地》商鞅深切地体会到权力在 “厉行法治”中的重要作用,故此突出权力的重要价值自然就在情理之中。我们在这里需要认真检讨的是,不要对法家任意地做一个专制主义的判定,从而一棍子打倒,使其不得翻身。无论如何,法家的思想不仅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渊源之一,而且也构成了中华法系发展变迁的重要前提,在历史的流变过程中,法家的权力主义的主张不断获得强化,甚至被以各种形式加以歪曲,影响了人们对法家宝贵思想财富的深入挖掘。
(三)法家法治类型的特质之三:重刑主义的道德关怀
在治理国家的方略中,儒家主张的是德化主义的思想进路,力图通过教化使全民皆善,自然也就不会去触及法律了,国家的治理也就自在情理之中了。因此,儒家在总体上主张 “轻刑”,然而教化真的能够发挥 “去刑”的功能吗?在法家的思想家那里,教化是不可能做到避免犯罪的,因为犯罪的根源并不在于教化的匮乏,而在于人性中 “趋利避害”的本能,本能的东西即便可以通过教化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但也绝对不可能在根本上加以杜绝。于是,重刑主义就成为了法家的普遍主张。〔20〕其实在儒学的原初经典以及颇具后世儒者之风的西周指出的统治者那里,严厉的惩罚乃至武力并不是被抛弃的思想之维,只是到了孔子那个时代才收到了冷落。“很明显,周代早期统治者们毫不犹豫地用严厉的刑法制裁来支持其 ‘神圣的仪式’。如果统治者的德性体现于他们施行道德影响的能力中,那么也同样要体现在他们施行正义惩罚的能力中。不过,后来的儒家对于此类武力的态度却发生了急剧转变。我们发现,尽管诉诸武力和刑法只是法家的一个方面,但却是这样的一个方面:能够援引很古老的传统,坦率地接受武力在社会秩序中的作用;即使在经典文本中,也能窥见这一古老传统的踪迹。”同前引﹝13﹞,第440页。当然,我们需要对法家的重刑主义做另一种分析。
重刑则首在 “去奸”、“去刑”,“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 ;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故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21〕参见 《商君书·开塞》。法家的这一论述是很深刻的,真正的 “刑”必然蕴含着原初的正义,实际上 “以刑去刑”就是用正义的运行机制去克服刑罚自身所具有的 “恶”的特质,商鞅可谓深得辩证法之妙,乃正是一个深刻的判断。
重刑亦在 “扬善”,“治国刑多而赏少,乱国赏多而刑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夫过有厚薄,则刑有轻重;善有大小,则赏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 ,必乱。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一国行之,境内独治;二国行之,兵则少寝;天下行之 ,至德复立。此吾以效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22〕同前引﹝21﹞。这或许就是 “德生于刑”的道理所在。如果说 “以刑去刑”乃是辩证法的一个方面,则 “德生于刑”恰恰是辩证法之能动性的体现。一种惩罚可能包含了一种道德直观,在对恶人的惩治中道德直观表达得淋漓尽致。在最为严厉的惩罚当中恰恰蕴含了一种道德关怀,〔23〕西方的法律实证主义与法家的思想颇有类似,但西方实证主义多采取法律与道德相分离的立场和态度,但法家在总体上并不拒斥道德。其实即便像法家这样与实证主义法学最为类似的中国思想体系,也不像一般的实证主义那样否定法律与道德的关联性。其实无论从内在还是从外在的角度去分析,也无论是从形式性还是实质性去论证法与道德的关系,法与道德在根本上都是不可能分离的。(参见Leslie Green,Positivism and The Inseparability of Law and Morals,83N.Y.U.L.Rev.1035.)而美国法哲学大师德沃金作为自然法哲学家也是一位反对法律实证主义的坚定思想家。(关于德沃金反对法律实证主义的叙述,可参见Frederick Schauer:The limited domain of the Law,90Va.L.Rev.1909)而实际上在中国以儒学为传统主导的语境中,按道理说应该是没有 “法家”或法律实证主义的市场,但在实际上两者却很有市场。这或许是一个悖论,一种历史的存在并不是理论设计的自然结果,其间的形成规律应该说是非常复杂的。道德不是停留于口头的说教,更不是人情化的妥协,在法律世界中它必然与正义相连,只有在正义中才能哺育道德的情操。
当代中国的法治追求愈益温情化,仿佛契合了世界轻刑化之潮流,然而中国社会的法治发展必须以中国自身的传统为基础,在异域文化中并不存在的规律,则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切不可忽视,更何况异域文化中法律之重也并非不得而见。法家之重刑,且其 “以刑去刑”和“以刑养善”都是十分宝贵的文化传统,其所富含的辩证智慧,正是我们今日法治建设所应当吸收的重要资源。
三、法家法治类型之评述
关于法家法治类型的评述,不能绕开中国现代哲学家贺麟的评判,他的评述至今依然让人收获良多。贺先生不抱任何狭隘的观念,而将中国古代社会的法治也视为法治的不同类型,〔24〕主要指的是申韩式法治、诸葛式法治和民主型法治。这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包含了正确对待法治的合理性因素。他把法家的法治看作法治的一种类型,现将其相关部分摘录如下:
申韩式的法治,亦即基于功利的法治。此一类型的法治的特点为厉行铁的纪律,坚强组织,夺取政权,扩充领土,急近功,贪速利,以人民为实现功利政策的工具;以法律为贯彻武力征服或强权统治的手段;以奖赏为引诱人图功的甘饵;以刑罚为压迫人就范的利器。“有功虽疏贱必赏,有过虽近爱必诛”,就是 “人君制臣之二炳”(见 《韩非子》)。此类型的法治的长处,在于赏罚信实,纪律严明,把握着任何法律所不可缺少的要素。其根本弱点在于只知以武力、强权、功利为目的,以纵横权术为手段,来实行强制的法律。不本于人情,不基于理性,不根于道德、礼乐、文化、学术之正常。如商鞅之徙木立信等武断的事,均同时犯了不近人情、不合理性、不重道德的弊病。徒持威迫利诱以作执行法令的严酷手段。此种法治有时虽可收富强的速效,但上养成专制的霸主,中养成残忍的酷吏,下养成敢怒不敢言的顺民,或激起揭竿而起的革命。〔25〕贺麟著:《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6—47页。法家缺乏真正的道德价值的支撑,自然也就难以获得一种制约论的思想观念,功利主义实乃法家之要旨。
贺麟先生认为法家的法治类型的优点在于赏罚的合理配置并且严格法律。这个评价是十分中肯的,你要搞法治就必须做到诚信,按照法律的规定,应该奖赏的就奖赏,应该惩罚的就一定要惩罚。这样法律才能逐渐内化为人们的心理结构,逐步获得良好的法治效果。破坏法治的重要因素往往是不能很好的坚持赏罚分明的原则,该赏的时候不赏,该罚的时候不罚。中国几千年缺乏法治观念不能说和赏罚不统一、没有严格按照法律办事有关。你能够看到很多人违法犯罪了,但却得到了法律的宽恕。不严格按照法律办事是中国的一个传统,说明了法家的这个思想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当然这里的原因很多,也许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法家说的严格法律不符合中国社会的结构。你看看中国的老百姓一般都反对徇私枉法,说起的时候简直是深恶痛绝,但如果自己或者自己的亲人也沾上徇私枉法的 “光”了,则一般就不会大骂徇私枉法了。中国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缺乏普遍的整体性道德关怀和治理期待。但是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是不能匮乏严格法律的精神的,所以法家讲得很好,我们应该发扬光大。当然,严格法律也容易出现问题,比如法律教条主义,正是因为严格法律所具有这样的可能性问题,所以才不符合中国古典社会的情理化要求。但是不严格法律而任情理,则往往不是通常人所能做到,所以法治的落脚点在于人治的道理也就十分明显了。〔26〕贺麟先生对于法治和人治的问题有个相当深刻的观点,他认为:“法治的本质,不惟与人治 (立法者、执法者)不冲突,而且必以人治为先决条件。法治的定义,即包含人治在内。离开人力的治理,则法律无法推动,所谓 ‘徒法不足以自行’,故世人误认人治与法治为根本对立,以为法家重法治,儒家重人治,实为不知法治的真性质的说法。”现今距离贺麟先生提出这种主张已愈70余年,但人们好像还是从对立的角度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这是没有辩证思维的表现,是典型的两极对立思维方式在作怪。(同前引﹝25﹞,第46页。)贺麟先生是把人治看作法治的前提,而我在这里则用了落脚点的说法,其实质则是一致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搞法治有困难,根本的症结在人,所以今天法治建设之成功必然落实在人的不断提升之基础上。于是就有了法治的落脚点在人治的说法了。
贺麟先生对于法家法治的不足谈得较多,首先贺麟先生认为法家法治强调了武力、强权、功利、纵横之术,但却忽略了情理、道德、礼乐文化。说法家法治不合乎情理,的确很是有道理,因为法家的这个主张是从严格法律中自然引伸的。这也是法家的法治的困惑所在,因为中国社会是熟人社会结构和人情社会结构,严格的法律主张自然不能契合社会的要求。当一个民族的文化结构都已经情理化的时候,严格的法律主张是很难成为这个民族的法治精神和理念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法家的法治理论充满了理想性,而儒家的法律思想却倒击中了中国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要害。法家虽然并不崇尚儒家所推行的道德,但却并不是完全忽略道德。“韩非子是主张刑德并用的,这是法的两个方面功能。他关于禁恶的主张,提示了威刑的作用。但他还崇尚因人之所欲而加以利用的养德,即以赏利促民向善。这与他关于富国强兵的实利主义精神相联结。在他看来,尽管耕种田力劳苦,但百姓为之,可以富裕;战事危险,而百姓为之,可以封功受爵。在他看来,耕作与军功是不证自明的富国强兵之道。因此,他认为,用力耕作与争献军功就是有德的行为,因为它符合治国之道,理应受到奖赏。”〔27〕同前引 〔7〕,第115-116页。法家之道德虽然具有进取指向,但终究难以避免实利主义的基本倾向。由此看来,法家所推崇的道德是一种新型的道德,与儒家所讲的有着很大的差距。法家的道德应该被看作是一种进取型的道德,比如韩非子所确立的道德即为一种自力更生之德,为一种鼓励进取之德。然而,新道德固然可贵,但却与宗法制的传统、礼义社会之道德不能很好地融合,这就使得法家终究难以与中国之情理社会相契合。
贺麟先生认为,法家法治会造就 “专制的霸主”、官僚阶层的 “酷吏化”、百姓 “敢怒不敢言”,甚至会酝酿社会革命。法家流派的一些思想家虽然也期望好的君王,但是由于法自君出,而君往往又在法之外,所以法家的法治理论实际上是一种没有 “限制”理念的理论。〔28〕在一定意义上说反倒是儒家的理论包含了权力限制的思想理念,不过儒家对于君王的限制不是通过法律机制,而是运用帝王当有的道德对最高统治者进行限制。君王有君王之德,以君王之德规范自己的行为,就可以达至明君之境界。在这个意义上说,儒家并不是专制的理论,中国专制制度的形成原因不能到一种理论中去寻找根据,那样既夸大了理论的作用,也和历史的实际不相符合。一旦君王的权力失去了限制,那么霸主的出现就很自然了。至于官僚阶层的 “酷吏化”,自然是由于 “彻底”地贯彻法家理念,缺乏了情理的依托所导致的结果。法家讲究惩罚,而惩罚又倾向于重刑,在对于惩罚的反复强调中,酷吏的风格也就养就了。酷吏在历史实践中成为法家文化的实践者,人们想到酷吏就会想到法家的法治思想,好像酷吏与法家具有内在的紧密关系。应该说,酷吏执法严厉,不避贵胄,的确是难得的。但酷吏往往以维护君主利益和中央集权为己任,为达到此目的,各种残忍的手段便在其政治法律实践中倍加运用了。酷吏会代表朝廷去镇压老百姓的 “反抗行为”,会去歼灭 “地主豪强势力”,会帮助君王 “铲除奸党叛逆”,他们以威猛的方法,酷烈的手段,成为了维护君主政体的帮凶。〔29〕参见武树臣:《循吏、酷吏与汉代法律文化》,载 《中外法学》1993年第5期。法家不讲限权,这自然是一种具有 “专制”色彩的取向,与儒家治道之道德限权不可同日而语。贺麟的说法自然是有道理的,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实践的确造就了一大批酷法吏。由于政治的残忍,法律的酷烈,惩罚的严厉,中国百姓往往 “敢怒不敢言”,这就培育了中国特有的 “顺民”,但即便这些顺民到了实在无法忍受的时候,也会揭竿而起,闹出一场革命。这的确是中国历史的常态,当然这并不是法家的理论造就的,但法家的思想的确会包含这样的逻辑,如果一味遵循法家的主张却不讲情理,不亲道德,不亲百姓,则社会革命必然成为改朝换代的契机。其实现实的政治往往将法家的思想主张给绝对化了,历史运行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自然也不能完全归咎于法家,尽管那些现象看上去好像与法家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须知只有在两个事物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才可以将一个事物的出现归之于之前的另一个事物,否则就不存在任何必然性的问题。
法家的法治类型在贺麟先生看来就具有上述的优缺点,但给人感觉好像贺麟先生对法家的法治类型否定性态度大于肯定性态度。同时贺麟先生认为,法家的法治类型是法治发展的低级阶段,尚需向前进化发展。“由申韩式的基于功利的法治,进展为诸葛式的基于道德的法治,再由道德的法治进展为基于学术的民主式的法治,乃法治之发展必然的阶段,理则上不容许颠倒。”〔30〕同前引﹝25﹞,第49页。贺先生擅长黑格尔哲学,自然也不能不受黑格尔思想的影响,因此在法治类型变迁上也体现了辩证法之 “发展”的理念。但若的确探究历史,诸葛式的法治类型实际上早就已经蕴含在先秦的儒家思想之中了,这恐怕不好说是从功利的法治发展到道德的法治,当然道德的法治的确是在汉代以后成为气候,并成为中国古典社会政治法律运行的重要机制的。
法家的法治未必就是低级的法治类型,其所包含的诸多合理性因素不仅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并且在现代中国依然值得认真对待。比如法家 “去等级化”的 “壹刑”思想,或许直到今天我们也未能做到,但毫无疑问这应当是任何法治所当具备的平等主义的美德。“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 ,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同官之人,知而讦之上者,自免于罪。无贵贱,尸袭其官长之官爵田禄。”〔31〕参见 《商君书·赏刑》尽管法家的思想还是为君王的特权留有余地,但毕竟较人情化的儒家更加符合法治的本性。由于儒家的 “情本体”结构的无限扩展以及在现实中的滥用,致使中国法治时至今日依然 “为情所困”,构成我们现在需要花费大力气解决的问题。人情固然有人情的道理,但人情若是 “私情化”而背离了合理性的要求,那么最终必然会失去人情的支持。法家的合理性正是人情的缺失之所在,认真对待法家的合理性资源是当代中国法治追求者理应面对的问题。
四、当代中国法治运行中的法家元素
法家不仅有着丰富的文本世界,而且也拥有一个由历史的流动所构成的真实世界。在这个真实的世界中,我们能够看到法家对现代中国的法学知识和法治运行诸多方面的深刻影响,而无论是法律知识还是法治运行中的法家因素的存在盖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依旧充满了法家的思想烙印。比如人们对于法的认知在现代社会依然存在着一种政治学的维度,而这种维度正是法家的维度。法家的法治理论一方面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法理学,另一方面又与西方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具有一定的暗合,而早期的实证主义法学政治学色彩明显。法家主张法自君出,法律始终与权力、君王、国家密切地关联在一起,这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法治理论,这种法治理论主张的是依靠强大的权力系统制定法律、推动法律的实施。〔32〕我们能够看到,现代中国的法治包括整个的法学理论都与法家的这种思想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法律由国家制定并在实践中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这是我们的法治期待。其实同时,中国当代法理学所呈现的实证主义化的倾向也与法家有着内在的关联。有时候我们自认为接受了所谓现代的思想理念,但回过头却发现在自己的历史中早就具有了类似的思想。如果传统中没有类似的思想理念,则现代人之所谓接受恐怕是很难实现的。法治的实现也是依靠强大的权力系统以及由其制定的法律体系,并在法律运行中严格按照法律解决现实问题。同时,法家的法治理论也是实证化的,法家的思想家很少去关怀和追寻法律背后的价值尺度,也不去特别强调隐含在法律世界中的道德因素。其实,当一个民族的道德面临危机的时候,法治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无论法家的法治理论与现代人所信奉的法治理念有着怎样的差别,它也是一种重要的法治类型,这种法治类型所具有的特殊性根植于战国时代的中国历史现实,对中国古典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能够看到,在历史上法律的运行机制以及人们关于法律的观念中,有很多因素都与法家有关,比如中国人一想到法律就会想到包拯的三口铡刀,就会想到监狱、衙门,这与法家使得法律酷烈化有着一定的关系。法家的法治理论虽然没有作为主流的意识形态被历代统治者所承继,但法家的思想理论却与儒家一起促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法律运行的机制和特征。
在当代中国法治运行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质与法家有重要的关联,一是法治运行中的权力主义,二是法治运行中的法条主义。这两个因素本身无所谓好坏,其关键依赖于具体的情境,在一个公正无私的环境中 “权力”会促进正义的实现,而在一个人情淹没良知的语境中则“权力”无疑会破坏法治的精神;在被教条主义充斥的环境中,法条主义将无法为法律确立良好的合理性前提,而在一个良好的道德语境中法条主义的弊端也会得到良好的纠正。因此,法治的运行总有一个情境的问题,情境主义的思维是思考现实法律之运行的一个重要维度。
在现代法治运行中,“权力”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权力”也控制着法治运行的许多环节。如果权力的突出地位不伤害法律的尊严,一切都能够做到如同法家所讲的 “壹刑”的话,那权力可以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其实在原初的法家那里,对 “权力”过度依赖本身就已经隐藏了许多危害,“权者,君之所独制也”,这个 “独制”却是大大的危害。法家虽然反对尧舜禹般的贤人之治,但其实法家也特别需要尧舜禹般的贤人掌握这个权力,然后这个权力才能够真正促进法家理想的实现。然而,事实上的君王大多数都不是圣贤,被 “独制”的权力也就易于为祸,尤其是当权力可以超越法律的时候,则权力主义就没有任何优越性可言了。当代中国的法治运行,权力化思维是非常突出的,这或许与法家的权力主义主张有着重要的联系。
权力化思维之最大表现恐怕还是在于行政化思维,总觉得在法治运行中还是服从上级比较好,至于法律的合理性问题也是由上级说了算。比如在法院的机制中,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和批复实际上就是权力化思维和行政化思维的产物。法律是一项论证的事业,法治更是一项论证的事业。如果法治运行的各个主体不能以法律及其所包含的合理性价值为依托,那就不可能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状态。法家特别讲究如何运用权力的艺术,在传统的流动中久而久之人们养就了权力化思维,这种已经内化的思维方式时刻都准备发挥其或优或劣的功能。在权力不能依靠良知限制的情况下,就必须依靠一种良好的运行机制保证权力能够 “为人民服务”。
法条主义是当代中国法治运行中的一个不容忽略的问题,法条主义与我们的诸多体制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法条主义也与参与法治运行的主体不愿意承担法治责任有关,还与政治学意义上的法学思维方式有关,这其中恐怕还与作为流动的文化传统的法家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对于法家的认识是这样的:“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法家所主张的法令统一,一切都有法律裁断,从维护法律的统一性角度看的确具备良好的合理性。然而法家解释法律的基础依然是法家的理论,而不是现实流动着的价值世界。正是这个价值世界的匮乏,使得法家的思想旨趣倾向于法律本身,而不去关注法律所依存的价值世界,而这个价值世界恰恰是法律合理性的根基之所在,并且也是解释法律的合理性前提。法条主义是一种缺乏现实责任感的主张,法家的理想主义正是与现实世界脱轨的表现,法条主义与法家之理想主义在思维方式上是一致的。
法条主义唯法律至上的合理性值得认真对待,法家的理想主义更让人尊重。然而现实的世界正是我们存在于其中的世界,也正是我们要改造的世界,同时也蕴含了一切事物合理性的源泉。在中国历史上,法家巧妙地实现了在现实的政治法律运行中与儒家携手并进;在当今法治运行中,法条主义应当与价值合理性的世界融合为一体,真正的实现法治运行中形式与实质、现实与理想、传统与现实的有机统一,真正促进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类型的实现。〔33〕法条主义之盛行在当前的中国不能说不剧烈,我常以为在西方这是一种科学和理性急剧膨胀的结果,在中国则是个体不愿意承担责任的突出表现。因此西方的法律实证主义所包含的法条主义尚且有一种科学理性的精神,而中国之当下的法条主义则完全是与权力主义和不负责任的态度紧密相连的。在一定意义上讲,以科学理性为基础的法条主义 (此处无贬义)或许是一个民族法治发展的一个必要阶段,即令是美国这样的国家也都经历了一个类似的时代。这种特质实际上是一种抽象主义或者说概念主义或者说普遍主义的思想进路。(Willian M.Wiecek:The Lost World of Classical Legal Thought:Law and Ideology in America 1886-1937,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p4.)也许此种思想发展历程有利于法之确定性理念的形成,但若在缺乏信仰的民族或许要另当别论,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具体的法治运行中的任何一种现象都不是由历史上的或者异域的某一个单一的因素所塑造的,而必然是多种元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对传统进行认知的时候,当下的现实世界总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认知背景,因为只有在传统与现实的对接中我们才可能合理地把握历史与现实。对于法家法治类型的认知也无法离开我们当下的背景,正是这个背景决定了我们对法家的认知程度。法家作为传统在今天的法治运行中是一种实际的存在,这需要在今天的法治生活中不断地体悟和反思,匮乏对传统的反省就难以多方位地理解法治发展的不同维度。认识传统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体验的过程,拥有自身体验的知识往往是真正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