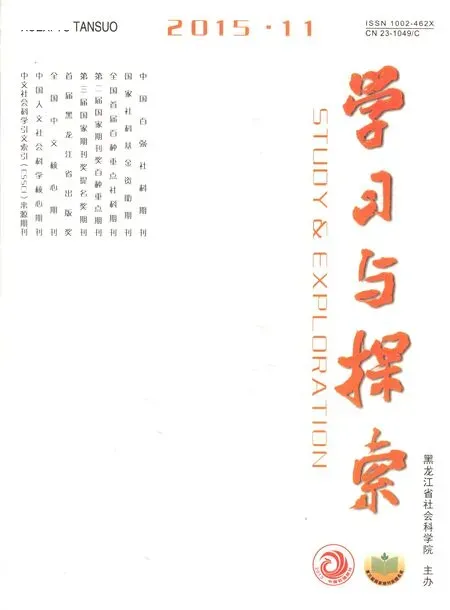“空间实践”与诗学想象
——西欧中世纪诗学的空间问题
张 昕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 610064)
·当代文艺理论与思潮新探索·
“空间实践”与诗学想象
——西欧中世纪诗学的空间问题
张 昕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 610064)
西欧中世纪的历史进程是单线的,天主教教会以及教义主导的文明体系色泽并不鲜明,这也使得人们容易忽略这一时期具体的历史现实。空间是内孕于社会、文化、艺术等诸多层面的重要理论关注点,中世纪文学、艺术的表达当中涉及很多空间问题,如奇伟而富丽的哥特教堂的特殊架构、骑士叙事诗中的漫游描写等等。由中世纪特殊的历史语境出发,对空间与文化的关系问题的探讨,可以帮助我们规避中世纪浓重的神学色彩,较为清晰地把握中世纪文化、社会的诗学表现。
西欧中世纪;空间;诗学;隐喻
自西罗马帝国灭亡到东罗马帝国陨落的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欧洲文明在两个方面出现了表面上的断裂:一是没有明显承续古希腊—罗马文明的辉煌,二是北方民族的入侵造成的长期战乱令欧洲陷入“黑暗年代”的泥潭。实际上,基督教的适时出现及其在社会、人文层面的引导作用,使得地理上零散的欧陆始终处于一个稳定的、一体的文化状态之中。随着北方民族入侵而来的就是宗教归化以及封建王朝的建立,古典哲学、艺术的继承则更多隐性地包含于教廷和俗世政权对文化的统辖当中,如柏拉图神秘主义对神学思想的影响,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对教父学者的哲学观及其释经原则的影响等。更为鲜明的是在遍布中世纪的各色宗教建筑中,以信仰和权力的互动关系为依托的“礼拜空间”(教堂)综合应用了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艺术要素。这样,欧洲中世纪就如一个文化集合器,其表层以空间载体的形式表现出来,以教堂、古堡固定了人们的想象空间,以远征(如十字军东征)理想化地试图弥合地域统一与信仰差异之间的鸿沟。因此,就历史线条的纵向推进,结合区域变更的横向组合来看,在“世界宗教”的幻梦当中,中世纪文明有着较强的空间性:实际的空间操作以及精神性的“彼岸”向往。两者相符相生,在以信仰为核心的文明体系中表现出“显”与“隐”的张力,属于欧洲中世纪的诗性的空间也就因此浮出水面。
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在《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五百年》(Fromdawntodecadence:form1500tothepresent, 500YearsofWesternCivilization)一书中认为,整体来说,16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仅对欧洲的“最西部”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区域覆盖“从德国、波兰、奥地利、意大利向西直到大西洋”的区域,因而称之为“西欧”(the Occident)更为合适[1]。宗教改革的效果与中世纪天主教的统治无疑是相对应的,在此基础上,结合当代对欧洲地理区域的划分,本文即以西欧作为明确讨论的对象,分析西欧中世纪文明当中空间与诗学的联系。
一、历史变迁:现实与艺术表达的空间对位
法国中世纪史学者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在总体上如是评述中世纪时期:
一方面,中世纪是一段充满暴力的历史时期,人们生活环节恶劣,完全受大自然左右,同时,中世纪也是一个极富创造性的历史阶段,它为西方文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也许更为重要,只有呈现出在物质、社会、政治现实层面中世纪怎样打上象征和想象世界(symbolism and imaginary world)的烙印的,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中世纪[2]Ⅷ。
在《中世纪文明:400—1500》(MedievalCivilization400—1500)一书中,勒高夫强调北方民族势力的加入,使得欧洲政治格局和文化面貌发生了渐进的变化。质言之,以宗教绝对的精神力为导向,一个试图建立“世界宗教”(World religion)的天主教社会逐渐在西方形成。尽管天主教的这一努力一直没有真正实现,但是其颇具实效的统治手段引发了极强的文化向心力。教廷“世界宗教”的努力发轫于拉丁文化与北方蛮族文化的融合。公元5世纪到7世纪,来自北方日耳曼部落的西哥特人和东哥特人分别南下侵略,西哥特人覆灭了西罗马帝国,东哥特人则占据了伊比利亚。5世纪另一个日耳曼部落汪达尔人(Vandals)曾洗劫罗马,烧毁了大量古罗马建筑及艺术品,至今英文中仍以“汪达尔”一词为荼毒艺术品的代名词。北方民族的历史性介入在实质上改变了欧洲的权力地图,他们对罗马帝国的破坏,他们“旅行式”(tourist trip)的侵略方式[2]11,他们对拉丁文化的默认,影响当时欧洲社会的诸多层面。作为关键的历史事件,蛮族入侵的过程和结局揭楮了西方天主教统治的新变化。
第一,在新血液的不断冲击下,农村生活逐渐取代了古罗马曾经一度繁荣的城邦生活[2]24。生存空间的变化首先服务于逐步展开的中世纪封建制度。“土地才是有关中世纪的一切的基础”[2]57,基于土地制度的生产劳作可以更好地巩固封建政治。更为重要的是,相比古代意义上自由的“城民”,农民的劳动者身份在精神上具有高度的集中性,他们更易接受天主教神启与救赎的教义,信仰与实际的生活方式达成一致。然而,城乡空间并不就此完全对立起来。始于13世纪,意大利托斯卡纳的商人寡头和市民们将分封或奖励得来的土地租给所谓“佃农”(métayers),这是中世纪土地制度最初转型的开端。列斐伏尔认为,佃农不同于奴隶或佣人的生产积极性与城镇资本持有者的类似“农场”的空间安排,实际预示着城镇与乡村之间的“空间上的辩证关系”[3]78。在这个意义上,“空间”是人造产物,它不是预先存在的,既非乡间也非城市,而是“两者之间新生关系的结果”[3]78,此时,基本的空间生产得以达成。以此为基础,蛮族入侵随之带来的生存空间变化,实际是历史偶然性的、人为的空间重新布局,新的生存方式以城镇的方式建构,新的生存模型则在融合实际空间与个体想象的宗教建筑当中展现出来。
第二,有关北方蛮族的破坏情结,当时的史官弗雷德加(Chronicler Fredegar)描述道:“如果你(蛮族国王)想要劫掠为自己赚取名声,那就破坏掉所有已经建造起来的东西,杀掉占领地的所有人;因为你不能建造得比你之前的人更好,那么没有比破坏更好的赚取名声的方法了。”[2]17可见,在具体的历史语境当中,“你不能建造得比你之前的人好”从侧面说明了北方民族对罗马文化的真实态度:“他们不是作为威胁出现,而是罗马体制的仰慕者。”[2]114因此,蛮族势力得以在历史的演进过程当中成为维护欧洲教廷的中坚力量。此外,从北方民族的态度当中可以看到,他们的破坏并不意味着重建,而是融合其中,这也在主观上促进了鼎盛期的中世纪大量教堂,即“礼拜空间”的出现。在西欧中世纪文化表征当中,列斐伏尔空间三分法之一的“空间实践”表现得较为明显。所谓“空间实践”关注“特定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以及空间系列(spatial ensembles)”,它“与社会空间和个人与该空间的关系,是一定程度上的‘空间能力’和‘空间表现’”[3]33。如果信仰是维系异质文化融合的纽带,那么,标志着教廷与王朝共荣的“空间实践”,则推动了个体想象与现实生活的合一。
以俗世与教廷给予的关系为表征,宗教文化制约下的文化同质化并不足以说明民族性的消逝,多民族的西欧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民间俗语(vernacular),民族情绪一直是构成中世纪文化的恒定条件。法兰克人有与伊斯兰异教徒作战的《罗兰之歌》,西班牙人有反抗摩尔人统治的《熙德之歌》。在这些宣扬民族荣耀的英雄史诗当中,天主教教义成为英雄领导族民团结对外的利器。这里,西欧中世纪不同民族的文学、艺术表现有着弗朗科·莫莱迪(Franco Moretti)所谓“文学地图”的时效和意涵[4]。此外,从民族志(ethnography)的角度讲,中世纪曾经有许多“居民社区”(communities of inhabitants)[5]230,社区是漫长的中世纪的家庭观念的演变形态,12世纪到13世纪,传统的农民跨越漫长的世纪形成一种“人与空间的辩证”[5]230。这种人文、社会空间的自发改造,一方面是在历史进程当中对旧有秩序的反拨,另一方面则呈现出独特的、属于中世纪欧洲的民族地图。该地图潜在尝试的人文扩张为后来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们反封建、反教皇统治的潮流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学底蕴。这种底蕴的达成,无疑和近百年中在制度之外重新组合社群空间的努力相关,他们的努力或许没有达到古希腊时期的社区式文明,但是在表面平稳、实则变动不居的历史语境下,中世纪“居民社区”的矛头直指其时坚固的权力分布。
总体来看,蛮族入侵给西方世界带来的变化,新势力极强的流动性不断推动着西方各地理区域版图的交合,在客观上促进了板块大分裂(the great divide)后所谓欧洲的形成,而统一欧洲的基本要素则是使北方民族甘心臣服的天主教。文化融合带动了生活空间的变化和游移,一神信仰和教义品行满足了当时人们对“不变”的需求。在宗教巨大的精神合力感召下,黑暗的战争年代保留了文化的种子,拥有各自语言的北方诸族并没有打散拉丁语在欧洲的分布。拉丁语因为教廷势力的扩大以及随之而来的教义普及的需要,始终作为官方用语和文学用语存在[5]152,这在实际上加速了西方世界各异质文化的同质化。列斐伏尔《空间生产》(TheProductionofSpace)一书开篇大量提及所谓的领导权,这里的“领导权”以社会空间为表现,相比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显得更加具体。至于空间生产与文化领导权的关系,列斐伏尔称:“我将展示可操作的、工具性的空间角色,它是得于既有生产方式的知识和行为。”[3]11作为社会性的、知识与行为的结合体,支配空间的文化霸权的掌握者就需要充分利用空间的生产和分配。在中世纪欧洲,封建统治和教廷统治并行不悖又互抱敌意,然而,就人们日常的思想样态来讲,教廷无疑拥有高一层次的文化霸权,而封建王朝则为霸权的实施提供了权力空间。
提及封建王朝的载体——现实的地理空间,晚期中世纪大规模的教堂工程就是空间生产与操控的典型例子,其中的执行者正是日耳曼、法兰克等王朝。法国加罗林王朝在教堂建设方面一直走在诸国前面,高耸、宏大的巴洛克教堂是中世纪法国的特色之一。如法国加洛林王朝曾大规模兴建教堂,而追求古罗马时期凯旋式拱门等艺术特色的背后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传统。相比古罗马时期,多民族融合的中世纪封建王朝更加注意形式感或“时尚”,比如加洛林王朝时期的一些建筑物“表明了将文化风格、宗教、政治、思想形态意图联系在一起的浮夸努力,同时又努力开发一种独立的、原创的风格”[6]。不难想象,这种理念影响下的建筑风格会有诸多细节的杂糅。这些细节的空间重构是以不同层面的文化要素为支柱的,这就为我们透过礼拜空间审视中世纪文化提供了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从建筑艺术的角度来说,创造了属于中世纪的“空间诗学”。
二、个体与空间:“彼岸”向往
充满宗教意味的西欧中世纪社会因其神秘而往往显得凝滞。实际上,从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该时期的欧洲文明版图是流动的,如同鲍曼强调所谓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虽然生活在天主教的绝对权威之下,人们的感受也不是稳定的。依据这一点,中世纪的空间实践有着两个层面的表现:教堂的空间实体的象征意义是直观的而非抽象的;个体对空间的直观感受与空间想象综合成为独特的、中世纪式的“地理梦幻”。
1.空间结构与直观象征
与中世纪早期因北方民族的介入而改变的生存空间相比,宗教社会的日益发展和巩固的直接产物是大规模的教堂建设工程,教堂成为“西方基督世界的欧洲最引人注意的外在标识”[2]56,如法国哥特式建筑的兴起,以其夸张的感性冲击力预示着时代的变化。在突出的尖顶、拱门等结构特征中,装饰性哥特的象征意指是非常明显的,每一位信徒都可以从中感受到来自信仰的压力、上帝的伟岸以及上帝精神的不可企及。即便有着鲜明的象征意义,中世纪艺术表达对空间的敏感程度与当代艺术形式相当,但是显然不具备诸如毕加索《拿着曼陀林的女孩》(GirlwithaMandolin,1910)那样的抽象性。首先,在中世纪建筑艺术中,空间意味着“间隙或延展(interval or extent)、指向能够具象理解和测度的东西”[7]24。其次,就建筑物的象征意义来讲,与“彼岸世界”相对,“教会对空间的把握和操控的信心是为了确认对‘此世界’的控制”[7]25。可见,对空间构造的明晰把握和对空间感的超越要求是中世纪建筑艺术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空间操控的权力在教会,而具体的礼拜空间的建构则掌握在封建王朝手中。中世纪的哥特建筑始终与法国人相连,所谓opus francigenum(Frenchmen work)的大量建筑工程为法国带来了诸多荣耀,哥特式无限延展的形式感实际上满足了当时的法国国王扩张皇室权力的欲望[7]25。除了表现权力空间的积极张扬之外,哥特式建筑从外观到内饰都表现出极强的宗教象征意味。如教堂内部壁画讲究“绘画的丰富”(Varietas, pictorial richness),其布局使得空间变作“一个象征体系”,百合花作为“处女的标识”出现在画面前端甚至远方的塔楼上,而“向左侧迅快隐去的长廊则成为象征着处女贞洁的封闭空间”[7]52-53。可见,对“彼岸世界”的向往象征性地嵌入到空间的实际生产当中,而这种想象的神性或者说诗性,是与个体身份相关的,也就是列斐伏尔所谓的“空间实践”的创造物与个体的关系。
列斐伏尔认为,特定社会空间具有稳定性,它“不透明”,充满“黑洞”[3]228。社会空间有着封闭和压抑的特征,但是空间内部的实体结构丰富,能够塑造为反照外在世界的镜像。此外,就个体的人而言,“看似凝固的物质空间,实际上内化或者体现了人类活动的各种事件、事物与过程”[8]。这时,社会空间的社会意义才得以凸显。表现在教堂建设上,礼拜空间的建构纵向上有历史沉淀中的艺术要素,横向上有严密的空间布局,当信徒置身其中忏悔祷告,我们可以较清晰地察觉到教堂作为礼拜场所的巧妙地利用空间创造与历史相勾连,予人深邃的、隐喻式的想象。人身的意义能够在礼拜中得以呈现和延展,很大程度上规约于礼拜空间的生产和架构之中,因为“初看表现出生物形态(biomorphic)和人类学特征的社会空间朝向超越这种实时的直观性(immediacy)”[3]228。由此可见,于当代造型艺术的表达差异之外,中世纪艺术表现在深层次上的理念也并不抽象,在种种尖顶、壁画、长廊的观感当中予人的超越感受,都是发生在实际空间之内的,是已经设计完备的,因为教会和王朝要借助集聚的宗教空间实现对“此世界”的控制。
2.社会空间的精神实质
“物理空间和物质空间的内心感知,因为由艺术创造表达出来的空间包含了创造性,由此形成的空间意义关系会构成人们不同的感知模式”[9]。在中世纪,固定的空间结构需要发挥想象达到教义需求的实践效果,而人们的个体视野毕竟无法受此局限,中世纪天主教“世界宗教”的梦想因此从未泯灭。世界性的幻想意味着更广泛的地理空间的需求,十字军东征是天主教廷对“世界宗教”的向往达到极致的表现,落实到信徒个体,固定的生存空间在坚定信仰的同时也指向了更深层次的、与上帝绝对精神的交流。他们将“东征精神(crusading spirit)打造成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能够使西方世界的模糊梦幻与沉闷忧虑(vague desire and muffled anxieties)变得现实具体”[2]69。西部天主教势力针对东部异教势力的九次远征整体上是失败的,但是“远征军中的下层平民仍然最受东征精神性(spirituality)和神话性的感染”。教会鼓动人们理想化的精神境界可以变为实在的现实,“诸多没有为土地等现实问题束缚的基督徒为之心动,东征朝圣之旅可以实现他们所有的愿景:冒险、财富以及永恒的救赎”[2]69。不难看出,十字军东征本身具有极强的象征意味,在教义的统辖中,以具体的实践行动为纽带,神性与人性首次“真实”地链接在了一起。也就是说,在空间的流动当中,“东征精神”是中世纪人们与社会空间之间张力的动态表现。
虽然在现实层面教廷的东征计划是失败的,收复“圣城”的旗帜不足以应对“空间旅途”中的种种变量,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东征精神”的打造却是成功的:“东征精神”以极强的象征意味在流动中传播了天主教义;“东征精神”给予人们滞涩的生活以“空间感”,这种转换可以避免产生一些社会问题。提及社会问题,除十字军的“圣城向往”的财富与权力的空间想象之外,一直以来,人们对印度洋抱有美妙的幻想,直到15世纪马特勒斯·曼努斯(Martellus Germanus)的航海图出现了印度洋这个一直存在于中世纪人们的梦幻当中的海域[5]190。这一海图(portolano)的出现是对科技、经济进步的推进,也必然打碎西欧世界对东方世界的浪漫幻想,给人们曾经狭隘的人文视野和地理观念打开了一个新的出口[5]190-191。此时,虽然真正大规模的东方远航尚未开始,礼拜空间的神圣与幻想的统一已经因为世界性视野的敞开而逐渐失色,然而中世纪人的空间想象继续在艺术创作中得以表现。与地理空间的重新核定相当,一直以来主导中世纪教堂建筑样式的哥特式建筑此时由装饰主义演变为垂直式,其中飞扶壁的设计能够最大限度地切割有限的空间,在几何构造上对称的同时,密集的网格因优雅的组合形式使人感受到空间上的舒展。
在列斐伏尔眼中,个体与社会空间的关系有着双重的本质意义。
一方面,一个人(即考虑中的任一社会成员)将自己与空间联系起来,使自己置身于空间之内。该人同时面对自身的直观性和客观性……他是一个主体……(存于)一个特定的社会状况下——试想一直处于稳定状态,并因此在某种状态之内同时为该状态所暗示——一个角色或者一种功能:一个个体的人以及一个公共身份[3]182。
另一方面,空间充当媒介或调解的角色:在每个平面、不透明的形式之上,个体试图把握之外的一些东西。这使得社会空间变作由光、“此在(presences)”以及影响占据的透明中介[3]182。
在这里,列斐伏尔表明了对个体而言社会空间的两点表现:个体可以被动地由空间来确定其公共身份,比如礼拜中的信徒,或者相对动态的十字军骑士;社会空间在较大程度上是精神性的。在中世纪文化的空间表现中,固定场所作为神性媒介,十字军东征、地理幻想等历史实践则在稳定的神性与变动的人性之间创造了一个完整的、有机的精神空间。
三、诗学表现:空间隐喻
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的“文学空间”(the space of literature)理论认为,在文学语言否认确定性表述的情况下,“语言掌握着‘空白地’(absence)。它是无言的,它已经表达过了;当它消逝的时候,它仍然在延续。” 在文学空间当中,语言“无须被听到”,因为语言“模仿回声”,会以“密集的耳语”(whispering immensity)的形式使作品成为一个“回荡的空间”(reverberating space)[10]。布朗肖的表述或许有些抽象,其意指与英伽登“空白点”的论调有相似之处,两者都强调文学语境及其可能达到的想象性的外延。比较来看,布朗肖的文学空间理论在结构主义的倾向之外,提出文本空间“回声”的往复性,因为在缺乏具象的时间线索之时,文本的空间意义是直观且明显的。在这一层意义上观察中世纪文本,可以说,空间意义以隐喻的方式在文本流动的想象当中。
比喻,或者说寓言式地阐释经文意义是中世纪神学家们的常用手法:一方面针对当时大众文化状况的现实,以喻体说明问题更易为大众接受;另一方面,在神学意义上,上帝的意志是不可能完全呈现的,必须要包裹在适当的形式当中。
库尔提乌斯(Ernst Robert Curtius)以文本呈现为基础分析了中世纪文本中不同的隐喻类型,其基本线索为中世纪修辞学家所追求的文本形式感,现举要整合如下。
1.航海的隐喻(nautical metaphors):这一类型的隐喻表现为将航海过程与写作行为相比拟。在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眼中,“创作诗歌如同航海”,写作过程和航海同样“危险”,尤其在掌舵者是“不熟练的水手”的时候[11]128-129。西塞罗以航海比喻演说的整体,修辞家应该拿起“辩证法的船桨”(oar of dialectics)进行“雄辩的远航”(the sails of eloquence),昆体良则认为身为修辞家,应是一名“坚韧的水手”[11]129。推及中世纪,将《圣经》翻译成拉丁文的神父哲罗姆(Saint Jerome,347—420)视其解释经义的工作为“阐释的航行”(the sails of Interpretation),圣灵则是护送他航行的“和风”(breeze)[11]129。
2.肉身的隐喻(Corporeal metaphor):这一类型的隐喻表现为突出特定的人体部位来服务文意的整体。《理想国》中多次出现“心灵之眼”的比喻:“当灵魂的眼睛真的陷入了无知的泥沼时,辩证法能轻轻地把它拉出来,引导他向上……”[12]柏拉图以“心灵之眼”象征人对智慧的追求,凭借对真理的执着人可以不断“向上”,接近至上的“理式”。柏拉图的比拟方式及其效果引起了中世纪思想家的重视。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以“唇舌的手艺”(handiwork of tongue)歌颂上帝之美,以“心灵之手”(heart’s hand)驱散文学阅读带来的信仰困惑[13]。人体隐喻的加入使得文本更加切近的同时也锐化了表达效果。因此,从接受层面来讲,库尔提乌斯称之与后世语言风格鲜明、怪异的巴洛克文学相通[11]137-138。
3.剧场的隐喻(theatrical metaphor):相比肉身的隐喻,这一类型隐喻的神学特性更为突出。象征人与绝对真理之间的距离的“矮墙”是柏拉图“洞喻”的关键道具,“矮墙的作用像傀儡戏演员在自己和观众之间设的一道屏障,他们把木偶举到屏障上头去表演”[14]272。只有当“矮墙”的帷幕拉开,人们才能辨别出事物的真假,这无疑是柏拉图在调侃当时古希腊盛行的戏剧。对绝对性同样执着的中世纪作者延续了柏拉图的路线,他们将宇宙比作舞台,不同的人扮演不同的角色,一切行动都受到上帝的操控,如奥古斯丁就曾以“喜剧”隐喻人的贪婪和欲望[11]138。
在以上的梳理当中,我们首先能够看到中世纪诗学对古希腊—罗马传统的继承,同时,隐喻方法的中世纪化比较鲜明地表现出与宗教神学密切相关。借助对中世纪历史进程的观照,其隐喻方法的运用多跳过时间进程,直接进行空间想象。从如上三种方式的修辞来看,在应用隐喻方法的文本空间当中,作者往往通过空间想象来描绘神圣的彼岸世界,而“远航”的现实意味无疑可以为文本提供一条模糊的时间线,那么,可以说以隐喻为标识的中世纪诗学方法试图达成一种时空统一的努力,这一点同样表现在礼拜空间的建构中。首先,隐喻的方法是为信仰与神性服务的,是“绝对空间”与“抽象空间”的糅合[3]234-236。其次,文本作为精神的产物,其本身具备的超越意义在特定修辞方式的引导下凸显了“此处”与“彼处”的辩证关系。加斯顿·巴什拉(Gaston Bachlard)在《空间诗学》中称:“外部与内部(outside and inside)构成了一个分区的辩证。”[14]211“此处” (this side)和“彼处”(beyond)是对内部和外部的模糊重复,因为“任何事物都有外在形式,即便是无限”[14]211。
我们寻找决定存在的可能,并通过这种语言、作为超越所有状况,给所有情形一种特定的情形……“这里”和“那里”的辩证关系因而被提升至绝对意义,该意义依那些不幸地被赋予了不可约束的本体论决定力量的副词而定[14]211。
当“此处”和“彼处”脱离了日常语境呈现在文学空间当中,其“反复”就不再是语言表面上的副词意义了,而是文本空间中的“回声”。在西欧中世纪的历史语境下,这种“回声”比较鲜明的文本表现就是隐喻的修辞方法。中世纪作者以带有明确意指的喻体令文本空间激荡起来,使得“此处”和“彼处”往复循环,完成神学上的超越意义的同时实现独特的、属于中世纪诗学的空间想象。
四、结语
在欧洲文明的进程当中,中世纪是不可逾越的历史时期,在天主教主导的权力版图和精神世界当中,构建社会空间的“空间实践”有着明显的实际意义。比之今日,中世纪个人与社会空间的互动关系更多地在神性与人性之间徘徊。当然,中世纪的神性本身具备明确的宗教意指,与后现代“陌生化”“神化”的观念无法相提并论,但当涉及社会空间中的个体问题,中世纪文化的相关表现可以予人更为明晰的印象。在空间问题上,神与人是张力的联系,不存在一方主导的现象:固定空间规约个体,以直接的、人化的神性,即象征性的空间来实现宗教目的;中世纪文明与异质文化的宗教性融合息息相关,人们的地理幻想,包括“世界宗教”的梦幻,实际指向一种独特的开放视野,即制造纯粹的“精神空间”使得人们的地理想象流动起来。就此可言,在西欧中世纪具体的文本表现中,以隐喻为代表的修辞方法在神学色彩的想象层面指向了一种“空间诗学”,在其辖区,“此处”与“彼处”的渊源能够将人与神的关系具象化。
[1] 巴尔赞 雅. 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五百年[M].林华, 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3.
[2] Jacques Le Goff. Medieval Civilization 400—1500[M].Oxford: Blackwell, 1988.
[3]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Oxford: Blackwell, 1991.
[4] MORETTI F. Graphs, Maps, Trees: Abstract Models for Literary History[M].London: Verso, 2007.
[5] Jacques Le Goff. Time, Work, and Culture in the Middle Ages [M].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6] SCHUTZ H. The Carolingians in Central Europe, Their History, Arts, and Architecture: A Cultural History of Central Europe, 750—900[M].London and Boston: Brill, 2004:350.
[7] CAMILLE M. Gothic Art: Visions and Revelations of the Medieval World [M].London: George Weidenfeld & Nicolson.1996.
[8] 阎嘉.不同时空框架与审美体验: 以戴维·哈维的理论为例[J].文艺理论研究,2011,(6).
[9] 阎嘉.戴维·哈维的地理学与空间想象的维度[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3, (11).
[10] BLANCHOT M. The Space of Literature [M].Lond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2:51.
[11] CURTIUS E.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 [M].New York: Harper& Row, Publishers, Inc., 1963.
[12] 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300,272.
[13] AUGUSTINE S.Confessions[M].London:Penguin Books deluxe edition,1961:85.
[14] BACHELARD G. The Poetics of Space [M].Boston: Beacon Press, 1992.
[责任编辑:修 磊]
2015-07-26
张昕(1988—),男,博士研究生,从事西方文艺美学研究。
I0
:A
:1002-462X(2015)11-013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