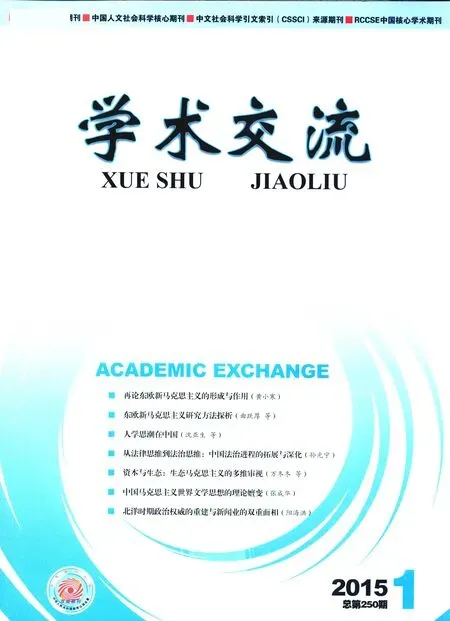北洋时期政治权威的重建与新闻业的双重面相
阳海洪
(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新闻传播学研究
北洋时期政治权威的重建与新闻业的双重面相
阳海洪
(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辛亥革命推翻皇权后造成权力真空,形成政治权威危机,各种政治力量希图主导中国的权威重建之路。政治权威的核心是权力合法化,这些政治力量在重建权威的过程中,极力要求传媒服从其意志,以建构符合其意图的合法性基础。因此,不同的权威重建路径,形成了北洋时期新闻业的双重面相:由传统型权威而来的“专制”面相和由法理型权威而来的“现代”面相。在这双重面相中,法理型权威及由此而来的“现代”面相是符合历史潮流的选择,但因北洋时期的武力政治,绞杀了中国传媒的现代性转型,使之重回传统官报之路。
新闻史;“专制”面相;“现代”面相
北洋时期在中国新闻史叙述中,因其本身的复杂性,呈现出不同面相。近来,学界以“现代性”视角审视北洋新闻史,寻求另一种书写方式。王润泽教授认为,北洋新闻业在“物质基础”、“运营模式”、“媒体经营”、“新闻业务”和“新闻理论”诸层面都取得了现代性突破。[1]370吴廷俊教授亦指出,北洋新闻业在官报、党报主流到民营企业报的报业格局转型、政论本位到新闻本位的新闻内容转型和职业报业启程并发展等三个层面上实现了现代转型。[2]这些论述,为我们建构了北洋新闻业的“现代”面相。
在由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需要有足够权威的中央政府来整合社会,以实现现代转型。政治权威的核心就是政治权力的合法化。民众只会服从他认可的政治权力。因此,合法性意味着民众是基于某种价值、信念而认可、支持某种政府统治和管理,是有效统治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唤起并维持民众对政府合法性的信仰是维持统治的前提。简言之,中国现代转型是一个包含秩序与权威的双重重建过程。北洋时期是一个方生方死的时代,辛亥革命推翻了皇权,创建了中华民国,在把中国从封建帝国变成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但在帝制废墟中并没有产生现代型国家,民国很快陷入了武人政治局面,形成政治权威危机,各种政治力量希图主导权威重建之路。这些政治力量在重建政治权威过程中,会极力要求传媒服从其意志,以建构符合其意图的合法性基础,由此造成了北洋时期新闻业的“专制”与“现代”等不同面相。
一、传统型权威与“专制”面相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虽为民国总统,但革命党人对他充满了不信任,北洋集团与国民党之间陷入恶性对抗。为强化中央权威,袁世凯以武力镇压二次革命,废弃地方议会,并在1914年抛弃国民党,独自制宪,成为“帝王式总统”。为维持统治,袁世凯将心腹派驻各省,希望强化国家权威。但袁所赖以发家的北洋集团是依靠利益和庇护关系组成的军事-官僚集团,其内部团结依赖“主从式的效忠观念来维系,在层层庇护的基础上建立传统的恩惠和忠诚的交换关系”[3]。这种“低水平结合”造成军权下沉、地方藩镇化的局面,严重削弱了国家权威与权力的基础,国家权威的缺乏难以形成稳定的政治秩序。面对内忧(“袁家将”的离心离德)外患(革命党人的质疑与革命)的危局,“袁氏误解病源,以为皇帝的名号可以维系那崩散的局面,故第二步才是帝制的运动。”[4]在袁氏看来,权力不能集中,则群情涣散,会造成社会动乱。“民国就得有议会,而议员又事事掣肘,实不胜其苦,倒不如乾(干)脆称帝。”[5]重建社会秩序的需要与个人野心的膨胀,使得袁世凯以军事实力为依托,在帝国主义和周围亲信的支持下,希望变更国体,复活皇权,建立传统型权威,以维系地方对中央的认同,将离散力量重新纳入轨道。
传统型权威指的是“固有权力的神圣性是支配团体中大部分人之所以服从的理由,即传统被视为神圣的”[6]。它将国家权威建立在传统之神圣性及由此神圣传统所授命之统治者的合法性上,其基本特点是尊奉习惯和家长式独断。袁世凯是从如下两方面来重建传统型权威的:一是恢复帝制,利用传统制度以重建政治秩序;二是尊孔崇圣,利用传统符号以重建价值中心。这两种努力都服务于重建传统权威,以稳定政治秩序的努力。袁氏仿照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做法,恢复爵位制度,更改官制和礼制,公布国玺条例,颁布《尊崇孔圣令》和《祭孔告令》,意图将“孔教为国教”订入宪法。1914年9月28日,袁世凯亲率文武百官到天坛举行祭天大典。袁氏更改官制与尊孔祀孔之目的,在于借助这些传统符号,恢复礼治秩序,“以礼仪确定等级化角色与规范的权力秩序”[7],为自己制造“天命论”的合法性基础。与传统型权威相对应的是家长式统治方式,北洋集团多从旧官僚而来,既“乏科哲学识”,亦“无世界眼光”。他们以武人干政,对现代政治比较隔膜,而对封建专制言论管制的文武两手则相当熟悉,使北洋新闻史呈现出“专制”面相。
(一)制造称帝舆论为传媒的运作基础
民国初造,民众尚未得民主练习。袁世凯利用此种机会,组建筹安会,收买、创办传媒,通过《亚细亚报》等喉舌,极力鼓吹帝制,为其称帝造势。袁世凯与他的顾问们将中国“特殊化”,认为中国“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实行共和,“难望有良好之结果”。因此,“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8]。中国欲求富强,必须“先去共和”,“非立宪不足以救国家,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之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救亡之策,富强之本,皆在此也。”[9]并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授意各省及各机关上呈国体变更书,为复辟制造民意依据。一些被收买的报纸,几乎天天报道国人渴望恢复帝制的新闻,充分利用传媒,操纵民意,将自己建构成救民于水火的“真命天子”,为自己重造传统权威,复活皇权制造舆论,以期赢得民众的支持或使之顺从。
(二)家长式的传媒管理方式
与传统型权威相对应的是家长式的传媒管理方式,其特点就是专权。为压制不同政见的报刊,以使言论“归一”,袁世凯制订了许多法律制度,禁止报纸刊登各级官署禁止刊登的一切文字,以强化舆论管制。袁依靠“枪杆子”起家,其新闻法治也就带有强烈的军阀色彩。他仗恃北洋军,强化军事机构与军警统治,以暴力方式压制言论自由,整肃舆论。报纸在发行前须送报样给警察机关备案,建立新闻检查制度,由陆军部执行,对违反规定者,科以军法,并在各地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以落实该制度的实施。袁氏的新闻检查,没有明确标准,全凭检查人员的主观意志行事,“构党狱以残异己,布鹰犬以钳舆论,巧聚敛以尽奢侈,扩军队以防违抗”[10],对报业横加摧残,制造了“癸丑报灾”。
袁的死亡造成中央集权中断,各路军阀在各省建立势力范围,争夺地盘。面对舆论监督,军阀们迷信武力能解决一切问题,对不合己意的报纸和报人,采取强力镇压,凭个人好恶臆测,军人和官吏可以滥加援引,肆意迫害报人。甚至政府部门和地方军队都可以命令、训令等形式对新闻界发号施令,对报纸横加干涉,极力摧残新闻自由。用张宗昌的话说,“反正报上登载的消息,只许说我好,不许说我坏。如果那个说我坏,我就以军法从事。”[11]由于派系政治文化的多变性和不稳定性,“对新闻业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掌握政权之人的专擅和一念之间,他们出于各种集团或个人目的,钳制新闻传布、捕杀报人,这是新闻业面临的最大和最直接的威胁。”[1]11
二、法理型权威与“现代”面相
辛亥革命不同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它发生在中国开始拥抱现代性的时代,建立法理型权威成为现代国家的核心。法理型权威是一种受法律规则支配的权威,它对包括官员在内的所有公民的大多数行动具有约束力。统治者只是源于法律之授权而暂时享有权力,它必须按法律规范的轨道运行,一旦越出法律的边界,民众就可以否定统治者权力的合法性。
法理型权威将法律奠定为政治生活的基础,官员经由法定程序选举产生,他只有在得到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才能发号施令。人民对统治的服从,实际是对产生权力的那套法律制度的服从。民元之后,“君权神授”遭到解构,确立了人民主权的政治合法性原则,保护人民权利成为政府的基本义务,并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厘清了政府权力的边界,三权分立和议会民主制度为政府奠定了最基本的制度框架、法权乃至道德基础。北洋集团在袁逝世后,群龙无首,派系分裂和地方割据进一步加深,民国政治更呈“碎片状”,北洋军阀虽都觊觎最高权力,“欲自为中心势力之竞争者”,但都无法凭借实力压制其他群雄。历史潮流之推动与实力政治之限制,使各军阀都表示支持约法,服膺民意。参与护国运动的西南军阀亦反复强调,他们此次兴师,“其大义在拥护国法”,反对帝制。在“碎片化”的政治格局中,北洋政府恢复了临时约法和国会等民主形式。各级政府都表示要,尊重约法在国家政治中的神圣地位,显示出建构法理型权威的努力。1917年,段祺瑞“再造共和”,成立新的国会。此后的政治舞台,虽历经皖系、直系、奉系等军阀统治,但此套民主框架都大体维持着。在这套框架下,中国破天荒地产生了国会,并以国会为枢纽,初现政党政治雏形,人民选举总统,制定法律,监督政府,弹劾官员,向着现代政治迈出了第一步。此种建构法理型权威的努力形成了北洋新闻业的“现代”面相。
(一)权利成为传媒的运作基础
法理型权威以法治国,以限定国家权力和保护公民权利作为基本内容。因此,权利成为民国传媒的运作基础,公民的表达权、知情权和舆论监督权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在表达权上,言论自由被写入约法,办报成为合法职业。中国报业管理走上法治轨道,有利于报纸享受新闻自由权,为传媒现代性转型营造了生长空间。
法理型权威所尊奉的理性原则在实质上和程序上都确认了民众能凭借其理性能力去自我评判和体认政治的合法与否,这为中国传媒由意识形态灌输的政论本位转向新闻本位提供了可能。作为北洋时期最有名的新闻学者,徐宝璜和邵飘萍对记者反复致意:传媒仅仅关心新闻的真实、客观与全面,满足公民知情权。“只有事实,可成新闻”,“苟非事实,即非新闻”[12],提供新闻成为传媒之天职,发现新闻、报道新闻和评论新闻的能力成为评价记者专业素质的标准。为保证“以真正之新闻,供给社会”,传媒在报道中必须持客观立场,以保证新闻的真实准确。新闻本位观念的树立,引发了传媒一系列现代性转型:通讯社勃兴、通讯取代政论,成为报纸的主要文体,职业记者与团体涌现。为免受外在势力的干扰,保证新闻真实与言论独立,传媒开始重视报业经营,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方法,使中国新闻事业的现代化转型得到了先行现代化国家的经验观照与指导,拉近了与世界报业的距离。
法理型权威是以政治绩效作为其前提的。政府解决现存问题和满足社会需求的能力成为支持、维系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并且此种管理绩效必须是可以由民众来验证和监督的。在法理型社会的政治构架中,传媒作为公民权利的载体和实现形式,成为监督权力运作的公共平台和民众参与政治的有效渠道,为中国传媒的现代性转型提供了“入口”。北洋时期,各地军政府当局摆出尊奉言论自由的姿态,在地方法规中写入“不得干涉报馆”的条款,召开新闻发布会,主动向报界公开政务,以接受媒体监督。此时政党政治亦开始登场,各党派竞相创办传媒,互相监督,以为自己增加选举筹码。传媒本身也以法律为依据,揭露官员的不法行为,希望将权力关进“铁笼子”里。林白水办《公言报》,一年内颠覆三阁员,揭发两赃案,被誉为“新闻界的刽子手”,在林氏看来,新闻监督有如许能量,是政府尊重法律的结果。“以合肥那样蛮干的家伙,也不能不有三分尊重舆论,因此也就暗暗的劝他辞职。你想吧,那时候的合肥,简直跟项城差不多远,他以总理之尊,却不能保护一个把弟兄,可见当时北京城还有些纪纲。”[13]“可见当时北京城还有些纪纲”,说明法律成为传媒开展舆论监督的“护身符”。
(二)官僚型的传媒管理方式
与法理型权威相对应的就是官僚型管理方式。职业官僚受过专业训练,其职权依据法律规则及得到法律授权的行政管理人员所发布的命令,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因此,北洋时期的官僚型传媒管理方式,具有如下特点:一是“以法治媒”,此点前面已有论述。袁氏死后,北洋政府以约法为基础,废止了《颁爵条例》、《附乱自首特赦令》、《报刊条例》等一系列与帝制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依法对传媒进行行政管理,显示出以法治媒的努力。尽管北洋时期官僚型管理还带有过渡时代的专制色彩,但“在晚清和民国的新闻制度建立中,作为制度选择,它本身保持了进步性,当时的法律和事实都可以证明,作为言论自由的一个基本制度形式,当时的民间报纸获得了合法的生存空间”[14]。二是“去价值化”。政府以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为职责,而在价值问题上保持中立与缄默,它不能也不应该干涉人的宗教信仰和道德选择。在中国新闻史上,官报“始于汉唐”,“历代因之”。官报为政府“价值偏好”之体现,政府创办官报,其目的在于传播符合政府价值偏好的符号,以建构利于政府执政的舆论环境。但这种“去价值化”的官僚型管理方式和军人对符号建构的漠视,造成了北洋时期官报式微、政党报纸消亡,而民报由此兴盛,成为报纸发展主流[2],并促成了五四时期思想文化大繁荣的局面。
需要说明的是,“传统型权威”、“法理型权威”是逻辑分析中的“理想型”。在现实政治运作中,北洋时期政治权威重建是错综复杂,彼此交错的,都会进行改造、调适和对其他权威路径的借用。因此,每一种权威建构路径都不会建立在某一理想类型之上,或者说任何国家权威建构路径都是这些理想类型的综合体。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不同权威建构的主导方面进行抽象和概括,以能更加清楚地理解这段历史。
三、结语
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是天命论,君主权威源自“天意”,“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天命论把合法性奠定在神秘之天意上,但天意无言,神秘莫测,任何人都可凭借暴力,“马上得天下”。不管是在夺权过程中还是在“得天下”以后,造反英雄和在位君主都知道利用传媒,强化言论控制,使天意之解释符合己意,将自己宣扬为“替天行道”的英雄和神意的体现者。近代中西交通,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天命论的不合理,中国当效法西方建立民主制度,政府之权力源于经过民众讨论同意之法律授权。这种法理型权威,将权利和民意设定为政治的合法性基础,且以“选票”这种可见形式予以实现,为权力转移创造了一种软着陆机制,由暴力政治走向民主政治,是中国权力转移和权威建构的范式革命。法理型权威强调法律和程序的神圣,任何矛盾必须在轨道之内求得解决。在这样的框架内,传媒成为表达各方观点和反映各方利益诉求的社会公器,各方在经过观点交锋和利益博弈后所达成的共识是整合社会,形成政治权威的基础。
在转型过程中,国家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是需要一定的社会准备条件的。如果没有强大的公共领域,在缺乏政治权威与基本政治认同条件的情况下,“众神并立”的意识形态争论就会造成各阶层的裂痕。现代传媒本是暴力政治的对立物,它呼唤国家统一,期待经由合法程序实现权力转移,并为之提供制度保障。但中国因民主协商资源稀缺,暴力往往是实现权力转移与权威重建的唯一手段。权力的获取方式会影响到权力的结构和特点,在权威建构路径与传媒形态之间存在深刻的关联。一般而言,依法律、程序而来的权威会支持开放多元的传媒架构,而以暴力夺取的权力则会寻求“言论听一”的新闻制度,以证明暴力的合法性。因此,与西方依靠市场经济来培育传媒的现代性因素、推动政治民主化不同,传统的暴力政治与专制政府才是中国传媒现代化的最大敌人,只有在权力破碎的缝隙之处,传媒才能呼吸到自由的空气。
[1]王润泽.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业及其现代化(1916-1928)[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吴廷俊.民报主流发展与职业报业启程:北洋政府时期新闻史重考[J].国际新闻界,2012,(8):115-122.
[3]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89.
[4]胡适.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N].努力周报,1922-09-10(2).
[5]吴长翼.八十三天皇帝梦[M].北京:文史出版社,1983:83.
[6]顾忠华.韦伯学说[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66.
[7]李俊领.仪式与“罪证”:1914年袁世凯的祭天典礼[J].扬州大学学报,2012,(1):104-109.
[8]李有泌.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8.
[9]杨度.君宪救国论[J].东方杂志,1915,(10):13-15.
[10]来新夏.北洋军阀史(上卷)[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315.
[11]李日.张宗昌的新闻观[N].杂文报,2009-01-23(2).
[12]徐宝璜.徐宝璜新闻学论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3.
[13]王开林.千秋白水文章[J].书屋,2005,(8):44-51.
[14]谢泳.历史困境中的记者命运[J].南风窗,2007,(18):88.
〔责任编辑:曹金钟 王 巍〕
G210
A
1000-8284(2015)01-0187-04
2014-12-09
湖南省教育规划课题“民国新闻教育思想研究”(湘教科规通[2014]006号)
阳海洪(1969-),男,湖南冷水江人,副教授,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访问学者,从事新闻史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