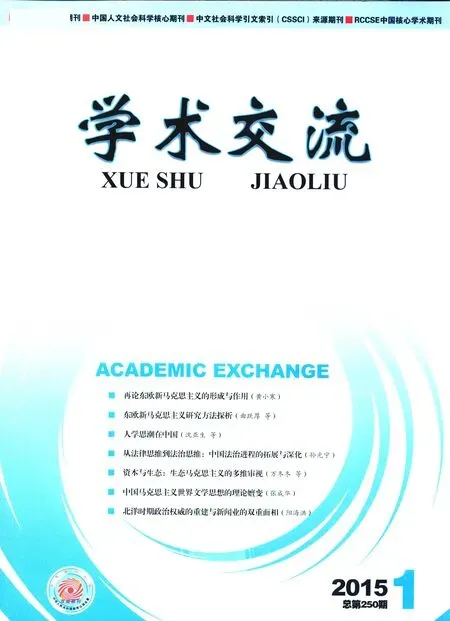资本与生态: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多维审视
万冬冬,王 平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
经济学研究
资本与生态: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多维审视
万冬冬,王 平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
奥康纳、福斯特、岩佐茂和伯克特等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阐发,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张性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着总体性的矛盾,资本与生态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资本逻辑与生活逻辑相对立,资本积累危机和人类社会发展危机是资本主义产生的两类环境危机。这些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进行多维度的生态批判和审视,对我们更深入地认识生态危机的根源和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资本逻辑;生态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多维审视
一、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
奥康纳通过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来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在生态方面的“理论空场”,并以此开启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存在着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且还存在着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他把这种矛盾称之为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张性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包括自然条件)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着总体性的矛盾,这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而且也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奥康纳指出,以前的社会主义者和非社会主义者之所以没有从总体上对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根本原因在于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作用,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在天亮的时候却折起了翅膀”的“密纳发的猫头鹰”。奥康纳认为,尽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但是他也注意到了自然系统在资本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重要性。奥康纳在马克思界定的三种不同的生产条件即“个人条件”、“自然条件”和“一般性的公共条件”的基础上加上一个“社会条件”。在他看来,只有从这些生产条件出发,我们才能真正揭开生态危机的“神秘面纱”。
资本主义生产以自然为基础,资本自我扩张的机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自然界的一个重要中介。“资本内嵌于自然过程之中,改变着自然规律及可能的发展趋势,或者在创造一种先前不存在的自然界之新形式和新关系的意义上改变着自然界。”[1]46资本的本性是增值和追逐最大化的利润,然而,自然界是无法进行无限的自我扩张的。这样,自然界本身的有限性与资本的无限扩张性之间就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商品化必然会导致人类与自然界的分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积累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
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主义从经济上对空间和外部自然界的占有和破坏。资本的不平衡发展和联合发展在空间上导致了全球范围的生态破坏。奥康纳明确指出,在过去的二百年间,北部国家即“第一世界”在享受财富增长的同时,南部国家即“第三世界”却遭受着严重的环境污染,成了“全球性种族屠杀”的最大牺牲者。“北部国家的高生活水平主要源于全球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可再生资源的减少以及对全球民众生存权利的剥夺。”[1]8特别是在21世纪的今天,“全球化资本扩大和加深了对人类和自然的控制”[1]246。资本的联合发展在不平衡发展所造成的影响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污染的程度、扩大了污染的范围。资本内部存在着许多矛盾,包括个体资本的利益与总体资本的利益之间的矛盾、个体资本的利益或不同资本的利益之间的矛盾、个体资本和总体资本的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之间的矛盾。资本的扩张逻辑及其内在矛盾造成了生产条件的破坏,并对其进一步的积累产生了限制。为了克服资本自身发展所受到的自然和社会限制,资本往往通过调整生产力条件和生产条件再生产的社会关系来重构自身。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资本进行重构只会加深而不会解决生态危机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破坏了其生产条件,它的“终结”是资本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此基础上,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孕育着社会的“反对力量”,这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奥康纳提出,必须放弃对“分配性正义”的追求,恢复对“生产性正义”的追求,使社会生产以使用价值而不是以交换价值为目的。奥康纳所设想的“生产性正义”的生态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在生态上合理而敏感的社会”[1]278。
二、资本与生态的矛盾不可调和
福斯特系统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认为资本与生态是相悖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全球性生态危机归咎于人性、现代性、工业主义或经济发展本身,它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对利润的无限追求必然会导致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只有进行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变掠夺式开发环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保护环境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内含扩张的逻辑,它以资本的形式积累财富为目的。在“利润之神”面前,一切环境保护行动都被资本视为必须克服的障碍。他以《京都议定书》的失败为例,说明了资本积累是如何阻止人类为解决环境问题而采取措施的。
在严峻的全球性生态危机面前,环境经济学家由于忽视资本主义的这一内在逻辑而提出了一些不合理的观点。福斯特对此一一进行了驳斥。首先,环境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非物质化”(dematerialization)将成为解决所有环境问题的“良药”。但是,在福斯特看来,试图通过经济的非物质化来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只是一个“危险的神话”。实际上,资本主义技术的进步在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的同时,也使经济规模日益膨胀,导致对自然资源需求的增加,陷入“杰文斯悖论”之中,从而给环境带来更大的破坏。其次,环境经济学家通过赋予自然以经济价值而将自然环境纳入到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福斯特认为,环境的破坏不能归咎于市场失灵,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制导致的后果。这种通过市场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方式比环境问题本身还要危险,因为它会使资本主义成为一种“生态帝国主义”。最后,环境经济学家提出用将生态价值与文化融为一体的道德革命来解决生态危机。福斯特认为,这种道德革命忽视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运行逻辑,它实质上是一种“更高的不道德”行为。
资本与生态之间之所以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是因为资本价值观的影响。福斯特从三个方面精辟地分析了资本价值观对生态的灾难性影响。第一,资本价值观派生出控制自然的世界观,这种观念使资本把自然视为一种外在的事物而毫无顾忌地对其进行掠夺,从而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第二,在资本价值观的统治之下,资本主义的技术进步在给生产力带来极大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第三,人在资本价值观的支配下异化成一种“机器”,盲目地追逐虚假的物质需求,导致大量消费物质和污染环境,并自己“吃下污染”。福斯特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我们想拯救地球,就必须超越资本主义的“生物圈文化”,“构建一种具有更广泛价值的新的社会体制”[2]。
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具有内在的反生态特征,它与生态的可持续性不相协调,它是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真正敌人。所以,为了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以更好地保护我们“脆弱的星球”,必须进行社会和生态革命,建立一种不是由追逐无限的利润而是由满足人类的真正需要所支配的社会。只有这种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拯救人类和自然界。
三、从资本逻辑到生活逻辑
日本学者岩佐茂从资本逻辑与生活逻辑的对立来剖析资本主义的环境问题,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资本逻辑占支配地位的社会,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活方式,正是这种方式造成了严重的环境破坏。为了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共存,从大量废弃型社会走向循环型社会,必须变革社会经济体制,把“硬途径”技术转变为“软途径”技术,废除资本逻辑,构筑一个基于生活逻辑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岩佐茂指出,20世纪是一个全球环境遭到破坏的世纪,以利润为目的的资本逻辑造成了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日本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爆发了产业公害。对于公害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体制造成了公害,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害是由技术的发展及工业化、城市化引起的。在岩佐茂看来,“与其说是技术的发展及工业化、城市化‘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公害,还不如说公害是由于只从追求利润的功利主义观点出发而采用新技术造成的”[3]19,资本的增值本性是引起公害的真正原因。岩佐茂认为,日本政府由于未能体悟到引起公害的这一本质原因而提出“每个人既是环境破坏的制造者又是受害者”,这实际上是一种“国民总责任论”,并且这会陷入道德主义之中,而这种道德主义难以解决环境破坏的问题。他以汽车尾气带来的大气污染和家庭垃圾问题为例,说明了不能简单地从资本主义的消费生活方式而必须从生产方式来考察资本主义的环境问题,因为消费生活方式从根本上来说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消费生活方式造成的环境破坏实质上是由生产方式造成的。所以,为了防止资本主义消费生活方式给环境造成“负荷”,必须把消费生活方式的变革与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统一起来,将现在的环境掠夺型的生产与消费体制转变成环境保全型的生产与消费体制。此外,岩佐茂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逻辑对环境的破坏与民主主义的成熟度也是密切相关的。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全球性环境问题,我们必须作出改变,变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活方式为有益于环境保全的生活方式。为了实现这种转变,“就必须构筑废除了资本逻辑的社会主义社会”[3]152。在这种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不是按照资本逻辑而是按照生活逻辑来进行的。以生活逻辑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生态社会主义,这种生态社会主义在超越资本主义“胎记”的基础上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
四、资本主义的两类环境危机
伯克特指出,马克思考察了由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两类环境危机,即资本积累危机和人类社会发展危机。资本主义环境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危机的一部分,而历史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两类环境危机,必须要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建立起共产主义的联合生产。
资本主义的第一类环境危机是资本积累危机,它是由资本生产的无限物质需求与原料生产的有限自然条件之间的不平衡造成的。伯克特认为,为了保持资本积累的持续,资本对原料的需求增加,因而对原料储备的需求也相应增加。物质需求量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在物质供应短缺或不确定时期,需要增加物质储备以及固定资本的无形损耗使个别企业加快固定资本储备的周转。资本为了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对自然物质的需求必然是无限增大的。所以,伯克特指出,资本本身的无限扩张性与有限的自然条件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第二类环境危机是人类社会发展危机,它的产生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空间结构即城乡产业分工扰乱了物质和生命力的循环,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这种危机是一种比由于原料供给中断而造成的资本积累危机更严重的危机。马克思从三个方面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是如何造成人类社会发展危机的。第一,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发展造成城市中工业和人口的大量聚集,这不仅破坏了自然环境,而且还对人类健康造成了危害。第二,伴随城市中工业和人口的大量聚集,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不断增加,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城市的环境。第三,资本主义工业城市与农业乡村之间的差别所造成的物质循环破坏了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
伯克特指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表现在“为利润而生产与为人类需要而生产之间的冲突,生产条件与生产者及其共同体之间的异化,以及社会化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4]178,它是造成资本积累危机和人类社会发展危机的根源。所以,为了解决资本主义产生的两类环境危机,实现更少限制、更新生态(pro-ecological)的人类发展,必须要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建立起共产主义的联合生产。
伯克特用七个生态标准来证明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代表了一种理想的社会形式。这些生态标准就是:认识到管理自然条件的社会责任、生态知识在生产者和共同体中的广泛传播、生态风险的规避、在全球范围内对人类的生态影响进行有效控制的社会合作、尊重人类多样化的生活方式、与自然条件相联系的生态伦理以及认识到财富观的亲生态定义。[4]240在伯克特看来,共产主义联合生产与这些生态标准是一致的。所以,伯克特强调,共产主义联合生产具有生态合理性。
五、结语
上述学者对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之间关系的阐发既有相同点,也存在差别。其相同之处:第一,以资本逻辑为主线展开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批判,指认资本逻辑是生态危机的根源;第二,从哲学、经济、文化和社会层面全面地批判和透视资本主义制度;第三,目的在于建构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其不同之处:第一,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具有两重矛盾和危机,而伯克特则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只有一个,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第二,在马克思与生态学之间的关系上,福斯特、岩佐茂和伯克特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本身内涵生态维度,马克思是一位生态学家,而奥康纳则认为马克思没有对生态问题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没有把生态问题看作由资本积累所造成的一个主要问题,马克思不是生态学家。第三,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具体设想不同。奥康纳通过赋予历史唯物主义以文化和自然维度,强调建构一种生产性正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福斯特通过进行生态革命来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岩佐茂通过构筑以生活逻辑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来设想生态社会主义,伯克特则通过自然的社会化来建构生态上合理的共产主义联合生产。相比奥康纳把生态运动纳入到生态社会主义的建构中,岩佐茂强调环境保全与发展人权相统一、环境影响评价立法化以及废弃物的减量、再使用和再生利用而言,福斯特和伯克特关于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的建构路径更多的是一种学理诉求,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第四,奥康纳和岩佐茂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比较温和,他们所要建构的实质上是一种改良型的生态社会主义,而福斯特和伯克特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要激进一些,革命型的生态社会主义是其理论旨趣。
但是,奥康纳、福斯特、岩佐茂和伯克特等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所做的生态批判也有其理论局限性。他们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认为生态危机已经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并否定资本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资本既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也是一个游荡在全世界的“幽灵”。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如何在利用资本和限制资本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以便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从而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抓手,这是一个重大而迫切的问题。奥康纳、福斯特、岩佐茂和伯克特等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进行的多维度的生态批判和审视,尽管在理论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它对我们更深入地认识生态危机的根源和建设“美丽中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James O’Connor.Natural Causes:Essays in Ecological Marxism[M].New York:The Guilford Press,1998.
[2]John Bellamy Foster.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02:59.
[3][日]岩佐茂.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M].韩立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4]Paul Burkett.Marx and Nature: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M].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9.
〔责任编辑:刘 阳〕
F032.1;F062.2
A
1000-8284(2015)01-0127-04
2014-08-0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的资本限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2CZX007)
万冬冬(1985-),男,江西南昌人,博士研究生,从事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王平(1958-),男,陕西耀州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