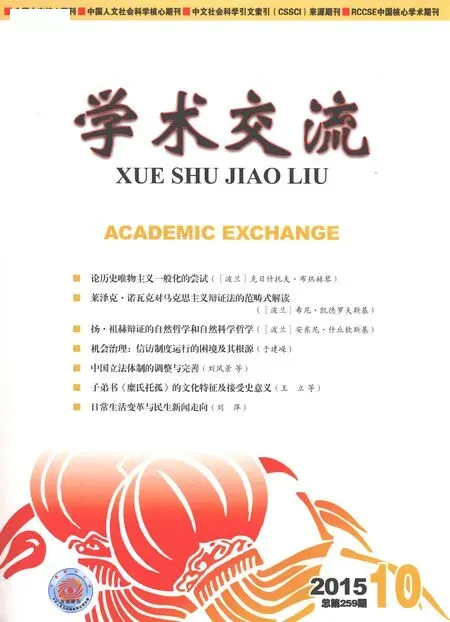俄罗斯文化中的深层结构特征及其理论旨趣
周来顺
(黑龙江大学 文化哲学研究中心,哈尔滨 150080;北京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北京 100089)
外国哲学研究
·俄罗斯哲学专题·
俄罗斯文化中的深层结构特征及其理论旨趣
周来顺
(黑龙江大学 文化哲学研究中心,哈尔滨 150080;北京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北京 100089)
文化作为一种无处不在的、历史凝结成的生存样式,总是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去塑造和引导着民族精神。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哲学家,对俄罗斯文化的深层结构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俄罗斯文化具有二元性、宗教性、精神性与使命意识等特征。白银时代哲学家对俄罗斯文化中深层结构特征的探讨,并非仅仅是作为思想家视野中一种纯粹的理论活动,而是聚焦在对俄罗斯现代化出路的理论探索上。他们力图通过对俄罗斯文化特征的探索,指明俄罗斯文化的特征及其限度,进而为俄罗斯现代化出路的探索提供理论参照。
俄罗斯文化;俄罗斯理念;现代化;宗教;文化
作为“思想中的时代”与“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既表征着时代性、民族性和个体性的理论诉求,也透视着民族性文化精神中的深层结构与理论内核。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弗兰克等为代表的白银时代哲学家创建的哲学体系,被认为是“最具俄国特色与气派的哲学体系”。白银时代哲学被誉为俄罗斯哲学史上的“黄金时代”,不仅在过去而且在当今俄罗斯学界都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并且这种影响在今天仍在发酵。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文化作为一种历史凝结成的生存方式及社会运行机制,具有人为性、群体性及超越性等特征,文化总是以一种潜在的方式影响和塑造着民族精神。白银时代哲学家从自身独特的哲学视角出发,对俄罗斯文化中的深层结构特征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种探讨并非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理论探索,而是聚焦于俄罗斯现代化出路的理论探索上。他们力图通过对俄罗斯文化中深层结构特征的分析来指明其特征与限度,从而为俄罗斯现代化出路的探索提供理论参照。
一、俄罗斯文化中的二元性结构
俄国著名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曾深刻地指出了一个国家的地理环境与文化因素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地理环境既是影响该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也是评述该国文化与精神气质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前提。而别尔嘉耶夫也同样深刻地洞察到俄罗斯的地理环境与文化因素之间的有机联系,指出“俄罗斯精神的景观与俄罗斯土地是一致的”[1]。尽管我们并不认同博丹、孟德斯鸠,包括克柳切夫斯基等人所持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观点,他们认为“自然界的作用是由各种各样的地理变化决定的:各个部分的人们在地球上占着不同的地区,自然界赐给他们不同数量的光、热、水、瘴气和疾病,赐给他们不同数量的恩惠和灾难,而人们的地区上的特点就是由这方面的不同所决定的,……这些东西显然是受周围自然界的影响而产生的,而这些东西的总和,就是我们所说的民族气质。因此,外面的自然界在历史生活中同样是作为一个有一定的人类社会生存的国家的自然条件来观察的,并且作为一种力量来观察,因为它对人们的生活和精神气质起着影响”[2]。当代俄罗斯哲学家沙波瓦洛夫也同样指出地理环境对俄罗斯民族心理与文化特征的影响,指出“自然条件(包括俄罗斯地理的特点)为民族心理的独特性创造了前提条件。但是,这一独特性要在高级文化产品中体现出来,显然还需要附加条件,要求个体付出努力,也即志向和意志”[3]70。俄罗斯独特的地理因素,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对俄罗斯文化的深层结构产生了影响,使俄罗斯在产生之初便在空间上面临着东西方的威胁与挤压。而这种由地理因素所带来的影响也反映在文化上,处于东西方交汇处的俄罗斯,其文化自产生之初便受到东西方文化的无形影响与熏陶。基于此独特的文化背景,我们看到在俄罗斯文化上呈现出独特的“二元性”结构。可以说,俄罗斯文化中的这种二元性结构,一方面体现了俄罗斯文化中的矛盾性与张力意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俄罗斯文化的两极化和复杂化,俄罗斯文化呈现出封闭与开放、单一与杂多、分裂与统一的相互交错与较力。可以说,俄罗斯文化中所呈现出的这种二元性结构,奠定了其文化特征的基本基调,并在其日常生活、社会习俗、民族性格、政治制度等方面得到了集中体现。
俄罗斯文化的二元性结构首先体现在民族性上,民族性的形成与该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基因密切相关,正是由“共同的文化基因,共同的文化遗产、共同的文化活动、共同的文化期望构成了民族的基础”[4]。无论是俄罗斯民族的国家观念、还是其对待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态度上,俄罗斯在文化结构中都呈现出了极为奇特的二元性结构。在国家观念上,一方面俄罗斯是最具个体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国家。我们看到,在俄国历史上不但作为社会精英阶层的政治家与思想家大多反对集权统治,崇尚我行我素的无政府主义与绝对的个体主义,作为社会底层的普遍民众也常常是不问政治,不去经营自己的土地。就此,别尔嘉耶夫很形象地指出俄罗斯的国家观念是女性的,俄罗斯在国家事务中永远期待着统治者、期待着新郎,俄罗斯的“‘土地辽阔而肥沃,但它没有秩序。’……俄罗斯是驯服的、女性的土地……俄罗斯人民希望成为一块待嫁的土地,等待着丈夫的到来”[5]5-6。另一方面,俄罗斯却又可能是世界上最具官僚化、集权化的国家,其在世界上建立了最庞大的国家机器,甚至运用一切手段、使用一切力量、付诸于全部血液去捍卫这一国家机器。在民族文化趋向性上,俄罗斯一方面是世界上最反对沙文主义、民族主义的国家,另一方面却又是世界上最具沙文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国家,它“以为自己是唯一负有使命而否定整个欧洲的国家,在它看来,欧洲已经腐化,是魔鬼的产物,注定应该毁灭”[5]9,而自身则负有用强力与残酷去解放其他民族的神圣使命。
白银时代哲学家认为,俄罗斯文化中的这种二元性结构也体现在文化发展规律上,既俄罗斯文化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中断性”与“连续性”始终交错并存的特征。可以说,俄罗斯文化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这种“中断性”“跳跃性”是贯穿始终的,而这一特征很难在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发展中寻觅到。俄罗斯文化在纵向发展的过程中总是毫无过渡地从一端跳到另一端,如从“罗斯受洗”前的多神教文化到东正教文化,从十月革命前的宗教文化到苏维埃时期的共产主义文化,无不集中体现出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极其鲜明的中断与跳跃性。一方面,俄罗斯文化在其发展中,“或者倒向一方,或者倒向它的对立面,没有任何渐进过程”[6],呈现出极强的断裂性与分散性。另一方面,俄罗斯文化又始终呈现为一个统一的、连续的文化整体现象而存在。在俄罗斯,新文化的产生并非意味着旧文化的彻底消亡,而是呈现出难以想象的并存,如在俄国文化发展史上呈现过“‘双重信仰’、‘双重思维’、‘双重影响’、‘双重感情’、‘两种文化’(贵族文化与平民文化)、甚至‘两个首都’(古罗斯时代是基辅和诺夫哥罗德,后来是莫斯科和彼得堡)和‘双头鹰’形象作为国徽等现象”[7]。对于这种奇异的文化现象,正如丘特切夫所言,无法用理智去衡量和把捉俄罗斯,对俄罗斯只能信仰。
在白银时代哲学家看来,俄罗斯文化中的这种二元性结构也体现在民族文化精神与对待土地的态度上。在民族文化精神上,俄罗斯是一个叩问神性之思,一个崇尚灵魂的燃烧与追寻精神的自由,一个流浪着追寻上帝的国家。但与此同时,俄罗斯又是一个不尊重个体自由与权力、压迫与奴性十足、怠惰与保守并存、沉浸于物质生活与繁文缛节的国家,以至于别尔嘉耶夫不无悲情地说“俄罗斯是那么滞重,那么懈怠,那么懒惰,那么沉溺于物质,那么苟安于自己的生活,简直无法挪移半点”[5]14。同样,在别尔嘉耶夫看来,俄罗斯从统治者、贵族、商人、知识层、伴侣、农民都不热衷于向精神高地的攀登与个性的觉醒,这种对待个性与精神的态度甚至在十月革命后也没有改变,革命后的俄罗斯依然是一个重集体主义而缺乏个体主义的国家。进而,这种二元性结构也反映在对待土地的态度上。一方面,基于俄罗斯贫瘠的土壤、漫长的霜冻期、恶劣的自然环境等因素,形成了索洛维约夫所言的俄国所独有的“液态因素”景观,即俄罗斯农民不断地迁徙、流动,俄罗斯农民就“像风滚草一样”(索洛维约夫)和“流动在沙漠中的沙子一样”(克柳切夫斯基)不断地开拓土地、安置家园,却又不断地从一个地方迁移另一个地方。俄罗斯人从来不会像其他民族那样管理土地,仿佛是土地的“异乡人”。但另一方面,俄罗斯人又最眷恋土地,甚至除了土地之处别无他求。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民族的发展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不断的征服与拓展领域的历史。这种扩张使俄罗斯从一个欧洲内陆国家最终发展为既有多个出海口,又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
正是基于此,白银时代哲学家指出:在俄罗斯,一切命题都会转向自身的反面,如从奴役到自由、从连续到中断、从民族主义到世界主义、从沙文主义到普济主义、从集权主义到无政府主义等。在对造成这种二元性文化结构原因的深层分析上,白银时代哲学家认为这与俄罗斯文化中“男性”与“女性”两种文化因素的不协调,特别是长期以来驯服的、柔弱的女性文化据于主导性因素密切相关。他们认为俄罗斯要想走出这种二元性、矛盾性、无出口的文化怪圈,只能向内在的、个体的、男性的精神性深度展开与发展,在控制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膨胀的同时促进男性意识的最终觉醒。而且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坚信,“目前这场世界大战将把俄罗斯引出没有出口的怪罪,惊醒它身上的男性精神,向世界展示俄罗斯的男性面庞,建立东欧与西欧应有的联系”[5]16。白银时代哲学家对俄罗斯文化中二元性结构及其破解出路的分析不无道理,而俄罗斯文化中体现出来的这种矛盾性、对抗性和背反性等特征,则是俄罗斯文化所具有的二元性深层结构的集中体现。
二、俄罗斯文化中的宗教意识
俄罗斯是一个有着强烈宗教关怀的民族,宗教文化渗透到民众生活的各个角落,在俄罗斯“没有一个题目比宗教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或者引起更热烈的讨论……在墓地、森林、火车站、市集、小酒馆,以及农民简陋的小屋里无拘无束地谈论宗教。……成千上万的朝圣者长途跋涉……。他们的谈话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有关上帝、拯救和永生这些永恒的问题”[8]。在白银时代哲学家看来,东正教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其对正统性与末世论观念的重视、对灵修与圣徒传统的强调、对神人性与神秘主义的理解等,无不渗透到俄罗斯的文化结构中,并长远地影响了俄罗斯的政治体制与民族性格等。著名学者弗洛罗夫斯基在《俄罗斯宗教哲学之路》一书中深刻地指认了罗斯受洗的巨大意义:“罗斯受洗是俄罗斯精神的觉醒,——是召唤她从‘富有诗意的’幻想走向精神清醒和深思熟虑。”[9]而沙波瓦洛夫也同样强调“罗斯受洗”及东正教对俄罗斯的独特历史作用,认为东正教“对俄国社会、文化以及俄国人的思想教育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他宗教。俄罗斯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与东正教教会及东正教教义有着必然联系。所以罗斯于988年接受基督教(罗斯受洗)的意义深远,已远远超出纯宗教的范畴,应将其视为人类文化和历史宏观领域的重大事件”[3]458。这也就是说,自公元988年“罗斯受洗”后,东正教的传入对俄罗斯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基于东正教传入后对俄罗斯政治体制、民族性格、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影响,决定了在俄罗斯文化结构中不可避免地、无处不在地呈现与弥漫着浓重的宗教精神。
首先,白银时代哲学家指出,俄罗斯文化结构中充盈着神圣意识。叶夫多基莫夫认为俄罗斯文化中的这种神圣意识与其宗教传统是密切相关的,俄罗斯文化就本质而言即是从宗教土壤中汲取营养而成长起来的文化。在叶夫多基莫夫看来,甚至连18世纪的各种反教会思潮和19世纪后半期兴起的各种空想社会主义、虚无主义等思潮,唯有从俄罗斯宗教传统出发才能理解。自公元988年“罗斯受洗”开启了自身的基督教化进程后,宗教思想渗透到俄罗斯社会的各个角落,既促进了俄罗斯文化精神的生成,同进也强化了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而与俄罗斯文化中这种神圣性密切相关的,便是俄罗斯文化中的苦难意识,对于这种苦难意识我们可以从俄罗斯圣像画中苦难的基督形象中得到体认。实则,俄罗斯当代文学家索尔仁尼琴就曾对俄罗斯文化中苦难意识与神圣意识有所论述,认为“俄罗斯文学总是面向受苦受难者”,“俄罗斯人民所信仰的是背负着十字架的苦难的基督”,认为在俄罗斯文学、艺术、音乐等领域都体现着这一特点。
其次,白银时代哲学家指出,俄罗斯文化结构中具有重精神性特征。俄罗斯文化具有崇尚理想与精神性价值、崇尚救世与普济主义、崇尚自我与利他主义的精神传统。这种对精神性原则的重视,从作为俄罗斯民族精神集中写照的知识分子身上得到了明显的体现,从公认为俄罗斯第一个知识分子的拉吉舍夫到民粹派的“到民间去运动”都充分体现了这种重精神性的取向。就整体而言,俄罗斯知识分子藐视物质生活而重视精神生活。当然,在对俄罗斯文化结构中重精神性原则的成因分析上,学者们认为这与俄罗斯的宗教传统相关,也与俄国社会中的集权统治与残酷迫害密不可分。布尔加科夫曾深刻地指出:“一方面源于统治阶层将知识分子与日常生活的强制性隔离,这种在培养了人的幻想能力的同时,进而也培养了人的温情的、乌托邦主义的精神取向,另一方面这种残酷的政治迫害也在他们身上逐步形成了受难与忏悔的思想意识。”[10]也正是基于对精神性特征的重视,使白银时代哲学家没有仅仅停留于对东正教经卷与原有文化的片面解读中,而是力图通过对传统资源与现代资源的有机吸收与融合基础上,来开新出对俄罗斯现代化出路探索的独特理论路径。
再次,白银时代哲学家指出,俄罗斯文化中具有平均主义的观念。俄罗斯文化中这种对平均主义观念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与俄罗斯长期存在的村社传统密切相关。我们看到,无论是斯拉夫主义、民粹主义、欧亚主义还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等思想流派,历来都有重视村社文化的传统。他们通常将村社文化赋予了田园诗式的理想化色彩,认为作为合理、规范、公正承载者的村社是俄国所特有的,是俄罗斯“活的灵魂”与“精神的起点”,认为在村社中体现与保存着俄罗斯原初的、公正的平均主义、平等主义观念。就村社的构成与运行机制来说,“是由生活在同一个区域、共同拥有土地的一个或几个村落的农民和城市的部分或全体居民,为着共同的利益而结成的社会联盟”[11]。村社是最基本的、独立的社会组织机构,生活在其中的人既要友好相处并服从于村社的管理,又要承担起自身的责任。就村社的运行模式来看,在村社中起主导作用的是长期沉淀的、无意识的历史传统,这其中包括成员间的相互依存、团结、尊敬、爱慕等。村社拥有从精神活动到文化活动,从日常生活到非日常生活,从规定收缴赋税、管理农田耕种到社会生活的多种职能,包括文化职能、经济职能、宗教职能、司法职能、保障职能等。正是基于村社的职能和特征,使俄罗斯众多的理论家与革命家对村社赋予了极大的期望,甚至“误认为俄国的落后恰恰是自身的优势所在,认为俄国可以依托原初的村社传统直接绕过西方资本主义的罪恶,进而进入到更好的社会制度之中”[12]102。我们从作为俄罗斯知识精英、实践家与民众所向往的村社文化传统中,从他们认为村社所特有的、保存完整的平均主义观念中,可见俄罗斯文化对平均主义的重视与期许。
此外,白银时代哲学家还指出,在俄罗斯文化中还存在着禁欲意识、苦难意识与罪感意识等,而这些特征的存在都与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传统直接相关。例如,俄罗斯知识分子常常持一种罪感意识,他们不仅向上帝,而且向社会、向民众忏悔,他们认为自身在民众面前是有罪的。在这种禁欲意识、苦难意识、罪感意识等的支配下,他们认为自身充当着“理念人”与民众利益“捍卫者”的角色。他们常常把维护民众利益、寻求社会正义作为压倒一切的“真理”而信仰,甚至当“真理”与民众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往往会因维护民众利益而舍弃与牺牲“真理”,源于在其看来之所以“需要真理,恰恰是为了将后者变成社会变革、民众利益和人类幸福的工具。……如果真理的毁灭能够给民众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人们的生活将更加幸福美满,那么就让它作出牺牲;如果真理妨碍了‘打倒专制制度’的神圣号召,那末就去打倒它”[13]。可以说,尽管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行为换来的常常是民众的不解甚至告发,但他们仍怀有一种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
三、俄罗斯文化中的使命意识
在对俄罗斯文化中的深层结构特征研究过程中,白银时代哲学家还指出俄罗斯文化具有强烈的使命意识。这种使命意识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在理论上塑造着该民族的文化精神与价值走向,另一方面,又在实践上导引着该民族的存在方式与实践取向。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俄罗斯文化中存在着的这种使命意识是贯穿于始终的。无论是在平民与贵族阶级的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知识分子的文学、艺术、哲学、宗教作品中,都涌动着强烈的末世意识、终极意识,认为俄罗斯民族是被赋予了伟大使命的终极性民族。我们看到,这种强烈的使命意识也在以恰达耶夫、基列耶夫斯基、特鲁别茨科伊、费多罗夫、布哈列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列昂季耶夫、索洛维约夫、梅烈日科夫斯基、维舍斯拉夫采夫、弗洛罗夫斯基等为代表的俄国知识分子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们无不追寻着终极性的真理,无不向往着天空、向往着远方,无不扮演着普遍拯救的“朝圣者”形象。同时,这种沉重的使命意识也表现在他们对他者的救赎意识上,他们认为俄罗斯民族不但赋有对自身,也赋有对其他民族的救赎使命。
在白银时代哲学家看来,俄罗斯文化中的使命意识与俄罗斯民族的自身遭遇及其危机意识是密切相关的。处于东西方交汇之处的俄罗斯,文明历程的形成相对较晚,是在“黄昏”时才起飞的,因而自产生之初即面临着东西方从文化到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碰撞和挤压。也正是基于这种独特的地理、文化位置和自身遭遇,使俄罗斯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与这种危机意识密切相关的使命意识与末世情结,为俄罗斯的自身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信念支撑与动力源泉。基于自身的独特遭遇与精神历险,俄罗斯认为自身与其他民族相比“是特殊的民族,是被赋予了特殊历史使命的民族”[11]36,甚至是“全人类最终文明的体现者”[14]122。他们认为,俄罗斯民族是神选的民族,是赋有神性的,担当着实现社会真理、人类友好和普世救赎的使命。与此密切相关,他们认为俄罗斯文化也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欧洲的特殊文化类型,并且是最高的、最优秀的和最完善的类型……认为这是独立的、在这一独立性上是高于欧洲的文化历史类型”[14]123-124。在白银时代哲学家看来,俄罗斯不仅在过去曾拯救东正教于危难之中,并将“第三罗马”屹立于莫斯科,使“双头鹰离开了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hore),展翅飞翔在俄罗斯广袤的草原上。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圆顶上已倒落的十字架又重新竖立在莫斯科圣母升天大教堂上,它今后成为全部东正教基督徒的普世教会圣庭”[15]38。而且,在现今的国际事务中,俄罗斯已展示出这种力量与使命,俄罗斯在军事、政治等方面也同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西欧各国仍是以一种歪曲、封闭、地方和落后的形象来指认俄罗斯,他们认为“俄罗斯还是完全不可知的,是某种异己的东方,时而以其神秘迷惑人,时而以其野蛮而令人厌恶……西方并没有感到,俄罗斯的精神力量可以决定和改变西方的精神生活”[5]2,在白银时代哲学家看来,西欧各国并不了解俄罗斯,甚至在他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的表面吸引与沉迷背后,也是带着一种猎奇“异国风味”的心态去阅读。而实则,俄罗斯是“东西方完整的结合体,是自成一体的完整世界。俄罗斯民族是蕴含着伟大力量的未来的民族……不但将解决西方无力解决的问题,甚至还将解决西方从精神深处都无力提出的问题”[12]73。他们认为,人们虽没有认知到俄罗斯所特有的精神和文化的力量与地位,但其精神与文化力量确实已在不断地、逐步地显现,最终会在世界历史的关键时刻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白银时代哲学家看来,俄罗斯文化结构中的这种使命意识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其对“俄罗斯理念”的追寻上。在俄国文化中,“俄罗斯理念”具有特殊的意义,有些学者甚至将其称为理解俄罗斯的“钥匙”。俄罗斯学者对于“俄罗斯理念”的内涵有多种理解,如А.И.阿列申在其主编的《俄罗斯哲学》词典中,从广义和狭义角度对“俄罗斯理念”进行了分析,认为在广义上“俄罗斯理念”是俄罗斯全部文化与精神特征的总和,而在狭义上则是指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发展到一定程度所达到的精神高度。又如俄罗斯当代著名哲学家А.В.古留加在《俄罗斯理论及其创造者》中同样从俄罗斯民族的终极使命角度来透视“俄罗斯理想”,指出“俄罗斯理念的核心是泛人类的爱,是兄弟情感,其与民族的终极使命密切相关”[16]。从总体上看,就理论来源来说,“俄罗斯理念”与东正教传统密切相关,可以说从11世纪伊拉利昂主教的《论教规与神恩》、12世纪编年史家涅斯托尔的《往年纪事》、15世纪菲洛泰修士提出的“莫斯科第三罗马”、16世纪宗主教尼康提出的“精神首席权”等著作与思想构成了“俄罗斯理念”的萌芽;就形成机制来说,“俄罗斯理念”代表着俄罗斯文化与精神的核心内核,是与俄罗斯民族的使命意识密切相关的,认为俄罗斯民族是赋有弥赛亚使命的民族;就理论特质来说,“俄罗斯理念”强调俄罗斯精神文化的独特性,强调其是不同于东西方两大文化类型的“第三种类型”;就终极指向来说,“俄罗斯理念”指向对人类理想社会图景的终极寻求,代表着一种共同的、理想的、公正的价值理念。
虽然历史上俄国众多的宗教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在自己的理论与实践主题中,都在一定程度上或隐或显地关涉到了“俄罗斯理念”问题,但“俄罗斯理念”作为一个独立的词汇被明确提出并得到广泛认同,则相对较晚,直到187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才明确提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强调“俄罗斯理念”是全人类共同联合的思想,应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界限。在此之后的索洛维约夫则对“俄罗斯理念”思想作了进一步推进,完全了其理论化、系统性、体系化的建构。索洛维约夫对“俄罗斯理念”的探索,源于对俄罗斯民族独特地位与使命的自我期许以及对时代性危机的深切认知,他认为面对着时代性危机和东西方教会各自的限度,俄罗斯不应在缄默不语和蒙蔽双眼中从事自己的历史事业,而是应该“参与普世教会的生命,参与伟大的基督教文明的发展,依据自己的力量和独特的天赋参与进来——任何民族的唯一真正的目的,唯一真正的使命,就在这里”[17]189。索洛维约夫认为俄国理论界应探索出“第三条道路”来克服这一危机,认为这一道路便是在“俄罗斯理念”指引下的实践路向。而且在索洛维约夫看来,“俄罗斯理念”并不是空洞、抽象的,而是具体、真实的。要真正认知“俄罗斯理念”就应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基督教理念为基准点,源于“俄罗斯理念”的进一步实践化“不可能在于放弃我们的洗礼。俄罗斯理念,俄罗斯的义务要求我们承认我们与普世的基督教大家庭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其伟大证明就在这里。因为真理只是善的形式,而善与嫉妒无缘。”[17]206俄罗斯民族的伟大使命就在于以基督教为根基实现教会间的联合,在这种联合中将不但实现教会间,而且将实现国家、社会、教会三者之间的统一,从而摆脱作为精神权力的教会与作为世俗权力的国家之间的对抗与危机。但在此需注意的是,这三者之间的统一并不是用一个因素去消灭另两个因素,而是一种有机的、绝对的、内在的、联系的统一。在索洛维约夫看来,“俄罗斯理念”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类似“神权政治社会”样态的理想社会图景,神权政治是神与人的因素的有机结合,“神权政治社会”则是由代表神人意志体现者的“先知权力”、代表神的因素的“祭司权力”、代表人的自由因素的“君王权力”三者间的有机统一所决定的。在这三者中,“先知权力”有其特殊的意义,源于“先知在神权政治中既是其组织的根源,又是其终结。它在一种意义上来说是第一权力和绝对权力,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只是第三权力,受其他两种权力的制约”[18]。
白银时代哲学家在对俄罗斯文化中的使命意识的进一步分析中,也特别强调和分析了“俄罗斯理念”的重大价值。他们甚至认为,“俄罗斯理念”中所富有的对理想社会图景的寻求与马克思主义学说具有共同的指向性,认为这正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接受、选择并实践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维度。例如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力图建构的“全人类联合体”思想与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比较性分析中,指出两者在终极目标上是一致的,都是力图建构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社会图景。而在对“俄罗斯理念”的实践化探索上,他们同样强调俄罗斯民族的使命意识,强调俄罗斯应摆脱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斯拉夫主义与西方主义之间的无谓论战,而应建构一种新的“俄罗斯理念”进而克服时代性危机。在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看来,这种新的“俄罗斯理念”应体现俄罗斯的弥赛亚主义使命意识。俄罗斯弥赛亚主义寻求的是将国家、民族、个体从物质的欲望与精神的桎梏中救赎出来。不但如此,在对“第三国际”产生机制的分析上,白银时代哲学家甚至认为“第三国际并不是一个超越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国际’,而是俄罗斯民族理念的翻版”[19]。总之,白银时代哲学家不仅指出了俄罗斯文化中呈现着强烈的使命意识,而且指出了“俄罗斯理念”是这种使命意识的集中表达。在他们看来,“俄罗斯理念”并非僵化、静止、不动的,而是以一种不断变换的姿态来适应时代发展,并为俄罗斯民族提供终极性的、实践化的价值支撑。
此外,白银时代哲学家还指出俄罗斯文化具有综合性、神秘性、苦难性、集体性等特征。而白银时代哲学家通过对俄罗斯文化结构的分析,并非仅仅要作某种纯粹的理论探讨,而是有着极其强烈的理论关怀与实践意向的。他们通过对俄罗斯文化结构的探索,力图指出俄罗斯文化中所蕴含的积极因素及其限度,以便为俄罗斯现代化出路的探索提供理论支撑。通过对俄罗斯文化结构的分析与探索,使白银时代哲学家清醒地意识到以东正教为根基的俄罗斯文化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与不合理性,并进而对之展开了深层的批判。但他们认为,在对俄罗斯现代化出路的理论探索过程中,仍不应对传统文化进行简单的、彻底的否定,因为俄罗斯文化及其未来既不可能建基于对西方文化的全盘吸收,也不可能建构于对传统文化的彻底舍弃。俄罗斯只有合理的吸收自身以东正教为理论底色的文化传统,并与现代西方文化进行某种有机的结合,才可能寻求到俄罗斯及其文化的未来。我们看到,白银时代哲学家在对俄罗斯现代化出路的探索过程中,也确实追寻着这样一条理论路径,他们在对以俄罗斯现代化出路为最终旨趣的理论探索中,始终格外注重民族文化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如何在既能保持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又能做到与现代文化因素进行有机的结合,进而避免自身民族文化根基的断裂与虚无主义的盛行,和由此所导致的一个“群魔乱舞的时代”的降临。
[1] [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M].邱运华,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3.
[2] [俄]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1卷)[M].张草纫,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8.
[3] [俄]沙波瓦洛夫.俄罗斯文明的起源与意义[M].胡学星,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4] Струве П Б.Patriotica:Политика,кулитура,религия,социализм[M].Москва,1997:66.
[5] [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M].汪剑钊,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6] 朱达秋,等.俄罗斯文化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34.
[7] 任光宣.俄罗斯文化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3.
[8] [俄]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M].高骅,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5-6.
[9] [俄]弗洛罗夫斯基.俄罗斯宗教哲学之路[M].吴安迪,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1.
[10] Булгаков С Н, и др.Вехи: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о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M]. Москва:Иэ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авда〉,1991:35.
[11] [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上卷)[M].张广翔,等,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445.
[12] Бердяев Н А. Русская идея[M]. Москва:ООО《Иэ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2004.
[13] [俄]基斯嘉柯夫斯基,等.路标集[M].彭甄,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7-8.
[14] [俄]索洛维约夫.俄罗斯与欧洲[M].徐凤林,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5] [俄]叶夫多基莫夫.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M].杨德友,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16] Гулыга А В.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и её творцы[M]. Москва:Иэдательство Соратник,1995:203.
[17] [俄]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M].张百春,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18] [俄]索洛维约夫.神权政治的历史和未来[M].钱一鹏,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19] Бердяев Н А.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M].Москва: ЗАО《Сварог и К》,1997:371.
〔责任编辑:余明全 曹 妍〕
2015-05-1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世纪初叶以来苏俄文化观的演变及其启示”(12CZX00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3批面上资助项目“现代性危机及其精神救赎——别尔嘉耶夫历史哲学思想研究”(2013M530554);黑龙江大学学科青年学术骨干百人支持计划项目“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思潮研究”
周来顺(1981-),男,黑龙江勃利人,副教授,博士,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俄罗斯哲学、文化哲学研究。
B512.5
A
1000-8284(2015)10-003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