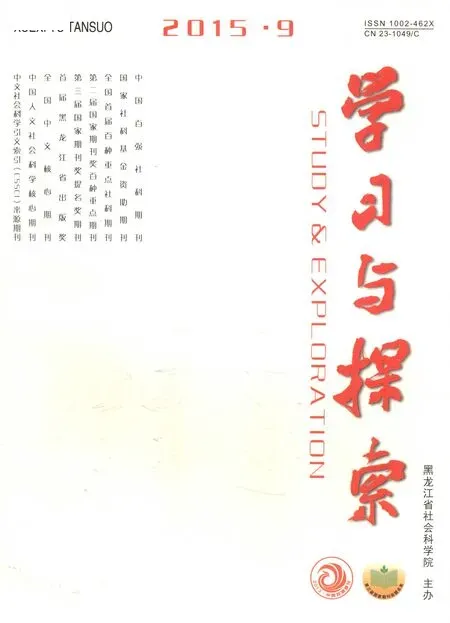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生成及其维度
梁 玉 水
(吉林大学 文学院,长春 130012)
·当代文艺理论与思潮新探索·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生成及其维度
梁 玉 水
(吉林大学 文学院,长春 130012)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始源于体验,奠基于反省,诉诸实践。体验的现代性批判、反省的现代性批判、实践的现代性批判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三个基本维度。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正是从以“诗意批判”为中心的体验的现代性批判出发,经由以“资本批判”为中心的现代性的反省,而最终诉诸以“现实的历史批判”为中心的实践的现代性批判。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问题的研究,应该从这三者所构成的“现代性问题关联域”中做整体性的把握。
体验;反省;实践;马克思;现代性批判
马克思的思想出场于“现代性”这一历史与问题语境中,“‘现代性’是真正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本性相适应的本源性的理论视域”[1]。只有在“现代性”视域中深入考察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历程和内在生成路径,我们才能更深刻地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形象,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当前,马克思哲学研究者紧紧抓住“资本”这个现代性社会的秘密症结,从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视角开展了富有深度的“资本批判”研究,认为“资本分析是现代性诊断的核心”,“正是通过对私有财产资本化及资本追逐剩余劳动的历史现实的分析,马克思深刻地揭示出现代社会异化劳动的根源”[2]。因而,对资本做现象学考察,解开“资本之谜”,就能断言资产阶级的命运和共产主义的前途,揭示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如此,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研究就集中在瓦解资本的逻辑、瓦解与资本联姻的现代理性形而上学这样一个经济学哲学问题上。然而,现代性作为一个“总问题”是复杂的、多层面的、多维度的,涉及诸如经济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学、艺术学等众多的“问题关联域”,现代性批判也应该是在多层面、多维度甚至多学科的联合并置中开展的富有建设性的批判研究。就“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这一问题研究而言,我们既要思考马克思为什么要批判现代性,也要把握马克思如何批判现代性,以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如何生成和建构等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在现代性总体历史语境中,结合马克思一生的思想发展历程,在马克思的精神发生学、精神现象学的意义上,基于人的情、知、意心理功能和结构层面,以诗歌、资本、历史为关键词,以体验的现代性批判、反省(或反思)的现代性批判、实践的现代性批判作为整体的、有机的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进路和维度,揭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始源于体验、奠基于反思、诉诸实践的内在路径,进而把握马克思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美学的、逻辑的、历史的生成,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和阐述马克思的思想贡献、哲学变革和“致力于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历史实践。
一、体验的现代性批判
“现代性”作为马克思思想研究的核心话语范畴,既体现在社会与历史的“现实”层面,表达“一个客观的历史巨变”[3]总序3;也体现在意识与哲学的“思想”层面,表征“属于哲学反思所把握的时代本质与精神”[4]37;同时,现代性又作为一个心理学范畴,体现在精神与心理的“经验”层面,表现“无数‘必须绝对地现代’的男男女女对这一巨变的特定体验”[3]3。这种特定的“体验”,也即现代性体验,它既包含着伯曼所强调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现代性氛围,也包含着“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异化”的现代性经验。以“感觉”和“体验”为中心所进行的现代性批判构成了马克思的“体验的现代性批判”。对马克思的“体验的现代性批判”所进行的考察,其意义在于,它是将马克思作为一个“感性地”“个体地”“历史地”“激情地”存在并生活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的“人”,而不是一个“无表情”“无面孔”的思想的机器。“体验的现代性批判”,就是“现代性体验”作为“现代性批判”,从而也就是对产生“现代性体验”的那个世界的反思和批判。以“感觉”为中心的现代性批判,就是要消除现代性社会中那种“非人”化的感觉,进而,也就是要消除那使人的感觉“非人”化的现代性社会,寻求现代性社会和人的“非人”化存在的“反题”,最终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成为富有“人性”的感觉。
在感觉的世界中、在感性的意义上所进行的现代性批判,是德国近现代思想史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传统,这个传统由卢梭、康德、歌德、费希特、谢林等一脉传承,最终在德意志浪漫派诗哲那里集大成为浪漫主义。由于这种浪漫主义最初表现为泛审美化的哲学,即一种以诗化形式出现的浪漫哲学,因而,也被称为“诗化哲学”。德意志浪漫派诗哲有感于人的感性世界和心灵世界的机械化、贫困化而对心灵、感觉、想象力加以凸显和强调,以对抗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现实存在的物质化、庸俗化、“散文化”状态。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认为,“不理解大抵根本不是缺乏理解力,而是缺乏想象力”[5]。即我们不理解一个东西,不是因为我们缺乏理智,而是由于缺乏感受。施勒格尔所表达的正是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显露的理性的抽象统治以及人的感觉世界的贫乏和了无生气,也即感觉世界的贫困和异化。文学艺术是时代的敏感神经,是“人”的感觉世界的活泼经验。米兰·昆德拉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曾说: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一个小说家,那他就不再是一个哲学家。“他只有作为小说家,才成其为伟大的思想家”[6]。正是小说家的感觉、体验、敏锐和洞察,才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够把握住世界的真相和存在的本质。换言之,如果马克思没有对现代社会敏锐的、深入的感觉和体验,也就不可能有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的自觉。德国的现实的状况不能不在感性的意义上、在感觉的世界中影响着少年、青年马克思,并形成马克思关于德国社会的最初世界图景,这种世界图景在“感觉”的意义上表现出人的不自由以及存在的压迫感、窒息感、抽象感、异化感。受到良好的文学熏陶,有着良好的文化修养的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受到了德国浪漫派的影响,并切身地感受到了这种存在的压迫和窒息,渴望着自由、自我、心灵和想象。年轻的马克思由此以浪漫派的文学手法试图表达自己对于现实世界的感觉与体验,创作出了为数不少的诗歌作品。并在诗歌中初步地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尽管是以诗意的形式而形成的诗意世界观。但从这些诗歌中已经可以看到,马克思所希冀以求的是——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感觉,并使人能够在历史的现实中真正配享人的感觉。即使在放弃诗歌写作和文学创作之后,马克思依然紧密关注着文学的现实,并从古典文学作品中汲取着文学的营养。作为人类审美精神、自由意识的集中表达的文学艺术,以其对现实的富有戏剧性的表现力洞若观火般地照亮着人类存在的戏剧,对于马克思而言,文学艺术乃是具有审美经验现象学意义的精神自我和精神武器,它培养、增进了马克思的感觉世界的敏锐和深度,表达着对现代性社会的“最初”批判。
到1844年的时候,马克思的思想已经能够以较为成熟的理论形态而获得表达,此时,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私有制的分析和批判成了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主题,马克思对感觉世界的异化所做的批判此时已经有了历史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基础。“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也只具有有限的意义。对于一个挨饿的人来说并不存在人的食物形式,而只有作为食物的抽象存在……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7]191-192马克思从经济学哲学的角度考察了人类感觉世界的发展和目前的异化状态,阐明了感觉与历史、现实的深刻的辩证关系,既揭示了感觉的“世界历史意义”,又揭示了作为现实的、历史的“感觉的状况”。对资本主义条件下贫穷的、忍饥挨饿的人,也即无产阶级的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状况做出了经济学哲学的分析和批判。正是基于感觉世界的异化所做的经济学哲学分析,使得马克思发现,无论对于资本家还是工人来说,他们的感觉世界都处于异化的状态中。而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形式,也即资本主义私有制。正是“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7]189。在私有制之下,人的一切感觉,包括肉体的感觉和精神的感觉,都被一种“拥有的感觉”所代替,这即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导致的感觉的异化。这种异化了的“感觉”与人所应有的主动的、自由的、享受的感觉是相悖的。对于感觉世界的异化的现代性诊断,最终归结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私有财产。马克思指出,只有消除这种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扬弃私有财产,人的感觉才能够真正成为人的感觉,感觉才会具有人性的色彩。“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7]190。通过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消除人的需要和享受的“利己主义性质”,使得自然界失去纯粹的有用性,物按照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也就使得人的感觉复归为人的感觉。这种扬弃私有财产的运动,在马克思看来,就是共产主义实践。正是在共产主义的扬弃私有财产的实践中,实现了人的感觉世界的人性的复归,感性和理性在实践中获得统一。共产主义就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也只有在这种私有制的扬弃之后,才能够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7]191。也即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本质力量。至此,马克思在体验的现代性批判层面上完成了对人的“感觉”世界的“异化”和“解放”的全部形而上学思考,完成了“感觉”世界的现代批判,即体验的现代性批判。
马克思对“感觉”的体验批判和形上思考,贯穿在马克思一生思想发展的始终。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就是使得人成为自由的、全面的、丰富的、发展的人,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感觉”,使“受动的”感觉变为“主动的”感觉,成为富有美学意味的“享受的”感觉。马克思的“体验的现代性批判”的指归是要实现人的感觉的“人性”,使真正的人的感觉——“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也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7]191——在现实的、历史的实践中丰富起来、发展起来。“体验的现代性批判”“感觉世界的人的复归”是马克思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维度——审美维度。“体验的现代性批判”是马克思的第一次现代性批判,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诗意的形态”,是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美学的完成”。
二、反省的现代性批判
以“感性”“感觉”的方式所进行的“现代性批判”是以“理性”的方式进行“反省的批判”的前提。随着马克思诗意世界观的扬弃和思想的深入发展,对现代性的批判也就从“体验”的批判进入到了更为自觉的“反省”的批判阶段,或者说从“体验的内省”进入到了“思想的反省”时期。当然,这两者并非截然对立、平行并置的,而是互相辩证、内在统一的。“体验的现代性批判”构筑着感觉世界的深度,并激发着关于现实社会及愿望图景的想象力,而“反省的现代性批判”又增进了对于现代性体验的理解,从而使得现代性的体验更加富有深刻性和切身性。“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8]。“反省的现代性批判”最终使得马克思在更深刻的、更现实的意义上确证并理解了在感觉世界中所感受着的、体验到的现代性,也在更科学的意义上论证了“人类解放何以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的“历史的”可能性和“实现的”现实性。在诗意世界观阶段中的现代性体验、感悟、感觉,最终在哲学的操作过程中获得了明晰化、概念化、思想化的形态。马克思的“反省的现代性批判”或现代性反省,主要包含着三个主要层面,即宗教批判、哲学批判和资本批判。
对于马克思而言,宗教的批判是当时德国思想解放和精神自由所必需的“实践的需要”。德国人“自己内心的僧侣”“自己的僧侣本性”,尚未得到批判和解放,因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7]3。宗教批判的意义在于确立“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真理。对宗教批判的需要,使得大批青年黑格尔分子退回到英国的经验主义和法国的唯物主义那里去获得宗教批判的思想资源,并最终与黑格尔的体系本身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并在费尔巴哈那里达到了峰顶。费尔巴哈在宗教现象学的意义上,使得神学的“人学秘密”被彻底揭穿了,并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了“哲学的王座”。但是,由于抽象的人学观和客体直观的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是不彻底的,他把人的本质归还给了人,但是只是归还给了“抽象的”“内在的”“无声的”人,他批判宗教和上帝,但是只是认为将上帝和人的关系颠倒过来就完成了批判,“就得到了真理的纯净光辉”[9]486。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批判地指出,费尔巴哈没有从“实践的方面”去理解人、事物和感性,也就“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7]499。因此,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只是一种理论的、抽象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对宗教的理论批判只是对那个产生宗教的苦难尘世的批判的“胚芽”而已,彻底地反宗教的斗争应该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7]3,就是要用“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用物质的、现实的力量“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7]11,这也就是马克思的“实践批判的”宗教批判观。
在1843—1845年这一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进行的工作主要是清算自己的哲学信仰,从而超越旧哲学,即以黑格尔哲学为“完成形态”的本体论思维方式的哲学以及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哲学;确立了新世界观,即从“市民社会”中寻找真理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实现了“实践的思维”方式的哲学变革,也进而完成了从“哲学反思”到“反思哲学”,从“哲学批判”到“批判哲学”的思想历程。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从而对“旧哲学”的批判是联系着神学的批判来完成的。在这方面,费尔巴哈给予马克思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恩格斯语)[10]4。正是费尔巴哈炸开了黑格尔的体系,揭穿了黑格尔哲学的神学性质。在《未来哲学原理》中,费尔巴哈指出“黑格尔哲学乃是转化为一种逻辑过程的神学史”[9]497,“在黑格尔哲学的最高原理中,已经有了他的宗教哲学的原理和结论……黑格尔辩证法的秘密,最后只归结到一点,就是:他用哲学否定了神学,然后又用神学否定了哲学”[9]494。费尔巴哈进而阐明了“新哲学”观,指出新哲学是恢复了“人的本质”的“光明正大的感性哲学。”[9]501但是费尔巴哈依然没有脱离开本体论思维方式的哲学禁锢,他依然为自己的哲学预设了一个先在的基点,寻找到了一个现实的“实体”——“现实的人”,但是对于这个“现实的人”,费尔巴哈没有把他当作“从事感性实践活动”并“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因而,费尔巴哈的“人”还是抽象的“人”,费尔巴哈的“物”“现实”“对象”还只是具有“感性直观”的有限意义。正是在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和“整个近代哲学”的批判基础上,马克思批判性地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和“历史”发展观念,扬弃了费尔巴哈的“人”学、“感性”学,最终确立了“现代唯物主义”,也即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这种新哲学是“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去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阐释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关系……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11]137而“正是在标志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的意义上,恩格斯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代唯物主义’,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11]137。马克思的“哲学批判”,也就从对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的反思和批判,转向了反思和批判哲学本身,这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哲学向世界观的转变”。“实践的思维”方式的哲学是“在实践中”“改变世界”以“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的哲学,而不是“在理论上”“解释世界”以“说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的哲学。正是在“实践的思维”的意义上,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区别于“纯粹的经院哲学”,区别于以往的“哲学”,并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502。
如果说哲学批判以及对哲学本身的批判为人类解放事业锻造了思想武器,那么,资本批判则使得这把思想之剑磨刀霍霍,新发于硎,成为插向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把淬火利刃。而哲学批判也为马克思展开资本批判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7]112马克思通过对费尔巴哈的人道或人本主义哲学的批判,使得抽象的人道或人本主义真正成了“现实的”人本主义、“历史的”人道主义。这也就为资本批判提供了哲学前提和“现实的人”的人学视域。《莱茵报》时期之后,马克思逐渐地发现无论是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对“现实物质利益”的考察,还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最后都会不约而同地聚焦在“资本”这个“现代社会”的内在灵魂和核心原则上。“资本乃是解开现代社会秘密的一把钥匙”[2],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隐秘症结所在,是“现代社会”建构的内在逻辑原则。不理解资本逻辑,就不能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不瓦解资本逻辑,就不能瓦解资本主义社会。因而,对资本的现代性批判也就构成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最重要的内容。对宗教、对哲学(理性形而上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最后都归结在对“现代资本”的批判之中。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是马克思反思资本主义经济事实和社会现实,探索人类解放的真实历史道路,即寻求“历史之谜”的最终解答的关键“现象”。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马克思通过“现象学”的“实践直观”而不是“朴素直观”,深刻地剖析了资本,揭开了资本背后的真实的“社会关系”和“历史关系”:指出资本的本质是“社会关系”而不是“物”,从而揭开了蒙在资本的“物”的现象背后的真实的剥削关系、奴役关系的面纱;指出资本的本质是“历史关系”,而不是“自然关系”,从而证明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方法绝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12],揭穿了资本主义温和的政治经济学关于“正义”和“劳动”自古以来就是唯一的致富手段的田园诗般的自然想象;指出资本的“物”的现象背后的“关系”终将成为“历史关系”,从而揭示了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宣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必将因资本的“逐利本性”“自噬本性”而被“世界性地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所扬弃的历史命运。现代性社会中的“宗教之谜”“哲学之谜”,最后的原因皆在“资本之谜”,“资本”作为现代社会的“症结”和“秘密”,成为马克思诊断现代性、理解现代性、反思现代性、重建现代性的枢纽和关键。
以“资本”批判为中心所进行的现代性批判,构成了马克思“反省的现代性批判”的主要内容。马克思扬弃诗意世界观、“转向现实本身寻求真理”所进行的“对尘世的批判”“对法的批判”“对政治的批判”乃至于“对哲学的批判”,最终都归结于对“资本”的批判。通过“反省的现代性批判”,马克思建立起了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论证了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完成了“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哲学革命,哲学从此成为“力求成为现实”的“为历史服务的哲学”。“反省的现代性批判”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思想的形态”和“逻辑的完成”。
三、实践的现代性批判
马克思通过“反思和诊断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和困境,透视繁荣辉煌的现代社会表象背后所蕴含的另一面”,揭示了“资本的升值与人的贬值之间的内在悖论、资本的命运与人的生存命运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1],从而完成了现代性的“病理学诊断”;马克思通过“对近代欧洲历史运动的细密分析,证明了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1],从而说明了现代性的“发生学原因”;马克思通过“论证处于资本全面宰制之中的现代性必然被一种更富人性的生活景象所代替,预言在一个全新的社会中,人的生命将从非人的资本力量的绝对掌握之中解放出来,实现总体性、整全性的生成”[1],从而完成了现代性的“未来学预言”,也就是马克思著名的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这种病理学、发生学、与未来学的现代性反省路径,形成了马克思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是现代性的批判性重建者。但是,反思的、反省的现代性批判,是马克思以“思想的武器”所进行的“理论的批判”,因而,毕竟还只是“解释世界”的现代性批判。这种“反省的现代性批判”的实践意义在于它对现代性“世界”,也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了深刻的、辩证的经济学哲学分析和社会历史学诊断,揭示了这个现代性世界的历史命运,从而使得现代性批判成了一个“改造世界”“人类解放”的“实践课题”。 现代性批判也就从“解放何以可能”的“人类解放理论”的探讨,转向“解放如何可能”的“人类解放道路”的探索。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出发,结合着对资本的剖析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发展规律的分析,描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的社会关系的演变形态,揭示了人类的解放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道路,也即从“人的依赖关系”形态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态,并最终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实现人的“自由的个性”和“全面的发展”。而超越“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扬弃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形态,最终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就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共产主义”方案。“共产主义”作为现代性批判,不是思想的批判,而是历史的批判、实践的批判;共产主义作为现代性批判的完成,不是思想的完成,而是历史的运动、实践的过程——“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7]539
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是有着多个层级的概念。它首先是一种意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段话表达了“共产主义意识”这一观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个阶级,这个阶级承担了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到社会的福利,并且被排斥于社会之外;“这个阶级构成了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7]542。这种“共产主义的意识”也可能在别的阶级中产生,“只要它们能够认识到这个阶级的状况”[7]542。这是一种具有“原始情感”“本能反抗”性质的共产主义,是一种改变现实的革命愿望;其次,“共产主义”是一种从抽象原则出发而产生的思想,一种如恩格斯所谈到的“哲学共产主义”思想。这种共产主义还没有站在新世界观的基地上,没有从“现实的人”和“历史的观点”出发,只是一种在思想中所实现和完成的革命,解放只是作为“思想中的解放”;最后,在最根本的、最实质的、最革命的意义上,共产主义是一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马克思说:“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7]231-232这种共产主义行动是一种“现实地”“扬弃私有财产”、实现“人类解放”的革命运动。这种“人类解放”不是一种思想活动、思想解放,而是一种历史活动、历史解放,是一种“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7]527的解放。这种解放的主体只能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之所以是共产主义革命和人类解放的历史主体,首先在于无产阶级的特殊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的被剥夺、被压迫的社会地位使得无产阶级表征着“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恢复到自己本身”[7]17。这个阶级所要求的不是“历史的权利”,而是要求“人的权利”;其次在于无产阶级的特殊的历史身份。无产阶级自身就是“社会解体”的结果,它之所以能够完成共产主义革命,消除一切异化劳动,是因为这个阶级“在社会上已经不算是一个阶级,它已经不被承认为一个阶级,它已经成为现今社会的一切阶级、民族等等的解体的表现”[7]543。正是无产阶级的这种社会历史性的属性,使得它不“消灭自己”,不“解放自己”,就不能“解放全人类”;使得它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消灭自己”,从而“解放自己”。
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指出解放只有依靠“群众”,依靠无产阶级,才能最终实现能够真正达到“人的高度的革命”[7]11,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是人类的解放,无产阶级就是革命的“被动因素”和“物质武器”。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批判的真正主体,就是无产阶级。“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在思想中扬弃私有财产”不等于“在现实中扬弃私有财产”,“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只有通过共产主义革命,以“物质的力量”为武器,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实现人类的解放,并最终“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7]46。因而,对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7]527。“使得现存世界革命化”就是要使现实在历史的发展中,越来越趋向于“思想”——这种“思想”也就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只有“现存世界”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革命化”——这种“革命化”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之间的矛盾的愈益“冲突化”、无产阶级与资本家斗争的愈益“普遍化”以及无产者之间关系的愈益“联合化”,这个时候,“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的革命才能必然发生。马克思说:“在我们的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个正在进行的自我扬弃的运动,在现实中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但是,历史最终将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行动。”[7]232这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就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真正转变和形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将产生“世界历史性”地联合起来的解放主体,即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最终,由这一世界性地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在“现代性”文明的地基上执行“现代性”的遗嘱,敞开通向共产主义道路的大门。人类解放及个人的全面、自由、个性发展最终得以可能。科学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最终方案,是围绕着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个性发展而做出的蓝图设计,其中内嵌着、深蕴着“美学的”“逻辑的”“实践的”基本维度。而对如何实现这一方案的回答,即马克思所说的以往的哲学都只是“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也就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实践的形态”和“历史的完成”。
毋庸置疑,“现代性”是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本性相适应的本源性的理论视域,剖析、诊断“现代性”的历史命运,肯定、继承“现代性”的历史成果,批判、扬弃“现代性”的历史形态,思考、发现人类解放的“现实性”的历史道路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基本关怀。以“现代性”为理论视域,考察作为“感性地”“历史地”“现实地”“激情地”存在于“现代性”社会中的“人”的马克思的思想演进和生成,可以发现,“科学共产主义”作为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体验现代性、诊断现代性、反省现代性、批判现代性,并最终超越现代性、重建现代性的现代性批判成果和现代性重建方案。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以及“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最终形成和最后实现乃是基于以下路径:始源于体验,奠基于反思,诉诸实践。以“现代性”批判与“人类解放”追求为中心,揭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基本维度,有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美学的、逻辑的、历史的生成,从而更深刻、更全面地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形象,理解和阐述马克思的思想贡献、哲学变革及“致力于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历史实践。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也只有更加全面地把握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和“现代性重建”的内涵及其维度,基于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个性发展的“现代性重建”及其历史实践才是真正有马克思主义内涵的伟大历史实践。而这对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和维度的理解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1] 贺来.“现代性”的反省与马克思哲学研究纵深推进的生长点[J].求是学刊,2005,(1).
[2] 俞吾金.资本诠释学——马克思考察、批判现代社会的独特路径[J].哲学研究,2007,(1).
[3] 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M].徐大建,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4] 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 施勒格尔.雅典娜神殿断片集[M].李伯杰,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64.
[6] 昆德拉 米.小说的艺术[M]. 孟湄,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75-76.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86.
[9]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66.
[11] 孙正聿.孙正聿哲学文集:哲学的目光[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21.
[责任编辑:修 磊]
2015-05-2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期文艺理论建设与文艺批评研究”(12&ZD013);吉林大学科学前沿与交叉学科创新项目“马克思现代性批判问题研究”(2014QY031);吉林大学青年学术骨干支持计划项目“马克思主义美学基本问题研究”(2015FRGG05)
梁玉水(1979—),男,讲师,哲学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美学与美育理论研究。
I0
A
1002-462X(2015)09-013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