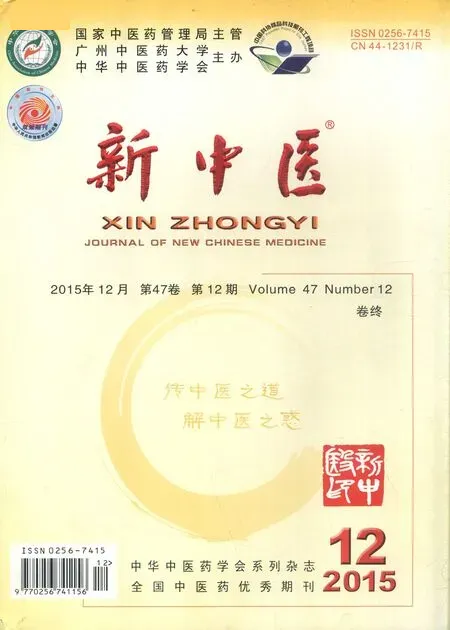儿童难治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治验1例
夏小军,段赟
1.甘肃省肿瘤医院,甘肃 兰州 730050;2.庆阳市中医医院,甘肃 庆阳 745000
儿童难治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治验1例
夏小军1,段赟2
1.甘肃省肿瘤医院,甘肃 兰州 730050;2.庆阳市中医医院,甘肃 庆阳 745000
紫癜;难治性;血小板减少;摄血汤
目前,国内尚无公认的慢性难治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Refractory Idiopathic Throm bocytopenic Purpura,RITP)的定义。有学者认为,由于脾脏切除术是迄今为止治疗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ITP)最有效和疗效最持久的治疗措施,因此,如果患者没有接受脾切除术,一般不将其归为RITP[1]。但基于当前我国较少实施脾脏切除术之现状,加之美罗华等一些行之有效的新药在国内推广与应用,所以有部分学者在RITP诊断或范围界定时不将脾脏切除作为必要条件[2~3];又基于脾脏切除对小儿损伤大,可并发血栓形成且脾脏切除后患儿血清IgM、外周血辅助性T细胞、抑制性T细胞(TH、TS)均显著低下,人体免疫功能明显下降,易发生凶险感染[4],故1986年全国小儿血液病会议拟定无脾切除术之规定的RITP诊断标准[5],在基层医院至今仍在沿用。笔者认为,以上均可为我国制定统一的RITP诊治指南提供有益的信息,脾切除术不一定作为诊断RITP的条件更符合我国现阶段的临床实际。本病例患者对糖皮质激素治疗无效,或激素依赖,血小板数量始终不在安全范围,虽未进行脾切除术,但实属难治,故诊断为RITP,既符合有关文献诊断标准,又是对疾病诊断要切合临床实际的一种探索。根据RITP以出血为主的临床表现,RITP可归属于中医学的血证、发斑、葡萄疫、肌衄等病证门类。对该病的中医或中西医结合治疗尚处于探索阶段,文献报道较少[6]。
1 病例简介
郭某,男,7岁,2008年5月16日就诊。患儿于2006 年11月6日因感冒发热,全身皮肤出现多处青紫斑点,伴发鼻衄,血小板计数(BPC)5×109/L,在当地医院诊断为“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ITP)、上呼吸道感染”,住院治疗5天后身热退,皮肤青紫斑点未见消退,仍鼻衄不止,BPC 3× 109/L,遂转往西安某医院,经血象、骨髓象、血小板抗体监测等检查,仍确诊为ITP。先后经住院及门诊予足量强的松,足疗程大剂量丙种球蛋白,标准剂量环磷酰胺等药物,其间多次输注血小板,治疗6月后皮肤青紫斑点减轻,偶发鼻衄,BPC始终在10×109/L以下。后又转辗多家医院多方治疗,仅在输注血小板后BPC可上升至(10~20)×109/L,约10天后又开始下降,且随着激素等药物的撤减,出血症状又明显加重。入院前3月以来强的松用量调整为30m g/d,分2次口服,静脉滴注丙种球蛋白12.5 g/d,每月连续输注5天,可勉强控制出血。入院5天前出血症状加重,BPC 6×109/L,故转入本院治疗。症见:形体虚胖,动则气怯,面色欠华,大如满月,两颧潮红,神情倦怠,少气懒言,烦躁汗出,食欲不振,咽干口燥,全身肌肤散在黯红色瘀点瘀斑,口腔及舌边尖各有血泡一处,双侧鼻腔时有渗血,色泽淡红,舌质红、苔少而干,脉细数。血象:BPC 5×109/L,血红蛋白(Hb)108 g/L,红细胞计数(RBC)4.0×1012/L,白细胞计数(WBC)4.6×109/L;骨髓象:增生活跃,粒红巨三系增生,全片共见巨核细胞146个,分类22个,可见幼稚巨核3个,成熟无血小板形成巨核16个,裸核3个,血小板罕见;生化全项:谷丙转氨酶57.8 U/L,谷草转氨酶 62.7 U/L,甘油三酯 1.92 mm ol/L,总胆固醇 6.7 mm ol/L;ANA抗体谱十五项测定:阴性;腹部B超提示大致正常。西医诊断:RITP。中医辨证:气阴两虚,虚火灼络之血证。根据中医辨证,拟益气养阴、滋阴降火、凉血止血之治法。处方:黄芪20 g,党参、当归、阿胶(烊化)、龟板胶(烊化)、麦冬、生地黄、旱莲草、紫草、焦三仙各10 g,墓头回、仙鹤草各15 g,甘草6 g。5剂,每天1剂,水煎服。强的松仍按原剂量服用。
2008年5月22日二诊:服药后鼻衄有所减轻,皮下青紫斑点新出者较少,精神略见好转。原方更进7剂,并停用丙种球蛋白。2008年6月1日三诊:仍偶发鼻衄,但可自止,口腔黏膜及舌边尖血泡消失,皮下青紫斑点明显减少,精神逐
渐好转,咽干口燥减轻,仍纳差,入夜腹胀,易感冒,舌质淡红、苔白微腻,脉细。辨证为气阴渐复,脾失健运之证。上方去龟板胶,加大腹皮10 g,砂仁6 g。每天1剂,水煎服。此后每周复诊1次,均以上方为基础方,偶有1~3味增减,或增减剂量,服用2月后出血已止,全身症状明显好转,BPC均持续在(5~10)×109/L。遂开始递减强的松,中药仍以上方为基础适量加减,每天1剂,水煎服。又守方加减服用2月余,未发出血,虚肿消失,未发感冒,2008年9月10日BPC上升至15×109/L。遂停用强的松,上方加减续服。
服用中药治疗半年,至2008年12月17日,BPC 14× 109/L,Hb 132 g/L,RBC 4.86×1012/L,WBC 5.6×109/L。患儿未发出血,体力恢复,纳食增进,舌质淡红、苔薄白,脉细。此时虽无明显症状,但BPC始终不上升,考虑患儿久病伤气,脾气更虚,且久病必瘀,因虚致瘀,故拟凉血活血、益气摄血、宁络消斑之法,用摄血汤(笔者验方)加减,以气血阴阳同调。处方:墓头回、白茅根、茜草、仙鹤草、黄芪各15 g,党参、当归、茯苓、白术、肉苁蓉、鸡血藤、生地黄、赤芍、牡丹皮、黄芩炭各10 g。每天1剂,水煎服。上方化裁服用3月余,至2009年3月20日,BPC上升至32×109/L,仍以上方为基础适当加减,或调整剂量,持续服用。2009年10月20日,BPC 48×109/L,开始上学。2010年7月12日,BPC 66×109/L,逐渐上升,疗效巩固。至2011年12月2日,BPC上升至82×109/L,期间偶因他因而致间断1~2天之外,均持续服用中药,均未发出血,亦很少感冒,更无任何不适及副作用发生。考虑疗效已显,改中药汤剂隔天1剂,水煎服。自2012年8月6日起,停用汤剂,改用院内中药制剂摄血丸(组成类同汤剂),每次1丸,每天2次,服用至今,BPC始终在(68~94)×109/L。
2 体会
本例患者,初次接诊,既有肌衄、鼻衄等标实见症,又有明显的气阴两虚之本虚表现,加之用药杂乱,则更耗气阴,故在维持原用糖皮质激素的基础上,选用大剂益气养阴、滋阴降火之品,合以凉血止血,以标本同治,急止其血。服药12剂,出血减轻,精神好转,知药中病机,效不更方。治疗2月余,虽BPC未见上升,但出血已止,诸症减轻,始递减激素。4月后诸症悉除,BPC略上升,遂停用激素,单纯中药治疗。半年后虽未发出血,但BPC未见上升,考虑久病脾虚血瘀作祟,故拟凉血活血、益气摄血之法,以宁络消斑。宁者,和也;此宁络即气血同治,阴阳同调之谓。服药3月余,BPC逐渐上升,开始上学,仍坚持治疗。3年后BPC接近正常,疗效已显,遂中药隔天服用1剂,8月后改服丸剂,以固疗效。
小儿脏腑娇嫩,形气未充,脾常不足。本例患儿,初诊时虽肌衄、鼻衄俱著,若单纯应用苦寒之品以凉血止血,则更伤脾胃,致使脾气更虚,摄血无力,出血不止;过早加用活血化瘀,又恐加重出血;一味益气养阴,则缓不应急,不能遏止病势。故临证辨证用药时,分清轻重缓急,注意本虚标实和疾病转归等,对于患者出血证的控制和临床疗效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7],即使BPC十分低下,中药止血之功亦勿容置疑。经有效治疗,出血未发,诸症减轻,似乎无证可辨,但BPC始终上升缓慢。然综合ITP之病机,不外热、虚、瘀三端。此时助火伤阴之激素已撤,机体气血阴阳仍处于不平衡之状态,若按常规单纯健脾益气摄血,则甘温之剂既有耗阴之弊,又有闭门留寇之虑,恐难一时取效。故宜气血阴阳同调,并适时加用活血化瘀,以祛瘀而生新,从而使BPC上升。本例患儿,病程较长,转辗多处,久治未愈,家长焦虑,病儿恐惑,无奈之下,求治于中医。曾建议住院治疗,但遭家长及患儿拒绝。对此,作为医者,首先应严密观察病情变化,权衡标本缓急,并耐心与患儿及其家长沟通,争取配合,并持之以恒,始可取效。该例患儿4年多来先后服用中药汤剂1300余剂便是明证。
[1]杨仁池.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治疗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J].国际输血及血液学杂志,2007,30(6):485.
[2]杨晓红,唐旭东,许勇钢,等.难治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患者免疫功能状态分析[J].浙江中西医结合杂志,2008,18(11):682.
[3]黄晓军,胡大一.血液内科[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259.
[4]赵东菊,张铭秋,杨瑞民.部分脾栓塞治疗儿童难治性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临床探讨[J].医师进修杂志:内科版,2004,27(9):40.
[5]杨天盈,张之南,郝玉书,等.临床血液学进展[M].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2:313.
[6]许亚梅,李冬云,陈信义.难治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中医治疗初探[J].北京教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1(2):31.
[7]胡令彦,周永明.周永明教授辨治出血性疾病的临床经验[J].西部中医药,2012,26(2):50.
(责任编辑:骆欢欢)
R249;R554+.6
B
0256-7415(2015)12-0273-02
10.13457/j.cnki.jncm.2015.12.121
2015-03-30
夏小军(1965-),男,主任医师,研究方向:血液病的中西医结合诊治。
段赟,E-mail:binbindua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