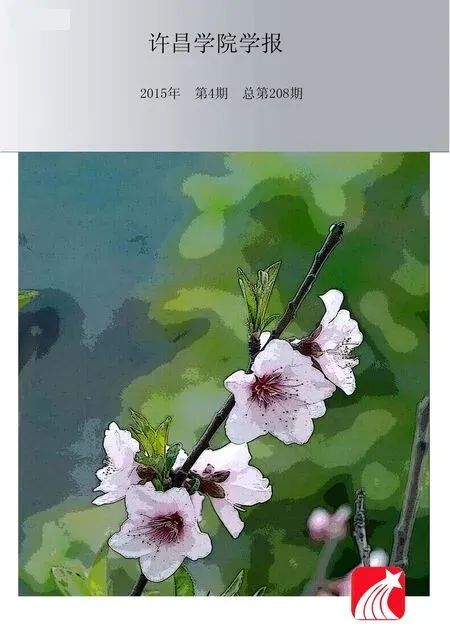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张爱玲的图像叙事
周 黎 燕
(浙江理工大学 文化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张爱玲的图像叙事
周 黎 燕
(浙江理工大学 文化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图文并置的用意在于形塑丰富的表意世界。张爱玲的图像叙事有五类,插图、封面画、扉页画、自绘像和照片。图像作为潜在的、隐性的艺术手段,成为文本叙事的扩张与隐喻,另一方面,图像为张爱玲提供了一方自我展演的舞台,以某一时空的定格永葆生命的真实与永恒。时间与空间、想象与直观的融汇为我们创设一幅景象绚丽的本文语境,从而在四十年代的十里洋场缔造了一个别具意味的文学场。
插图;封面画;照片;图像叙事
作为艺术的一个分类,文学叙事不是独立的,而是与戏剧、绘画、摄影等其他形式相生相成,以一种“改变世界的操练”实现“对现实的丑陋和重负的摆脱”,[1]284形塑丰富的表意世界。1994年6月,张爱玲的《对照记——看老照相簿》一书由台湾皇冠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文末她感慨往事如烟:“时间加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繁弦急管转入急管哀弦,急景凋年倒已经遥遥在望。一连串的蒙太奇,下接淡出。”[2]81作为被主体化的客体,图像是本文意义的表象或隐喻。在四十年代张爱玲“繁弦急管”的荣华盛年,图像叙事便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背景音乐,进而成为用以表达文学乃至个人诉求的有机部分。
张爱玲的图像叙事有五类,插图①本文插图均见于张爱玲相关文章初次刊发地《杂志》月刊。资料来源:上海图书馆近现代文献室。、封面画、扉页画、自绘像和照片。作为一种书籍艺术,插图并不是作品的图解,它不但具有绘画的品格,而且承担传情达意的叙事功能。鲁迅曾指出“书籍的插图,原意是在装饰书籍、增加读者兴趣的,但那力量,能补助文字之所不及,所以也是一种宣传画”,并且,它契合读者的阅读期待,“大众是要看的”。[3]故此,插图可呈现“方寸虽小,气魄极大”的气象,在予人艺术欣赏的同时,开拓文学叙事的空间,丰富读者的阅读感知。另一方面,绘制插图不仅需要生花妙笔,对于作品的准确解读更是重要前提。叶浅予曾指出:“给诗画配图,除了必须具有诗人的气质,还必须具有特殊的头脑,将意识形态翻译为抽象图像。”[4]26三十年代的叶浅予、梁白波、黄苗子等画家糅合西方现代派、抽象派和中国木刻、传统年画等风格,或恣意,或古朴,或谨严,为“新感觉派”配设了不少文画相谐的插图。

图1
“好的艺术原该唤起观众各个人的创造性,给人的不应当是纯粹被动的欣赏。”[5]193随着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第二炉香》的华丽登场,张爱玲开始挥洒自幼酷爱的画笔,为小说绘制插图,以激发读者“各个人的创造性”,让文学想象获取更丰盈的审美享受。张爱玲的插图既指向具体故事,又有超越具体所指的抽象性、普泛性内涵。她是一个对图像叙述有自觉意识的人,她的图不仅是文的附带———旨在释文,更是一种独立的叙事方式,她追求图像那种难以为文字所包含的意味。[6]就文中插图而言,大致有两类,一为开篇前山水、人物造型等配图,多为点缀。第二类为人物肖像,她不时用白描或漫画的笔法绘制人物形像。《花凋》中“郑先生与郑夫人”的插图笔法简练,形神兼具。一缕烟,一杯茶,胖胖的郑先生悠然而坐。消瘦的脸,尖尖的下巴上翘,郑夫人斜睥着倒梢眉,风吹起旗袍下摆一角(见图1)。这是一对视儿女婚姻为产业投资的夫妻。颇具意味的是,这帧插图显现了两种异质元素——郑先生与郑夫人的组合与关联。郑先生是放松的,肥胖的,任凭世事动荡仍可安享一口青烟;郑夫人则是紧张的,消瘦的,与这个世界是对立、冲突的,一如蓄溢着由于丈夫滥情生发的无尽愤懑。这种构图上的二元性与统一性预示了女儿川嫦的惨淡人生,因为不论紧张还是放松,郑先生与郑夫人在意的都是自己。眼见女儿病重、婚姻无望,他们互为推诿,弃之不顾,任其自生自灭。“花凋”之下,插图既写真又审丑,物质社会的炎凉世故、封建大家庭里的人情淡漠均可据此“迁想妙得”。[7]3

图2

图3
图像解读须放在历史的上下文中来展开,“如果把形象孤立起来,切断它所处身的前后关系,这些形象中没有哪个可以得到正确的解释”。[8]12张爱玲的插图,倘若单独地观赏,从美术的角度,构图、刀法、风格都未见独到之处,但联系着上下文展读,匠心立见。《茉莉香片》中的插图情境浮现,气韵流溢。小说讲述了一个弗洛伊德式的忧伤故事。聂传庆暗恋同学言丹朱,先母冯碧落恋人言子夜教授的爱女。传庆“纤柔”、阴郁,丹朱美丽、活泼。后来在羡慕、妒忌乃至憎厌的精神压迫下,聂传庆心生畸形,暴打丹朱以自我宣泄。当传庆在书房寻找当年言子夜赠冯碧落杂志所题手迹而不得时,曾陷入了对母亲的怀念与幻想。一个女人就是一个故事,“她在那里等候一个人,一个消息。她明知道消息是不会来的。”“前刘海长长地垂着,俯着头”,“青郁郁的眼与眉”,风吹袭她长而空的裙摆,纤弱的身子写满“昏暗的哀愁”。[9]聂传庆剪着手后立,垂目注视,目光所及是少女冯碧落,抑或她身后的那段二十多年的时空域地?这正是小说的精彩之处。因为在他看来,正是母亲当年的退缩导致他的人生错位,痛失为人敬仰的言家血统,跌落于颓唐的父亲与严苛的后母组成的家境。故此,聂传庆看冯碧落,既是观望,也是沉溺。二十岁的儿子与十七八岁的母亲前后并立,似近亦远,似真亦幻,前世与今生交织出一幅“参差对照”的景观。[10]而插图就配置在当年冯碧落与言子夜爱情图景的旁边(见图2)。情人之间,母子之间,这层层“浮世的悲欢”、隔空的哀怨如何化解?[11]凭谁说?图文并置令人恍然陷入小说的迷离之境。
就个体的人物肖像而言,《金锁记》里曹七巧的插图*有些作品,如《倾城之恋》中流苏、《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红玫瑰王娇蕊等人物画像,气象不大,多为自娱。1944年12月,散文集《流言》由五洲书报社初版,1945年1月,街灯出版社连续3版。书中收散文30篇,《风兜》、《青春》、《势利》等21个主题的手绘插图,以及照片三幅。这些插图与所选散文无关,多是围绕某一主题,或青春少女(《青春》),或大家闺秀(《大家闺秀》),或小市民(《小人物》),取材古今中外,发抒关于日常生活的讥诮或讽喻,穿行于散文之间,造就一份生动、活泼的意趣而已。最具人物精髓。作为“文坛的最美的收获”,[12]作为自陈小说中唯一“彻底”的人物,[13]曹七巧凝聚着张爱玲对于中国女性运命蹇怪的解剖与批判。关于曹七巧的容貌,文中并未细描,但插图神态毕现,呼之欲出,活画出叙述者眼里的曹二奶奶。出身麻油店的七巧虽算不上漂亮,但也五官端正,圆弧的前额、坚挺的鼻子和樱桃朱唇本可形构一张温柔的脸庞,但经受多年封建大家庭的人际历练,曹二奶奶长成了一双犀利的三角眼,一对高挑、坚硬的小山眉,拖曳出一股肃杀、凌厉而不可侵犯的傲慢气焰(见图3)。

图4

图5
而紧裹脖子、高高竖立的元高领如同曹二奶奶的心意告白。“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元宝领代表“歇斯底里的气氛”与身心分裂的“无均衡的性质”。在《更衣记》中,张爱玲阐释元宝领两度兴盛的浪潮及其历史意义。一为晚清西风东渐之际,元宝领“高得与鼻尖平行的硬领”“逼迫女人们伸长了脖子”,但“与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称,头重脚轻,无均衡的性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二是三十年代元宝领再度流行,“直挺挺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下面的丰柔的肉身”,“革命”加剧了女性的身心分裂,“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气”里飘荡着“讽刺”和“绝望后的狂笑”。[14]在曹家大院,既无西风侵袭,也未见“革命”兴起,但蛰伏在人性深处的金钱欲望是一把古老而沉重的枷锁。它是七巧们为自己落下的金锁,妖艳迷魅而终生无以挣脱。它消蚀了七巧浑圆的胳膊与热烈的爱情,陪葬了长白、长安们的青春活力。七巧挥舞“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四面割着人”,[15]而元宝领就是那一把锋利的刀片。图像具有提供最大视觉信息的能力,大众读者有时不一定深得小说的真味,但面对这帧形状乖张、意象突兀的人物肖像,“金锁”的意味终可觅得一二。
而张爱玲在书籍的装帧方面也用心颇深。装潢的优美,足以引起读书的兴趣。如果书籍的内容好,装潢又富于艺术的色彩,那就相得益彰,真令人有不忍释卷之感了。[16]551944年9月,小说集《传奇》出版,这是张爱玲一生的杰作。初版的封面是她自己设计的,整个一色的孔雀蓝,没有图案,只有黑色隶体字——书名和作者名,尽管浓稠得使人窒息,但放在五颜六色的报摊上,还是有一种视觉冲击力。4天后再版,张爱玲摒弃前作,采用了炎樱画的封面,以她最喜欢的蓝绿作底色,画面的内容十分饱满:“像古绸缎上盘了深色云头,又像黑压压涌起了一个潮头,轻轻落下许多嘈切嘁嚓的浪花。细看却是小的玉连环,有的三三两两勾搭住了,解不开;有的单独像月亮,自归自圆了;有的两个在一起,只淡淡地挨着一点,却已经事过境迁——用以代表书中人相互间的关系”。[5]205封面以“人相互间的关系”寄寓世俗人生的悲欢离合、聚散无常,而论者更是由此解读小说的文化地理学意义,“那蓝色决不是海,不为象征着汪洋,而是象征着陈腐的宝石蓝,我们的老祖母或其友人们所服御过,而今日尚保留在香港的门阀里面的衣服”。[17]不过,个中深意,读者实难揣摩。
对这个意象嘈杂而令人费解的封面,张爱玲终究不满意,1947年小说集《传奇》增订本出版之际,启用了第三个封面。仍由炎樱设计,借用了晚清吴友如所作《已永今夕》图(刊于《飞影阁画报》,1891年6月):“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望里窥视。如果这画面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见图4)”[18]2由于增设了“现代人”窥视的意象,这个封面意到笔随,运思、意境都获得论者的一致好评,以至于成为张氏小说的最佳注脚,颇具玩味。在幽灵般“现代”的压迫下,骨牌世界中的人们“忘却了时代,也被时代忘却,整个地封闭在旧的生活方式中,始终背向着时代盲目地挣扎”。[19]122封面俨然成为张爱玲其人其文的标志性图像。
如果说,插图、封面画多是为文而作,图像被视作一种潜在的、隐性的叙事手段,那么,扉页画则是杂志藉此走向读者、市场的重要窗口。它立足杂志的办刊理念,结合读者大众的审美情趣,以“文”外的图像方式表达杂志诉求,谋求艺术与市场的双赢效应。《杂志》是缔造张爱玲“传奇”的主打期刊,对此,张爱玲投桃报李,不仅提供稿源,而且多次为之绘制扉页,有《三月的风》(第13卷第1期)、《四月的暖和》(第13卷第2期)、《小暑取景》(第13卷第3期)、《等待着迟到的夏》(第13卷第4期)、《跋扈的夏》(第13卷第5期,同期刊有《诗与胡说》一文)、《新秋的贤妻:格个绒线,颜色倒蛮清爽》(第13卷第6期,同期刊有《忘不了的画》一文)、《听秋声》(第14卷第1期)7帧。从第13卷第1期至第14卷第1期,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随季节变迁,每期《杂志》都刊有张爱玲应时而作的扉页画。开卷即见,赫然在目,故此,张爱玲不仅散发出作为文学新星的熠熠光芒,也显示出一种顺手拈来的文人意趣,一份才女难得的生活情趣。如《新秋的贤妻:格个绒线,颜色倒蛮清爽》(见图5),秋意乍起,贤妻开始为家人准备御寒织线衣,颜色清新,恬淡素雅,更有殷殷暖意,体贴入怀,一如《杂志》对读者的温馨提示。
除了《杂志》,与张爱玲业务联系最多的就是苏青主编的月刊《天地》。《天地》封面时有张爱玲的手笔。该刊自1943午10月10日创办至1945年6月终刊,共出21期。张爱玲是供稿最多的作者,其中有16期都刊有文字作品,文章有《封锁》、《公寓生活记趣》、《道路以目》、《烬余录》、《谈女人》、《童言无忌》、《造人》、《打人》、《私语》、《中国人的宗教》、《谈跳舞》、《双声》、《我看苏青》、《“卷首玉照”及其他》14篇。据目前资料所及,张爱玲为《天地》设计了两幅封面。一为第11至14期的封面,一个女人平躺着,身穿旧式褂子,头戴簪子,远处泛着浮云。这基本是照搬高更的名画《永远不再》的思路,因为“曾经结结实实恋爱过,现在呢,永远不再了”,但“没有一点渣滓的悲哀,因为明净,是心平气和的”。另一幅封面设计也基本搬用原作。据考证,灵感可能来自法国画家亨利·卢梭的《睡眠中的吉人赛女郎》,[20]122“一个女人睡倒在沙漠里……中途累倒了。一层沙,一层天,人身上压着大自然的重量,沉重清净的睡,一点梦也不做”。[21]两帧封面都展露 “一种最原始的悲怆”。而张爱玲与苏青的关系复杂,并不如常人以为的文人相惜,不时推崇对方。*王一心认为张爱玲与苏青的关系很诡秘。碍于文友及与胡兰成的情感纠葛等因素,张爱玲看似推崇苏青,其实是“降贵纡尊”,“多的是示以关怀甚至提携”,并非尊敬。参阅王一心:《海上花开:民国上海四才女之苏青传》,第137~139页,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比较给《杂志》的原创作品,这两帧封面虽也属于“忘不了的画”,但思路、立意方面几无新意,相关文字全可从《忘不了的画》一文中见出。可见,张爱玲之于《天地》并不十分用心,在名人如流的《天地》上多露脸、扬声名恐怕是她作画的主要动机。

图6

图7
视觉印象具有唤起各种情感的力量。在贺拉斯看来,“心灵受耳朵的激励慢于受眼睛的激励”,换言之,有时舞台的影响力较之于文字叙述更直接、强烈,甚至左右人们的情感认知。鲜美的水果,富于挑逗的裸体,令人生厌的漫画以及使人毛发竖起的恐怖图画都影响着人们的情感,引起我们的注意。[22]170如果说插图、封面画、扉页画是文本叙事的扩张,那么自绘像则近乎自由、直接的个人秀。1944年张爱玲进入盛名时期,1月《万象》杂志开始连载其小说《连环套》。不曾料想,连载期间遭到傅雷(署名迅雨)的批责。在4月《万象》刊发的《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中,傅雷褒扬《金锁记》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但指出小说叙事模式化、主题单一化,以及《倾城之恋》耽于“顽皮而风雅的调情”、《连环套》“内容的贫乏”[12]等缺陷。次月,《杂志》旋即刊发胡兰成的评论《评张爱玲》一文,并配发自绘像一帧(见图6)。这可谓张爱玲“自己的文章”的图解版。画中的她烫发,身着西式束腰洋装,亭亭而立。因为以黑作底,虽面向读者而立,但看不到任何表情、神态,不过,刻意勾勒的脸部、洋装轮廓、体态线条等分外流畅、鲜明。这帧自绘像不乏写真,更有夸饰与想象的成分,线条的精心勾勒显然意在展示都市女作家的摩登范儿,黑底则标示一种岿然面对世人评议的孤傲,如论者所言,“她画别人,有点近漫画笔法,轮到画自己(或拍摄),知道自己并不美丽,注意的是风度,气质,不自觉地露出一副凄清的旷世才女相来。”[23]3
照片是一种奇特的媒介,一种新的幻觉形式:在感知的层面上是虚假的,在时间的层面上又是真实的。[24]309工业社会将其民众转化成形象的瘾君子。需要由照片来确证和美化经验,这是每个人如今都醉心的美学用户第一主义。[25]35张爱玲深谙乱世中的人们无意留心文学的兴衰哀荣,作品的畅销需要不断地制造亮点或卖点,以刺激读者的购买欲。作品集之所以有照片,她自陈为投合读者一窥真人的猎奇心理,“纸面上和我很熟悉的一些读者大约愿意看看我是什么样子,即使单行本里的文章都在杂志里谈到了,也许还是要买一本回去,那么我的书可以多销两本。我赚一点钱,可以彻底地休息几个月,写得少一点,好一点;这样当心我自己,我想是对的。”[26]声名鹊起之际,张爱玲频频亮相杂志,以视觉形象拓展文本叙事所不能抵达的空间。铸造摄影之特性的乃是姿势。[24]290她时而端庄,时而怅惘,时而低首垂眉,以丰富的肢体语言表达关于世事纷飞的万千心绪。1944年12月,散文集《流言》由上海五洲书报社初版,附照片三帧。一为仰头望上,似若有所虑;一为身着清朝大褂,依墙而立,图旁作先知式的预言:“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的。”第三帧则是青春飞扬的面部,眼神向侧面顾盼,下标一行文字(出自《〈传奇〉再版的话》一文):“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5]205这既是张氏“苍凉”美学的真人秀,也展现即使末世来临,我心安然的淡定与自得,因为其时张氏作品已然“像谣言传得快”,[27]1四十年代最华丽的海上传奇正“繁弦急管”般隆重开演。
对乱世的惶恐与自我的迷恋令人着迷于某一时刻的定格,以期永葆生命的真实与永恒。摄影的重要性在于准确及时地把某一个时刻记录为图像。按下快门就能捕捉到转瞬即逝的某一刻,这一刻虽然短暂,却最接近于对当下时刻的认识。[24]861945年7月21日《新中国报社》召开的纳凉会上的两帧合影则展现了张爱玲在镁光灯下的即时心理。一为金雄白、陈彬龢、陈女士、李香兰、张爱玲、炎樱、张女士的集体合影,一为《李香兰女士与张爱玲女士》的合影(见图7)。有意思的是,两帧合影中,都只有张爱玲一人端坐,或众人围聚,形成拱月之势,或名噪一时的亚洲影星李香兰盛装而依,“侍立一旁”。[2]58这既是杂志社运用视觉媒介的宣传与造势,缔造海上传奇的有意而为,也正合这位明星作家有意打造“看”与“被看”的心理诉求。说到底,神情也许是某种精神方面的东西,一种把生命的价值神秘地反映到脸上去的东西。[28]171她头微微低下,眼神朝下,“无视”正面的镜头,一副“自标高格”的模样,“就是清风明月,她觉得好像也不足以陪衬她似的”。[29]36
莱辛认为诗与画两种艺术关系紧密,“经常携手并行,诗人总是要向艺术家看齐,而艺术家也总是要向诗人看齐”,不过,诗终究胜于画,“有一些美是由诗随呼随来的而却不是画所能达到的;诗往往有很好的理由把非图画性的美看得比图画性的美更重要”。[30]51而贡布思希认为,“图像的真正价值在于它能够传达无法用其他代码表示的信息”。[22]175可见,诗与画两种艺术方式均有其独到而对方难以企及的空间所在。就绘画而言,张爱玲的画作多为人物素描,没有色彩,文化学意义的“画面的外延”也很稀薄,[28]39故应物象形、骨法用笔的格局不大;就文学而论,她的“苍凉”美学虽独树一帜,终究难以跻身大家行列。但是,张爱玲的绘画、影像与文学联袂而出,*1994年《对照记——看老照相簿》一书的出版再次应证张爱玲迷恋运用图像与文字自我展演的心理,以至于老之将至还翻检往事点滴,沉溺于岁月流散的华丽碎片,为后人预留一本个人传记的图本。时间与空间、想象与直观,表达形式的融汇为我们创设一幅景象绚丽的本文语境,从而在四十年代的十里洋场缔造了一个别具意味的文学场。
[1] 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论人的奴役与自由[M].张百春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2] 张爱玲.对照记——看老照相簿[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
[3] 鲁迅.“连环图画”辩护[J].文学月报,1932(4).
[4] 姜德明.插图拾翠:中国现代文学插图选[G].北京:三联书店,2000.
[5] 张爱玲.流言[M].上海:五洲书报社,1944.
[6] 姚玳玫.从吴友如到张爱玲: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海派媒体“仕女”插图的文化演绎[J].文艺研究,2007(1):134-146.
[7] 顾恺之.画品.孟兆臣校释[M].北京:北方文艺出版社,2005.
[8] E.H.贡布里希.象征的图像[M].杨思梁,范景中译.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0.
[9] 张爱玲.茉莉香片[J].杂志,1943,11(4)
[10]张爱玲.童言无忌[J].天地,1944(7、8).
[11]张爱玲.《太太万岁》题记[N],大公报(上海),1947年12月3日.
[12]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J].万象,1944,3(11).
[13]张爱玲.自己的文章[J].苦竹,1944(2).
[14]张爱玲.更衣记[J].天地,1943(3).
[15]张爱玲.金锁记[J].杂志,1943,12(2).
[16]申符.才子英年——谢六逸集[G].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
[17]柳雨生.说张爱玲[J].风雨谈,1944(15).
[18]张爱玲.传奇[M].上海:上海山河图书公司,1947.
[19]余彬.张爱玲传[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0]王一心.海上花开:民国上海四才女之苏青传[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21]张爱玲.忘不了的画[J].杂志,1945,13(6).
[22]E.H.贡布思希.图像与眼睛:图画再现心理学的再研究[M].范景中等译.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89.
[23]吴福辉.序.张爱玲散文全编[G].来凤仪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24]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视觉文化导论[M].倪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25]苏珊·桑塔格.论摄影[M].艾红华,毛建雄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
[26]张爱玲.“卷首玉照”及其他[J].天地,1945(17).
[27]张爱玲.红楼梦魇[M].台北:皇冠出版社,1977.
[28]罗兰·巴特.明室:摄影纵横谈[M].赵克非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29] 潘柳黛.记张爱玲.回望张爱玲[G].金宏达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30] 莱辛.拉奥孔[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责任编辑:石长平
2014-09-18
周黎燕(1970—),女,浙江诸暨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及传播。
I207
A
1671-9824(2015)04-007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