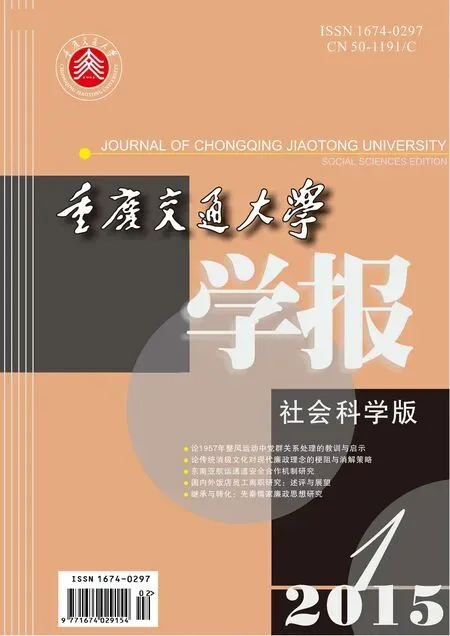释意理论对口译过程中无意语码转换现象的解构
高 博, 吴晓龙
(1.南开大学滨海学院公共外语教研室,天津300270;2.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300222)
一、引言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加强以及国际间交往活动的日益频繁,对于专业口译译员的需求量变得越来越多。如何提高口译教学水平,培养出高质量的口译人才,成为了各高校外语专业亟待解决的问题。然而,由于口译过程的复杂性和学生的差异性,教师在教授口译课程中通常会面临各种问题。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口译学习者尤其是口译初学者(通常为中英双语能力不平衡者)在口译过程中会不时地出现“无意语码转换”(unconscious codeswitching)现象[1]。这种现象不仅破坏了译语产出的连贯性,也损害了译语的交际意图。本文拟从语言转换的心理机制角度出发分析口译过程中无意语码转换现象产生的原因,并以释意理论为基础提出解决该问题的方法。
二、口译过程中的无意语码转换现象
(一)语码转换的定义及分类
语码指的是用来交际的符号系统,包括语言系统以及语言的各种变体,如方言、语体和语域等[2]。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是指在同一次对话或交谈中,说话者从使用一种语码转向另外一种语码,或从一种方言转换为另一种方言[3]。导致语码转换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如体现社会地位、顺应社会文化、表达特定情绪等。这些语码转换现象具有明显的社会意图和交际意图,属于“有意语码转换”。在很多情况下,一些语码转换现象的发生是由于二语习得者所持的双语能力不平衡,在话语产出过程中不能合理分配注意力,导致进行二语陈述时不自觉地使用母语或相反的情况。这些情况称之为“无意语码转换”现象。
(二)口译过程中无意语码转换现象的成因
1.英汉语言间的形式空缺
语言是一个民族集体智慧的体现,不同的语言反映了不同民族之间独特的社会行为和思维方式。英语和汉语之间有着异质性(heterology)的差异,这种巨大的差异体现在语言层面上,表现为英汉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着大量的不对等、甚至不存在的词或结构,因此,在两种语言的转换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词汇或句法上的“形式空缺”[4]。我们发现在实际口译教学过程中,由于受到单位翻译时间和工作记忆容量的双重压力,学生在处理目的语和源语间“形式空缺”时,会无意识地选择母语来填补语言空隙。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例如学生将“豆腐渣工程”音译为“Dou Fu Zha Projects”。“豆腐渣工程”是汉语中特有的表达方式,用来形容质量较差的工程或设施。在口译过程中,由于找不到与其直接对应的英文表达方式,在有限的翻译时间内学生会不自觉地搁置源语中特有的词汇,形成无意语码转换。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现象对于双语能力不平衡的口译初学者来讲尤为明显,说明无意语码转换现象的出现频率与译者的目的语水平密切相关[5]。
2.话语标记语的无意语码转换
Schiffrin认为,“话语标记语(discourse marker)是一整套的多功能词汇,包括连词、感叹词、副词以及短语,而它们的具体功能则主要在于限制话语的构建及理解,具有表达和概念的功能,但不表示真实条件。”[6]这说明话语标记语担负着重要的交际功能,这种交际功能必须在一定的语境条件下才能实现。冉永平以汉语话语标记语“你看”为例,旨在说明翻译过程中话语标记语对语境的依存性[4]:
(a)“我这副手套多少钱买的呢?你看,就一转身,我忘了!”
(b)“你和他赌个什么气?你看,你现在是公司里最年轻的科长,可别拿前途开玩笑!”
(c)“他办事情可真叫个利索。你看,才多大会功夫,一桌饭菜就端上来了!”
上例中,话语标记语“你看”显然不能全部直译为“you see”,结合上下文语境及其话语功能,应将3个例句中的“你看”分别译为“Alas”,“After all”和“Look”。这些例句清晰地表明,在翻译话语标记语时,译者不能只将注意力集中在语言形式上,更重要的是以语境为基础挖掘语言形式背后隐含的语用信息。对于口译初学者来讲,由于对文本的语言形式和字面语意的过度依赖以及受到工作记忆容量的限制,在对包含具有话语标记语的长语轮(long turn)进行口译时,译者在理解源语过程中往往出现语意缺失,这种缺失严重破坏了源语语境,进而影响译者对源语中话语标记语的理解。在对大量口译初学者进行观察后,笔者发现,由于缺乏对源语语境全面的理解,译者在翻译话语标记语时通常采用以下三种方式:(1)漏译。即不译源语中的话语标记语。(2)直译。不考虑语境,将源语中的话语标记语直接转换为相应的译入语。(3)无意语码转换。迫于翻译时间的压力,译者来不及分配注意力资源去考虑语境,在翻译成品中无意识地保留了源语中的话语标记语,形成无意语码转换。
3.词汇的可及性程度
所谓词汇的可及性程度(availability of vocabulary)指的是在词汇的产生和理解过程中,从大脑记忆系统中提取某个语言或记忆单位的便捷或难易程度[7]。这种词汇可及性程度通常被视为诱发无意语码转换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观察操阿拉伯语和法语的摩洛哥人在谈论某个话题时不断发生的语码转换现象,Bentahila发现这些语码转换者对于两种语言中合适的词汇都有所了解[8]。据此,他提出了可能导致此类语码转换的两点重要原因:一是对于这些双语者来讲,某一种语言使用起来更加方便;二是某一种语言里的词汇比另一种语言里的词汇更加容易回忆起来。受到词汇可及性程度的影响,双语能力不平衡的译者在口译过程中通常会选择使用自己较为熟悉一方的语言表达方式来对源语进行阐释,导致译者在译文中无意地保留了源语的表达方式,造成译文的双语码现象。通过教学实践,笔者发现这种转码现象更多地发生于英译汉方向,且多数转码词汇为学生较为熟悉的术语或缩略语。例如:
原文:The GATT dealt with trade in goods.The WTO covers service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 well.
译文:GATT管的是货物贸易,WTO管的是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
上例中,译者没有将GATT、WTO译为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关贸总协定)及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而是保留了源语的英文形式。这是因为在口译过程中,译者更加倾向于选择自己认为最方便的语言形式对源语进行记忆,以上两词的英文表现形式明显比汉语简洁。因此在单位翻译工作时间的压力作用下,译者无意识地保留了源语的形式,形成了无意语码转换。
三、释意理论对无意语码转换现象的解构
(一)释意学派的翻译观
释意学派认为翻译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词义层次、话语层次和篇章层次。词义层次为非语言使用层次,该层次的翻译是指机械地翻译词的本义,即逐字翻译,其结果是简单的词语对应;话语层次指翻译话语的语义含义,是脱离语境和交际环境的句子翻译;篇章层次指的是翻译语言含义和认知知识结合产生的意义[9]。释意学派将篇章层次的翻译视为己任,指出释意的本质就是对篇章的深刻理解和清晰表述。他们认为翻译的对象不是语言,而是借助语言表达的意义[10]。为了理解语篇的篇章含义,释意学派要求译者将翻译看作一种交际行为,这种行为不仅包括译者对语言的转换,还需要译者调动自身的认知知识及百科知识等非语言因素对源语进行有效的补充。与其它翻译学派相比,释意学派更加强调交际主体及其认知作用,其研究过程带有更强的动态性。
释意学派认为两种语言间的转换不是单纯的语言代码转换,而是意义(sense)的翻译。意义的产生和提取需要经历一个特殊的阶段——“脱离语言外壳(deverbalisation)”阶段。这个阶段是指理解一篇文章或一段讲话和用另一种语言重新表达的一个阶段,指伴随语言符号产生的认知和情感意义,是对语言符号的超越[11]。释意理论认为只有在脱离语言外壳之后,意义才能保存下来。成功的口译应该达到意义上的对等,而不是语言层面上的对等。通过对口译过程的研究,勒代雷发现译者会将每一间隔听到的字词归纳成意义,然后将字词的语言含义和自身认知补充,结合成意义单位。意义单位会在译者脑中交迭出现,形成整体意义[12]。
(二)释意理论对无意语码转换现象的解构和启示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释意学派将意义视为翻译的主要对象。这就要求译者必须专注于语言形式背后的意义,而不是语言本身。由于口语表达具有瞬时消失的特点以及译者自身受到短期记忆容量的限制,译者在口译过程中通常需要通过笔记的方式存储信息。然而,译者不能完全记录讲话人所讲的全部内容,只有依靠调动自身语言外的知识边听边分析,才能将源语所要表达的关键信息和话语逻辑用简短的字词符号记录下来。此后,译者需要对所做笔记内容进行解读,尽量忠实地传达出源语所要表达的意义和情感,而不是简单地进行语言代码的转换。
以释意理论为指导,教师应该引导口译学员摆脱源语语言形式的束缚,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到提取源语的意义中来。在容易引起学生口译过程中产生语码转换的语言点上,教师应该积极调动学生启用自身认知知识和百科常识等非语言因素对源语内容进行释意。例如,在处理一些不熟悉的科技或文学专用词汇上,译员可以通过使用已知的由同行业专家建立的同一主题的对应词对源语进行解释[10]38-39;针对英汉两种语言中的形式空缺,译者可以采用“加注”的翻译方法,即进一步阐释源语中特有的表达方式,避免产生无意语码的转换。
此外,释意理论改变了传统口译中关于“等值”的观念,它将口译过程中完成的“等值”分为两步:“即在理想的交际状况中,译者要首先完成理解的意义与原作者的欲言之间的对等;接着,他还要完成借助他的重新表达手段,原作作者所理解的意义与译文所理解的意义之间的对等”[13]。对口译教学而言,正是这种对“等值”的特殊理解以及对“意义”的强调,解放了译者对源语语言形式的过度依赖,有效地减少了口译初学者在口译过程中无意语码转换现象的发生频率。
四、结语
释意理论的提出是口译理论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对口译教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核心观点——“释意”及“脱离语言外壳”从根本上改变了口译学习者尤其是初学者在口译过程中对源语语言形式过度关注的思维习惯,避免了由此带来的无意语码转换现象。可见,释意理论对口译实践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因此,口译教师应该进一步挖掘和丰富释意理论,使其具有更强的理论延伸性和实践指导意义,为口译实践和教学做出更大的贡献。
[1]顾韵.学生口头报告中无意语码转换现象分析[J].国外外语教学,2004(4):32-36.
[2]Waudhaugh R.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M].3rd ed..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 Ltd,1998.
[3]Scotton C M,Ury W.Bilingual strategies:The social function of code-switching[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1997(13):7-19.
[4]冉永平.翻译中的信息空缺、语境补缺及语用充实[J].外国语,2006(6):58-65.
[5]Poulisse N,Bongaerts T.First language use in second language production[J].Applied Linguistics,1994(15):36-53.
[6]Schiffrin D.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M].Rev.Massachusetts:Hamilton Blackwell Publishers,2001.
[7]谢亚军.可及性:英语指称词语表达的认知阐释[J].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5):73-76.
[8]Bentahila A.Motivations for code-switching among Arabic-French bilinguals in Moroco[J].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1983(3):93-118.
[9]龚龙生.从释意理论看口译研究[J].中国外语,2008(2):80-84.
[10]勒代雷.释意学派口笔译理论[M].刘和平,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1.
[11]许钧.翻译释意理论辩——与塞莱斯科维奇教授谈翻译[J].中国翻译,1998(1):9-13.
[12]高彬,柴明颎.释意理论的历史性解读[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3):72-76.
[13]袁筱.论释意理论的忠实概念[J].外语研究,1997(3):4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