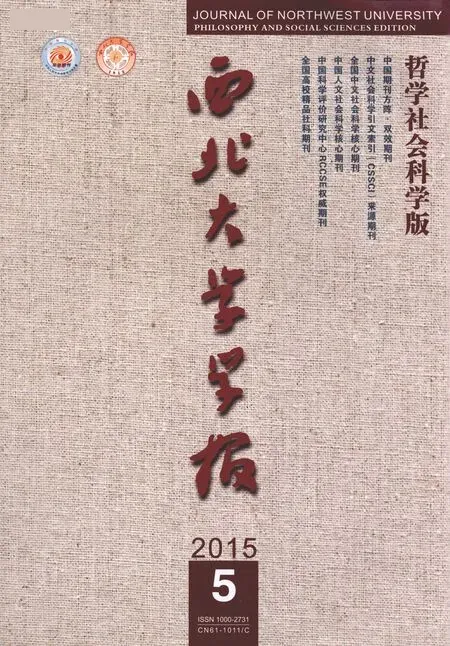火色生情
———论中国文学中“火”意象的文化内涵和生命精神
邱晓(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069)
火色生情
———论中国文学中“火”意象的文化内涵和生命精神
邱晓
(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9)
摘要:中国文学中的“火”意象是一个充满了诗意想象的文化意象和生命意象,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特殊的生命精神。一方面,它是宇宙元素和生命能量的象征;另一方面,它是爱情的象征。从文化内涵和生命精神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学中的“火”意象,是为摆脱当今文学研究中技术化和实证化弊端的一个努力。
关键词:“火”意象;宇宙元素;生命能量;爱情象征
事物一旦进入人类的视野,就再不是纯粹的自然事物了,人类的智慧和文化总要赋予它一定的意义,即如“火(燃烧)”这种原本是自然界产生的化学现象,在被人类认识、掌握和利用的同时,也被附加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人们用智慧研究它,用生命感受它,用艺术赞美它。于是,火,不仅是一个自然物象,还是深具文化内涵和生命精神的文学意象。当然,不同的民族和时代赋予火以不同的文化内涵和生命精神,创造不同的火的文学形象,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就中国文学中的“火”意象作一番初步考察。
一、作为宇宙元素和生命能量的“火”
虽然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明确宣称宇宙本身就是一团燃烧着的火,“万物都是由火产生,也都消灭而复归于火”,直接肯定了火的起始意义,但是世界上再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华民族那样,坚定地把火的宇宙论意义贯彻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从而对火有着非同寻常的崇敬了。与其他民族一样,中国人之所以如此看重火,首先是因为它强大的实用价值,它在漆黑的夜晚带给人们光明,在寒冷的冬天送给人们温暖,在野兽的咆哮声中赠与人们安全。因此,当圣王伏羲仰观俯察、于天地万物中取八种物象而作八卦时,火便是这八种物象之一,是为“离”卦。可见,在圣人的眼中,火是作为宇宙意象而出现的。(八卦中的离卦自身重叠形成六十四卦中的离卦,也是火的征象。)同样,在五行学说中,所谓金、木、水、火、土,火也占有一席之地。当五行学说与阴阳、八卦学说结合的时候,火的重要性更加突显,在当时的宇宙图式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火,与和它对立存在的水一起,构成了宇宙图式中的南北轴。可以这样说,当人们把“五行”简化成“四行”、八卦简化成两仪,并融合阴阳观念一同来构筑一个统一的宇宙观时,火与水的终极意体现出来。在单纯的八卦学说中,火(离卦)原本是天和地(乾和坤)的“次女”;但是在整合阴阳、五行、八卦学说的成熟了的中国哲学所描绘的宇宙图式中,火以阳性的身份,代替天(乾)占据了至高无上的位置,所以《春秋考异邮》说:“火者,阳之精也。”(《后汉书·五行志二》)《河图·汴光篇》也说:“阳精散而分布为火。”更因为火有气而无质,有功能而无定形,所以西晋潘尼在《火赋》中才说:“览天人之至周,嘉火德之为贵,含太阳之灵辉,体淳刚之正气。先圣仰观,通神悟灵;穷神尽数,研几至精。形生于未兆,声发于无象;寻之不得其根,听之不闻其响,来则莫见其迹,去则不知其往。似大道之未离,而元气之灏养!”[1](P1000)潘尼把火看作宇宙至刚至健的“正气”,认为它生杀万物,神妙无穷。而在王充的想象中,整个宇宙是一个大炉子,“阳气”的燃烧就是这个炉子最重要的特征,“天地为炉,大矣;阳气为火,猛矣”。
既然火是一种宇宙元素,那么它理所当然地也是一种普遍的生命元素,加之生命特征与人体热度之间的直接关系,中国人遂认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团火。中医认为火有温热身体、使人视物光明、腐熟水谷、促进新陈代谢等一系列维持正常生理机制的功能。在中医的认识中,心脏为生理活动提供原初动力,是人体最重要的脏器,所以心脏是“君主之官”,而这个人体脏器的君主在五行当中恰恰对应着火,因此中国传统医学把心脏称为“火脏”。又因为火是一种普遍的生命元素,所以人体各个脏器也都是有火的,如肾脏,本是“水脏”,但是也有火,即肾火、命门之火,这是人体先天的生命之火。“命门火衰”,便预示着生命即将结束。当然,人体脏器之火并不是燃烧得越猛烈越好,所以《黄帝内经·素问》说“壮火散气,少火生气”[2](P51),“少火”是正常的生理之火,“壮火”则为戕害身体的病理邪火,如肝火、肺火、胃火等等。清代名医郑钦安受“少火生气”的观念的影响,创立“火神派”医学,认为人的立命之根为真阳,所谓真阳即是火,“真阳二字,一名相火,一名命门火,一名龙雷火,一名无根火,一名阴火,一名虚火”[3](P3)。
除了传统医学,道教的神仙家、炼丹师也对人体生命之火极为重视。这些道教徒希求长生不老或飞升成仙,他们认为神仙之所以与天地同寿是因为神仙的身体是“纯阳之体”,所以成了仙的吕洞宾就叫“吕纯阳”,全真教的几个大师的道号为重阳、丹阳、玉阳,阳即为火。还珠楼主的绝世奇书《蜀山剑侠传》写仙魔大战,仙人的生命能量就是“南明离火”。道教炼丹师的炼丹也着眼于一个“炼”字,他们的炼丹一定是用火来烧的,李白写他的求仙就说“炼火烧金丹”[4](P635)、“炼丹费火石”[4](P718)。最有名的是神话中的太上老君,他的八卦炉里的仙丹正是用一种特别的火———三昧真火炼制而成。
因此,中国人形容一个人的生命力强为“火气大”,形容一个人身体虚弱为“没火气”,形容一个人年老体衰为“风烛残年”,形容一个人行将就木为“油尽灯枯”。因而在中国文学中,“火”意象往往是生命的意象。《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用巫术延续自己生命的时候,点燃了七星灯。《喻世明言·新桥市韩五卖春情》写主人公吴山因好色而将丧命时说:“只因这妇人入屋,有分教吴山‘身如五鼓衔山月,命似三更油尽灯’。”[5](P38)《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要等到灭掉油灯里的一茎灯草之后,才安然逝去。金庸《飞狐外传》这样描绘马春花将死的场景:“只见一间阴森森的小房之中,一灯如豆,油已点干,灯火欲熄未熄。马春花躺在炕上,气息未断。”[6](P616)欲熄未熄的灯火就是欲死未死的马春花的象征。同样,当程灵素去世的时候,金庸又这样写:“破庙中一枝黯淡的蜡烛,随风摇曳,忽明忽暗,他身上说不出的寒冷,心中说不出的凄凉。终于蜡烛点到了尽头,忽地一亮,火焰吐红,一声轻响,破庙中漆黑一团。胡斐心想:‘我二妹便如这蜡烛一样,点到了尽头,再也不能发出光亮了。’”[6](P639)继承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良多的贾平凹,对这一点的认识更自觉,所以在《秦腔》中他借小说人物引生的口说:
我正经告诉你,我是能看见人头上的光焰的。一个人的身体好的时候头上的光焰就大,一个人的身体不好了,光焰就小,像是一豆油灯芯,扑忽扑忽,风一吹随时就灭了。气管炎张八哥的光焰就小。王婶的光焰几乎都没有了。中星他爹的还行。还年轻的陈亮光焰昏黄,我问他怎么啦,他说他感冒了三天,大热天的一犯病浑身筛糠,还要捂两床棉被子。最奇怪的是秦安,他去医院那天,光焰柔弱得像是萤火虫,从医院回来,赵宏声三天给他换一贴膏药,没想到光焰又起来,他已能下炕,又开始在村里转悠,头上的光焰如长了个鸡冠子[7](P179)。
写到快去世的夏天智时,又说:
夏天智的眼睛闭着,他已经失了人形了,我看他的头顶,头顶上虽然还有光焰,但小得弱得像个油灯芯子[7](P534)。
生命力减弱时的火焰不但如贾平凹所言亮度减弱,热度也大打折扣,因此王维《秋夜独坐》描写迟暮之年的衰朽要写“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同样是描写灯火,但是这火焰并不强烈,似乎像秋风秋雨一样凄凉;“诗鬼”李贺刻画苏小小的亡魂时说“冷翠烛,劳光彩”[8](P32),烛火原是温热的,但是这里的苏小小是个女鬼形象,所以和她相伴的烛火(其实是磷火)也是冷冷的,它已经不具备生命的温热体征了。按照这样的逻辑,如果说鬼也能用火,那么“鬼火”一定是冰凉的,汪曾祺在小说中恰好就讲过这样一个鬼故事:
有一个人赶夜路,远远看见一个瓜棚,点着一盏灯。他走过去,想借个火吸一袋烟。里面坐着几个人。他招呼一下,就掏出烟袋来凑在灯火上吸烟,不想怎么吸也吸不着。他很纳闷,用手摸摸灯火,火是凉的!坐着的几个人哈哈大笑。笑完了,一齐用手把脑袋搬了下来。行路人吓得赶紧飞奔。奔了一气,又碰得几个人在星光下坐着聊天,他走近去,说刚才他碰见的事,怎么怎么,他们把头就搬下来了。这几个聊天的人说:“这有什么稀奇,我们都能这样!”[9](P85)
由于各种原因,尤其是生活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古人对人体的生命之火极为珍惜、不肯有半点浪费,因此古人尤其是古代知识分子理想的生命精神便只是不温不火,他们的生命之火不能熊熊燃烧,他们的生命追求也自然不是热烈的。所以在古典文学当中,以熊熊烈火来隐喻生命精神的作品少之又少。直到新文学运动之后,新文学家们才点起生命的火把、唱出热烈的生命之歌。先是郭沫若,他那唱响新诗号角的诗集中处处跳动着火光:在《凤凰涅槃》中,诗人化身为自焚的凤凰,“火便是你/火便是我/火便是他/火便是火”[10](P21);在《天狗》中诗人变成“如烈火一样燃烧的天狗”[10](P28);在《炉中煤》中诗人又成为黑奴一般的煤炭,为祖国“燃烧成这般模样”[10](P32)。唯美诗人徐志摩这样赞美理想中生活的勇者:“勇士的金盔金甲/闪闪发亮/烨烨生/顷刻大火蟠蟠,火焰里有个/伟丈夫端坐。”[11](P51)徐志摩一生葆有一颗赤子之心,对世间的一切充满热情,所以当他因飞机失事而去世后,梁遇春写《吻火》祭奠他说:
人世的经验好比是一团火,许多人都是敬鬼神而远之。隔江观火,拿出冷酷的心境去估量一切,不敢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火焰里去,因此过个暗淡的生活,简直没有一点的光辉,数十年的光阴就在计算怎么样才会不上当里面消逝去了,结果上了个大当。他却肯亲自吻着这团生龙活虎般的烈火,火光一照,化腐臭为神奇,遍地开满了春花,难怪他天天惊异着,难怪他的眼睛跟希腊雕像的眼睛相似,希腊人的生活就是像他这样吻着人生的火,歌唱出人生的神奇。这一回在半空中他对于人世的火焰作最后的一吻了[12](P172)。
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也热情讴歌有着烈火一样人生的梵高:“你的热情到处燃起火/你燃着了向日的黄花/燃着了浓郁的扁柏/燃着了行人在烈日下/他们都是那样热烘烘/向着高处呼吁的火焰。”[13](P84)艾青也是生命之火的赞美者,他的心胸“被火焰之手撕开”[14](P96);他要求被燃烧,“请给我以火,给我以火”[14](P98);他感激那在黑夜里燃烧起来的野火:
让你的欢乐的形体/从地面升向高空/使我们这困倦的世界/因了你的火光的鼓舞/苏醒起来!喧腾起来
硬骨头的牛汉,为了祖国可以“将自己当作一束木炭/燃烧起来”[15](P24);每年都被砍伐的灌木,把他顽强的生命凝结成比树还要巨大和坚硬的根块:
江南阴冷的冬夜/人们把珍贵的根块/架在火塘上面/一天一夜烧不完/根块是最耐久的燃料/因为它凝聚了几十年的热力/几十年的光焰[15](P73)
这种热情、顽强、浓烈的生命意识,是中国新文学不同于传统文学的重要的现代性,时代风气使然,即使悲哀、冷静如鲁迅者,也宁愿烧完而不愿做冰谷里的“死的火焰”。
二、作为爱情象征的“火”
中国人信奉一种肉体与精神合一的身体哲学,所以,作为一种普遍的生命能量,火既是生理的,也是精神的。说愤怒,则谓大动肝火———在人体脏器与情绪的对应关系中,肝主怒;说性爱,则谓欲火中烧。尤其是对于性和爱的欲望,火的形象更是不可替代的文学隐喻。钱锺书曾引安迪生语,“各国语文中有二喻不约而同:以火燃喻爱情,以笑喻花发,未见其三。”[16](P124)加斯东·巴什拉(G.Bachelard)也认为,人类对火的经验是一种十分性化的体验,所谓摩擦能够生火,正是人类从男女肉身的摩擦交合时体温的升高得到的启发。
早在上古时期,中国人的歌谣就已经把火与男女之情糅合在一起吟唱了,《诗经》描写男婚女嫁往往写到“柴薪”,如《汉广》“翘翘错薪”、《南山》“析薪如之何”、《东山》“烝在栗薪”、《车舝》“析其柞薪”、《白华》“樵彼桑薪”等皆是,因为“古者嫁娶以燎炬为烛”。自此之后,中国文学里就时时闪现着情爱的火光。李商隐写他的苦恋要写“蜡炬成灰泪始干”“分曹射覆蜡灯红”“何当共剪西窗烛”。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里写她与赵明诚志同道合的恩爱生活时,也特意写到了燃烧的蜡烛:“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17](P310)这对夫妻钟情于金石古玩,每天晚上展玩藏品都要耗费一支蜡烛,烛光照耀下的爱情升华成了对艺术的痴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蒋兴哥要出门远行时,对妻子的嘱咐是:“娘子耐心度日,地方轻薄子弟不少,你又生得美貌,莫在门前窥看,招风揽火。”招风揽火,揽的是他人的爱慕之情吧。《红楼梦》第二十一回写道:“那个贾琏,只离了凤姐便要寻事,独寝了两夜,便十分难熬,便暂将小厮们内有清俊的选来出火。”出火,出的也是情欲之火。李少红导演的电视剧《红楼梦》将这个细节改编为贾琏拔火罐,倒也是含蓄有趣的比喻。
当然,古典文学对情欲之火描写最为出色的要首推《水浒传》中潘金莲调戏武松一节。当潘金莲打定主意要“撩斗”武松的时候,就早早“去武松房里簇了一盆炭火”,火盆一出,敏感的金圣叹就批点道:“火盆此处出现”;武松回到家中,潘金莲即让他“向火”而坐,并且她自己也“掇个杌子近火边坐了”;当武松觉察到情况时,却只是“把头来低了”,“自在房里拿起火箸簇火”;潘金莲见武松不应,错把武松隐忍的愤怒当成害羞,“劈手便来夺火箸,口里道:‘叔叔不会簇火,我与叔叔拨火;只要似火盆常热便好。’武松有八九分焦躁,只不做声。那妇人欲心似火,不看武松焦躁,便放了火箸,却筛一盏酒来,自呷了一口,剩了大半盏,看着武松道:‘你若有心,吃我这半盏儿残酒。’”[18](P213-214)虽然潘金莲的烈火碰到的不是干柴而是冰水,但是她的欲望之火确曾大胆地燃烧过。
相对于潘金莲那种世俗女子的情欲烈火,矜持、含蓄的“花间女子”们点燃的爱火却怎么也烧不起来,于是一部《花间集》中处处是半明半暗的火、将要熄灭的火、残火:“银烛尽,玉绳低,一声村落鸡”(温庭筠《更漏子》) ;“兰烬落,屏上暗红蕉”(皇甫松《梦江南》) ;“春漏促,金烬暗挑残烛”(韦庄《谒金门》) ;“暗灯凉簟怨分离”(阎选《河传》),“红烛半消残焰短”(尹鹗《临江仙》)。或者她们已经绝望,爱欲之火已经熄灭,闺房之中仅仅飘荡着迷离凄楚的香烟:“深处麝烟长,卧时留薄妆”(温庭筠《菩萨蛮》) ;“至今尤惹御炉香,魂梦断,愁听漏更长”(薛昭蕴《小重山》) ;“月光斜,帘影动,旧炉香”(牛希济《酒泉子》) ;“玉炉寒,香烬灭,还似君恩歇”(孙光宪《生查子》)。
现代作家从古人手中接过了燃烧着爱意的火把。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塑造一个大胆追求情爱的现代女子,开篇便写“伙计又跑来生火炉”[19](P1),因为莎菲怕冷,需要温暖,需要爱情的温暖。《酒后》写一个少妇在酒精(注意,酒是会燃烧的水,酒也是火)的刺激之下,想要做当着丈夫的面亲吻丈夫朋友的举动,于是作者凌叔华着意为主人公点起一炉火,为她营造了一个温暖的空间:“夜深客散了。客厅中大椅上醉倒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酣然沉睡;火炉旁坐着一对青年夫妇”,“壁炉的火,发出那橘红色柔光射在他俩的笑容上;几上盆梅,因屋子里温度高,大放温馨甜醉的香味。”[20](P35)酒精,花香,再有炉火,难怪不会火色生情。徐讠于在小说《笔名》中编造一个故事,写的就是“富有的寡妇的火一般的欲望”[21](P356)。沈从文《都市一妇人》描写一个寡妇和年轻军官的相爱,绝非偶然地把他们比喻成一对火把:“也许,一个快要熄灭了的火把,同一个不曾点过的火把并在一处,会放出极大的光彩。”[22](P105)施蛰存是用精神分析来刻画人之性意识的文学好手,他改写拼命三郎的故事《石秀》,写到石秀初见潘巧云的那个晚上,特意给石秀点了一盏灯:“却说石秀这一晚在杨雄家里歇宿了,兀自的翻来覆去睡不着。隔着青花布帐眼睁睁的看着床面前小桌子上的一盏燃着独股灯芯的矮灯檠,微小的火焰在距离不到五尺的靠房门的板壁上直是乱晃。石秀的心情,也正如这个微小的火焰一般的在摇摇不定了。其实,与其说石秀的心情是和这样的一个新朋友家里的灯檠上的火焰一样地晃动,倒不如说它是被这样的火焰所诱惑着,率领着的,更为恰当。”[23](P172)石秀确实是被诱惑着,然而诱惑他的不仅仅是火焰,而且是这火焰象征着的满怀情欲的潘巧云。迟子建《清水洗尘》写一个男孩子天灶朦胧的性意识,通篇都让这个孩子守着火炉烧水:“火焰把天灶烤得脸颊发烫”“(炉火)用金黄色的小舌头贪馋地舔着乌黑的锅底,把锅里的水吵得嗞嗞直叫。”[24](P142)“天灶笑了,他拨了拨柴禾,再次重温金色的火星飞舞的辉煌情景。在他看来,灶炕就是一个永无白昼的夜空,而火星则是满天的繁星。这个星空带给人的永远是温暖的感觉。”[24](P148)
爱情是两性的燃烧,那么爱情之火也是有性别的。冯至的诗作《歌》代表了一个普遍的看法———如果说女人是水,那么男人就是火,水是女性意象,火是男性意象:
看许多男人的睡相/都像将爆未爆的火山/为什么都这般坚忍/不把火焰喷向人间/哪座山不会爆裂/若不是山影浸入湖面?若没有水一般女人的睡眠/山早已含不住了它的火焰[13](P74)
与冯至持同样看法的是迟子建,她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写到:“河流开始是笔直的,接着微微有些弯曲,随着弯曲度的加大,水流急了,河也宽了起来。最后到了一个大转弯的地方,堪达罕河就好像刚分娩的女人一样,在它旁侧溢出一个椭圆的小湖泊,而它的主流,仍然一门心思地向前。”看,水是女性化的!同时她借尼都萨满的话说:“男人的爱就是火焰,你要让你爱的姑娘永远不会感受到寒冷,让她快乐地生活在你温暖的怀抱中。”无疑地,火是男性化的!不过,对于朱天文笔下的同性之爱,火的性别不具威胁,两个男人之间的爱情照样可以火烧火燎:“我们挨到莫莫好怅惘离去,牵着单车的身影,五步一徘徊,突然高呼一唱,毛主席是无产阶级祖国的舵手,消失于转弯黑暗里,我们已烈火燎原一路烧回屋子去了。”[25](P66)她把伟大领袖的名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稍加戏谑,却也乐而不淫、别有一番风味。
在笔者的阅读经验中,现代作家里用火意象来隐喻情欲,做得最高妙的是金庸,因为他的《神雕侠侣》塑造了一个被情欲操控而失去理智的火性女人———李莫愁。在小说中李莫愁的每次出场似乎都携带着一把火,哪里有火哪里就有李莫愁,杀人放火原是李莫愁的拿手好戏,趁火打劫更不在话下。最后李莫愁也是死在火中:
李莫愁撞了个空,一个筋斗,骨碌碌的便从山坡上滚下,直跌入烈火之中。众人齐声惊叫,从山坡上望下去,只见她霎时间衣衫着火,红焰火舌,飞舞周身,但她站直了身子,竟动也不动。众人无不骇然。……瞬息之间,火焰已将她全身裹住。突然火中传出一阵凄厉的歌声:“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唱到这里,声若游丝,悄然而绝[26](P1119)。
可见李莫愁是个火性女子,她一生杀人放火,最后葬身火海,她将整个人生都燃烧成极具破坏力的邪火。如果从犯罪心理和犯罪行为的角度来看,李莫愁是典型的纵火犯。据现代的研究,纵火犯往往“有婚姻、职业和性方面的问题,并且表现出其他各种犯罪和反社会行为”[27](P368),这简直就是为李莫愁量身定制的犯罪画像。不过,李莫愁的邪火也是缘于爱火,正是她初恋男友的负心,使她的一腔爱火、情欲之火变成妒火、怒火,她四处杀人放火只是为了宣泄她的胸中之火,她最后葬身火海不是他杀而是自杀,像这样一个火光四射的女人谁又能杀死她呢?不是绝情谷的情花之火烧死了她,是她心中的情欲之火引燃了自己,这正印证了犯罪学家的一个观点———对于纵火癖者来说,“纵火是为了替代性欲,火所具有的强大的破坏力反映了纵火癖高涨的性欲和性虐待倾向”[27](P366)。
三、结语
自然不仅为人的物质生活提供原材料,也为人的精神生活提供原材料。人类生活不仅是与自然发生物质交换的过程,也是与自然发生精神交往的过程。“火”意象在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中的原初性、稳固性和丰富性,向我们直观地展示了这样一种宇宙元素对于人类精神生活的意义。“火”意象在人与物质自然交往的最初阶段便进入了人的精神生活当中;而在历史的发展中,无论是作为宇宙元素、生命能量,还是作为爱情的象征,“火”意象自始至终都指涉着人类存在最原初的自然性和肉身性。无论在哲学、科学、宗教还是文学、艺术当中,火(以及与火具有同等地位的水、土、风、光等自然元素)都具有“理念”的性质,它是人类把握和改造世界、认识和表征自我的过程中所要凭借的最基本的东西。它是自然之物,同时也是文化之物,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以维持所依赖的基本营养。
然而,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到后工业时代的今天,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愈来愈被技术所阻隔,人与自然之间的精神交往也越来越为工业制成品和商品所阻隔。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领域中“符号学”盛行的局面实际上是这种历史境遇在思想领域的反映,这使得文学作品成为了“自我指涉”的、自给自足的、“不及物”的幽灵,使得人们遗忘了文学与物质自然的原初关系,遗忘了物质自然对于审美活动的奠基意义。笔者认为,文学是“及物的”(这里的“物”指的是包括人的身体在内的物质自然),而作为文学本体的意象是人与自然进行精神交往的直接产物。因此,我们应该抛弃“符号学”思维中包含的“技术统治论”观念,进而从人类最原初、最直接的生存经验和生命体验的角度对文学和文学形象的自然根源进行更为深刻的挖掘。另一方面,学术界现阶段的文学研究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越来越走向实证研究和文献考订,这又导致人们太过执著于“物”而遗忘了“人”,许多文学研究者借着文化研究的幌子往文学的体腔里填塞古董旧物,于是文学又被变成了考古学、博物学,从而丧失了我们面对文学经典应有的领悟能力和阐释能力,以表现宇宙、自然和人的生命精神为核心的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被视而不见,甚至被刻意回避。如何克服这些弊端,是我们从文化内涵和生命精神的角度对中国文学中的“火”意象进行初步研究的初衷,疏漏之处,敬请方家批评。
参考文献:
[1]严可均辑.全晋文中册[Z].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黄帝内经素问译释[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3]郑钦安著.周鸿飞点校.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4]王琦注.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
[5]冯梦龙.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M].济南:齐鲁书社,1993.
[6]金庸.飞狐外传下册[M].广州:广州出版社/花城出版社,2008.
[7]贾平凹.秦腔[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8]王友胜,李德辉校注.李贺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3.
[9]汪曾祺.汪曾祺小说:下[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
[10]郭沫若.凤凰涅槃[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11]顾永棣编.新编徐志摩全诗[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
[12]梁遇春.散文选[M].北京:中国出版集团/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3]冯至.十四行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14]牛汉.艾青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15]牛汉.牛汉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16]钱锺书.管锥编[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7.
[17]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8]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10.
[19]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20]凌叔华.绣枕[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9.
[21]徐讠于.徐讠于文集:第六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22]沈从文.丈夫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23]施蛰存.施蛰存文集十年创作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4]迟子建.与水同行[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25]朱天文.荒人手记[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
[26]金庸.神雕侠侣:第四册[M].广州:广州出版社/花城出版社,2008.
[27]巴特尔等.杨波审校犯罪心理学[M].杨波,李林,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赵琴]
【文学研究】
Emotions Coming from Fire: The Culture Connotation and Spirit of Life of the Fire Image in Chinese Literature
QIU Xiao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127,China)
Abstract:Fire in Chinese literature is a culture and life image full of culture connotation and spirit of life.On the one hand,it is a symbol of the universe element and life energy.On the other hand,it is a symbol of love.Studying the fire image i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and the spirit of life is an effort to get rid of positive and technical abuse in the studies on literature.
Key words:fire image; universe element; life energy; symbol of love
作者简介:邱晓,男,山东淄川人,西北大学讲师,博士,从事文艺美学和唐诗研究。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12J108) ;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专项基金(13JK0244)
收稿日期:2014-03-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15-05-011
中图分类号:I2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