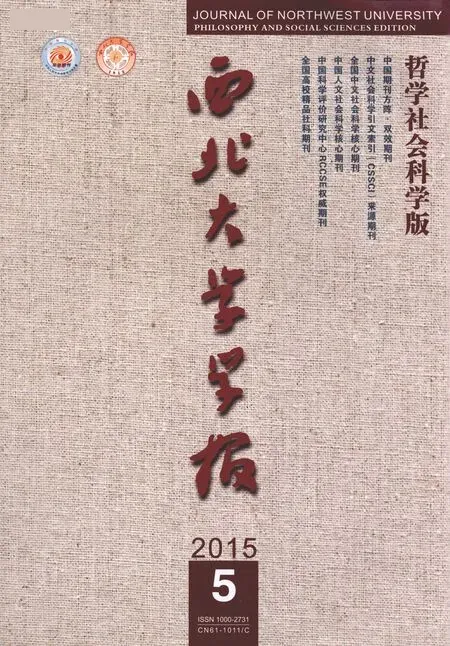恶魔性:欲望与时代的撞击
———以贾平凹《古炉》为例
孙立盎(陕西学前师范学院中文系,陕西西安 710100)
恶魔性:欲望与时代的撞击
———以贾平凹《古炉》为例
孙立盎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中文系,陕西西安710100)
摘要:恶魔性在以“文革”为背景的新时期文学文本中呈现以下特征:首先,具有恶魔性因素的人物往往生命力旺盛,欲望强烈,不甘平庸;其次,恶魔性缘起于人的原始欲望,正常情况下,它以潜伏状态存在,如若遇到理性薄弱或丧失的时代,便升腾而起;第三,它往往以一种宣泄原始生命蛮力的狂暴形态出现,具有毁灭性的特征。贾平凹的《古炉》通过人性原欲之恶魔性的角度,反思被压抑甚至异化了的人性欲望以及失去控制的社会运动带来的种种危害,从而达到对民族性格的重新审视和建构。
关键词:恶魔性;原始欲望;“文革”;毁灭性
一
恶魔性(the daimonic)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词根是daimon,古希腊语里写作δαμωυ,在西方文学创作中具有悠久的传统。从古希腊柏拉图的《会饮篇》、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到但丁、莎士比亚、弥尔顿、歌德,直到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马斯·曼等的作品中,恶魔性因素都有呈现。在古希腊时代,daimon并不是一个纯粹反面的词,它似乎是一种中间力量,介于人神之间,会在人丧失理智的时候出现并推波助澜[1](P233)。罗洛·梅(Rollo May)认为,它具有控制性的力量,往往通过性与爱、愤怒与激昂、对强力的渴望等表现出来[2](P126-127)。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恶魔性就屡有出现。鲁迅笔下的疯子、魔鬼、狂人正是西方恶魔性原型在中国特定现实环境和文化背景下的变形。新时期以来,在张炜、老鬼、阎连科、张抗抗、铁凝、陈忠实等人的作品中,都有恶魔性因素出现。简要梳理,不难发现恶魔性的一些共同特征:首先,恶魔性大都显现于这样一类人身上,他们一般都具有生命力旺盛,欲望强烈,不甘平庸等特点。其次,恶魔性的产生与出现,和人物原始欲望的备受压抑、无法满足直接相关。当这种压抑性的力量以某种无法撼动的权威性面目出现,使物欲、权欲、性欲等原始欲望被忽视、无法正常释放时,潜伏在人性深处的恶魔性就会蠢蠢欲动,但常常会被理性制约和克服。如若遇到革命、暴乱、变革等理性薄弱或丧失的时代,它便升腾而至。第三,恶魔性往往以一种狂暴形态呈现,宣泄着人类原始生命蛮力,展示出堕落、病态乃至疯狂等毁灭性特征。
《古炉》以一个儿童的视角,通过对贫困闭塞的古炉村百姓的婚丧嫁娶、吃喝拉撒、柴米油盐等日常生活的展示,记述了“文化大革命”在古炉村的发生和衍变,审视和思考了宁静的山村也难逃此难的原因:是什么将古炉村裹挟进这场革命的洪流之中;为什么原本和平相处的邻里乡亲转眼间反目成仇甚至你死我活;是什么使人们变得如恶魔般残酷冷漠;等等。作家对这类问题的思考并未简单化为政治层面对“文革”的否定或批判,而是着力于人的探讨,发掘人性因素与社会因素之间的关联与制约。正如陈思和教授在谈到“文革”文本时所言,“人性因素与社会因素构成了一对互动的关系”,一方面,原欲等人性因素受到现实社会环境的制约;另一方面,一场历史性的灾难与人性中的原欲、疯狂、变态等因素相关。可以说,从个人的原始欲望到民族的疯狂记忆,这之间如果能用一个词概括它们的联系,那就是“the daimonic”(恶魔性)[1](P238)。
二
《古炉》中的主要人物,应该说都与神灵有关。所不同的是,蚕婆、狗尿苔、善人等一类人,以其信念、精神、行为超越着世俗的争斗和现实苦难的羁绊,度己度人,对自己及同类悲悯、关爱,虽立足不幸的人生此岸,精神灵魂却向着神圣的彼岸延展。贾平凹在《古炉》后记中说:“这些人并不是传说的不得了,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有神性的人。”他们的神性较为完整而纯粹,都“有一种圣的境界”,而“我恍惚认定狗尿苔其实是一位天使”[3](P606)。而以夜霸槽、天布为代表的另一类人,虽也与神灵相关,但却是半神性半魔性的人物。根据历来对“daimon”的解释和理解,他们即为恶魔性人物。
夜霸槽作为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其身上的恶魔性因素最完备全面。他生命力旺盛、欲望强烈、思想活跃、行为果敢,心高气傲、不甘平庸,和周围大多数依赖惯性生活的村民们有很大不同。他建议支书说古炉村该有个代销店,他在公路边钉鞋补胎,在小木屋做粮食交易……这些思想和行为在一切公有制,一切计划性经济的时代,在封闭保守的古炉村,无疑已跃入雷池;不仅如此,他的行为习惯都有意无意和古炉村人保持着不同,他戴墨镜、抽纸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所以他不被周围人认同。类似的人物还包括《蘑菇七种》中的老丁,《玫瑰门》中的司猗纹等。
这样一群人,绝非生活中的平庸者,他们的特征更接近于楚克尔(Wolfgang.M.Chukerr)所言的“天才艺术家”。按照楚克尔的说法,这些人的身上的迥异性,来自于上天赋予的力量。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对此也有所论及,他认为恶魔性包括性的冲动和原始生命力,是将神性和人性相结合的一种力量,它并非来自外界,而是来自人内在的生命驱动力[4](P240-241)。甚至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人的性格就是他的“daimon”。正是由于上述一类人听从了内心神灵的召唤,才会傲然不羁。如靡菲斯特正是看到了浮士德身上的这种特质,才愿意来到人间,和他立下赌约,使浮士德的恶魔性人格更加凸显。
三
恶魔性的出现,有人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两个方面的原因。恶魔性缘起于人的原始欲望,是人性的组成部分之一。正常情况下,它处于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但当原始欲望如食欲、权欲、性欲等被忽视或被压抑时,它就可能显现。《古炉》中霸槽的各种欲望不仅无法满足,甚至被深深压抑。他虽然脑子灵活,想法很多,但根本不被重视,还总是被朱大柜防备着。最早他建议在古炉村开代销店,但“结果支书让开合办了店而不是他霸槽”[3](P27);自己钉鞋补胎收点费用却被村干部时时处处催着上交提成;小木屋的粮食交易被取缔;与杏开的情爱受到多方阻挠,不得称心……生活落魄、缺衣少食,老屋摇摇欲坠,维持起码生命状态的物质基础随时都会坍塌。虽然半神性的力量给予了他们不同寻常的能力,也给了他们超凡的精力,拥有这一切本可以活得更快意,但现实却并非如此。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各种原因,不仅他们的能力无处施展,甚至连基本的生存欲望都难以满足,霸槽感到“古炉村快把人憋死了”,他内心憋屈,无处发泄,“觉得他一身本事没个发展处,怨天尤人”。而他要在古炉村里实现“自己说了算”的欲望是那样强烈,“要吃就吃美”,“要找就找最好的女人”,现实却让他感到窒息般的憋闷。霸槽犹如陷入泥沼的马匹,徒有气力无处可使,生命力被压抑,生命价值被漠视。天布成立大刀队,表面看起来是不满霸槽的嚣张,实质是对霸槽挑战自己在古炉村的权利的报复与压制。作为古炉村民兵连的连长,加之支书的庇护,天布一向瞧不起“浪荡鬼”霸槽,但没想到“文革”中却被霸槽抢先成立了榔头队,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行动。这使他的权力欲受到了极大的挑衅和威胁,所以,大刀队的成立势在必行,这是他维护自己权力欲的第一步。以后双方你争我夺,你死我活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这一欲望的追逐与满足。
生存欲望无法满足的何止霸槽和天布。饥饿在很长时间内是中国农村面临的首要问题。解放后不久,中央政府在农村先后进行了土地改革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将长期陷于动荡、困顿的农民整体性纳入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内,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农村赤贫的状况,然而,广大农村底子薄、贫困人口多,加之随着政策又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尤其是人民公社化运动脱离了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所以直到“文革”,很长一段时期里,许多农民是饿着肚子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的。古炉村人未能例外,每到春荒时节,揭不开锅是常有的事。因为贫穷,拥有一棵皂角树会让主人倍感富有,瞧不起别人;分配稍有不公就会引起轩然大波;因为饥饿,村人见到野物绝不手软;在救济粮面前,个个眼馋爪利,不惜互相攻击互揭伤疤。当人性最基本的欲求———生的欲望都无法合理满足时,人性中的恶魔便再也无法蛰伏了。
正常的生命需求被漠视被压抑,在古老中国大地已非罕事。中国社会很早就建立起了各种强有力的秩序之网,每一个体都是网中的一个节点,个体的任何行动都会牵一而动百,从而将个体牢牢固定在某一位置,即使有想法也需三思而后行,在充分权衡利弊得失后,个体的生命需求往往显得微不足道。中国农村,“文革”前,宗法制伦理道德秩序和社会主义公社化政治秩序是维护村庄安宁、生活平静的两股无形而强大的力量。前者,存在千年之久,早已内化为村民们的行为道德规范,无需教导和强制,大部分人不仅自觉地遵守而且以它作为评价他人道德高下、人品优劣的准则;后者,虽为新生事物,并以强大的国家机器作为后盾,但农村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并没有因为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而销声匿迹,加之农民普遍缺乏现代政治意识,文化基础薄弱,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新的专制和腐败。农村干部的任命、农活的分配方案等大小事务多是少数人说了算。古炉村里,支书朱大柜便是“说了算”的人。很长时间内,他掌管着村里的一切,不仅给村民断是非、了纠纷,更掌握瓷器的买卖、款项的收支、人员的任用、救济粮的分配等权力。村民们已经习惯了支书的权威,他让你坐着你就不能站着。虽然大多数古炉人家总是填不饱肚子,但他家里人却经常偷着晾晒吃不了的点心;当有人宅屋都快要倒塌掉时,他却想方设法赶走善人,为自己低价买公房给儿子做婚房铺路……他一手遮天,虽然大家心中生出许多不满,但一时也没有办法,只能默默忍受。正如代销点让开合办了,霸槽虽然气愤也无可奈何一样。显然,这是一种强大的根深蒂固的压抑性的力量,任何个人都很难撼动它。
欲望如此强烈,压抑如此之深,突破如此之难,如果没有合适的时机,如果生活仍是一片死寂,霸槽们也许会感到沉闷,但也可能随波逐流,茫然一生,至多发发牢骚骂骂人,人性中的恶魔也会沉没于无意识的汪洋之中。而“文革”,正是一种诱发性的力量,它打破了几乎所有的秩序,使那张无形大网千疮百孔,在剥夺一部分人生存权利的同时,使另一部分人的生命欲望极度膨胀,人性中的恶魔性暴露无遗,进而彻底失去控制,如决堤之水,轰然而至,所到之处,覆没一切,包括朱大柜、黄生生、麻子黑、秃子金、水皮、守灯、磨子等人心中,原本沉寂着或有所控制的恶魔性也张开了锋利的魔爪。
同样,在《蘑菇七种》《血色黄昏》《坚硬如水》《隐形伴侣》《玫瑰门》等作品中,均有恶魔性因素出现。不难发现,上述作品中恶魔性的出现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社会因素,即“文化大革命”。“文革”的发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恶魔性的萌发,甚至在“文革”的上层权力斗争中,也多次出现类似的暗示。例如毛泽东在“文革”初期批评党的各级领导人时,不止一次使用了与魔鬼意向相关的比喻,如阎王殿、小鬼等;“文革”的民间话语中,也大量出现“牛鬼蛇神”等,这些与恶魔共名的话语体系无疑暗合着文本中的恶魔性。的确,“文革”作为解放后群体理性薄弱乃至失控的一段特殊时期,是恶魔性的高发时期。正如贾平凹所言,“贫困、不公平、不自由容易使人性中的魔鬼出来,而当被‘政治运动’着,就集中爆发了”[5]。当古炉村人因为贫穷、不公、干部腐败而心生怨气,憋闷已久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发泄途径时,“文革”来了,霸槽、天布等人闹起来了。“文革”对于当时国家的上层权力集团而言,是其意识与权力的冲突与争夺,如果说在大都市,“文革”还有较为明确的目的的话,那么对于偏远落后的农村而言,它完全是盲目的。然而如同过浮桥一般,人处浮桥之上,“谁也并不故意要摆,可人人都在惊慌地走,桥就摆起来,摆得厉害了肯定要翻覆”[3](P604)。浮桥的翻覆,将村中积怨已久的人心彻底搅乱了,平日里的怨恨、利益、幻想如同浮桥下水中的泥沙一同被翻搅了上来。用小说中的话说,就是“春上天一暖和,地里的啥草都起根发苗了”[3](P298)。大家不解着“文革”,又利用着“文革”,各种心思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中张扬起来、肿胀起来,没有了边际。当彼此的私欲发生冲突时,更激起加倍的贪欲、仇恨与报复,最终演化为肉体的搏斗,如同打开了的潘多拉盒子,人性中的恶魔终于摆脱了束缚,在“革命”的旗帜中挥舞着残酷的魔爪,毁灭着一切。正如贾平凹所言,“在我们身上,除了仁义礼智信外,同时也有着魔鬼,而魔鬼强悍,最易于放纵”[3](P605)。
当“革命”的风暴吹向古炉村时,霸槽迅速开始了行动:成立了红色榔头队,做了“造反派”的头目,破四旧、揪斗走资派、“黑五类”牛鬼蛇神;同时,征服日渐坐大的对立面,砸瓷窑、抢粮食……可以说是他将古朴的古炉村拉入了“文革”的泥沼,使古老的村庄陷入血雨腥风之中。往日的古朴宁静彻底被毁灭,人人自危,互相猜忌;庄稼没人料理,河堰不再休整,上工的钟声不再响起,一切秩序被打破被推翻。而夜霸槽在此过程中完全陷入癫狂状态,像被魔鬼附了身,几乎不吃不睡,夜以继日地忙碌他的“事业”,梦想更大的“成就”。
与霸槽一样陷入疯狂的还有天布等人,正像霸槽的疥疮一样,人性中的恶魔也会很快传染开来。小说中写道:“天布就说:姓朱的都是正经人么,扳指头数数,榔头队的骨干分子都是些啥人?能踢能咬的,好吃懒做的,不会过日子的,使强用狠的,鸡骨马头,对啥都不满对啥都不服的,不是我说哩,都是些没成色的货!灶火说:‘文化大革命’咋像土改一样,是让这些人闹事哩。”[3](P329)虽然鄙视着霸槽一伙,但天布他们又何尝不是在步霸槽的后尘呢?成立大刀队,与榔头队武斗。在争斗中,个个好强使狠,偏执而丧失理智,不仅导致古炉村百年古树被炸,大批青壮男人死的死,伤的伤,连自己也最终葬送了性命。
四
恶魔性扎根于人类原始生命的本能欲望之中,总是在群体理性薄弱或丧失的时代以某种与人性相沟通的形态发出它的存在信息,呈现出巨大的毁灭性特征:无视法律、践踏秩序、破坏人伦。不少“文革”叙述,包括《蘑菇七种》《坚硬如水》等,通过恶魔性因素的呈现,是为了揭示时代的疯狂与混乱;而《古炉》则始终执着于人性,“文革”是它展示人性的一个载体。贾平凹曾有过这样的表述,他不在于写任何大的事件,他的兴趣点在于事件里边的人性的一些表现[6]。
的确,早在其创作之初,贾平凹就开始了对于人性的探寻。在早期的作品中,更多地是对人性美的肯定与讴歌。男人们侠肝义胆,铁汉柔情,如天狗、五魁等,也许他们的行为未必合乎正统价值尺度,但其言必行、行必果的行为方式,似乎让我们又看到了曾经的游侠的影子;而女人们或善良圣洁、温柔娴淑,或柔情似水又刚烈如火,如小水、天狗的师母等,体现了作家对于人性美的追求。随着人生体验和艺术感悟的逐步深化,作家投向生活的目光更加冷静而深邃,对于人性的思考和表现也趋于冷峻和深刻。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一批作品如《古堡》《浮躁》中,已经较为集中地揭示人性中的狭隘、自私、愚昧、保守等特质,90年代以后,在《高老庄》《秦腔》等作品中,继续揭示人性的负面因素,至《古炉》,则借助“文革”这一背景,将其引向深入,深入人性的黑暗面,不是展示现象,而是挖掘根源,通过人性原欲之恶魔性的角度展示人性的复杂与丑恶,反思被压抑甚至异化了的人性欲望以及失去控制的社会运动带来的种种危害,从而达到对民族性格的重新审视和建构。
参考文献:
[1]陈思和.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2]罗洛·梅.爱与意志[M].冯川,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
[3]贾平凹.古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4]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5]贾平凹,李星.关于一个村子的故事和人[J].上海文学,2011,(1).
[6]韩鲁华,储兆文.一个村子和一个孩子———贾平凹《古炉》叙事论[J].小说评论,2011,(4).
[责任编辑赵琴]
【文学研究】
The Daimonic: the Clash of the Desire and the Times: The Analysis of Old Furnace Written by Jia Pingwa
SUN Li'ang
(Chinese Department,Shaanxi Xueqian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100,China)
Abstract:The new-period-literature i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and the daimonic of this age appears in the three features: First,the person who carries the daimoic feature always has great vitality and strong desires,and he is unwilling to be mediocre.Second,the daimonic origins from the original desire,and it exists in dormant state in normal condition,but if in the loss of rational era or in the weakness of rational era,it would rise.The third,the daimonic would appear in the violent from in order to express the original life vitality,which has a devastating characteristics.The Old Furnace written by Jia Pingwa reflects the repressed even the alienation humanity in the way of the revealing the daimonic.It also reflects how terrible the harm is which is brought by the irrational social movement.The novel tries to re-examine and rebuild the national character.
Key words:the daimonic; original desire;“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evastating
作者简介:孙立盎,女,陕西商洛人,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副教授,从事西方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4I22)
收稿日期:2014-05-1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15-05-010
中图分类号:I206.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