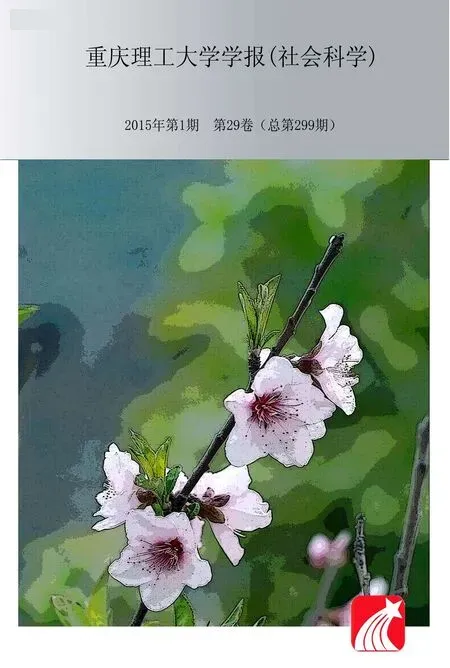当代诗歌情感空间的两种表征范式
鄢 冬
(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呼和浩特 010070)
把诗歌文本多变的体式、复杂的意象凝聚起来的力量是情感的力量。“情感,是艺术生命的激素。它刺激和孕育艺术生命,是沟通艺术创作者和欣赏者的桥梁。在创作过程中,情感还起着构思和提炼的作用,强烈的爱憎之情还常常导致作家原来创作构思的变化,这是被不少创作实践证明的。”[1]169诗人的情感或浓烈或平淡,表达方式或直观或含蓄,都是诗人独特的体验。诗歌中的情绪极难被破译,原因在于编码的过程十分复杂。“情感世界及其存在既不完全是理性的、决定论的,也不完全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世界。它是一个由无数有细微差别的事物、奇特的符号和内在的间接内容所充满的世界。它产生于具体的社会情境中,产生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采取的情感态度过程中。”[2]91文本背后的编码过程首先受个别的特殊的情感经验的影响,但这个别的特殊的情感经验背后,一定可以觅见共同的、普遍的特质。尽管诗歌情感的表现形式千差万别,但建立在共同的情感基石之上所展现的文字表现了诗人的特殊情感经验。属于诗人个体的情感经验营造了诗歌文本的情感空间:“情感空间的产生,是情感对世界生机弥漫的支配,是诗人创造力自由驰骋的表征。”[3]178情感空间是一种心理空间,也是一种可以被具象化的空间。
空间距离的存在,使得文本的情感组织得以保鲜,既不会过分浓烈,同时也会有适当的神秘感。距离在诗歌领域似乎有些抽象,但也有具象的范式,“远方”是距离形式的体现之一,“远方”的近义词如“天空”等也成为“距离”的注脚。这里的“远方”首先是物理世界的远方,但在诗歌中,其精神内核更值得关注。“远方”的精神内核便是将“心理的距离”表征化呈现,正因为如此,它遂成为诗歌中重要的意象。“远方”是诗人诗歌中常见的空间意象,但同时,当“远方”在诗歌中的含义以虚指居多时,它便成为空间情感的表现体。它的出现揭示了距离对于审美的重要,也证明了空间的存在对于情感组织的重要;诗人所承受的情感经验有可能转变为诗歌创作时的情感素材,而情感素材汇集起来便是一股情感的力量。“文学大师给我们展示了他们辉煌多彩的心灵,同时给我们以启示,那就是真正丰富、深刻的感情源泉却不来自于作品,培养作家素质最广阔的天地是生活实践,有了文学作品的熏陶,又加上生活的磨炼,感情才能发达起来,作家的心理素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1]78此外,不同的情感素材将汇集不同的情感力量,孤独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种。孤独,是一种相对独特的情感存在,它体现了在集体主义的背景下,个体的存在相对于群体而言的无依靠感,再加之这一情感状态与诗人的忧郁气质极其相似,所以诗歌中的孤独体现的又是典型的情感范式。“诗表现的心灵不但是原生态心灵的升华,也是升华了的心灵的符号化。”[4]262-263
一、距离的魔力——“远方”和“天空”
距离并不直接营造空间,但距离的存在客观造成空间的存在。在文学作品中,审美活动的完成需要靠适当的审美距离支撑。首先,距离使得审美活动得以客观、公正。诗歌中忌讳“激情写作”,尽管像郭沫若、闻一多等大诗人可以在澎湃的状态下写出诸如《凤凰涅槃》《一句话》这样的诗篇,但对于一般的诗人而言,需要用理智抑制自己的激情,再把适度的激情移植到所营造的那个世界中去。激情写作有时固然能给诗人或者读者带来畅快的体验,但无论是对语言控制力的要求,还是对情感控制力的要求,都不是一般诗人所能及的。激情写作,有时反而显示了无能且浅薄的语言控制力,甚至会产生偏激而极端的情感表现。适当距离使得诗人情感得以保鲜。情感的距离在古代诗歌中就有较好展现,如“求之不得”:“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诗经·关雎》);“若即若离”:“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蒹葭》);“伊人远去”:“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柳永《雨霖铃》)。适当的审美距离使得文本具有情感、语言上的张力。
在诗歌文本中,“远方”是比较典型的距离存在形式,同时也是诗歌中较具代表性的意象,能表达一种“期待感”的情愫。远方既是诗歌中的空间意象,但同时由于“远方”又可以寄托或表征诗人多种情感元素,因此部分“远方”是空间情感形式的存在。区分“远方”是空间意象还是情感形式,要看具体诗作中的“远方”究竟是实指居多还是虚指居多,实指多为空间意象,虚指多时便成为空间情感的存在形式。当“远方”只是远方时,远方便是空间意象,当诗歌中的“远方”所投射的内容比远方更“远”时,它就成为了空间情感的范式。远方体现的是空间的无极限。远方表达的是观察者目光所及的距离之外的空间,与科学概念中的距离不同,远方无法用数字来衡量,它是一个十分朦胧的概念,甚至提出它时,就已经有了诗歌的味道。海子的《九月》充斥着古典美,全诗透露一种含蓄的、内敛的诗风。“远方”在此诗中充当重要角色,是铺垫:“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是焦点:“远方只有在死亡中凝聚野花一片”。另一首《远方》则更能让远方显得不那么苍茫,带着几分厚重和灼热的期待:“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遥远的青稞地/除了青稞 一无所有/更远的地方更加孤独/远方啊 除了遥远 一无所有/这时石头/飞到我身边/石头 长出 血/石头 长出
七姐妹/站在一片荒芜的草原上/那时我在远方/那时我自由而贫穷/这些不能触摸的 姐妹/这些不能触摸的 血/这些不能触摸的 远方的幸福/远方的幸福 是多少痛苦”。西川的《远方——给阿赫玛托娃》,把远方用数个“一”来呈现,显得孤寂而清冷:“一片梦中的雪野”“一株白桦”到“一只木椅”“一盏台灯”“一张白纸”“一张面孔”。“一”是修饰量词的最小单位,它的出现给人以孤独感。同时,“一”又是充满力量的存在,象征着从无到有,从渺小直到伟大的力量。
天空也是远方,它代表远方所能达到的高度。台湾诗人白灵的《风筝》耐人解读。风筝是日常生活中的物象,天空是极其飘渺的物象,常见但并不普通。这首诗中,把天空和风筝拟人化,使得画面充满动感:“长长一生莫非这样一场游戏吧/细细一线,却想与整座天空拔河”,风筝在天空下飞翔,渐渐越飞越高,直到远离人们的视野,仿佛这根线拉的不是风筝,而是整座天空,于是“我”“拉着天空奔跑”。空间和叙述主体合二为一,天空不再成为飘渺的存在,而是如同触手可及、不再遥远的亲密恋人。《路标》里的“远方”更为飘渺:“他累累象贴满药方,打着心结的老兵/披着岁月的勋章,他胡乱指着/旅人唇语中的远方”。远方本就已经遥远,通过旅人的叙述,则更加拉长了目光不能及的空间,一个远方之外的空间出现。“指”本应是有明确空间定向的行为,但通过“打着心结”的老兵“胡乱”地指出,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人确信,正因为这样一种不确定,造成了空间的不稳定感。物理空间不能精确定位,文学空间于是便可以拥有无限的阐释和解读。对于老兵的人性关怀、对于战争造成两地分隔的控诉、对于岁月无情的慨叹、对于距离的追溯和思考,成为这首诗中可以寻见的个中究竟。
天空可以变形,由远及近,直逼视线。周伦佑的《想象大鸟》是把时间描写和空间书写结合的典范。大鸟可以是大鹏鸟,对于大鹏鸟的想象从远古开始;大鹏可以是鱼,从鸟到鱼,穿行的不同空间让读者倍感新鲜;大鹏鸟的天空更惹人遐想,那是十分神秘而传奇的天空。然而,作者陡转的笔锋却让形势大变:“当有一天大鸟突然朝我们飞来/我们所有的眼睛都会变成瞎子”,视觉冲击力无与伦比。作者在二维的平面内,通过文字给读者营造了一场3D盛宴。当远方的天空离我们很远的时候,读者产生一种相对安全的审美心理,而“当有一天”这两句铺陈而来的时候,则瞬间肢解了读者的安全感,给读者带来精神上的高度紧张,同时伴随着冒险的无限的刺激。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宗教文化的影响,天空往往被寄托以神灵之所。无论是中国土著宗教道教,还是佛教、伊斯兰教,神灵们尽管国籍各异,但都居住在天空,或者是天宫,或者是西天,或者是天堂。天空是人类目之所及甚至触手可及的已知,却又是遥不可及的未知。这恰恰和宗教的精神内质相吻合:神在成为神之前,都是历经人间苦难,三灾九劫,而一旦成为神,则众生不再平等,神需要众生来膜拜。昌耀的《天空》就把天空视作精神之居所,有种宗教式的仰望和神秘。西川名作《在哈尔盖仰望星空》:“被群星的亿万只脚踩成祭坛/我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放大了胆子,但屏住呼吸”,更是直接表达了对于天空中幽秘力量的敬畏和崇拜。
由于阳光散射的缘故,蓝光被人眼大量捕捉到,晴朗的天空呈现的是蔚蓝的形态。李琦《秋天的北方》:“……天空澄澈,蓝得让人想哭/联想到那些纯洁的事物/在这样的天空下获得生命/做人或者植物/都感觉是一种幸运”。蔚蓝,成为天空的颜色,王雪莹《蔚蓝的忧伤》,便表述的是蔚蓝的远方带给人期待和向往:“沿天空的道路/抵达无边的蔚蓝/候鸟的荣耀 就是/在宿命的鞭子下穿越/荆棘与荨麻铺就的山水/而 每一种色彩都具备了/更多的含义 比如‘蔚蓝’/不再单纯指代明澈和愉悦……”。“蔚蓝”指代天空,甚至比天空本身代表更多的内容,如纯净、清澈而魅惑的存在。
二、孤独——都市文明的精神体察
孤独使诗人具有精神上的超越感。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首先营造的是一种寂静空冷的气氛,而紧接着“念天地之悠悠”拉宽了思维的长度,把天地都压缩到自己所思所想的范围,“独怆然而涕下”的情绪显得不突兀,反而有一种酣畅淋漓之感,这就是一种伟大的孤独。孤独者并不都是诗人,但诗人会把孤独的特质带到诗歌中去。都市文明下的诗人,产生出一些不同于古代社会的孤独类型。诗人在现实生活中倘若展示孤僻生冷、清高严肃的一面,会让人觉得十分不舒服,但是在诗歌里,这些特质反而会成为独树一帜的或者震撼人心的书写元素。如海子的《在昌平的孤独》:“孤独是一只鱼筐/是鱼筐中的泉水/放在泉水中/孤独是泉水中睡着的鹿王/梦见的猎鹿人/就是那用鱼筐提水的人/以及其他的孤独/柏木之舟中的两个儿子/和所有女儿,围着诗经桑麻元湘木叶/在爱情中失败/他们是鱼筐中的火苗/沉到水底/拉到岸上还是一只鱼筐/孤独不可言语/1986年/”。除去个性的孤独之外,海子的孤独极具普范效应,是一种现代性的孤独: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文明进入城市文明,作为敏感的个体,海子感触良多。八十年代的昌平,算是在喧闹的北京城中难得的一块平静之地,但依然让海子找不到归处。城乡相遇时灵魂失落的不光只有海子,诸如骆一禾、昌耀,都是这一类的孤独者。对比而言,顾城式的孤独显得独特,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对撞之后,理想破碎的孤独。顾城是当代诗人中的纯粹主义者,他的童话世界根本无法在现实中实现,是背对现实所做出的异想天开之构想。他的世界具有强烈排他感,他的孤独是坚决的,而且很难改变。对于自我的过分重视,是顾城诗歌的特点,如顾城《灵魂有一个孤寂的住所》:“灵魂有一个孤寂的住所/在那里他注视山下的暖风/他注意鲜艳的亲吻/象花朵一样摇动/象花朵一样想摆脱蜜里的昆虫/他注意到另一种脱落的叶子/到处爬着,被风吹着/随随便便露出干燥的内脏”。
诗人把自己架空于人群之上,刻意营造孤独感,这样的动机有其内在原因。首先,给诗人主观上提供了独立思考的空间,使得他们可以在相对自由的状态下发挥;其次,诗人必须采取批判的手段才会让文字充满深厚的力量。没有批判的诗歌没有深度和厚度,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诗人孤独的精神坐标,也会让他放开手脚有力批判而不顾及其他。此时的抒情、思考都与生命交织,具有震撼力。如东篱的《背着风筝穿过大街》,风筝意象的使用惟妙惟肖。风筝本就是极其孤独的物像,和作者的孤独交相辉映。风筝的“飞”,是带着镣铐的舞蹈,而作者的“飞”,也带着对于生命束缚的拷问和对于无家可归的最后挣扎、叛逆。
诗人在诗歌中可以数次用“一”来强调孤独。如胡杨《侧面》:“一匹马的悲伤,一头骆驼的荒凉/是阿尔金/一眼泉水的孤独/一只鸟怎么也飞不出的湖泊/是阿尔金/一个人带上马的悲伤/骆驼的荒凉/还有那一眼泉清凉中的孤独/还有那鸟翼上/薄薄的霜/阿尔金就更远了/远在人心灵的高处”。有的诗人在此基础上还要加以变化,从“一”中生发出多,主体的想象世界喧嚣而丰富,但这是以动来反衬静,以热闹来反讽孤独,是一种更为深刻的孤独。如华万里《一个人的夜晚》:“一个人的夜晚也有许多虫声站在身边/它们把草叫得很响,把荷塘/叫得更圆。它们好像在告诉我:一个人/独处不可想到孤单,一个人/看荷花不要全部看完。尤其是站在月下/有着亲密的影子。尤其是/妹妹睡在藕里,还没有出来。想到这些/我就从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我就从两个人变成了三个人或者五个人/我就像虫声一样亮了起来/亮得很震惊,亮得很宽/偶尔,还露出细微的闪电”。
孤独是都市文明的产物。前文曾经就城市的书写做了一个粗略的勾勒,诗人对于城市中的日常生活说不上满意。诗歌中经常会采取对象化的方式,将城市中的孤独者描绘一番。如三米深的诗《天桥上的乐队》:“五个盲人并排坐在天桥上/用不同的乐器合奏《两只蝴蝶》/他们看不见世界/也可能从未见过蝴蝶/可他们还是努力地睁大眼睛/把红皮的证件一字排开/没有人知道,他们从何而来/明天又将辗转何处/翩跹在歌曲里的两只蝴蝶/定然会带着这座城市/与生俱来的孤独/扇动着翅膀,飞向相反的方向”。天桥的存在,让城市的空间更广阔,也无形之中提升了城市可用空间的高度。但天桥的存在,也让无证摊主、小偷、骗子、流浪歌手、乞讨者成为流动的风景。在城市中天桥的地位难以稳固,它横亘在闹市之中,所起的作用有时仅仅只是分流以缓解交通压力,而以上这些人的存在,给天桥增添了许多另类的注解。一个城市天桥数量多,除了给城市增添一道道靓丽风景线之外,也同时证明城市中人口之多。在汪洋人海中,每个人都渴望寻找自我的位置,满足自我的存在感。正如汪峰的《存在》歌词中所描述的那样;“谁知道我们该如何存在/生命的尊严已沦为何物/是否找个理由,继续苟活/还是展翅高飞,保持愤怒。”城市中的那些默默活着的底层人民,茫然的生活方式让人动容,他们的生存只出于本能的需要,或者说只来源于生命意志。
诗人同时也可以被归类为知识分子。一个优秀的诗人,必然是出色的知识分子。不同文化形态下渴望被认同的孤独,是知识分子的困惑,也属于诗人的常见症结。如骆一禾的《小人物》:“在没有掩饰的无耻面前/我很孤独/没有我/一切都堂皇正大/只有我不可以有我/只有我不正大/只有我”。诗人在前现代与后现代思考方式中抉择时,也产生了孤独。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极为不均衡,东西部、南北方差异极大,这就造成各个地方的诗人思考方式的不同。选择哪一种生活方式,就要采取那一种生活方式所许可的思考方式。改革开放之后,广东成为炙手可热的热点地带,许多人因此开始学习粤语,学唱粤语歌,随着港台明星涌入,人们开始学习港台腔,并不是那么具有听觉快感的嗲声嗲气,成为年轻人膜拜的主流,日韩流、欧美风的侵袭,表面看是一种文化形态的入侵,实际上是一种思考方式的渗入。在多元化的今天,许多人丧失了本源文化,根性文化的脱落,使得一些人享受到了彻头彻尾的孤独和空虚。如芒克《重量》所描述的那样:“……我们活着/我们仍旧活着/人活着就是一种奇迹/人人都是幸存者/人类永远是灾难的主角/就因为我们是人/我们是人/小心,一不小心/我们便可能会成为灾难的同谋”。
然而,当诗人在书写孤独的时候,他的孤独就已经得到诗歌文本的疗伤:“人在诗歌中,可超越所有社会的孤独和距离,谈及任何东西。这些文学作品用崇高而优美的语词,战胜了现实中的孤寂,它们甚至可以把孤寂表现为一种形而上的美。罪犯和圣徒、王子和仆人、贤士和愚夫、富贾和穷汉都可以对话交流;其自由奔放,可谓是真理之诞生。艺术和艺术人物的纯洁人性所表现出的统一体是非实在的东西:他们是出现在社会现实中的东西的倒影。”[5]13这也正是诗歌的玄妙之处。
三、结束语
诗人的情感本是极其个性的、主观的存在,但通过文本载体体现出来,则显得并不虚幻。诗人的空间情感也是独特的、属于个体的经验,但由于诗人和非诗人所处的环境会有重合,因此他们的情感经验也一定有所交叉。“区别真正的艺术与虚假的艺术的标志,就是艺术情感中的真挚与否。赤子之心,至性至情,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能感动自己,才能打动别人,从作家艺术家心里流出来的作品,才能装进欣赏者的心里。可以说,作家艺术家要进入某种情感的境界,才能进入艺术创作的境界。”[1]182在诗人诗作中,空间情感的表达也可能会产生若干心理图式,从而参与并影响普通人的记忆建构。空间情感形式中没有产生心理图式的部分也并不是无用的。在读者阅读的过程中,空间体式和空间意象是第一顺序被接受的,读者接受之后,会暗自将诗人的情感体验妄加揣测,这样的揣测有可能偏离了作者的本意,对于诗歌而言,并不全是坏事。“误读”的出现,一方面增加了诗歌的可鉴赏性,另一方面,读者的参与是与诗人合作的过程,一种情感的生发要靠诗人,但多种情感的合成要靠诗人和读者的共同运作。当读者成为诗人的合作者,一首诗歌就由诗人独特的情感表达而走向大众化情感表达,从而有可能再次产生“共鸣”,形成心理图式:“情感主体的自我是被过去缠绕着的,这种过去是一个在人们的社会性和社会相互作用中发现其关系的过去。这个由无数个体所体现的过去,提供了一个只有以它作为根据,才能对人们此时在世界中从事的活动进行判断的参考框架。”[2]141诗人需要注意的是对自身的情感经验进行甄别,时刻注意去除极端化的情感。极端的情感并不一定让读者接受,过于个性化的情感经验也难以得到更深的体会,反而会在读者那里产生不良的偏差,这种性质的“误读”是诗人所不希望看到的。诗人谨防在创作时用一种虚假的情感性来要求读者:“则虚假的情感性,或虚假的情感理解产生于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即每个人错把自己的感受当成了他人的感受,并把自己的感受解释为他人的感受。”[2]238
[1]林建法,管宁.文学艺术家智能结构[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
[2][美]诺尔曼·丹森.情感论[M].魏中军,孙安迹,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91.
[3]吴晓,曹苇舫.论意象的存在形态与情感空间的创构[J].浙江社会科学,2003(4):178.
[4]吕进.新诗文体学[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262-263.
[5][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李小兵,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