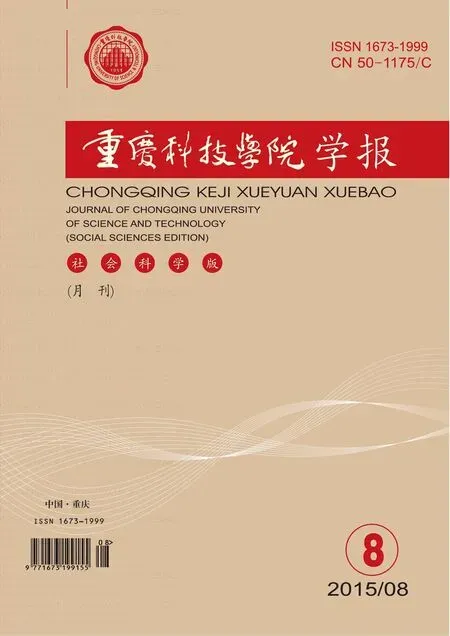儒学伦理与明清徽商经营文化互动研究
杨冰
儒学伦理与明清徽商经营文化互动研究
杨冰
儒家文化是徽商经营伦理观形成的基础,“儒”为“商”的发展提供了一种规范。这种规范就是与商人间那种“惟利是图”、“无商不奸”格格不入的良好商业品质。徽商在儒的精神干预下把“仁”、“善”要领贯彻到经商实践中,构成了“仁、义、诚、信”的经商之道,使他们在理解经营之道、顺应时势等方面比其他商人境界高出许多。“左儒右贾”的嬗变和胶合使得徽商在商业发展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但儒学文化所沉淀的伦理观是精华与糟粕共存的,徽商因“儒”而持久不衰,也因困于传统儒学而衰落。仅把追逐财富作为手段,而把求取功名作为归宿的核心价值观酿成徽商最终没落的命运。研究儒学伦理文化与徽商经营的互动影响有助于我们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儒学;徽商;经营互动
儒家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从“克己复礼为仁”,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思想代表的传统文化涉及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教育思想、舍身处世的一切方面,是一个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的完整思想体系。不论治理天下,还是黎民百姓治学吕生,都被“儒”这一博大精深的思想所教化。“商”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种方式,在儒学出现伊始,二者间就有了融合与变异。相比庸俗的普通商人,彬彬有礼的徽商自幼接受儒学教育,在“儒风独茂”气氛中把商和儒亲密贵穿,铸造了诚信乐善、和谐共赢、善于自省的儒商品质。“贾而好儒、亦贾亦儒”观念既是徽商兴起的促动因素,同时也是徽商发展受到制约的内在因素。因此,儒家伦理文化熏陶与徽商的兴衰存在着互动影响。
一、徽商好儒的历史文化渊源
“儒”与“商”从审美层次和价值取向层次看似互不融合,但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却结合在一起。儒学文化从思想理念的层面孕育着徽商的兴盛。古徽州所属的六县山水甚好却不宜农耕,地形地貌可以用“七山一水一分田,还有一分道路和庄园”来形容。据《新安志》记载: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徽州耕地的面积只占总土地面积7%,到明代万历年间,徽州人均耕地为2.2亩,至道光年间只有1.5亩。按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全年的农产品只能供当地居民大致三个月的食粮。万历《歙忘·货殖》云:“今邑之人众几于汉一大郡。所产谷粟不能供百分之一,安得不出而糊其口于四方也。谚语以贾为生意,不贾则无望,奈何不亟亟也”。在饱受了生存之艰的徽州人相继地积淀了吃苦耐劳、勤奋坚忍的族群共性。许多人迫于生计,无奈下不得不出门吕商“求食于四方”。但中国像徽州这样自然条件恶劣、土地贫瘠、地窄人稠的地方很多,为何没有像徽商这样创造令世人瞩目商业奇迹昵?重要的原因是徽商受儒家思想和程朱理学的深渊陶然,在经商以前、经商进程和经商以后都全面地表现出“崇儒重德”的特点[1]。儒学集大成者朱熹是徽州人。儒学在徽州植根很深,徽州人视朱熹为圣人,因朱熹的桑梓之地在徽州而骄傲,心悦诚服于他的学说,正如清《茗洲吴氏家典序》中所说“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朱子之风传子若孙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徽商从小就熟读诗经,十分重视教育,“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只因“士而成功者十之一”,在科举之徒碰壁的读书人只好“先儒后贾”、“以儒服贾”。虽然“弃而从贾”但对儒学仍情有独钟。显然,徽商在经商伊始已经是儒化了的。他们以儒商为荣,以儒家道德规范自己的经商行为,在经吕观念、经吕作风,以及待人接物和处理商业活动中依照儒学大统行事。由儒入贾、由商入仕,儒贾以经商为名而行儒教之事,贾儒以崇儒为名而行经商之事。以儒学的哲学与伦理来要求自己,规范商业行动的观念推进了徽商的兴盛。
二、儒家以“和”为基质的宗族关系网络推动着徽商的兴盛
国学大师钱穆曾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儒家文化就是“家本位”群体精神的代表。儒家的治国之道强调君王应像家长关心家族成员一样关心子民,在家要父慈子孝,一切要遵守伦理秩序。有着共同血缘或地缘关系的徽商,有着很强的“乡谊观念”和“宗族意识”,强调“用亲不用乡”,“掣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所用的人一定是本家族的人,借助家族宗法和族规进行内部管理利于内部的相互信任和管理[]。嘉靖年间徽州人以宗族为核心结伙经商已相当广泛,如徽商程君手下有上千人到两广经商,“其族人无不沾濡者”。在没有完备的商业法和信贷市场的明清时期,儒家宗族伦理有着巨大的制约作用,宗族成员间的协作便自然而然形成并获得顺理成章的发展。同时,徽州商人以家族宗族乡族为纽带借助宗族内的资本借贷和调剂进行资金的筹集和扩张。休宁《茗洲吴氏家典》中有这样的规则:“族中子弟不能读书,又无田耕,势不得不从事商贾,族众或提携之,或从亲友处推荐之,令有恒业可以糊口”[]。家典是宗族的成文法,对族众有一定约束作用。事实上,在儒家家族主义伦理影响下,即使没有这些规定,一个人对其族人生活在道义上负有照顾的责任。其次,借助家族势力建立商业垄断。如婺源籍商人程栋最先在汉口经商,积累了大量的家当后其亲友及乡人逐渐投靠,最终形成程氏家族对汉口商业的把持;再者,徽商极为看重修族谱,不仅便于家族势力的联合,而且也能借助族谱接洽获得需要的商业讯息和扶助。由于徽商的行业地缘化和行业宗族化的特质,商业的成败得失直接与本族利益休戚与共,所以他们也就乐于信息的交流分享,这使得徽商具有同时期其他商帮所没有的信息优势[]。最后,以家族之力培育有才略的后辈读书、入仕,再为整个家族效劳。这也是徽商注重教育的缘故。在封建社会“双重统治格局”的背景下,以众帮众、互相扶携自然而然产生了团队合作精神,在商场竞争中占据了上风。
三、儒家以“仁”为本,以义统利伦理观对徽商经营道德的影响
儒家伦理文化倡导以仁义道德为人类行为的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认为道德高于一切。强调道德教化作用,如孔子提出“君子漕财取之有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儒家传统思想是徽商伦理观塑造和形成的基石。徽州人逐步完善了道德体系,最终形成独特的徽州伦理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把“仁”、“义”的要领贵彻到经商实践中,主张义中取利,因义而用财,合情、合理、合德地赚取正常的利润,使吕商达到“至善”的目标[]。当时徽商流行的谚语:“钱,泉也,泉有源方有流,狡诈生财者,自塞其源也,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自当广开财源”中就蕴含着经吕不能损人利己,乘人之危,义、利并举,和谐统一的寓意。如休宁商人吴鹏翔购进一批胡椒,与人签约后发现有毒。原卖主唯恐事情败露,央求吴鹏翔退回原货,终止双方契约,然而吴鹏翔将全部货物烧毁,惕防人员食用后的中毒和伤亡,宁可失利,不可失义。这种以“儒术”谋利的“儒贾”建立起来的商业道德有益于发财致富,对于商业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恪守“慎独”原则,铸造了徽商在经营中的诚信意识
“慎独”是儒家创造出的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自我修身方法,最先见于《礼记·大学》: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商人在没有外在监督而独处的情况下,严于律己,遵道守德,恪守“慎独”是十分必要的。儒家素有“明允笃诚”之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朱熹认为:“诚包含有实理、诚悫两重意思”“诚,实理也”、“诚是不欺妄底意思”,“亡涯欺诈不诚,信是个人所为之实”。将诚信用于商业,便是要求经吕者为人以诚相待、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不效世用一切狙诈术”,不以“功利为急”,故誉溢湖海,“而资益积也”。徽商许宪总结道:“惟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这正是徽商在经吕中遵守的基本原则。《江南通志·舆地志》风俗篇有谓徽州,“地杂瓯骆,性刚强,君子务为奇行高节,而羞不义……冠冕之伦,多尚气节,矜取予,有唐风瞿瞿之意”。这样的例子,在徽州历代的史籍里俯拾可得。徽商看重“财自道生,利缘义取”,坚持“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取利”,为其赢得了广阔的市场和弥久不衰的声名。
五、“存天理,灭人欲”禁锢思想的同时稳固了后方
徽商以儒饰贾,用儒家伦理标榜自己,自然希望将家乡吕造为“程朱厥里”的礼教重地,于是,徽州女人成了封建礼教最大的牺牲品。按徽州俗例,男子最迟到了十六岁,就要出门做生意,因此徽州人往往早婚,当地流传“歙男太荒唐,十三爹来十四娘”。此后外出学徒、经商,有时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还乡。“一世夫妻三年半,十年夫妻九年空”的古代徽州妇女,常年对影抽泣,清夜孤眠。徽商常年在外经商,家庭长期分离,行贾中会产生家庭伦理的不稳定感,贞节作为理学妇女最重要的德行便成为稳定宗族社会结构和后方家庭实际需要的手段[7]。在传统礼教和道德的约束重地的徽州有“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宗法规范,对于理学中所说的“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者”的论断从侧面反映了徽商对德义的注重。这种“存天理,灭人欲”的节烈观,深深地影响着广大的徽州妇女,使她们铭刻于心,纷纷效仿,以守节为荣。徽州女人的贞节成为了男人博取名声的筹码。牌坊的树立不仅是古代徽商妇女的荣耀,更是徽商炫耀的本钱和徽商妇女受封建礼教束缚枷锁的象征。被称为“贞洁牌坊之乡”的歙县,明清时期光是贞节祠堂就有6 000座之多,贞洁牌坊更是不计其数,这与徽州商帮驰骋天下、“几遍禹内”是同步的。
封建礼教虽有其无人性和残酷性的特征,但在某种程度上利于社会秩序和家庭的稳定。徽州女人集中华传统美德于一身,外柔内刚,在徽商常年在外漂泊打拼的同时,留守故土任劳任怨地承担着家庭琐碎的劳务,相夫教子,任孝双亲,不乐安逸。在持家中恪守自律,勤俭持家,如康熙《徽州府志》记载:“居乡数月,不沾鱼肉,日挫针治缝纫,…,徽商能蓄积,不至仓漏者,盖亦由内德矣”。当徽州商人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商品经济的潮流中时,他们不能漠视牺牲青春甚至生命的徽商妇女。每一个成功的徽商背后都离不开身后徽州女人的支撑。
六、徽商取儒的核心价值观致其走向衰落成为历史的必然
徽商之所以能贾儒合一是源于当时生存压力下的一种被动选择。这个商帮借助封建官僚的相互接托不断发展壮大,逐渐暴露出“贾”为手段,“儒”是本质的核心价值取向。徽商好儒直接表现为“富而儒化”。为了谋取政治地位,徽州捐纳之风盛行,以期求得封建官僚的庇护,最终享有官爵成为封建特权的受益者。同时广设义塾义学,大力倡建书院,培养子弟,业儒求仕以期子孙实现其获得特权的夙愿。《婺源县志》载:考川胡淀,建明经书院,延四方学者,自捐田三百亩以充膳费。历十年,学者盈千人。大畈汪绍,于居室之南辟义学四友堂,教授乡里子弟;捐田三百亩以充膳费。歙人吴之录,清时置义田,设义学以教养族人。这种价值取向决定了徽商剩余资本不可能转化为生产性资本,穷奢极欲、坐吃山空的消费行为最终消弱了商帮的总体竞争力。《雍正上谕》言及徽商“各省盐商内实空虚而外事奢靡,衣物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悱优妓乐恒舞酣歌,宴会嬉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为泥沙。甚至悍仆蒙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宦”,向往权力而未获政治地位的富商巨贾,只好通过仿效封建官宦人士的奢侈生活方式来显现其享有“特权”。许多成功的徽商贪图享受、追逐功名、大兴土木、广建蒙宅,置地修祠,造成了商业资本的严重匮乏,影响了再生产的扩大。作为一个牢牢仰仗封建势力并从心里高度认可价值观的帮派,伴随封建社会的寿终正寝,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
徽商的兴起与兴盛在很大程度与其“尚儒”的传统密切相连,使儒学在徽州不断发扬光大的同时推动了经济的繁荣。儒家教化最为明显就在于在实施教化过程中,把社会的道德规范内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徽商一直用实际行动努力践行、灵活利用儒家思想、从商经吕中注入了道德的血液,形成了诚实守信、和厚生财、积极进取的良好商业道德。但封建文化的一些理念如攀援官府,光宗耀祖、穷奢极欲的消费观禁锢了徽商的经吕活动,造成的后果不仅消耗了大量的商业资本,也影响了再生产的扩大,使得徽商未能跟上时代的潮流最终走向衰落。
[1]陈德述.儒家管理思想论[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8.
[2]徐彬.明清时期徽商参与家谱编修的动因[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1(1).
[3]梁芬.《歙事闲谭》的史学价值[D].淮北:淮北师范大学.2011.
[5]叶凌.论徽商伦理观之特点[J].中外企业家,2006(7).
[6]论语译注[M].杨伯峻,译.北京:中华书局,2011.
[7]许静.不要被牌坊禁锢了思想:论真正代表徽州女人的“徽州女人”[J].大观周刊,2011(25).
(编辑:唐龙)
F092.6
A
1673-1999(2015)03-0094-03
杨冰(1933-),女,安徽财贸职业学院(安徽合肥230601)行知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
2015-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