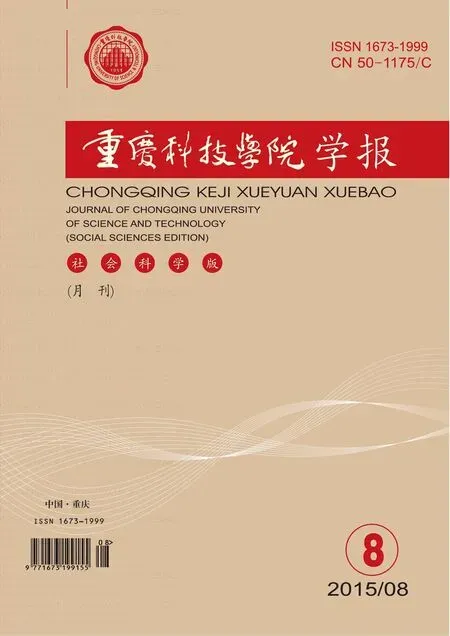盗窃网络虚拟则产的行为走性探讨
——基于刑法解释理由
费翔
盗窃网络虚拟则产的行为走性探讨
——基于刑法解释理由
费翔
盗窃罪的对象是“财物”,不应包括“财产性利益”。将“财物”解释为“财产”,属于以目的解释理由对刑法文义的类推。刑法特剔规定盗窃商业秘密的行为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承认盗窃虚拟财产成立比侵犯商业秘密罪更重的盗窃罪,存在体系解释矛盾,将造成侵犯商业秘密罪与盗窃罪法条竞合处理的冲突。对盗窃虚拟财产行为,宜按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或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定性。
虚拟财产;财物;财产性利益;刑法解释;罪刑法定
我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已逾20年,网络游戏产业、社交产业蒸蒸日上、初具规模,但对如何保护网络虚拟财产的问题仍然聚讼纷纭。刑法层面,争议最大的是盗窃网络虚拟财产是否构成财产犯罪。问题的关键是盗窃罪的对象(财物)是否应该包括网络虚拟财产。这涉及对刑法用语含义的解释。将虚拟财产解释为财物,是否超出了“财物”的文义而走向了类推解释?将盗窃网络虚拟财产的行为定性为盗窃罪,是否不需要顾及同样使用“财物”一词的其他地区刑法典的解释?是否忽略了体系解释的要求,而存在解释逻辑上的矛盾?
一、虚拟财产性质认定中目的与文义的关系
在刑法解释学上,文义与目的是决定解释结论的两个最高位阶的解释理由,正确的解释结论必须同时符合法条的文义与法律的目的。实质解释论认为,对构成要件的解释必须以法条的保护法益为指导,而不能停留在法条的字面含义上。“解释一个犯罪的构成要件,首先必须明确该犯罪的保护法益,然后在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内确定构成要件的具体内容。”[1]由此可见,在目的与文义这两个同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解释理由中,目的是优先被考虑的,而不是首先从文义出发。这就意味着:对刑法用语的解释限度与处罚必要性或处罚妥当性(保护法益的目的)呈正比例关系,处罚必要性越高,对刑法用语进行扩张解释的必要性也越高;刑法用语的解释限度与刑法用语的通常含义成反比,处罚必要性越高,对刑法用语按照通常文义进行解释的必要性就越低。即:解释的限度=处罚必要性/通常文义。所以,实质解释论者对解释结论是否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说明,依赖于是否超出了“可能具有的含义”,如果超出,就是类推解释;否则,是罪刑法定原则所允许的扩大解释。相应地,肯定盗窃虚拟财产构成盗窃罪的前提,就是将虚拟财产的财产性利益归入《刑法》第264条的“财物”,没有超出“财物可能具有的含义”。张明楷教授认为,刑法中的财物不仅包括有体物与无体物,而且包括了财产性利益,这已经突破了“财物”的字面含义。在此意义上,将虚拟财产作为刑法上的财物是可能的[2]。首先,盗窃数额较大的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具有处罚的必要性,所以有必要对“财物”作扩大解释;其次,盗窃财产性利益的行为本身具有明显的法益侵犯性,将其作为盗窃罪处罚,容易被一般人接受,不会侵犯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其三,将盗窃罪对象的“财物”解释为包含财产性利益,与《刑法》相关条文(第2条、第13条)是协调的,不产生任何矛盾[3]。笔者以为这些理由还存在着可商榷之处。
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侧面与这里“财物”的解释没有关系。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后来基于实质法治的需要,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侧面被提出,即所谓现代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它包括刑罚法规的明确性原则和刑罚法规内容适正性两个方面的内涵,旨在限制立法权。诚然,通过正确的刑法解释可以避免将刑法变得“不适正”,而将不当罚的行为排除(出罪)[4]。如果为了处罚的必要性而扩大文义(入罪),那么就是以实质侧面为理由僭越立法权。因此,所谓“盗窃数额较大的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具有处罚的必要性”,这并不是对“解释是否违反文义”的说明,而仍然是对目的解释(是否不利于保护法益目的)的强调。
是否超出国民预测可能性,应当是针对文字含义解释结论本身而言,而非针对行为的当罚性。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一个显著区别就在于:类推解释的结论超出了一般公民的预测可能性。国民对当罚性的意识与其对法文意义的预见可能性,是两个不同的问题[5]。“凡具有处罚必要性的行为,对其进行处罚,一般人容易接受,因此便没有超出国民预测可能性”,这样的论证其实仍然是以国民对当罚性的意识为根据的。类推适用也是根据刑法目的与任务的一般规定和犯罪的一般概念抽象地得出结论的[6],上述论证不是与类推解释的逻辑一样吗?
将“财物”视为“财产”是将下位概念上升为上位概念。刑法中外延最广的概念是“财产”,它包括一切具有财产价值的有体物、权利、利益等。《刑法》第2条和第13条规定:“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那么,《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其下各法条所表述的“财物”,应当作为“财产”的表现形式来理解,即将“财物”解释为具有“财产”性质的利益。也就是说,“财产”是上位概念,而“财物”是下位概念。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的“财产”,除了具有实体表现形式的“财物”之外,还应当包括股份、股票、债券等权益性财产,即财物以外的、无形但具有经济价值的财产性利益[7]。说“财物不仅包括有体物与无体物,而且包括了财产性利益,这已经突破了‘财物’的字面含义”,可是,这又是按照何种标准而将“财物”划分为“财物+财物以外的利益”的昵?分则第五章涉及多种对象,除财务以外,还有通信线路、电信码号、单位资金、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等。
综上所述,肯定“虚拟财产是财产性利益、是盗窃罪对象”的观点,理由其实只有一个:盗窃虚拟财产的行为值得处罚,不处罚不利于保护法益。这种以目的为首要出发点而弱化文义的做法,忽视了“财物”与“财产”的不同范围,为类推解释开拓了空间。
二、盗窃罪对象不宜包括财产性利益
刘明祥教授认为,确定财产犯罪的对象应当以有体性说为原则,同时法律明文规定哪些无体物以财物论。对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无体物,不得任意解释为财产罪客体中的财物[8]。与直接肯定虚拟财产为盗窃罪对象的观点相对,上述看法是否定说的代表性观点。大陆学界关于财产犯罪对象的“有体说”、“支配可能性说”、“管理可能性说”等,其概念都是继受于日本和台湾地区刑法学。
其一,大陆刑法典中的“财物”,可以按照日本和台湾地区的用语进行解释,因为作行为对象的“财物”(动产)的汉语概念具有通约性。对财产犯罪的规定中,日本与台湾地区的刑法典都运用了汉字来表述“财物”与“财产性利益”:日本使用“財物”、“財產上不法の利益”,台湾地区使用“財物”、“財產上的不法利益”。两种表述几乎一字不差,大陆的简体字与台湾地区的繁体字意思也没有区别。判断某种解释是扩大解释还是类推解释,应当根据本国的刑法用语进行判断,而不能以外国刑法的用语进行判断。日本主张财产性利益属于财物的观点之所以没有得到认可,“是因为日本明文将财产罪的对象区别规定为财物与财产性利益”,因而在我国刑法没有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分别并列规定情况下,就不应当照搬日本的解释[9]。承认财产与财产性利益在日本是并列的概念,可为何财产、财产性利益到我国便成了隶属的概念?既然日本刑法将侵犯财产性利益的犯罪作为刑法中的特别规定,那么为何不能认为我国刑法典只规定了侵犯财产而未规定侵犯财产性利益的犯罪?如果我国大陆刑法典没有规定侵犯财产性利益的犯罪,而不影响对侵犯财产性利益行为的处罚,那么,日本和台湾地区对财产性利益犯罪的规定,不都成了可有可无的注意规定?
其二,日本、台湾地区刑法典中的“财物”指有体物,不包含财产性利益。如日本刑法典规定,“以暴行或胁迫方法强取他人财物的,是强盗罪”;“以前项方法得财产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与前项同”。台湾地区的刑法典中,将财产性利益作为犯罪对象时也均有专项规定。前田雅英认为,“物”这个名词以解释为有体物最为合理[10]。山口厚认为,从保持财物概念的明确性的角度出发,有体性说更为妥当。这也是现在的多数说,或者已经是现在的通说[11]。台湾学者林山田指出,权利例如债权或其他请求权等无体物,不能成为盗窃罪客体,已是不争之论。盗窃罪的窃取客体仍以有体物为限;无体物则有待条文的规定,方能成为本罪的窃取客体[12]。可见,将刑法未专门规定的财产性利益作为盗窃罪对象,属于类推解释。对此,已有共识。
其三,日本和台湾地区的刑法典规定,盗窃虚拟财产不构成盗窃罪,而构成“使用计算机诈欺罪”。对于网络虚拟财产即电磁记录,台湾地区1992年修法之前曾规定:“电能、热能及其他能量或电磁记录,关于本章之罪(第29章窃盗罪),以动产论”;修法之后,电磁记录不再是盗窃罪的对象。对于侵犯网络游戏装备等虚拟财产的行为,台湾地区刑法典第339条规定:“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将虚伪数据或不正指令输入计算机或其相关设备,制作财产权之得丧、变更纪录,而取得他人财产者,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前项方法得财产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这是借鉴了日本刑法典第246条的规定。台湾地区司法判例认为,本罪的行为包含了无故侵入他人电脑罪、无故取得他人电磁记录罪等妨害电脑使用的犯罪,因而对于无权侵入他人电脑盗取虚拟宝物等行为,应根据“全部法条优先适用”的原则,使用计算机诈骗罪论处[13]。
总而言之,我国大陆刑法典中的简体字“财物”与繁体字“財物”概念一致,均无法包涵无形的虚拟财产这种网络电磁数据。只要刑法典的用语没有改变,那么行为对象的指涉范围就是固定的。“1997年制定刑法时,虚拟财产实属罕见。在当时的情况下,将虚拟财产解释为刑法上的‘财物’,基本上属于类推解释。”[14]103在当下,将虚拟财产认定为刑法上的“财物”,仍属于类推解释。
三、盗窃虚拟财产与侵犯知识产权罪的体系对照
法律解释不能孤立地观察某个法律规范,还要观察它与其他规范的关联。对刑法进行体系解释是文本逻辑的形式要求,也是刑法公平正义的实质要求。正义的基本要求是相同的案件必须得到相同的或至少相似的处理,只要这些案件按照普遍的正义标准在事实上是相同或相似的[14]57。刑法解释合理性的基本标准就是无矛盾。将虚拟财产认定为“财物”,继而肯定盗窃虚拟财产构成盗窃罪,这存在体系上的解释矛盾。
其一,导致刑法罪刑设置不均衡。从虚拟财产的产生和存在形态看,网络游戏装备、QQ号等是电子数据,它们始终存在于运吕商的服务器内,游戏中的武器、坐骑、金币以及QQ号码等都只是一串二进制符号,是无形的、虚拟的物品,其财产性体现在这些虚拟物品可以交易,从而为购买者提供网络服务。这些电子数据是由专业技术人员编写的,网络游戏及游戏内的人物、武器装备等是智慧的结晶,可以称之为智慧财产、知识财产。就此而言,虚拟物品与知识产权客体如著作权人发布的网络小说的整体性构思、专利权人的专利以及商业秘密等在表现方式上是相同的,它们都是无形的。但是,网络虚拟物品在法律地位上不被评价为知识产权客体,无论开发者、运吕商还是用户对一件装备或一个金币、QQ号码等都没有独立的知识产权。概言之,虚拟物品与著作、专利、商业秘密等都是一种无形财产即财产性利益,但虚拟财产的法律地位大大逊色于后者。我国刑法典也正是基于知识产权(包括商业秘密)重点保护的必要性,才特别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罪。
如果无形的财产性利益属于“财物”即盗窃罪的犯罪对象,那么同样属于无形财产的商业秘密也是“财物”,也是盗窃罪的对象。根据《刑法》第219条的规定,盗窃商业秘密构成的是侵犯商业秘密罪,而非盗窃罪。侵犯商业秘密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处10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将原本连商业秘密都不如的、可以大量复制的网络电子数据提升到盗窃罪的层面保护,而将法律地位更高的商业秘密置于最高法定刑只有7年的侵犯商业秘密罪来保护,显然违背体系解释的基本要求。
其二,导致法条竞合处理冲突。如果虚拟财产等无形财产属于盗窃罪的对象,那么盗窃商业秘密也要认定为盗窃罪,这里就存在盗窃罪与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竞合关系,而且这竞合关系属于普通法条与特别法条的法条竞合。关于特别关系的处理,一般适用“特别法排斥普通法”的原则[15],也即盗窃商业秘密等行为应当适用《刑法》第219条侵犯商业秘密罪这一特别法条。如此一来,就必然导致罪刑不相适应。有学者认为,对于特别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应当适用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法律虽然无明文规定按普通法条处理,但也未作禁止性规定,而且按特别法条处理,明显不能做到罪刑相称。适用重法优于轻法原则,必须符合3个条件:(1)行为触犯的是同一法律的普通法条与特别法条;(2)同一法律的特别法条规定的法定刑,明显轻于普通法条规定的法定刑,并缺乏法定刑减轻的根据,而且根据案件的情况,适用特别法条明显违反罪刑相适应的原则;(3)刑法没有禁止适用普通法条,或者说没有指明必须适用特别法条[16]。
侵犯商业秘密罪与盗窃罪是同一法律的特别法条与普通法条。属于特别法条的侵犯商业秘密罪法定最高刑为7年,明显轻于盗窃罪的无期徒刑。《刑法》第219条、第264条都没有“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等特别指示。那么,盗窃商业秘密的行为应当适用重法条即盗窃罪。同理,其他非法获取商业秘密等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也存在应当适用财产犯罪的可能。如此,便架空了刑法特别规定侵犯知识产权罪的立法设置。论者又指出,“由于侵犯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无形财产的行为,被刑法规定为侵犯知识产权罪,故商标权等一般不属于财产罪的对象”,不构成财产犯罪[2]。可见,论者排除了盗窃商业秘密成立盗窃罪的可能,没有贵彻提出的法条竞合处理原则。
总之,若承认无形财产包括虚拟财产属于盗窃罪对象,那么没有理由否认商业秘密等无形知识财产也是盗窃罪对象。“作为财产犯罪对象的财物,并没有特别的限定”[9]。如此,侵犯商业秘密罪与盗窃罪等财产犯罪存在法条竞合关系。
四、盗窃网络虚拟财产不构成盗窃罪
刑法解释不能以处罚必要性、法益保护必要性推断刑法用语的含义,否则必将虚化罪刑法定原则,而为类推解释提供机会。虚拟财产在服务器内只是一串电子数据符号,有人愿意为这些没有实际价值的电磁记录提供巨额对价,并不意味着这些虚拟财产的价值就增长了;盗窃这些电磁记录不等于直接盗窃巨额现金。例如:甲为得到自己喜欢的一块石头支付了10万元,乙准备了10万元去买汽车。行为人A盗窃了甲的石头,行为人B盗窃了乙的10万元现金。对A、B行为的定性,显然结果不应该是完全相同的。盗窃虚拟财产给人造成的损失,只是电磁记录所对应的服务,而非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他人购买虚拟财产所支付的巨额对价,只是一种间接损失。对盗窃网游装备、QQ币等虚拟财产的行为,应当适用《刑法》第285条、第286条,按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或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定性,而不能以盗窃罪论处;否则,将面临文义解释、比较解释、体系解释的矛盾困惑。如果某些盗窃虚拟财产的行为,不适合按照侵犯计算机犯罪处罚,解释者也不能越俎代庖,法律漏洞的弥补应当留给立法者,这是遵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毕竟解释不是万能的,尊重法律就应该同时尊重法律漏洞。
[1]张明楷.实质解释论的再提倡[J].中国法学,2010(4).
[2]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3]张明楷.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02.
[4]苏彩霞.罪刑法定的实质侧面:起源、发展及其实现[J].环球法律评论,2012(1).
[5]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28.
[6]曲新久.区分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路径新探[J].法学家,2012(1).
[7]黎宏.论盗窃财产性利益[J].清华法学,2013(6).
[8]刘明祥.财产罪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38.
[9]张明楷.非法获取虚拟财产的行为性质[J].法学,2015(3).
[10]前田雅英.日本刑法各论[M].董璠兴,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10:148.
[11]山口厚.刑法各论[M].王昭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99-201.
[12]林山田.刑法各罪论:上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11-212.
[13]乐瑜.刑法分则体系重点整理:个人?社会?国家法益[M].台北:新保成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7:377.
[14]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95.
[15]陈子平.刑法总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453.
[16]张明楷.法条竞合中特剔关系的确定与处理[J].法学家,2011(1).
(编辑:米盛)
D924.3
A
1673-1999(2015)03-0023-04
费翔(1991-),男,南京师范大学(江苏南京210023)法学院2014级刑法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刑法解释学研究。
2015-0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