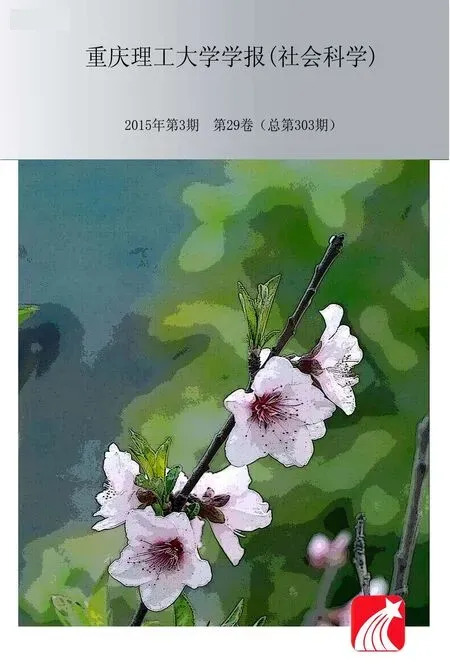何止译者: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活动之译员考析
刘 黎
(重庆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074)
一、前言
1793年乔治·马戛尔尼勋爵(Lord George Macartney)率领规模庞大的英国使团访华是中英关系中的重大事件,它是奠定两国正式外交的里程碑。尽管这次由英国发起的外交多被视为以失败告终,但它却成了中英文化交流史和中英外交关系研究的热门话题,经久不衰。
近年有学者开始涉猎英使团访华的翻译研究领域,并出了一些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如有学者对“英国国王乔治三世致乾隆皇帝国书”的翻译进行了详细解剖[1],也有学者将清宫档案中保存的外交文件的译文,与当代学者译出的使团成员笔记作了对比研究[2],还有学者宏观地讨论了当时翻译的历史局限和影响翻译的问题[3]。然而,谈及中英双方沟通的桥梁——译者时,论者要么匆匆带过,要么忽略不提。译者是谁?他们如何被选定?他们在这次外交活动中起到什么作用?这些问题的研究能帮助我们了解特定历史时空下译者的特点,并可引发我们对历史语境与译者关系的思考。
二、历史考析
毋庸置疑,译者是任何翻译行为的主体。在英使访华事件里,中英双方都认识到翻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物色和安排合适的翻译人员对双方来说都绝非易事,这要归因于中英关系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封建中国历来的对外政策。
明末海禁,严格限制中国人同外国人来往。英国东印度公司伦敦总部的人曾一度希望,英王詹姆斯一世能写封信给中国皇帝,获准英国商人到中国贸易,但该公司驻万丹(Bantam)的主管在1617年写信泼冷水说“没有中国人敢翻译并呈递这些信件;根据该国法律,这样做是要获死罪的”[4]10。清王朝建立后,沿袭明制,闭关政策更甚。大约自1715年,中国通事说一种新奇的“中英混杂行话”(pidgin English),它成了在广州贸易中广泛使用的语言[4]67。但这种语言难登大雅之堂。英国大班们苦不堪言,他们“经常难以找人把中文文件翻译成英文,并把他们的申诉正确地翻译成中文”[4]75。
当时中国通事地位低贱,随时有生命危险,英国人有关中国通事被戴镣铐和投监情况的记载屡见不鲜[4]97,103。在这样险恶的情形下,为拥有自己的翻译,1736年英国“诺曼顿号”船长里格比于宁波贸易时,曾留下一英国少年,让他偷学中文,此人便是洪仁辉(James Flint)。没曾料到,此举导致了1759年的“洪仁辉事件”,洪本人后在澳门被圈禁3年,他的中文老师、为其写中文诉状的刘亚匾被杀头。“洪仁辉事件”后,为“防范于未萌”,清政府出台了《防范外夷规条》(1759),其中第四条规定“外夷雇人传递信息之积弊,宜请永除”[5]。在广州的外国人受到更加严密的控制,而中国人也更不敢与外国人交往。清政府的强硬政策激起外商尤其是英国人的强烈不满,累请撤销无果,最终导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在此之前,洪仁辉、末文和巴顿(Thomas Bevan and Barton,1753年由东印度公司派往南京学汉语)等英国苦心经营培养出来的翻译均已作古,所以马戛尔尼无法在英国物色到翻译。
清政府虽然有培养译员的外事机构,如清初设立的会同馆和从明朝接手过来的四译馆,分别主管朝贡外交和翻译事务,但除使用汉字或东方语言的周边朝贡属国外,四译馆根本不可能胜任越来越多的涉及西方国家的外交事务。18世纪初,中俄交涉日趋重要,需要把来自俄方的拉丁语文件译成满文,将北京发出的汉文或满文文件译成拉丁文,清廷于1708年设立了俄文馆(在1862年并入同文馆);不仅如此,还于1729年设立了翻译馆,“教授旗籍子弟以拉丁文,俾能在中俄交涉中任译事。主馆事者为巴多明;多明卒,君荣继掌馆事,兼拉丁、满语通译”[6]690。但据钱德明神甫说:“1729年设翻译馆,此馆仅存15年,诸馆生从未任译员。”[6]515这些举措都是因对国际形势的误判而作出的错误决策,没能培养出能应对半个世纪后以英国为主导的外交翻译人才。因此,当马戛尔尼使团在1793年叩开中国大门时,中方没有通晓英语、熟悉英国国情的本国人可供委派。
三、译者何人
正是基于上述历史原因,中英双方为物色和安排译员事宜颇费周章,最终选定的译员都是双方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
英使团在筹备过程中深感寻觅译员的艰辛。正如副使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所说,“有一个绝对必要的,但是难以物色人选的职务,那就是中文翻译”[7]35。当时英国上下找不到一个懂汉语的人;而到广州当地物色翻译也不恰当,因为就算少数广州人懂得英文或葡萄牙语,但他们的外文知识非常有限,难以应付买卖交易以外的事项[7]35;最终使团决定到欧洲大陆寻找曾去过中国并学会了汉语后来又回国的人,或者出国学会了任何一种欧洲语言的中国人[7]35。斯当东被派往法国巴黎物色翻译未果,又辗转到意大利,在那不勒斯专门培养中国籍教士的中国学院(Chinese College)找到两位中国神甫——周保罗(Paolo Cho)和李雅各(Jacobus Ly)。关于这两位神甫的生平资料不多:周保罗不在方豪考证的同治前欧洲留学生名单内;李雅各汉名李自标,原籍甘肃武威,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并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与另外7位中国青年一起去欧洲学习传教[8]383,393。在清廷文件里,李雅各被称作“通事娄门”,这其实是Plum不太准确的音译,使团成员因他姓李而玩笑地称他为Plum(李子)先生。这两位中国神甫不懂英语,但会拉丁语和意大利语,而使团中少数高级成员懂拉丁语,在当时看来,他们已是使团翻译的最好人选,故斯当东带着他们于1792年5月18日回到英国,并许以150英镑年薪聘他们担任翻译[9]292-305。
另外,副使斯当东的儿子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以马戛尔尼见习童子(page boy)的身份随团去中国。一路上小斯当东跟随中国翻译学习中文,进步较快,其父不无得意地在回忆录里称赞他虽然学习不够努力,但感觉敏锐、器官机能灵活,容易找到学习中国语言的关键,并正确运用[7]247。小斯当东在必要时能充当一名相当称职的翻译[10]88。使团船队到达澳门后,两位中国翻译之一周保罗执意与搭船回国的另外两名中国神父一起离团上岸,如此一来,使团繁重的翻译任务就落在了李神甫及小斯当东的肩上。
中方译员的安排同样面临困难。英使访华的消息早在使团出发后不久就通过广州洋商蔡世文传达到广东巡抚郭世勋,并立刻上奏乾隆。广东官员担心使团的目的是要投诉广州的对外贸易,曾尝试委派两名广东商人作为译员陪同特使进京,但东印度公司认为这两名商人英语能力太差,无法胜任翻译;而且,这两位广东商人也不情愿担任这工作,因为他们在广州的商务利益巨大,且害怕卷入中英外交瓜葛,故广东官员的安排未能成功[11]Vol.I:451;Vol.II:14。乾隆皇帝对英使团访华表现出极大兴趣,并专门下旨安排通事接待使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一史馆,内阁档案:10,见文献[12]),下同。由于当时中国并无通晓英语之翻译人才,且清政府长久以来都依赖在宫廷服务的西方传教士处理外交事务,故清廷派出七名在京西洋传教士作为翻译,他们是葡籍教士索德超(Joseph-Bernard d’Almeida)、安国宁(André Rodriguez),法籍教士贺清泰(Louis de Poirot)、巴茂正(Joseph Pairs)、罗广祥(Nicholas Joseph Raux),意大利籍教士潘廷璋(Joseph Panzi)、德天赐(Peter Adéodat),这些传教士也不懂英语,他们使用拉丁语为使团服务。
四、译者何为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拉开中英正式外交关系的序幕,英方聘请了不懂英语、毫无外交经验的中国人做翻译,中方委任同样不通英语的欧洲传教士为通事,双方译员以拉丁语为中介艰难地在清廷与英使团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在此过程中,双方译员的工作远远超过普通外交翻译的职责。
斯当东认为他物色到的中国翻译“能胜任其母语与意大利语或拉丁语之间的翻译”[7]292,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的评价过于乐观。李雅各年仅13岁时就去了欧洲,阔别20年后回国,对中国只有一些模糊的记忆。对中国文字已经生疏,同时他也不熟习中国宫廷文字的体裁格式(321)。此外,李雅各毫无中国官场经验,往往对官场上的客套话和委婉语信以为真[11]Vol.II:136,Vol.I:330。尽管李雅各的语言和翻译能力差强人意,但他对英使团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他非但没有像另外那名中国翻译周保罗一样,因害怕为外国人工作受到清政府惩罚而撇下使团离开,反而穿上英国服装、乔装成英国人,非常坚定地维护使团利益,他所做的有时完全超出了译员的职责。乾隆见礼品单上马戛尔尼的头衔被译为“钦差”,马上下令将之改为“贡使”以符合天朝体制,之后在圆明园组织安装设备,李雅各仍坚称英国送给中国皇帝的是“礼品”而非“贡品”[13]40,尽力为英国争取平等地位;在热河期间,马戛尔尼担心钦差大臣徽瑞不及时奏报,决定直接把信交给中堂大人和珅,当时没人敢瞒着徽瑞私自送信,最后是李雅各自告奋勇圆满完成了任务,据说沿途他还遭到民众骚扰和侮辱[11]Vol.II:255);当马戛尔尼拒绝练习三跪九叩觐见礼后,护送使团入京的王文雄、乔人杰两位大人要求李雅各示范一遍,但李雅各断然拒绝这一要求,维护英方尊严[14]90。有论者评价李雅各是“忠实的仆人,不称职的翻译”[15]30,这应该是对他在英使团工作的准确概括。
另外,年仅12岁的小斯当东凭借过人的聪颖和学习能力,快速地掌握了汉语并学会写汉字,成为英使团意外收获的“译员”。当使团第一次和北京派来的官员会面时,由于人数众多,李雅各一人应付不过来,小斯当东便试着做翻译,效果很不错[11]Vol.I:489;他还参与礼品单的翻译[14]100,这项任务很不简单,为突显礼物的贵重,马戛尔尼在礼品单里对各项礼物作了详细说明,所以翻译时颇费苦心;此外,小斯当东还担任誊抄中译文的工作[11]Vol.II:142,一些重要文件比如马戛尔尼有关觐见仪式的照会,虽然有人译成中文,但因害怕被认出笔迹,没人愿意誊写,最后就让小斯当东重写一遍,并加上一句“此呈系咤株士多吗嘶噹东亲手写”(一史馆,军机处档案:232)。
英方翻译人员构成比较简单,他们尽忠职守地为英使团服务,但清廷派出的由索德超为首的西洋教士翻译团,情况就更复杂一些了。
一开始索德超便获委任为“通事带领”(一史馆,内阁档案:10),即首席翻译,负责使团的接待和翻译工作,马戛尔尼在与索德超见面之前就从法籍教士梁栋材(Joseph de Grammont)处获悉索氏对使团怀有敌意,故马戛尔尼故意以法语和英语跟索德超交谈,使他无法完成翻译工作,进而谢绝他的服务。但索德超显然深受清廷重用,当马戛尔尼与乾隆在热河会面时,索德超被派往热河,负责带领马戛尔尼一行等候乾隆的接见(一史馆,文献:600),除此以外,索德超主要在朝廷方面工作。清廷档案中记载索德超进行过直接翻译的工作,如军机处档案记有马戛尔尼的信函交由索德超负责翻译(一史馆,军机处档案:198);他还负责查核他人的翻译是否准确,包括马戛尔尼送来的呈词和乾隆写给英国国王勅谕的翻译(一史馆,军机处档案:203,245);此外他还被派去察看马戛尔尼赠送仪器的运作情况(一史馆,军机处档案:146)。
马戛尔尼拒绝索德超为使团效劳,并向清廷提出委派一名懂欧洲语言的教士作翻译,朝廷便派来法国遣使会教士、法国传教会会长罗广祥,负责照顾使团。马戛尔尼对罗广祥印象非常好,并从他那里知道很多有关清廷和乾隆的情况。此外,罗广祥还参与翻译过一份很重要的文件——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的礼仪照会[14];他还与贺清泰合译出乾隆致英国国王第二道勅谕。乾隆派出的翻译团里其他传教士也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翻译工作,主要是学习安装英国人带来的机械礼品,并兼任翻译,对于使团的实际运作,他们并没有什么直接影响。
然而,这些不同国籍的传教士在北京不光是担任翻译那么简单,他们“充当各自的国家在中国的代理人,遇有涉及本国利益的事项,他们总要进行些活动”[11]。由于政治利益、宗教派系等矛盾,不同国籍的传教士都在明争暗斗、相互排斥,总的来说,葡萄牙的传教士自成一派,而其他国家的教士则结成另一集团,相互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3]。不同国籍的传教士对待英使团的态度也大不相同。以索德超为首的葡籍传教士对英使团很不友好,他们担心英国如果加深对华关系会威胁到葡萄牙在华利益,出于维护本国在华优势和对英国的嫉妒,他们对英使团的外交活动进行破坏。在去热河之前,当马戛尔尼提出让英使团先从驻地圆明园里的宏雅园移居北京城里时,索德超对此百般阻扰[13]36-37。更有甚者,在马戛尔尼使团离开中国之后,索德超等葡籍传教士仍在散布谣言,力图破坏英使团的声誉[13]37。相反,法国和意大利传教士对英国则友好得多。在他们看来,如果欧洲与中国有更好的关系,福音的传播可能有较大的进展,而他们将独得传教的好处,毕竟在传道的问题上,他们无须惧怕英国人[10]437。基于此,在翻译乾隆致英国国王第二道敕书时,两位法国传教士故意缓和原文语气,并加入一些对英王致敬的词语[16]137。可见,清廷派出的传教士翻译团都是以自身宗教利益和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为重,并没有忠心耿耿地为清廷服务。
五、结语
有论者认为缺乏合格的译者和翻译是马戛尔尼使团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3]。且不论这样的评价是否有夸张之嫌,但中英首次外交中的第三方——译者不应被忽视。由于历史语境的限制,中英双方都无法从本国人中选出合适的译员,而是非常巧合地使用了对方的人:英方聘请了中国人做翻译,而中方派出在京欧洲传教士任通事。尽管双方译员或因语言能力差强人意,或为自身利益不顾大体,在某种意义上够不上称职的外交翻译人员,但他们决不只是史书上一笔带过称作“通事”的几个名字。他们有自己的国家观、外交观和价值观,在英使团访华事件里,要么积极维护使团利益,要么竭力阻挠使团成功,他们的行为远远超过普通外交翻译的工作范畴,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甚至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1]王辉.天朝话语与乔治三世致乾隆皇帝书的清宫译文[J].中国翻译,2009(1):27-32.
[2]葛剑雄.世界上不止有中文[J].读书,1994(11):185-188.
[3]王宏志.马戛尔尼使华的翻译问题[J].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9(63):97-145.
[4]Morse,H.B.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53-1834[M].Oxford:Clarendon Press,1926.
[5]一史馆.朱批奏折·外交类:第37号[M]//清实录.第16 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8,760-1.
[6]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5.
[7]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M].叶笃义,译.香港:三联书店,1994.
[8]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上)[M].台北:学生书局,1969.
[9]Pritchard,E.H.The Crucial Years of Anglo-Chinese Relations,1750—1800 [M].New York:Octagon Books,1970.
[10]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M].王国卿,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11]Staunton,George.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M].London:Pall-Mall,1797.
[12]一史馆.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
[13]马戛尔尼.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M].刘半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14]Cranmer-Byng,J.L.et al.An Embassy to China:Lord Macartney’s Journal,1793—1794[C].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99.
[15]季压西,陈伟民.中国近代通事[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16]戴廷杰.兼听则明——马戛尔尼使华再探[M]//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