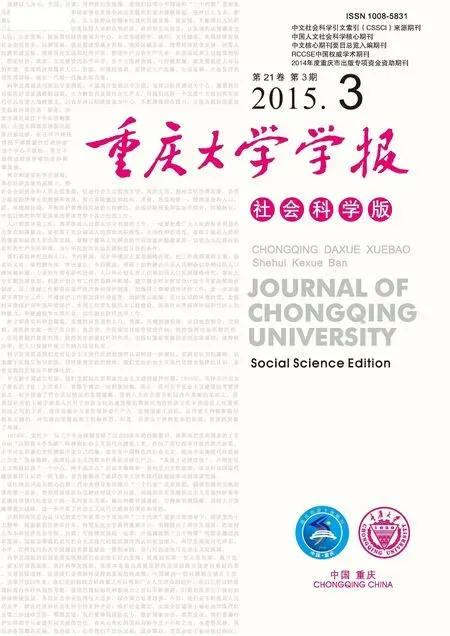左翼政治与经典构建中的玛丽•麦卡锡创作研究
张劲松
(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厦门 361021)
左翼政治与经典构建中的玛丽•麦卡锡创作研究
张劲松
(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厦门361021)
摘要:20世纪上半叶,美国左翼政治催生了一大批文学经典作品和作家。玛丽•麦卡锡及其文学创作尤为引人瞩目。其作品能进入经典主要有四个原因: ( 1)美国特殊的历史造就了她传奇的人生和不同凡响的文学创作; ( 2)她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既挑战了左翼文化阵营的男权意识,也改写了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女性传统,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 3)其小说从“实在本体”和“关系本体”两个方面为读者留下了巨大的阅读空间,具有特别的艺术张力; ( 4)她的自传体小说坦诚直面人生,注重读者的“向心阅读”,从而蕴含了丰富的经典元素。
关键词:左翼政治;经典性;双重本体;自传体小说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张劲松.左翼政治与经典构建中的玛丽•麦卡锡创作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3) :157 -180.
Citation Format: ZHANG Jinsong. A study of Mary McCarthy’s literary creation from the Left-wing politics and classical building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2015( 3) :157 -180.
修回日期:2015 -03 -12
20世纪30 -60年代的美国左翼政治催生了一大批经典作品,使美国文坛上大师如云、群星璀璨——诗人有:兰斯•顿休斯、斯特林•布朗、艾伦•金斯堡;剧作家有:克利福德•奥德兹、约翰•劳森、丽莲•赫尔曼、阿瑟•密勒;小说家有:杰克•伦敦、德莱塞、帕索斯、厄•辛克莱、玛丽•麦卡锡、拉尔夫•艾里森、诺曼•梅勒等。笔者在左翼政治与文学经典的构建视阈中,探讨玛丽•麦卡锡( Mary McCarthy,1912 - 1989 年)的文学创作,围绕着她与纽约文人和那个狂飙时代的联系展开研讨。笔者认为,麦卡锡的文学创作从个人经历与时代政治两个维度,艺术地概括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社会生活,挑战了左翼文化阵营的男权意识,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女性意识,藉此进入经典。
一、与时代相生相融的女性意识
文学经典在形成之初往往以通俗的形式出现,首先引起同时代人的关注,然后被不断阅读、阐发和评价,其经典性元素不断被确认,最终成为读者心目中的“经典”。麦卡锡自20世纪30年代登上文坛起,到作品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可,也经历了这一路径。
麦卡锡成长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时期,是当今美国文坛上颇富传奇色彩的作家之一。她特立独行,绯闻迭出,且诉讼缠身,成为文坛上的“热烈的闲话人物”。麦卡锡影响虽大,早就具备了“美国文学第一夫人”的实力,却由于我行我素的个性,被各种美国文学大奖拒之门外,直到晚年才获得爱德华•麦克道尔文学奖( 1982年)、美国国家文学奖( 1984年)以及罗切斯特文学奖( 1985年),并入选美国文学艺术学院院士。
俄国十月革命后,纽约逐渐发展为美国左翼文化的大本营,美国共产党总部就设在曼哈顿23街。这座城市地理上属于美国,但“苏联”作为一种文化象征,其影响广为弥散,无处不在。1933年,21岁的麦卡锡与
左翼演员哈•约翰斯拉德结婚,定居纽约。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麦卡锡有机会广泛阅读左翼文学作品,参加左翼文学活动,并得到著名左翼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 Malcolm Cowley)的赏识,开始在其主持的《新共和》杂志上发表作品。到1989年去世止,她先后出版近30部文学作品和多部文集、政论集,其中《女研究生群体》销量超过100万册,跃居排行榜首位,为她赢得了社会声誉;以自身经历为蓝本创作的《一位天主教少女的回忆》、《我的成长》和《知识分子回忆录》又为她赢得了传记作家之美誉,并且这3部传记小说早已成为美国传记文学的经典之作。
1937年,麦卡锡在与菲力浦•拉弗( Philip Rahv)的短暂同居之后,又结识了著名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 Edmund Wilson),翌年俩人正式结婚。这两个男人都是纽约左翼文化阵营的主将,尤其是后者在“纽约文人集群”(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中的权威地位就如同艾略特在现代派中的地位一样,可谓一言九鼎式的人物。由此,麦卡锡切入到纽约文人的圈子当中,从思想到艺术都打上了那个时代所独有的左翼激进烙印。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特殊历史造就了麦卡锡的传奇人生,使其文学创作的起点非同一般,研究者必先窥其周围的“纽约文人集群”——威尔逊、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拉弗、德怀特•麦克唐纳( Dwight Macdonald)、尼库拉•恰洛蒙特( Nicola Chiaromonte),才能了解麦卡锡的文学创作。我们必须看到,作家的创作与特定的时代密切相系,时代为她提供了契机与创作的源泉,其创作的内在精神源泉正是对时代的吸纳与扩张,作品不过是进入时代意识与想象的象征性方案。因此,在麦卡锡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中,那个已经远离我们的狂飙时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942年,麦卡锡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她的交际圈》,收入《残酷与野蛮的待遇》、《穿布鲁克斯兄弟衬衫的男人》、《无赖画廊》、《一位耶鲁知识分子的画像》、《神父,我忏悔》6个短篇。在短集中,麦卡锡以大量性暴露的描写,向社会发起女权主义挑战。短集出版后,立刻引起评论界的极大关注。考利非常赞赏《穿布鲁克斯兄弟衬衫的男人》,认为这是短集中最精彩的一篇。小说描写一位具有波希米亚性格的姑娘,在火车上邂逅一位中产阶级男士——布林,他喜欢穿布鲁克斯兄弟牌衬衫。在激情过后,当姑娘发现自己睡在布林的卧铺上,她选择离去,因为“我是我自己的轻松愉快的女人”。麦卡锡以反讽的方式运用了乔叟的箴言,折射出作家本人的波希米亚情结[1]206。阿尔弗雷德•卡津( Alfred Kazin)也认为麦卡锡在这部短篇小说集中运用反讽手法,揭示出人性的冷酷、幽暗、疑惑[2]156。威尔逊认为,柔韧似钢的行文用来评价这部短篇小说集最为恰当。更重要的是,《她的交际圈》是作家艺术风格形成过程中的作品,她大胆的性描写和以女性所独有的视角抒写的新政时期的社会生活,被后来的存在主义作家诺曼•梅勒( Norman Mailer)称赞为“引领之光”[2]283。如此一来,麦卡锡的文学创作在挑战了无产阶级文学中的男性霸权的同时,也刷新了现实主义小说中的女性传统,成为凸显新政时期女性主体意识的创新之作。
二战后,一股浓烈的反斯大林主义情绪弥漫在美国社会文化中,左翼的乌托邦政治也曾昙花一现,此时麦卡锡与阿伦特联系密切,她们积极探寻理想的社会模式。面对乌托邦的焦虑,左翼知识分子在1948年发起“欧美小组”( Europe - American Group),试图凝聚欧美的进步知识分子,在美苏两大集团之外另辟第三条道路。麦卡锡、加缪、麦克唐纳、恰洛蒙特、卡津、阿瑟•凯斯特勒( Arthur Koestler)、阿瑟•施莱辛格( Arthur Schlesinger)、伊丽莎白•哈德威克( Elizabeth Hardwick)、尼克劳•图西( Niccolo Tucci)等人都参加了“欧美小组”。翌年,“欧美小组”在经济困顿中瓦解。凯斯特勒似乎意犹未尽,坚信“欧美小组”的探索是有价值的,并把它赞誉为人类思想的“绿洲”。受此启发,麦卡锡把“欧美小组”的探索历程演绎为一部中篇小说,取名《绿洲》。
《绿洲》讲述了一群美国知识分子在厌倦了都市生活之后,从中部迁往宾夕法尼亚的一个废弃农场,去开创理想村舍的故事。他们中有作家、批评家、教师、杂志编辑以及商人。尽管这些垦殖者的政治倾向各异——有激进分子,也不乏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但积极探索未来社会出路是他们的共同追求。他们心甘情愿地过艰苦的垦殖生活,其活动场所就是小说中的乌托邦村舍,也是他们心目中宛如隔世的“绿洲”。这也是作家为他们设定的一个作为聚居的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个公共空间。这个空间尝试内部成员自由地参与公共事务而不受干涉,让他们去开创那种“真正的人的生活”。出于对未来社会前景看法的差异,他们分成了“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两派。以迈柯•德莫特为首的“理想主义者”认为,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危险——缺少圣徒、犯罪频现——这些都是必然的;以陶布为首的“现实主义者”则认为,村舍处于发展时期,应该及早消除此类丑恶现象。两派看似针锋相对,实则都只注重村舍居民的精神探索,而忽
视经济建设。随着他们之间的纷争愈演愈烈,在经济短缺的情况下,乌托邦村舍最终曲终人散。两派之间的思想纷争是贯穿小说始终的线索,藉此展现出麦卡锡的乌托邦政治理想。
《绿洲》出版后,被阿伦特称赞为“一部名副其实的小杰作”[3]。阿伦特如此关心这部小说,是因为她的“行动理论”( theory of action)不仅启发与影响了麦卡锡,而且直接成为小说的探索主题。麦卡锡自1944年结识阿伦特以来,俩人不断进行思想交流与碰撞,阿伦特的“行动理论”让麦卡锡坚信对人类心灵的探索是有意义的。《绿洲》正是俩人思想互动的艺术结晶。
20世纪40年代阿伦特初到纽约之时,她提倡哲学与政治合一的“行动理论”,以拓展长期受到思辨传统束缚的西方哲学的研究视阈,她把这些思想整理为《人的条件》出版。阿伦特在书中,把人的生活分为三个层次:劳动( labor)、工作( work)和行动( action),这三种活动分别代表着人的三种存在方式。劳动是最低层次的,是生物需求的经济满足;工作指人类主动制作经久的产品;行动最能体现人之为人的存在方式,它与自由、演讲、自发的政治舞台联系在一起,唯有通过行动,人才能展现自我。这里,她特别指出“政治行动”乃为人类真正自由的先决条件。受阿伦特的影响,麦卡锡对意识形态的思维方式持批评态度,她并不寻求某种政治生活的可替代程式,而是看重人类自身的精神探索。美国学者阿伦•瓦尔德( Alan Wald)指出,在1960年贝尔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之前,麦卡锡的《绿洲》已经以小说的形式演绎了此思想[4]。正是凭借着丰富的思想积淀,《绿洲》具有了深厚的历史穿透性、思想前瞻性与艺术独创性。
二、双重本体中的阅读空间
所谓经典应为“第一流的”,指“公认的、堪称楷模的优秀文学和艺术作品,对本国和世界文化具有永恒的价值”[5]。凡具有永恒价值的作品都有一个特征:“既是一种实在本体又是一种关系本体的特殊本体,亦即是那些能够产生持久影响的伟大作品,它具有原创性、典范性和历史穿透性,并且包含着巨大的阐释空间。”[6]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两个方面审视麦卡锡的文学作品:一是从实在本体论角度考察,将其视为因内部固有的崇高特性而存在的实体;二是从关系本体论的角度考察,将它视为一个被确认的过程,一种在阐释中获得生命的存在。其代表作《女研究生群体》在这两个层面为读者留下了巨大的话语空间。
196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女研究生群体》,销售量达100册之多,为麦卡锡走向经典奠定了社会公众基础。小说以凯与哈拉尔德的婚恋为主要线索,讲述瓦萨学院( Vassar College) 1933届研究生在纽约的创业经历及其女性意识的发展。麦卡锡在新政的大背景下,塑造了一组个性鲜明的瓦萨研究生群体形象。瓦萨学院素以培养积极进取、与时代接轨的女性而著称,所以其生源大都来自中上阶层。如同小说所描绘的那样,这些女生在瓦萨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不同程度地受到那个激进时代的浸染[8]7。
1933年6月,凯刚一毕业就同哈拉尔德在纽约举行了婚礼,同宿舍的7位同学都参加了他们的婚礼。虽然哈拉尔德毕业于名校,也不乏人生志向,可是在纽约他却只能穿梭于各种剧场打杂。瓦萨学院教育学生要保持开阔的胸襟,永远追求明晰的理想,这样的教育理念让凯对丈夫的艺术事业满怀信心。二战爆发后,凯与丈夫的婚姻也出现了危机,她独自一人住在瓦萨俱乐部。某天她依窗张望空中盘旋的军用飞机,不幸坠楼而亡。当年参加他们婚礼的同学又不约而同地从世界各地赶来参加她的葬礼,物事人非,每个人都变化很大。小说在浓浓的二战阴霾中结束。表面上看小说以塑造一组瓦萨女生群像为主,看似松散零乱,却有一条非常明确的主题贯穿始终,即表达了对女子如何在事业与感情之间保持平衡,并最终对社会有作为的叩问。
小说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折射出麦卡锡青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她把许多自我经历投射到小说中,像普里丝一样,她也有过几次流产的经历,威尔逊破坏了她想做母亲的信心。麦卡锡也嘲讽了这个群体对30年代的“时代精神”——一种新兴的科学技术、官僚体制、意识形态、审美情感的盲目膜拜,她把这一切归咎为新政意识形态的失败。梅勒认为,《女研究生群体》是不成功的,囿于女性思维,无法涵盖时代的“真实”[7]8。在梅勒看来,塑造群体形象的“集体小说”应该反映时代的重大社会事件,而麦卡锡的人物则缺乏进入其他阶层的英雄壮举,必将成为激情的牺牲品。事实上,麦卡锡所关注的是女性自身的追求和可见的女性进步观念,她并不在意其笔下的人物能否进入历史中心。麦卡锡通过女研究生群体形象的塑造,渲染了由于妇女介入了30年代的美国社会历史进程,从而使社会的基本力量和价值观念悄然发生变动。1951年,她在
《瓦萨女生》一文中强调了女子应该学有所成,推动历史进程,这样才能确保自己的姓氏不被更改①Mary McCarthy.“The Vassar Girl.”On the Contrary: Articles of Belief. New York: Farrar,Strarus and Cudahy,1961,p196.。
从《女研究生群体》中,我们可以看到麦卡锡在艺术手法上更加娴熟自如,能在作家的主观意图与小说所反映的客观社会材料之间保持一种协调。在这种协调中,社会的和个体的经验仿佛都是作家自己的创造一样,从她的笔端奔流而出。更重要的是,这种协调使小说与时代社会结构的激情相吻合。小说在叙述中带着奥斯汀的风格,麦卡锡藉此把“协调”推到极致。具体而言,麦卡锡在行文中追求一种“闲谈”的叙述方式,带有英国传统小说的舒缓格调,让瓦萨女生在闲聊中不断迭出小小的舌战。她把这种絮絮叨叨的“舌战”安置在日常生活场景中,并赋予它一种恰到好处的语调,又不断使用一些美国小城镇方言,以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小说出版后,此种独特的叙事风格当即受到文坛同行的推崇,在他们看来,麦卡锡的语言讲求古典的雅致,且能凸显出鲜明的质感和清新的感情,令人过目难忘②Constance Hunting.“Some Sort of Joy.”Puckerbrush Review( Winter,1982),p7.。就这种意义上看,麦卡锡文学创作的成功并非仅仅从个人经历中获取素材,而是内蕴着一种杰出的语言力量——对语言的神秘性的开掘,使其作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此外,小说的许多情境令读者感到窘迫、“弄错了”和“看似如此”。比如,多蒂在凯夫妇的陪同下,到医院寻求避孕措施就很典型。医生向多蒂演示如何使用子宫帽避孕,令她尴尬窘迫……从医院羞愧回来,多蒂找不到迪克,她黯然神伤地坐在街头的长凳上,一直到夜幕降临,引来巡警的好奇目光,最后她狼狈地逃回波士顿。小说扑面而至的就是窘迫,这是麦卡锡充分运用真实性所产生的艺术效果。她说:“想让自己窘迫,如果可能也让读者窘迫。”③Mary McCarthy.“Settling the Colonel’s Hash.”On the Contrary: Articles of Belief. New York: Farrar,Strarus and Cudahy,1961,p227.卡津把这总结为“毁灭式的”“捕捉隐蔽的弱点或人性中不一致的现象”[8]155。麦卡锡的小说有些可怕,你或许觉得自己被影射其中,“当我们听到麦卡锡正在写《女研究生群体》时,海伦( Helen K. Edey)惊叫,‘我们都说上帝呀,我们绝对被撕裂了’”[9]。详尽叙述潜在的窘迫、诘问和否定,且没有答案,是需要勇气的。对读者而言,这个过程也是窘迫的。在创作中,麦卡锡强调事实的暴露和窘迫,并让这种难堪和羞愧冲击读者。这样,作家的艺术风格已经形成——既根植于传统,又面向未来,把时代的左翼激情内化为艺术的独特追求。这也是麦卡锡能进入经典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充满艺术张力的自传体小说
麦卡锡的自传体小说也从“实在本体”与“关系本体”两个方面为读者预留了巨大的阐释空间。她在《一位天主教少女的回忆》、《我的成长》和《知识分子回忆录》3部自传体小说中,从真实与虚构之间寻找到属于自我的表现角度,以突破素材的历时性局限,达到揭示生命本身价值的目的。因此,其自传体小说也被赋予了特别的艺术张力。
麦卡锡在《一位天主教少女的回忆》中娓娓叙述了自己不幸的童年。她于1912年6月21日出生在西雅图市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其祖父是明尼阿波利斯的谷物商,信奉天主教;外祖父哈罗德•普雷斯顿( Harold Preston)是西雅图著名的律师,外祖母是犹太裔。如果再向前追溯,她的外曾祖父母都是德国犹太人,信奉新教。麦卡锡与阿伦特的深厚友谊,与她的德国犹太裔血统不无关系。父亲罗伊•麦卡锡( Roy McCarthy)生性喜酒、耽于幻想,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在1918年的一场流感中父母相隔一天离世。从此,麦卡锡和3个弟弟开始了孤儿生涯。
最初麦卡锡在明尼阿波利斯度过了童年,那是一个具有悠久天主教传统的美丽小城。然而,他们姐弟4人生活得并不快乐,他们受到叔父与婶母的虐待。这对夫妻是这4个孤儿的“大白鲸”,她写道:“我们这些孤儿不必为孤儿身份负责,但我们却被当作犯了某种罪责对待,孤儿的身世成了罪过。”[10]遭受虐待像噩梦一般地追随着麦卡锡,直到她30多岁时依然无法走出童年的阴影。
5年后,她被外祖父接到西雅图生活,终于摆脱了苦难。外祖父的图书馆藏书丰富,有狄更斯、托尔斯泰、布尔沃•利顿、大仲马等人的作品,麦卡锡徜徉在这些文学典籍之中,孤苦中多了一丝快乐。麦卡锡阅读童话,孤苦的童年在童话故事中被淡忘了。她在《一位天主教少女的回忆》中说,孤儿的生活养成她敢于反叛权威的激进性格,其实外祖父并没有强迫她过传统生活。1927年,麦卡锡开始独自徘徊在西雅图市的图书馆中,以身边的人和事为题材进行小说创作,图书馆的灯光伴随她度过了百无聊赖的青春期。在她看来,天主教信仰是连接自己与已故父母的生命线,她可以随时随地与天国的父母对话。
在舒缓、平淡的叙述中,麦卡锡力求在这些琐事的背后理出一条线索,做出一定的价值判断。所有这些都同作家的童年记忆联系在一起,从中升华出自我的追求。这些琐事因呈现自我而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麦卡锡热衷于自传体小说创作,按她自己的解释,是对童年经历和已故父母的痴迷眷恋。她就像一位业余考古学家,试图把所能找到的碎片缝合起来,构建出父母的形象。所以,她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叙述从亲戚们那里听来的关于父母的故事。这样,她所叙述的故事就不再是一堆琐事,而是经过心灵的互动而获得意义的经验事实,即成为展示自我生成的一组自传事实。正如哈德威克在传记的前言中所说:“她(麦卡锡)不会同意这仅仅是事实,相反,她常常把自传写作视为一面镜子。”[11]麦卡锡在《我的成长》中多次提到瓦萨学院塑造了她,“瓦萨使我更像我自己”,“其他的学院旨在发展,就像一颗种子等待发芽那样崭露出来,而瓦萨是在重塑”[12]。安娜•基切尔( Anna T. Kitchel)和海伦•桑迪森( Helen Sandison)的古典文学课程让麦卡锡受益匪浅。同时瓦萨也开设了“社会改革进程”、“美国工业发展及劳工问题”等新课程,培养学生面向现实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历史教师露西•特克斯特( Lucy Textor)从苏联朝拜回来,她的课吸引了学生。海伦•洛克伍德( Helen Lockwood)热衷于劳动妇女的教育,她主办的《当代报》让学生及时了解到校园外的事情,并把社会主义的种子播进学生的心中。瓦萨学院对麦卡锡的培养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奠定了她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其二,塑造了她激进的社会政治关怀。
在自传体小说的写作中,麦卡锡的激进表现在她敢于承认事实,并有勇气讲述出来,“以作家本人的名字叙述主人公的故事,需充分的勇气,这意味着名字背后隐藏着一些应该坦露的隐私”④Mary Ann Caws.“A Single Truth,but Tell it Sharp.”Stwertka,p141.。同时代的左翼作家丽莲•赫尔曼( Lillian Hellman)也创作自传体小说,但其风格与麦卡锡截然相反。赫尔曼在20世纪30、40年代活跃于影视与文坛两界,其《北极星》、《守望莱茵河》是当时美苏关系舒缓的象征性作品。这样的背景令赫尔曼老于世故,游走在美苏两大阵营之间。她在自传体小说《丑陋时期》中娓娓讲述故事,巧妙回避自我,精心粉饰自己在50年代的难堪怯懦。这种“世故”笔法令麦卡锡所不屑,相比之下,后者更加率真、无畏。俩人大相径庭的传记叙述风格反映出她们不同的价值观、艺术观。事实上,成功的传记作家应该二者兼得,然而麦卡锡的毫不畏惧,敢于袒露一切,更让读者赞叹。
敢于直面人生,与麦卡锡所提倡的“向心阅读”( centripetal reading )的文艺观密不可分。麦卡锡反对新批评的文本自足论,坚持揭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麦卡锡看来,读者与作家之间有一种亲密的血缘关系,恰如一间镜厅( a hall of mirrors)。作者孕育了文本,而优秀的读者对文本心生敬意,他们不是寻找什么,而是坚持文本的从属关系。在《征服上校》中,麦卡锡坚持作家肩负责任感,乔伊斯、詹姆斯等伟大的作家从来都很重视读者的阅读。麦卡锡认为,作者是言说者和观察者,读者应当跟随作者的引导⑤Mary McCarthy.“Settling the Colonel’s Hash.”On the Contrary: Articles of Belief. New York: Farrar,Strarus and Cudahy,1961,pp234 - -237.。麦卡锡认为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也说明阅读是一项社会事业,优秀的读者可以在作家的行文片断中发现最具象征意义的东西。对麦卡锡而言,文学创作带给她当作家的快乐,但她追求“真诚”,又使她成为“好战”的读者⑥Mary McCarthy.“Crushing a Butterfly.”The Writing on the Wall and Other Literary Essays. San Diego: Harvest/ HGB,1970,p98.。她坚持坦诚面对读者,尤其是在传记体小说中暴露自己的隐私,带有卢梭般的诚实。她的真诚无畏必然换来读者的心灵回应,这也是麦卡锡的自传体小说拥有大量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结语
综上所述,激进的时代使麦卡锡的创作在“实在本体”与“关系本体”两个层面上获得了丰富的内涵,蕴含了进入经典的充分元素。从“实在本体”角度上看,首先,瓦萨严格的古典文学教育为麦卡锡的文学创作打下坚实基础:一方面她从莎士比亚、奥斯汀和弗•伍尔芙等那里汲取养料;另一方面又因长期旅居法国,游走在法国现代派文学圈子中,使她对先锋文学较早体察,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甚至蕴含着某些更加前卫的艺术因子。其次,她在文学创作初期得到了威尔逊的悉心指导,后来不断发酵、释放正能量。成名后的麦卡锡也多次表示如果没有当年威尔逊的“严厉”,就不会有她的成就。离开威尔逊后,她又与阿伦特往来密切,二人在思想上碰撞激荡、相得益彰。此外,她从未脱离过纽约文人的圈子,这一切都使她的创作无论在思想深度还是题材的广度上,都超出了同时代的其他作家。
从“关系本体”角度看,她在各种文类之间自由穿行,时而进行小说创作、时而尝试传记兼及戏剧评论、政治评论。更重要的是,她无法割舍自己与文学之外的承担,尤其是与她从越战到尼克松水门事件所有的
政治介入隔开。文学之外的担当让她坚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干预性批判,在文学想象与社会现实的对立统一中寻求独特的艺术表达,从而使其创作具有了继往开来的艺术穿透力量。近年来,随着美国左翼文学研究的不断升温,麦卡锡也备受关注。她虽然算不上无产阶级作家,但她从个人生活与政治两个方面所表现出的艺术个性,带有一种探究本源的拉伯雷式的风格,与时代的脉动相生相融,使其影响不仅跨越了国界,也跨越了文学领域,成为20世纪美国左翼文学中的典范作家之一。
参考文献:
[1]BRIGHTMAN C. Mary McCarthy and her world[M]. New York: Clarkson N Potter Inc. 1992:283.
[2]KAZIN A. Starting out in the thirties[M]. Boston: Little Brown,1965.
[3]BRIGHTMAN C. Between friends: The correspondence of Hannah Arendt and Mary McCarthy 1949—1975[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1995:1.
[4]WALD A.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Anti—Stalinist left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80s[M]. Chapel Hill :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7:240.
[5]普罗霍罗夫.苏联百科词典[K].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625.
[6]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J].中国社会科学,2004( 3) :149 -150.
[7]王予霞.无法开释的左翼情结——玛丽•麦卡锡创作研究[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 2) :51 -54.
[8]NORMAN MAILER. The Mary McCarthy case[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rooks,1963 -10 -17( 3) .
[9]FRANCES KIERNAN. Seeing Mary McCarthy[M]. New York: Norton Company,2000:528.
[10]MARY McCARTHY. Memories of a catholic girlhood[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57:49.
(责任编辑胡志平)
[11]MARY McCARTHY. Intellectual memoirs: New York 1936 - 1938[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Publishers,1992.
[12]MARY McCARTHY. How I grew[M].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7:201 -203.
A study of Mary McCarthy’s literary creation from the left-wing politics and classical building perspective
ZHANG Jinsong
(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Jimei University,Xiamen 361021,P. R. China)
Abstract: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American left-wing politics has given rise to a large number of literature classic works and writers. Mary McCarthy is one of them,her literary creation is especially striking. Her works can enter classic for four main reasons: Firstly,the speci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made her legendary life and outstanding literary creation; Secondly,the female images which she created not only challenged the patriarchal consciousness in left-wing culture camp,but also changed American realism literature of women in traditionality,showing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Thirdly,from two aspects of“truly ontology”and “relative ontology”the novels have provided huge reading space for the readers with special artistic tension; Fourthly,her autobiographical novels can face life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reader' s“centripetal reading”,which contains rich classic elements. The four points above are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her to enter the ranks of the classic writers.
Key words:left-wing politics; classical; dual ontology; autobiographical novel
作者简介:张劲松( 1974 - ),男,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主要从事现代美国文学研究。
doi:10. 11835/j. issn. 1008 -5831. 2015. 03. 024
中图分类号:I712. 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 2015) 03-00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