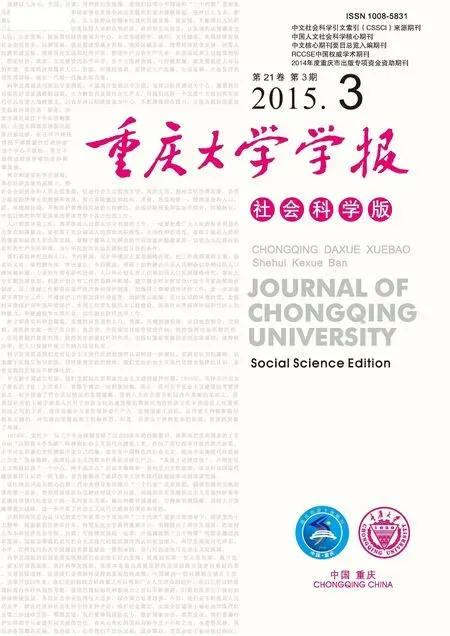论法治研究的方式
朱 俊
(贵州财经大学法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论法治研究的方式
朱俊
(贵州财经大学法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摘要:国内法治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对这些研究成果的再研究亦非常重要。文章认为,法治研究在当代中国有三种方式,一是扬弃方式,通过重述或比较的方式研究西方法治理论;二是历史方式,研究法治理论在古代中西方世界的发展以及在近代中国的生长历程;三是理论方式,从法治概念、标准、意义、路径、思维、理论体系等方面入手,建构立基于中国的法治理论体系。
关键词:法治研究;扬弃方式;历史方式;理论方式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朱俊.论法治研究的方式[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3) :128 -135.
Citation Format: ZHU Jun. On the way to study the rule of law[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2015( 3) :128 -135.
修回日期:2014 -09 -29
自晚清始,法治被引介入中国,便在此逐渐生根发芽,成为国人矢志不渝的追求①现代法治的概念并非原生于中国,但中国本土的法治亦有迈向现代法治的可能。参见程燎原《古代汉语典籍中的“法治”语词略考》(《学海》2009年第1期) ;程燎原《先秦“法治”概念再释》(《政法论坛》2011年第2期)。法治在晚清的情况可参见朱俊《论法治思维的初生——清末游洋记研究》(《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正因为法治是国人面对西方“侵略”而选择的“救亡图存”的工具之一,它在中国的命运便带有浓重的使命色彩。国人期待法治能给中国带来富强与文明[1]。因而,国人对法治的研究,在法治征服国人时,即是在扬弃——特殊的学习方式,有中国学人的主体性与问题意识——的氛围中进行,它融入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大潮流。从某种意义上讲,扬弃是国人研究法治的最初方式,亦是迄今为止国人研究法治的深层方式。这一方式不同于法治在西方历史上的发生方式,亦不同于法治在学术研究中的理论方式。换言之,法治研究通常有三种方式:一是扬弃方式,通过重述或比较的方式研究西方法治理论;二是历史方式,研究思想史上的中西方先贤如何思考法治以及法治在近代中国的发生历程——中国先贤思考的“法治”不同于西方与现代的“法治”;三是理论方式,即站在中国问题的立场建构法治的概念、标准、意义、路径、思维、理论体系等②区分法治研究的三种方式,灵感来自中国台湾当代新儒家对民主的认识,即民主在西方的发生逻辑、在理论体系中的逻辑、在后发国家建构民主的逻辑。参见林安梧《牟宗三前后:当代新儒家哲学思想史论》(中国台湾学生书局2011年版,第222、273、282页)。需进一步说明的是,这一分类并未穷尽所有的法治研究方式,它只是在宏观意义上把握中国的法治研究方式。。事实上,这三种方式在现实中并不容易区分。更确切地讲,当代学人都有可能同时运用了这三种研究方式——这说明中国学者对法治问题的多元探索。因为他们都生活在当下,都有中国问题意识,立基于这一问题意识而又扬弃西方法治理论,探究法治在中西方历史上的发展状况,以提出自己关于中国如何实现法治的理论构想。
一、法治研究的扬弃方式
扬弃方式并非简单的“拿来主义”,它意在“吃透”西方法治理论,有中国学人的主体意识和问题意识。言其主体意识,是中国研究者在研究,他在中国或背着中国传统在研究,哪怕他反对中国传统,就其反对而言,仍表明其不同于西方学者。言其问题意识,是中国学人的主体意识的进一步追问,他为什么要研究法治。这里,法治研究扬弃西方理论至少有三方面考虑:一是为了更正确地理解西方法治理论,不至于出现学
错了的尴尬局面;二是为了更好的文化交流,只有建立在正确理解基础上的交流才能达到目的;三是西方法治已走在中国前面,扬弃西方法治理论是想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即为中国法治发展提供借鉴,这是最直接的动力③这一研究目的可在各类翻译西方法学著作的《出版说明》中见到。例如《美国法律文库•出版说明》(约翰•W•斯特龙主编《麦考密克论证据》,汤维建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言其为最直接动力,与中国的近代遭遇相关,晚清中国败于西方是因为中国政治制度不行,故而学习西洋法治,引入法治以救国图存④有关法治如何进入中国的论述,可参见朱俊的博士学位论文《清末“游西记”中的“西洋宪政”图景》(重庆大学法学院2014年)的有关论述。。其中有两个根本性的判断:一是中国败于西方并非仅是军事上的失败,而是西方在政治法律制度方面战胜了传统中国,故而它代表了政治法律的发展方向,即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化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二是中国要想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追上乃至赶超西方,只有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扬弃西方法治理论。
事实上,现代化是中国的追求。因为作为一个广义概念的“现代化”,是“把握、描述和评估从16世纪至今人类社会发生的种种深刻的质变和量变”的一个工具,它强调人类社会经此现代化阶段而进入了现代理性的阶段,将自己的社会环境建立在富足而合理的基础上。因而,现代化既是过程又是产物,是人类社会生活全方位的理性发展[2]。在国人看来,这是中国应当追求的目标。晚清以来,历届中国政府均强调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即有35次提及“现代化”。而现代化“是一个具有其自身某些明显特质的进程,这种明显的特质足以解释,为什么身处现代社会之中的人们确能感受到社会的现代性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民主化、普及教育和新闻参与等,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层面,它们的出现绝非是任意而互不相关的”[3]。那么,作为政治现代化内容之一的法治亦在其中。“在现代化的理论模式中,法治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4]378。至今,法治已成为中国现代化和改革的内在需求,这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基本共识。而近代以来的中国学人始终致力于扬弃西方法治理论,通过重述或比较的方式吸收西方法治的理论精髓。
重述西方法治理论,是从不同角度和立场探究哈耶克、罗尔斯、德沃金、富勒、昂格尔、拉兹等理论家关于法治的理论当如何理解。这并非简单的重复,也不是单纯的将外文文献翻译为中文,它涉及理解问题,更确切地说,是诠释问题。即怎样正确理解西方的法治理论,这是中国学人扬弃西方理论的重要步骤。相比历史解读或理论原创,重述带有更多的学习色彩。当然,重述也并不否认学者的个人创见,它只是受制于原有理论。
以哈耶克研究为例。有学者强调哈耶克法治理论的关键在社会自生自发秩序与国家建构秩序的结合,两者在互动中使之保持法治状态[5];有学者则专注于询问哈耶克是否在一开始即认识到自发秩序还是在此过程中有一个转换的问题[6];更有学者从整体性的角度研究哈耶克的法治思想[7]。这是不同角度下对同一法治理论的研究。因而,它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受制于研究的视角而无法全盘把握,但它在这一视角下对法治理论的研究却足够深刻。亦有整全性研究某一人物或学派的法治理论,如赵红军的《昂格尔视域中的法治》[8],石友琴的《论哈耶克法治理念及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9],艾克文的《自然法思想与法治国家观念》[10]等论文。同样,这种研究方式受制于篇幅而难以深刻;如能深刻,则是佳作。
但无论如何,重述研究试图“吃透”西方法治理论,即精准理解和把握西方理论家对法治理论的思考和建构,做他的学生,学习他关于法治的理论,并试图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或以该理论来检讨中国法治理论的现状,或以该理论来检讨中国法治发展的状况,或从其他立场或角度检讨该理论的缺陷并提出进一步的建构性方案。“现代法制的建设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政治的力量,也有赖于学术的质量”,而学术质量不外乎依赖于三:“弘扬文化遗产、进行知识创新以及输入海外学说”,且“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这种缺陷,要振兴中国的法律学术,不得不特别致力于迻译和钻研西方典籍”[11]1。事实上,“近代中国法学,几由西方法儒学说发展生成,西方法学著述之译介,于吾国法治事业助益良多”[12]。
以比较方法研究西方法治理论,是为了在区别的意义上更准确的理解。这是因为,第一,比较且分类的方法,是人类最重要最基本的思维方式[13]。面对西方的众多法治理论,通过对其内容的同异比较,既能对其内容有更深刻的理解,又能确定其共性而抓住法治的关键性因素,还能在此共性的基础上将之类型化,更能发现其间的差异。重要的是对这个差异进行归纳和原因分析,将使研究者进入法治理论的核心领域。第二,比较还意味着将其他法治理论同经典法治理论进行比较,它既能确定这理论是否是法治的,还能确定这
法治理论存在什么问题,有利于新法治理论的完善。第三,如海因•克茨先生所言,“即使一位法律家,也只有具备有关外国法律制度的知识,方能正确地理解本国的法律”[14]1。即比较促进了对法律的理解,使法治在理论上更具合理性。对中国而言,“我国当代比较法研究的意义不同于历史各个时期,不仅具有一般学术意义:促进法学繁荣,提高理论认识,且在实践上具有异常重大的政治意义”[14]3。
有学者以拉兹、哈贝马斯的法治观作比较,强调拉兹以实践理性为起点,坚持分析实证主义形式法治观,引入法律权威概念来阐明法治的合法性,是权威法治;哈贝马斯则从交往理性出发,在批判形式法治观基础上提出程序主义法治观,是合法法治[15]。这里有法治类型学的凸显,将拉兹与哈贝马斯的法治观做了类型学上的区分。此外,亦有学者从形式法治观、实质法治观解读罗尔斯法治观的冲突入手,认为形式法治观不能解释罗尔斯对法律形式的要求源于对自由的保障,实质法治观不能解释为何罗尔斯认为法治与正义相容,主张将对自由的保障看作是对权力正当性的形式要求,进而理解罗尔斯的法治观[16]。通过这种学者间或类型间的比较,研究者试图“吃透”西方法治理论。
扬弃方式既通过重述试图正确解读西方法治理论,又通过比较以建构出西方法治理论的全景,在此基础上进行类型学研究,就其共性与差异,优点与缺点等予以知性考察,填补了国内有关法治理论的空白,拓展了国内研究的空间,为进一步研究或实践乃至学术交流提供了可能,满足了中国法治现代化的部分需求。
二、法治研究的历史方式
以历史方式研究法治,是学者追溯法治在中西方古代世界的思想渊源及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以明晰法治理论的来龙去脉。
学界有从思想史角度研究西方法治理论的,这是为了全面理解和把握法治理论在西方的发展脉络,其逻辑起点、理论发生、发展与演变等问题,都是关注的焦点。有学者追溯了古希腊的城邦法治,古罗马的共和国法治、帝国法治,英国、美国、苏联等国学者对法治的理论建构,勾勒了西方法治理论的发展概况,并从法治的概念、实体价值、形式价值、状态等角度解读这一历史[4];有学者则专注于近代以来的形式法治理论、实质法治理论的发展及其缺陷,以及西方学者寻求法治理论突破的理论构想,即走向回应法、习惯法、程序主义法等,探讨法治理论的未来发展方向[17]。简单讲,这种研究方式是以西方法治理论的经典为素材,或者从法治理论的发展状况入手,或者从法治理论对某一问题的探讨入手,以历史叙述的方式研究西方法治理论。它试图从这一历史叙述中找到西方法治理论发展的根基性因素,诸如法治的几大要素在哪一时刻怎样聚集起来,法治发展有怎样的经验可资借鉴[18 -20]。《法治论》在开篇即表示,“在法治学说这块已被开垦耕耘的田地里,我们会有许多收获;法治学说史中的那些精辟与深湛的卓越见识,将使我们获益非浅”[4]3。这句话点明了思想史研究西方法治的目的。
学界有从思想史角度研究中国本土的法治资源,以进一步厘清法治的概念,进而确认中国本土法治资源是现代中国实现法治的障碍因素抑或促进因素。有学者强调,先秦典籍与思想中的“法治”名词和概念有“以法为治”、“生法者君也”、“法之必行(包括“君主从法”)”、“救世、富强、致治、尊君”涵义,但其要义有严重的内在缺陷,流于空疏,与近现代以来的法治思想完全不同,需对此予以批判性反思[21]。有学者则认为,中国古代的德治关注政治主体层面,法治注重政治的客体层面,各有其利弊,并非绝对对立,亦不能一概而论,需使二者相互结合,互相补充,相辅相成[22]。有学者则强调,中西方法治在法的普遍性、成文法化和依法行政等方面有相似之处,但却不同于近现代以来的西方法治,仍然为一种法治方式,只是在沿用“法治”术语时要严格把握其内涵并区别于西方的“法治”,这是近代以来的学者对本土“法治”的形式共识[23]。有学者表示,中国古代的法治经历了从贵族法治到帝制法治的演变,与更为传统的“礼治”相对立、相区别[24]。
这些学者从思想史角度研究古代中国,是为了检讨古代中国的“法治”思想资源。他们或者从经典入手进行理论的存在性论证,或者从实践入手论证法治理论的存在性,或者进行意义性论证。且他们对这一传统资源有不同态度:有认同中国传统对法治有积极影响的,例如《传统文化对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内在限定》一文认为,“建构中国的法治社会需要吸纳现代法治观念和先进的法律文化,同时也必须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基础,承继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以建构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切合中国人习惯特点,具有现代法治精神的新的中国现代法律体系”[25];有认为传统对法治存在若干消极影响的,郝铁川认为“中国传统的‘性善论’导致了中国人长期以来崇拜权力而忽视权力制约……性善论导致中国人重视内心体验和直觉感悟,从而不利于现代程序法、证据法的建立与健全;性善论把人视为‘义务人’而非‘权利人’,进而压抑了现代民法在中国
的培育”[26]。应当讲,这些研究试图对传统的“法治”资源进行清理,从法治的立场检讨它对法治的利与弊,是利则当考虑如何与现代法治关联而促进其生长,是弊则考虑如何将之问题化并予以解决。
学界有研究中西方法治理论在中国近代以来的碰撞及其实践,以探求当下中国法治发展的历史因由。有学者通过对清末“游洋记”的分析认为,“法治思维”在洋务运动时期是挣扎在“治法”思维当中,这是其孕育期;“法治思维”在戊戌维新时期胎动,表现在时人认识到习惯与法律的关系,权利对人的重要性,“依法治国”的重要性,以及法律人共同体对于法治的重要性;“法治思维”在新政时期初生,时人开始关注法治对于德治的优越性以及司法独立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意义;然而,这一“法治思维”仍然仅是初生,以法治的标准检视,仍有不少缺陷存在[27]。有学者发现,国民革命时期司法曾被纳入国民党党国体制中,即“国民党化”,这一举措虽然有利于动员民众参与革命运动,却将党争带入司法,使其负面效应远大于正面作用,改变了清末以来中国司法的走向[28]。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是政治革命,法治在此有政体层面的价值,革命是推翻君主专制政体而建立法治政体,是通过革命而行法治[29]。有学者认为,清末民初中国宪法精神和中央政府体制的变迁,是从封建君主制(宪法大纲)转向虚君议会制(十九信条),民国成立后建立民主体制之大总统制(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与内阁制(临时约法、天坛宪草),再到袁氏窃国重回“洪宪帝制”,其间嬗递不变的是民主潮流与法治精神,这彰显出“法治精神与基本人权的保障,也必将是未来的正确方向”[30]。有学者从日常政治与非常政治的区分入手,认为近代以来的法治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强调中国当下的问题在“政治的回归”,既回到非常政治,又回到日常政治,即从非常政治中寻找法治历史发展的脉络和问题,促进中国出现宪法政治的转型,并从中催生出一个法治主义的常态政治,这是“我们中国人民”的时代问题[31]。有学者分析,晚清的戊戌变法、立宪运动乃至于辛亥革命都是现代性意义上的变法,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中国的改良与变法在本质上都是革命性的,但究竟是作为重新匡正的保守型革命还是作为一种绝对否定意义上的激进式革命,在三次变法中逐渐成为争论的焦点,这一问题伴随立宪革命、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进程,即晚清的三次变法越来越深入地走向激进主义,这为现代中国现代性浪潮的强大影响力奠定了基调,为未来中国一系列纷纷攘攘的变局以及一些灾难性后果抑或伟大成就埋下了伏笔[32]。这些学者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研究法治,是为了从历史的角度探寻当下中国法治发展的历史性因素。因为他们相信,当前中国法治的理论与实践所面临的问题,都可以从中国近代找到某种答案,对这一问题乃至于答案的历史性把握,有利于当下法治理论与实践克服这一问题,以推进中国法治现代化继续向前发展。
在这些研究近代法治的论文中,有三种不同的知识立场:一是客观历史发现,诸如朱俊、李在全等人,他们试图将法治在近代中国生长的客观情况呈现出来,即它有哪些资源,遭遇哪些困难。二是以革命或“斗争”范式解释法治的近代情况,例如程燎原、刘阿荣等人,他们试图树立革命话语的正当性,从而论证革命政权的合法性。三是以改良或“妥协”范式解读法治的近代历史,如高全喜、田飞龙等人,他们试图解构革命话语,建立改良的新历史传统,树立改良的历史权威。
三、法治研究的理论方式
在扬弃西方法治理论以及研究中西方法治思想史、法治在近代中国发展的基础上,中国学界逐渐建立起一整套关于法治的理论,形成了法治理论的学术自觉,即建立了一整套有关法治的概念、标准、意义、路径、思维、方式以及理论体系的学说。
中国学界关于法治的概念,是建立在与人治、法制、治法概念区分基础上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法学界关于人治与法治的争论中,无论是“法治说”,还是“法治与人治结合说”,抑或“摈弃法治与人治说”,都明确地不赞成人治,法治的尺度亦不在于是否“以法治国”,而在于法律本身所追求的价值以及由此形成的权威程序化的机制[4]104 -118。有学者强调,法治、人治都有自己的确定含义,决不是简单可以用“法”、“人”、“法的作用”、“人的作用”这些概念来替代的。因为它们不仅是一种理论、一种治国原则和方法,还是一种社会实践,与一国实行的政治法律制度密切相关。即法治与人治是对立的存在,尤其是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33]。法治区别于人治,并非意味着法治概念的确立,它还需与法制区别,直至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正式确认法治。有学者表示,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与经济制度等相对,而法治则是与人治相对立的一种治国理论和原则;从实践上看,有法制不一定都是法治的[34]。法制是上层建筑中的制度范畴,有阶级属性,是法治的工具和手段,与民主无必然联系;法治则是上层建筑中的思想范畴,有价值判断,是阶级的治国方法,表明法制的地位和作用,是一种合乎理性的价值的目的和秩序、结果或状态,与民主密切相
关[35]。此时,法治的概念在理论上得以基本证成。
但有学者强调,基于中国千年的“依法治理”传统而形成的“治法”思维是法治的重大障碍而言,法治概念必须与之区别。该学者认为,法治是同治法相对的概念,治法强调法律的手段论,与人治尤其是德治、礼治纠缠不清,追求秩序或“治”,无法找到“使法必行之法”,最终无法将法治的要求内化到政体的构造与制度中;因而法治强调法律不仅是政府治理的工具,更是“治理政府”的工具,与人治对立而绝不可能结合,追求秩序、人权、正义及管住“权力之手”,认为最有效且最关键的“使法必行之法”是民主宪政的政体,它是民主宪政政体的特质、精神与原则[36]。于此,法治概念得以完善。
在关注法治概念的同时,学界亦从标准的角度进一步界定并完善法治理论,这是在吸收富勒、罗尔斯、拉兹等西方学者提出的法治标准后,中国学人学术自觉的又一次努力。有学者提出了法治的“十条”规诫,即有普遍的法律,法律为公众知晓、法律可预期、法律明确、法律无内在矛盾、法律可循、法律稳定、法律高于政府、司法权威、司法公正[37]。另有学者提出了法治的“十大”标准,即法制完备、主权在民、人权保障、权力制衡,法律平等、法律至上、依法行政,司法独立、程序正当、政党守法[38]。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中国法治实践的不断深入以及世界正义项目对法治指数的不断推广,中国学界亦提出了判研中国社会法治发展的法治指数,数字化法治状况。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完成了《北京市市级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考核评价指标体系》,浙江大学法学院以2011 -2012年湖州市吴兴区法院为试点完成了司法透明指数评价项目[39]。
此外,为了证成法治这一概念与理论,学界亦论证了它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有学者从法治的价值出发,强调法治是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的一道屏障,它既能保障整个社会的基本秩序,又能保障个人不受不正当行为的侵害,以形式的程序追求实质的自由、平等价值,在法权体系中促进商品经济的自由发展[4]145 -192。有学者从中国国情出发,认为法治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是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以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内在要求,是保证国家稳定以实现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40]。
同时,学界也研究法治在中国实现的路径。有学者基于西方市民社会理论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模式”不匹配的实际认为,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必须立足于国情,走自主型道路,即必须坚持政府主导的“制度先行”、“法治先行”模式,以政府推导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发育、良性互动乃至于关系形塑,从而达致制度均衡的法治秩序[41]。但有学者却认为,当前中国法治发展的最大障碍在政府权力的滥用,而法治的关键却是在如何制衡权力,使权力处于法律的权威之下,政府主导型很可能出现权力尾大不掉的情形[42]。有学者主张中国当前的法治应从单纯的实体法治向程序法治并重发展,因为程序法治的基本内涵和价值表明程序法治具有优越性,它的基本问题关乎法治的基本目标,这是法治的应有之义[43]。有学者强调,法治路径不外乎建构唯理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两种理论建构,它们作为理论虽然独立,但在现实中却交织在一起,长期处于一种互动的状态,因而既需要强调国家的法治推进,亦需要关注民间自生自发秩序[44 -45]。也有学者认为,应当从法治实践的阻碍因素入手,即从公权力不受规范,权力行使不透明,权力行使的方式依靠人治建立起来的权力运行体系入手,强调高层领导的政治决断和信心,重点规范约束公权力并将之纳入法治轨道,确保法律有效实施[46]。并且,学界还关注法治的思维与方式。有研究认为,法治思维主要表现在法律事实过程之中,是法律及其基本原则对人思想的影响,它是受规范、程序约束、指引的思维,是在现阶段主要限制、约束权力任意行使的思维,是追求实现公平、正义并保护权力和自由的思维,是理性而讲究逻辑推理、修辞论辩和解释技术的思维[47]。而法治方式主要是指称权力运作的方式,是设计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行为方式,是基于法治思维所衍生的行为方式,是平和、理性地解决纠纷、处理问题的方式,是重视法律的程序性和遵守规则重要性的行为方式,是以法律语言为主的思维决策方式,法律语言在思维中起主要作用,是法律语言的行为方式[48]。更为重要的是,有学者基于中国问题,在吸收古今中外法治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理论。高鸿钧先生发现了现代西方法治理论的困境,即在效率与公平、自由与群合之间始终存在紧张关系,表现在封闭与开放、内信与外迫、确定与无常、普适与特惠、规则与事实五个方面;即便西方发达国家以进入现代社会第二阶段——政府干预阶段或福利国家阶段——来缓解这一紧张,效果仍不理想;即便西方学者主张法治理论向回应型法、习惯法、程序主义法发展,这一紧张仍然存在。因而,他主张,应进行价值整合,走出效率崇拜误区,拆除个人主义藩篱;应进行关系整合,摆脱金钱的奴役,解除权力的压迫;应进行结构的整合,即走向一种道同而谋的自愿共同体,建构一个道并行而不悖的多元社
会,并在此基础上自生自发出一个具有充分正当性的共同体法治。这是一种“科学实验”的法治构想[49]。邓正来先生则认为,中国法学缺乏“总体性”反思与批判,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暴露了自身的问题,即“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断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50 -53]。他在批判“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的基础上强调,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是矛盾且多元的,主观且可变的,它对中国的支配性和双重性对中国法学而言是挑战亦是机遇,中国法学当在此过程中建构起“关系性视角”,在审视“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建构起“共时性视角”,从“主权性中国”走向“主体性”中国[54 -57]。质言之,对邓先生来讲,法治理论在中国受到未加质疑的“现代化”范式的支配,需要对此前提性假说予以反思,并在此基础上认识全球化及其对中国法治的影响,在此过程中基于法治的理论积淀和实践积累,建构出法治理论的中国版本。程燎原先生从二分法入手研究所有方式政体,认为法治实际上只与某些政体亲近——是为法治政体,而其他政体则与法治绝缘——是为治法型政体。他认为,“法治政体理论在根本上把法治理解为,只有立宪政体才会要求并实现法律统治的一个政体问题”。从这一角度看辛亥革命,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等法律初步建构了中华民国法治政体的雏形,因为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民主立宪的法治政体[29]。这里,民国建构法治政体,意味着民国之前的和民国所针对的乃是治法型政体,即将法律作为一种工具而不是被法律所统治的政体。在是否被法律统治的意义上,政体被两分了,法治政体根本对立于治法型政体。因而,现代中国实践法治,应当以法治方式推进法治,在政体层面建构符合法治内涵的权力与权利(权力与权力、权力与权利)的结构性安排,并以积小功为大功的改良心态与方式推进中国法治的实践[36]。建构法治理论的中国版本,即使法治理论中国化,并使之服务于中国法治的当代实践,这是当代法治理论研究者的最终追求。就这一研究方式来看,它还不够成熟,还需进一步探讨与观察。
四、反思与结论
法治研究的这三种方式各有优势,都在满足学术界与实务界的知识需求。扬弃方式将目光对准西方法治理论,在重述或比较中解读,试图在正确解读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法治理论,为中国法治的理论与实践储备知识并参与法治的中外对话。历史方式则是从思想史或近代史的角度切入法治理论,梳理西方法治理论的思想史脉络,摸索出法治理论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梳理出中国法治资源的当代价值,在利弊二分的基础上清理历史资源;梳理法治在近代中国的生长史,在历史考证与历史解读中塑造中国法治的传统。理论方式则在概念、特征、标准、意义、路径、思维、方式等法治基础理论方面着力,立基于中国的历史与实践建构法治理论的中国版本。
不可否认的是,这三种研究方式各有其问题。对扬弃方式而言,将学习西方定位为目的,有消解中国问题意识的危险。虽然有部分研究以扬弃的西方法治理论审视中国现实,并提出中国法治建设的意见,但这仍然是少数,且有隔靴搔扰之嫌。因为从理论到实践有更多的细节需要把握,它必须深入到法治实践的末梢,并非学到西方理论即能指导实践,它只是在高空飞行而已。何况更多的研究将兴趣放在了全面把握西方法治理论上面。对历史方式而言,西方法治理论的思想史考察定位在为中国法治理论发展提供思路,但它毕竟只是西方经验。中国法治的思想史考察定位在为法治发展扫清了障碍,但法治的界定及其利弊标准本身仍然是争论的焦点,即其前提性问题仍然存在,这距离扫清障碍还有距离。近代法治话语的生长考察定位在知识发现,对当代问题的把握却有疏忽,即便是借近代问题谈当代问题,但问题之间仍有差异;至于解读近代法治话语的生长,其定位在塑造法治的历史权威上,有关解读方式本身亦存在争论。对理论方式而言,建构系统的法治理论是一个不小的诱惑,但这需要庞大的理论积淀,不仅是学者个人,还涉及学术本身。
当然,随着中国法治实践的不断深入,以及中国学人法学素养的不断提升,法治研究在中国将展现更为丰富的成果,不断呈现法治研究的扬弃方式、历史方式与理论方式,即在历史与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中国法治的问题并予以学理分析,在法治理论与实践的碰撞中,逐渐生成解决中国化的法治理论。
参考文献:
[1]王人博.宪政的中国语境[J].法学研究,2001( 2) :133 -147.
[2]亨廷顿.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M].罗荣渠,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28 -31.
[3]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89:30.
[4]王人博,程燎原.法治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5]张进铭,高雪萍.自发秩序与建构秩序的相容性——以哈耶克法治理论为视角[J].江西社会科学,2010( 8) :59 -63.
[6]邓正来.普通法法治国的建构过程——哈耶克法律理论研究的补论[J].开放时代,2002( 4) :6 -32.
[7]刘磊.哈耶克法治思想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11.
[8]赵红军.昂格尔视域中的法治[J].清华法治论衡,2005( 2) :211 -220.
[9]石友琴.论哈耶克法治理念及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Z) :106 -110.
[10]艾克文.自然法思想与法治国家观念[J].理论月刊,2003( 12) :112 -113.
[11]诺内科,赛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M].张志铭,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12]许章润.哈佛法律评论•法理学精粹[C].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卷首语.
[13]赵蓉英,邱均平.知识网络的类型学探究[J].图书情报工作,2007( 9) :11 -15.
[14]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M].潘汉典,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5]陆洲,刘训智.权威之法与合法之法——拉兹与哈贝马斯法治观之比较[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4) : 603 -609.
[16]龚蔚红,孙一平.以权力正当性的形式要求为基础的形式法治——对罗尔斯《正义论》中法治理论的解读[J].求是学刊,2012( 4) :95 -99.
[17]高鸿钧.现代西方法治的冲突与整合[J].清华法治论衡,2000( 00) :1 -59.
[18]曾尔恕.试论美国宪法制定的法治渊源——英国的法治传统及其在北美殖民地的保留[J].比较法研究,2006( 1) :1 -19.
[19]齐延安.美国的法治经验及启示[J].法学论坛,2005( 6) :124 -134.
[20]程汉大.法治的英国经验[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 1) :8 -16.
[21]程燎原.先秦“法治”概念再释[J].政法论坛,2011( 2) :3 -13.
[22]张祥浩.古代的德治、法治及其现实意义[J].东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 2) :24 -28.
[23]武树臣.法家法治思想的再评判——兼与杨师群统治商榷[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98( 1) :54 -63.
[24]李贵连.从贵族法治到帝制法治:传统中国法治论纲[J].中外法学,2011( 3) :459 -483.
[25]潘丽霞,高长思,陈亮.传统文化对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内在限定[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4) :89 -93.
[26]郝铁川.“性善论”对中国法治的若干消极影响[J].法学评论,2001( 2) :20 -24.
[27]朱俊.论法治思维的初生——清末游洋记研究[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3) :114 -121.
[28]李在全.徐谦与国民革命中的司法党化[J].历史研究,2011( 6) :37 -52.
[29]程燎原.中国法治政体的始创——辛亥政治革命的法治论剖析与省思[J].法学研究,2011( 5) :143 -163.
[30]刘阿荣.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法治精神的建立[J].史学月刊,2012( 1) :8 -11.
[31]高全喜.论共和政体——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种政体论思考[C]/ /现代政制五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32]高全喜,张伟,田飞龙.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33]李步云.法治和人治的根本对立[J].现代法学,1982( 2) :36 -39.
[34]李步云.从“法制”到“法治”二十年改一字——建国以来法学界重大事件研究( 26)[J].法学,1999( 7) :2 -5.
[35]孙育玮.“法制”与“法治”概念再分析[J].求是学刊,1998( 4) :54 -58.
[36]程燎原.“法治政体”之思:对当代中国法治理论“第三波”的展望[C]/ /中国法治政体问题初探.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
[37]夏勇.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与价值[J].中国社会科学,1999( 4) :117 -143.
[38]李步云.法治国家的十条标准[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 1) :78 -83.
[39]莫于川.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议题建设的标准问题研究——兼论我国法制良善化、精细化发展的时代任务[J].法学杂志,2013( 6) :9 -20.
[40]王家福,李步云.论依法治国[J].法学研究,1996( 2) :3 -9.
[41]何平立.市民社会、中产阶级与法治路径选择[J].社会科学战线,2011( 1) :191 -197.
[42]程燎原.从法制到法治[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43]王永杰.从实体法治到程序法治:我国法治路径研究的新进展[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 6) :52 -55,70.
[44]汪习根,刘澄.论当代中国法治路径的选择[J].中州学刊,2001( 5) :53 -56.
[45]苏力.当代中国法律中的习惯——一个制定法的透视[J].法学评论,2001( 3) :19 -33.
[46]马怀德.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J].廉政文化研究,2013( 4) :91.
[47]陈金钊.对“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诠释[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3( 2) :77 -96.
[48]陈金钊.诠释“法治方式”[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2) :1 -18.
[49]高鸿钧.现代法治的困境及其出路[J].法学研究,2003( 2) :3 -31.
[50]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上)[J].政法论坛,2005( 1) :3 -23.
[51]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J].政法论坛,2005( 1) :25 -42.
[52]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下)[J].政法论坛,2005( 3) :52 -72.
[53]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续)[J].政法论坛,2005( 4) :41 -72.
[54]邓正来.中国法学的批判与建构[J].政法论坛,2006( 1) :61 -83.
[55]邓正来.直面全球化的主体性中国[J].中国法学,2007( 2) :132 -144.
[56]邓正来.根据中国的理想图景[J].社会科学论坛,2005( 10) :5 -17.
[57]邓正来.“世界结构”与中国法学的时代使命[J].开放时代,2011( 1) :146 -152.
(责任编辑胡志平)
On the way to study the rule of law
ZHU Jun
( School of Law,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Guiyang 550025,P. R. China)
Abstract:Domestic studies of the rule of law continue to emerge,and then study of the results of these studies is also very important. The author thinks there are three ways of studying the rule of law in contemporary China: one way is sublation,namely researches the Western theory of the rule of law by way of comparison and restatement; the second is the way of history,that is researching the theory development of the rule of law in the ancient Western world,as well as in the growth of modern China; the third is the theoretical approach,which starts from the terms of the concept of the rule of law,standards,meaning,path,thinking,and theoretical system,and constructs the China-based theories of rule of law.
Key words:study the rule of law; abandon; the history of fashion; theoretical methods
作者简介:朱俊( 1986 - ),男,四川富顺人,法学博士,贵州财经大学法学院教师,主要从事法治与权利理论研究。
doi:10. 11835/j. issn. 1008 -5831. 2015. 03. 016
中图分类号:D920. 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 2015) 03-012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