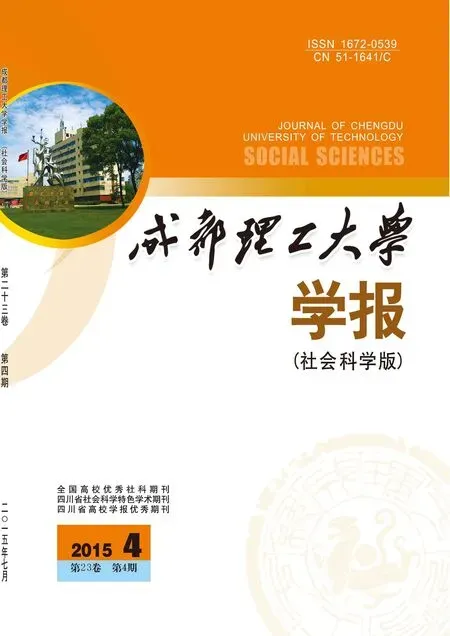温情与超越
——论亚里士多德悲剧观的人学归趋
汪 锐,汪 鹏
(1.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武汉 430079;2.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宜昌 443002)
温情与超越
——论亚里士多德悲剧观的人学归趋
汪 锐1,汪 鹏2
(1.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武汉 430079;2.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宜昌 443002)
悲剧在亚里士多德文艺思想中占据着比史诗更加重要的地位,它继续了“四因说”的一贯立场,将“摹仿”的对象放在现实的人的层面,突出人在实现活动中的丰富性、具体性;从西方早期特别是柏拉图的美学思想上看,它取消了《理想国》对诗人的消极态度,但并没有和柏拉图的诗学思想截然对立,它坚持悲剧要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推进;亚氏对柏拉图的温情超越实现了人学的归趋,厘清这一层关系对于了解希腊文艺思想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
悲剧;摹仿;四因;超越
悲剧(Tragoidia),字面意思为“山羊歌”[1]248。各家解释不一,归纳起来大约有这样几种意思:“(一)比赛的奖品是山羊,(二)演出时歌队围绕着作为祭品的山羊,(三)歌队由扮作山羊的萨图罗斯组成。”[1]248总之,与艺术表演中的歌队和山羊分不开。悲剧作为一种典型的艺术形式大概产生在公元前五、六世纪的雅典,闻名于世的悲剧作者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埃斯库罗斯都活跃在这一时期。在哲学领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出于自身体系的需要,赋予悲剧以不同的地位。长期以来,学界都将他们的悲剧观乃至文艺观看作是不同乃至截然对立的。但笔者认为,从表面看,柏、亚二氏在悲剧问题上态度迥异,但这只是他们认识论上差异所致;在最深处,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彻底摆脱柏拉图的影响,毋宁是一种温情的超越与人学的归趋。
一、悲剧在亚里士多德文艺思想中的地位
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的论述集中在《诗学》里,这里先检讨《诗学》的经典化历程,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亚氏悲剧观的接受情况。《诗学》被看成亚里士多德未经正式发表的著作,学界一般认为它还有一个散轶了的讨论喜剧的部分。和《形而上学》、《物理学》、《工具论》以及《尼各马可伦理学》比较起来,它较晚进入学者们的视界。长期以来,它和《修辞学》一起被当作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组成部分,连贺拉斯、维吉尔这样的文艺理论家和诗人都没有阅读过它,当时学者们甚至混淆了它和贺拉斯的《诗艺》。然而,15世纪文艺复兴之时它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先是G·瓦拉提供拉丁译本,罗伯泰罗是首先撰写《诗学》评论的意大利学者,其《亚里士多德诗艺诠解》在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接着朗巴第和马吉分别发表关于它的研究著作,意大利著名文艺思想家卡斯泰尔维特罗就是用意大利语撰写《诗学》评论的第一人,并且就其中的某些观点大胆地提出反驳。罗伯泰、明托诺和斯伽里格等其他的意大利学者也就其中一些重要观点投入研究。随后法译本、希腊本和拉丁本纷纷出现,甚至德国莱辛的《汉堡剧评》也深受其影响。从《诗学》的经典化过程,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个个事实:
《诗学》开始进入学者们的视域主要在文艺复兴时期,并且以意大利学者的翻译和研究为主。我们知道,文艺复兴借着复兴古希腊罗马艺术的形式,高扬被中世纪所窒息了的人性因子,在这样一种语境下,人自身价值不可能不成为学者们筛选、剔除文艺作品和学术著作的依据。《诗学》在这时被发现出来,正好说明了其自身已具备丰厚的人文内蕴。
《诗学》一书共26章,大体说来,前5章就诗艺的摹仿媒介、对象、方式和发生原理论述悲剧和喜剧,后4章把焦点放在史诗上,6至22章集中探讨悲剧及其6大组成因素。因为亚氏尽量将“诗”理解为一个悲剧美学概念,所以在相当程度上关于悲剧这一美学范畴的研究就代替了对“诗”这一文体的探讨。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在操作上也毫厘不爽,比如在悲剧“情节”里突出“突转”和“发现”,因为“突转”要求“此种转变必须符合可然或必然的原则”[1]89,另外,这也是推动故事发展,让悲剧主角性格完全呈现并引起读者怜悯和恐惧的有效途径。性格、语言、思想、戏景、唱段上的厘定也可以追溯到同样的叙述机制。不难看出,《诗学》是以悲剧为主体的,它的全部人学内蕴也奠基于悲剧,我们甚至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悲剧是其作为一代大哲以饱含热情的眼光看待人本身的一大思维结晶,这一成果很自然在后代引起重视。
相比较而言,柏拉图的文艺思想从篇幅到内容都逊色于他的其他著作。“诗”在他这里是为了建设理想城邦而需特别限制的。王柯平教授曾将柏拉图的文艺思想厘定为“心灵诗学”和“身体诗学”[2]88,即心灵的健康和身体的强壮都是城邦居民必不可少的素质。但在这二者之间又有明显的主次,即心理的纯洁是为了城邦守护者的“勇敢”、“激情”、“智慧”而服务的。在这个问题上,柏拉图表现出了哲学家不应有的焦虑和洁癖,他如此论述:“我们完全有理由拒绝让诗人进入治理良好的城邦。因为他的作用在于激励、培育和加强心灵的低贱部分,毁坏理性部分,就像在一个城邦里把政治权力交给坏人,让他们去危害好人一样。”[1]20并且柏拉图把“诗”的论述放在《理想国》最后部分,其目的仅仅是为了维护城邦的正义。换言之,“诗”并不是柏拉图非得要论述的一个话题,它只不过是为了防止“正义”被践踏的一种防卫。
简言之,悲剧在亚里士多德这里扮演着走向人学的桥梁,相对于整个体系而言它是自律的;但柏拉图的“诗”或“悲剧”却被压抑在一个必须要被提防的角落。相对于柏拉图而言,亚里士多德前进了很多。
二、悲剧摹仿行动
亚里士多德将悲剧定义为:“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1]63我们能够明显地感受到,相对于柏拉图的“摹仿说”,亚氏已经将视角转化到了现实“人”的层面。在柏拉图的“床喻”中,画家的床摹仿的是工匠做出的床,如此以来,“他就像所有其他摹仿者一样,自然地和王者或真实隔着两层”[3]392。柏拉图从知识或真理的可信度方面否定悲剧的价值,并胶着在他的三重世界(理念—现实世界—艺术)上。
按照柏拉图的看法,如果多数事物能够用同一名称来称呼,那么在认识上我们有理由假定它们只有一个形式或理念。“理念”的知识含量高于现实事物,艺术家摹仿的作品的真实度又要低于现实事物。换言之,具有丰富内蕴、与人相关的艺术不在价值考虑之内。《诗学》中亚里士多德对其做了两点改动:第一,悲剧主要聚焦在“人”这一特定的对象上;第二,即便摹仿人,也仅针对有行动力和实践力的具体的历史的人,而不为抽象的理念人。亚氏的治思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悲剧所摹仿的人是有着特定目的和担当的个体,他随着时间的推进会展现出自身的丰富性以致完善。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对亚氏推崇“情节”的做法表示过分惊异了。事实上,“情节”相对于性格、思想等要素而言是本体,人物的个性、思想、言语只有依靠情节的推动才能显现出来。
正是基于此,怜悯和恐惧得到疏泄。在亚氏看来,怜悯和恐惧不仅不会摧毁人的“激情”和“勇敢”,而且还能起到“净化”、“医疗”(Katharsis)的作用。“这些人不具十分的美德,也不是十分的公正,他们之所以遭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罪恶或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错误”[1]97,观众看到比自己好一点的人因为“犯错”而走向悲剧时内心的恐惧感就宣泄出来,这是符合常识的,每一个鲜活的个体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性格缺陷,如果能够让一个比我们自己优秀的人因为“错误”而身陷囹圄,这对我们的冲击无疑胜过完美君子或纯粹小人乃至和我们一样普通人的命运悲剧。这种“净化”又支撑了继续“行动”的动力,长此以往,观赏者既陶冶,又不至于因“怜悯恐惧”而失掉信心。需要指出的是,在亚里士多德这里,人心灵中的非理性部分必须像理性一样得到尊重,而对这种看似“脆弱”部分的处理在更广的视域内成为人“行动”、“完善”等实践才能良性循环的基础。换言之,亚氏悲剧观并不具有柏拉图式的功利目的,比如为了维护一种秩序而欢迎或拒绝诗人群体,他将视域牢牢控制在有待行动起来的“人”这一个体维度上,并且坚信,只要素材针对“行动”着的“人”,摹仿就找对了方向。这比柏拉图“诗增大了欲念的强度,削弱了理性的力量,破坏了心理的平衡”[3]264的思想宽容了许多,也人性了许多。
就摹仿对象而言,亚里士多德世俗化、个体化倾向相对于柏拉图抽象化、理念化追求跨出了一大步,我们认为这是亚氏人学归趋重要的一环。
三、悲剧的人物在于实现
在柏拉图看来,悲剧诗人必须被逐出理想国,因为:“诗是在满足和迎合我们心灵的那个(在我们自己遭到不幸时被强行压抑的)本性渴望痛哭流涕以求发泄的部分。而我们天性最优秀的那个部分,因未能受到理性甚或习惯应有的教育,放松了对哭诉的监督。”[3]405那么,哪些东西是合格的呢?柏拉图认为,我们灵魂中内涵着“激情”、“智慧”、“勇敢”三种组成因素,如果一种艺术作品有损而不是积极协调这三种核心素质,则它就是不符合正义原则的,在和格劳孔的辩论中,正义一直被定义为一种协调能力——对内协调灵魂的三大构成,对外协调城邦中劳动者、士兵和管理者。以“健壮的身体,高尚的智慧”为标志的城邦守卫者是柏拉图追求的人格理想。我们必须指出这种理想所具备的如下两个特色:
其一,这种人格理想以服务于理想国的建设和保卫为终极宗旨。人在理想国中毋宁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悲剧诗人并没有从知识或智慧上给城邦居民以指导,所以被逐出。
其二,这种人格理想仅仅关注人灵魂中“高尚”的部分,对于“低劣”的情欲则坚决回避。很显然,柏拉图并没有从人本的立场关注人本身具有的丰富性和多维性,借用马尔库塞的话说,他欣赏的人是“单向度的”。
何以会这样呢?我们必须追溯到柏拉图的认识论上来。柏氏认为,“理念”是本体,万物皆可以从“理念”上予以统筹;现实中散朴的事物只是对“理念”的分有,在知识上逊色于“理念”。诗人创作固然是对现实事物的摩仿,但其灵感的获得只有在陷入“迷狂”状态时才有可能,“诗人的灵感神奇而富艺术色彩,但灵感是神赋的。所以,与其说诗人在使用灵感,倒不如说灵感在驱使诗人”[1]259。柏氏的艺术发生观斩断了艺术素材的现实来源,把艺术家的主观能动性降到了最低维度,所以艺术家只能被逐出理想国。如果说柏拉图是静止地、抽象地看待艺术发生,那么亚里士多德则从具体的“人”的实现或自我完善上看待艺术的生成机制。
亚里士多德以“第一哲学”的姿态吸纳并发展柏拉图的思想,他把思辨的出发点从作为形式的“理念”推广到现实存在的万物,突出表现在“物因、式因、动因和极因”上。即事物的存在可从它的组成质料、所属的类别、发展动力和终极目的上去探讨。独立存在的现象固然是亚氏研究的一个视域,但他似乎更加关心不同事物的发展潜能以及终极实现,只有实现了的事物才是完善的。亚里士多德还把“实现”应用到伦理领域并和“善”、“幸福”、“公正”这些范畴联系起来。他说:“幸福是灵魂的一种合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4]32所有“实现活动”又都必须以目的为牵引,“医术的目的是健康,造船术的目的是船舶,战术的目的是取胜,理财术的目的是财富”[4]4。不管是“实现活动”还是“目的论”,我们都能捕捉到亚里士多德企图建立一种面向生存本身的哲学的努力。这种努力在《诗学》中保存下来了。
其一,情节的“突转”和“发现”。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的思维转换行动方向,或者让置身于顺达之境或败逆之境中的人物认识到对方原来是自己的亲人或仇敌。情节发展过程中的这两种视域更迭打破了事件的线性前进趋势,圆融辩证地把悲剧人物所具有的“潜能”呈现出来,而这一过程本身也使“人”更加立体化。
其二,“怜悯”和“恐惧”对观众的“医疗”。与柏拉图相反,亚里士多德对人性中“怜悯”、“恐惧”并没有采取“抑制”的态度,而是从积极的方向上将其疏泄掉。为了做到这一点,他特别强调悲剧的摹仿对象必须是犯了某种错误并跟观众较接近的人,这种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观众自己的影子。但值得一提的是,观众在舞台观赏时疏泄掉“恐惧”、“怜悯”情绪固然符合“实现”的目的,但从更深层次上讲,这也体现了亚氏对人尊严的维护,观赏者毕竟不是戏剧的主角,不用亲罹悲剧人物的心灵苦难。
亚氏摆脱了柏拉图静态的摹仿观,把“人”带向广阔的实践生存领域,“实现”了人全部的丰富性。
四、悲剧摹仿中的可然律与必然律
亚里士多德悲剧观固然在形式上走出了柏拉图“摹仿说”,但在深层次里还是和柏拉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温情的超越折射出了亚氏诗学思想巨大的包容性。亚氏强调“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1]81。“可然和必然”就意味着悲剧的素材有逾越现实层面的可能性,这与亚氏一向主张的对人的行动的摹仿似乎存在分歧。其实这正是他悲剧观的出色之处。
从认识论上讲,亚里士多德虽然没有把目光过多地聚焦到“理念”或“通式”上,但他赋予“怎是”以特别重要的意义:“善必与善的怎是合一,美合于美的怎是;凡一切由己事物,基本上自足于己、无所依赖于其他事物者,都该如是。若然如此,则即使他们都不是通式,这个便已足够了;也许毋宁说它们正都是通式,这也就足够了。”[5]151亚氏自己也承认,他的“怎是”在另外一层意义上跟“通式”有若干默契之处。不仅如此,在“四因说”中对“式因”的强调也是为了照顾到这一层意思。我们知道,在柏拉图那里,“理念”是以“通式”的形式出现的,或者说它们都有着超越现实层面的形而上诉求。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轻易否定这些,为了不被“通式”所束缚,他将“实现”的意义放在“潜能”之上。“所以‘混沌’或‘暗夜’不是历无尽时而长存,只因受到变化循环的支配或遵从着其他规律,这些规律得以常见于宇宙之间,故而实现总应先于潜能。”[5]273这样一来,相对于柏拉图而言,亚氏体系既保持了温情的超越,又没有背离形而上的传统。笔者认为,他的这种姿态正好体现在悲剧摹仿的可然律和必然律上面。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解,“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所谓‘带普遍性的事’,指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某一类人可能会说的话或会做的事——诗要表现的就是这种普遍性,虽然其中的人物都有名字”[5]81。通俗地理解,亚氏这里已经触及到了“典型性”问题,即为了突出事或人的典型特征,诗的创作者在材料取舍上遵从逻辑的成分要多于事实的成分。我们知道,历史总是被僵硬地镶嵌在时间秩序中,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亚氏无法容忍悲剧也以这样的姿态存在。他坚信“可能但未发生”的事远比“发生但不可信”的事有价值,诗人尽量做到剔除无关宏旨的琐碎情节,按照寻常情理推进故事发展。换言之,悲剧诗人必须照顾到“行动”中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人基于历史情境的选择、担当才是它的兴趣所在。亚氏在超越柏拉图的同时再一次将人置于舞台中心。
还需指出的是,虽然亚里士多德关注现实中活动的人,但其出发点依旧是形而上学,他不可能真正地从价值的层面讨论人在具体生活情境中表现出的丰富性,很显然,他所推崇的“实现”或“可然律必然律”仍旧洋溢着浓郁的功利色彩,但相对于柏拉图,他人性化了许多。
五、结语
总之,悲剧在亚里士多德文艺思想乃至整个体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他强调诗人要摹仿行动中的人按照可然律必然律推进的实现活动,相对于柏拉图而言,“人”被置于文艺中心。但这种超越只能是温情的人学归趋,因为亚氏体系的圆融辩证特征只能部分地顾及到人的生存。梳理清楚这一点,对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古希腊文艺思想的演进有一定意义。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2]王柯平.《理想国》的诗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Warmth and Beyond:An Analysis of Aristotle’s HumanismTrend From His Trategy Concept
WANG Rui1,WANG Peng2
(D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Media,China Three Geroge University,Yichang 443002,China)
Aristotle attach more importance to tragegies than epics,for the former is originated from his famous topic“four causes”said and imitate persons around us.As a result,characters’s lives become plentiful.Compared to Plato’s aesthetic c concept,although it change Plato’s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s poets,it consistent with latter in many aspects.Aristotle views that the poetry should observate laws their history happen.Aristotle’s poetic concept contains a humanism trend,which has an important effect on western Aesthetics.
Aristotle;poetics;humanism trend;tragedy
I106
A
1672-0539(2015)04-0033-04
编辑:黄航
10.3969/j.issn.1672-0539.2015.04.007
2014-09-30
汪锐(1989-),女,河南许昌人,硕士生,主要研究文学理论;汪鹏(1989—),男,湖北竹溪人,硕士生,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论,E-mail:163294264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