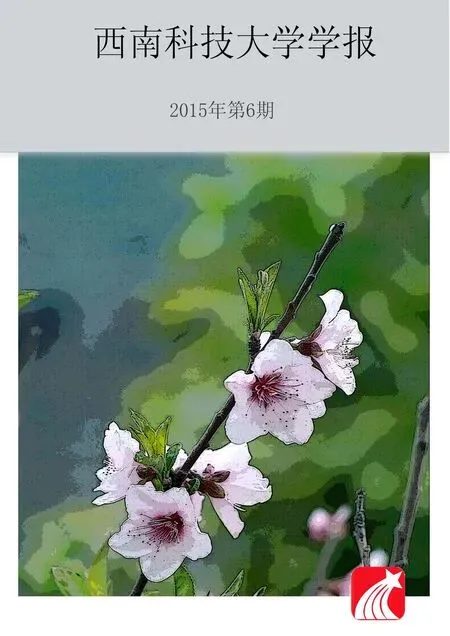隐名出资人法律地位研究
邓 鹏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重庆 401120)
隐名出资人法律地位研究
邓鹏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重庆401120)
【摘要】在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财产权属性受到公司人合性的影响,这造成了隐名出资时,股东资格认定的复杂性。认定股东资格,要以维护公司独立性为中心,遵循从公司内部关系认定走向外部合同关系的路径。在公司内部关系认定中,优先考虑形式标准。商事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不仅要尊重当事人的内心意思,更要关注内心意思的外部表示,以维护第三人利益和交易安全。名义股东转让股权的行为属于有权处分,不能参照善意取得制度而判断其效力。
【关键词】隐名出资;股权;人合性;有权处分。
隐名出资人法律地位的认定一直是公司法理论备受争议的焦点。如果对该问题不能从理论上进行廓清,则会影响公司司法实践中隐名出资人身份的准确认定。而且,出资人作为公司法律关系网上的一个节点,其身份之认定对其他相关主体法律关系的判定影响甚大。经过对相关文献的仔细梳理,关于出隐名出资人的认定有三种学说:形式要件说、实质要件说和折衷说。也有学者直接从公司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的界分来解决隐名出资人的身份问题。还有学者通过对各种能认定股东资格的证据进行了证据效力大小的排列,并以此来确定谁是公司的真正股东。理论上的百家争鸣可谓学术繁荣的象征,然而,在该问题上尚未形成共识也使得公司司法实践在隐名出资人地位裁判过程中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对于案情相同的案子,实务界甚至出现了截然相反的判决。最高人民法院也发现了其中的问题,希翼通过司法解释对此疑难进行释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公司法解释(三)》)对此作出了回应。《公司法解释(三)》基于对公司法律关系主体利益的衡量,明确了由隐名出资引起的股权确认纠纷的解决途径,实值赞同。《公司法解释(三)》第23条对享有股权的事实作了要求,即实际出资、认缴出资或者依法继受股权,且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24条规定实际出资人可以请求公司履行签发出资证明书和在登记机关登记,这一规定从反面另辟蹊径地说明了形式条件对于股东资格认定的重要性。接下来第25条第2款强调了实际出资应作为判断公司股东的要件,以实际出资为标准来界定实际出资人和名义出资人的关系。从上述规定可以认为实际出资人为该部分股权的真正所有人。但是第25条第3款突出了对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维护,其目的是平衡各方主体利益,实际出资标准在这里基于人合性的考量向形式标准妥协。然而《公司法解释(三)》第26条规定名义出资人处分该部分股权的行为应参照《物权法》第106条来处理。《物权法》第106条是关于物权善意取得的规定,适用善意取得的前提是行为人无处分权。此时,矛盾已经显而易见。对名义出资人没有经过隐名出资人同意而对外转让股权的行为如何定性存有矛盾。是有权处分?还是无权处分,并进而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因此,对隐名出资人的法律地位进行分析是理论发展的需要,也是司法实务的紧迫要求。
一、 问题的产生
理论上通常将出资人虽然实际出资,但是其姓名或者名称并没有被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或者工商登记材料上的情形称为隐名出资。简而言之,隐名出资是指社会主体借用他人(第三人)名义而出资的现象。[1]隐名出资这一社会现象的产生有着自身的土壤。从人性角度而言,这是人趋利避害的本性的体现;从经济视角观之,是人获取最大利益的本能使然。于前者,出资人可以通过隐名而规避现行法律、法规对自己从事经营活动的不利限制,甚至禁止;于后者,出资人很有可能因为自己不合时宜的显名而错失与他人进行交易的机会。正是这种实际出资人和登记、记载的出资人不一致的情形造成了二者谁能取得公司股东资格这一现实问题。《公司法解释(三)》对相关问题作出了回应,但是仍然有不足之处。在面临股东资格确认的现实时,似乎缺乏勇气鲜明地表明立场,给人们一种欲言又止的感觉,表现为对名义股东处分股权的行为是无权处分还是是有权处分的判断上举棋不定。
(一)实际出资与股东资格
资本是公司实体的基础。没有出资,就无法形成公司这一庞大实体。无论是法定资本制还是授权资本制,亦或折衷资本制,实际出资都是股东最基本的义务。但是实际出资是否具有创设股东资格的效力?有学者认为,如果实际出资人在没有规避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合同效力性强制规定的情况下,以名义股东的名义实际出资,应认定该实际出资人为公司股东。因为他们认为隐名出资人的出资行为是一个创设其股东资格的行为。
但是,部分股东没有出资或出资完全是虚假的,也不影响公司的依法成立。股东出资却并不一定是取得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2]诚然,在民事法律关系中,行为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法律行为为自己创设权利,并履行相应义务。但,这是以法律规定为前提的。法律上的资格由于与法律规定密切相关,故具有不可转让性。[3]尽管民事法律将绝大部分市民社会中的行为都纳入了民法庞大的体系之中,然而对于某一行为能否使行为人取得某种权利,仍然应该回归法律文本中需求答案。
股东是享有股权,并对公司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股东地位需要公司存续为前提。在我国废除了法定资本制的背景之下,股东资格的取得并不以该已经实际出资为必要。发起设立,只要有所认购股份的种类以及数量的记载即可。根据该认购就可以确认股东身份。[4]在公司中拥有股东资格并不一定能够享有完整的股东权利。如果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则可以通过行使相应的抗辩权对自己进行救济。在被股东会除名之前,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仍然具有股东资格,只是其权利应受到相应的限制而已。
进一步讨论,如果实际出资不具有创设股东资格的效力,那么实际出资的作用又是什么呢?实际出资的那部分资产构成了公司资本,是公司开展营业活动的基础之一。从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由严格变宽松的变迁来看,关于公司资本相关立法的目的在于更广泛的集聚社会闲散资金,提高资本流动速度和资本利用效率。可见,实际出资的功能不在于赋予出资人股东资格,而在于确定公司资本的真实性,提升公司参与市场竞争,与相对人进行交易的能力、实力。限定可以作为出资的财产是源于资本要实现的两大功能:一是警示功能,二是担保功能。[5]由以上分析可知,实际出资与股东资格之取得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出资的真正价值在于确保公司资本的真实性。
(二)形式标准与股东资格
也有学者从商事交易安全出发,认为股东资格的判断应着眼于商事行为的外观,以登记、公示所记载的材料为认定股东资格的标准,从而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现代商事交易具有快捷迅速的特点,公示登记所载的材料应具有公信力。公示于外表的事实与真实的情形不符时,对于依该外表事实所进行的商行为,亦须加以保护,以维护交易的安全。[6]通过公示相关资料,能够节省交易相对人调查公司基本情况所耗费的成本,符合商事效率原则。股东资格的表现形式是经由工商登记材料、股东名册或者公司章程体现的。而这一方式又是为商事法律所确认的。这样的制度安排,显然是以交易安全为出发点的。
无论实质出资标准还是形式登记标准,二者均有一定合理之处,但是都显得十分极端。实质标准和形式标准站在对立的两极,并没有对隐名出资所形成法律关系网络进行细致的梳理。而此刻,笔者并无意将涉及隐名资格的法律问题作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分而论之的简单化处理。因为实际出资人资格的并不是能够通过简单地划分内部、外部关系就可以得到根本的解决的。
二、股权的财产权色彩与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之矛盾
(一)股权的性质
实际出资人处于何种法律地位,实际出资人和名义出资人谁才是公司真正的股东,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有巨大争议。通常认为,股东是公司股权的享有者。对股东资格的认定就是对股权归属的确定。在传统的民事权利体系下,存在着人身权和财产权这两大类别。因此大多数学者对股权性质的讨论都被置于这两类传统权利类型下进行。关于股权性质的学说,在财产权下展开的具有代表性的学说有所有权说和债权说,在人身权下讨论的也有社员权说、股东地位说。也有学者在对传统学说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重新界定了股权的本质,认为股权是一种自成一体的独立权利类型。
确定股权性质与隐名出资下股东资格认定密切相关。如果认为股权是基于社员身份而取得的,那么隐名出资人在法律上就失去了立足点。另一方面,从出资与股东资格的关系来看,实际出资与股东资格的取得并不具有不可分离性。从资本制度由严变宽的改革进程来看,股东资格的取得与实际出资的可分离性愈发明显。股权的资本性决定了股权的非身份性和可转让性。[7]然而,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的人合性始终是不能回避的现实。正是在社员身份与出资的不断纠缠之下,股权性质也变得扑朔迷离。合理界定股权的性质,需要从股权自身的特点出发,从股权产生的历史使命着手,将股权置于股权得以存在的公司内部结构之下进行分析。
首先,大陆法系传统理论认为,公司是营利性社团法人。公司的社团性已为理论界认同。“一人公司的存在只是公司社团性的例外,也不能因此而否认公司作为一种社团法人。顾名思义,它们只不过是有限责任公司的一种例外,承认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并不是对公司社团性的否定。”[8]公司营利性不仅体现在公司通过从事经营活动获取利润,也体现为将经营活动所获取的利润分配给股东。出资人将自己财产的所有权依照相互间的协议组织起来而设立公司,出资人的目的在于利用公司法人这一具有独立人格的市场主体从事相关营业活动,获取利益。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具有不稳定性,出资人对经营判断的失误也是在所难免的,况且,投资本身就是一种具有风险的商业行为。公司的有限责任制度就在投资人和投资风险之间树立了一道屏障,它使投资人的财产损失被限定在其出资范围之类,免于全部财产成为责任财产,也就减少了财产损失。通常来说,股份是股权的数量表现形式,“一股一权”为股东承担相应责任划分了界限。无论从投资获取经济利益,还是利用有限责任来避免更多的财产损失,都可以发现,获取股权的目的在于财产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股权具有经济利益的一面。
其次,股权具有流转性。股权的可转让性是指相对人可以通过购买公司股份取得股权。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可以通过证券市场进行股份交易。有限责任公司比股份公司对股东人合性有更多关注,有限责任公司对股东人合性的维护并不是通过像普通合伙一样对合伙人所有权与经营权捆绑得以实现的,而是以同意转让股份的股东人数进行。股权的流转性充分说明了股权具有的财产权的性质。股权的本质仍是财产权。股权的权能都体现了它所包含的经济利益。[9]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对股权的流转进行适当限制是基于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考量。况且,有限责任公司本来就是法学天才的创造物,它是脱胎于股份公司的一种企业形态,这就决定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与生俱来的财产权性质。
再次,有学者对股权性质持“社员权说”的观点。他们认为股权并不是社员所享有的权利,而是因为本人具有的社员资格而享有的权利。社员权是社员资格的产物。社员权与社员资格的区分使得社员权具有了身份性。更进一步,社团都是人的结合关系。而社员资格的取得要求加入方和接受方表示一致为条件。我认为将具有较强的流通性股权视为一种具有身份属性的“社员权”是不妥当的。身份权是人身利益的体现,并不具有流通性。
最后,股东作为股权的享有者,除了可以获得财产性利益之外,也可以通过所拥有的股权影响、制定公司经营策略,对公司进行有效管理,增强公司的经营能力。在股东不便行使股权的情形下,股东可以委托第三人代理行使股权。股东会和董事会作为公司的意思决定机关,都是会议体,其意思决定权的行使不仅需要以会议的形式进行,而是需要根据团体的规则形成决议。[10]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股权具有财产权的性质,符合财产权的特性。然而股权究竟是何种财产权却有待深究。是物权,是债权,亦或一种新的独立财产权?学界在这一问题上尚无定论。无论如何,股权始终是股权,从股份有限公司到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改变。
(二)有限公司的人合性
股权因为公司存在而存在。在股份有限公司中,股份公司资合性较强,股份流动性较强,原则上不存在隐名股东的问题。[11]在股份有限公司中不会存在的隐名出资问题却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出现,这说明了体现有限责任公司个性方面的某种东西影响了隐名出资人资格的判断。这就是有限责任公司对股东人合性的要求。在有限责任公司中,之所以较难认定股东资格,实质在于两种公司形态对股东人合性的要求不同。有限公司在公司经营依赖股东间的相互信任关系,所有权与经营权一般不分离,公司资本的流动性较小,小的有限公司在对外交往时要靠股东的信用,与合伙和无限公司相像,一般而言,也属资合兼人合的公司。[12]有限责任公司对股东人合性的要求使得具有财产权色彩的股权与股东身份的混合。正是股权作为一种财产权所具有的流动属性与股东身份的唯一性的矛盾使得股东资格认定问题陷入泥沼。
人合是与资合相对应的术语,是指公司对外承担责任的基础是依赖于股东的良好信誉、声望以及公司的成立以各股东之间的相互信任为基础。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对外承担责任的基础在于公司资产。虽然在外部责任承担而言,体现的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资合性。但是,有限责任股东相互间又具有人身信任因素,具有人合的色彩。[13]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通常表现为投资人间的信任和合作。股东资格的取得则不再是以个人意志为基础的个人行为,而是以成员何意为基础的团体成员身份认同行为,是公司的团体性行为。[14]只要商事主体的投资人之间具有此种紧密的合作关系与相互信任,我们就可以说此种商事主体具有人合性。所以,有限责任公司仍然被视为具有强烈人合色彩的商事主体。[15]《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作了限制,设置了与股份有限公司相区别的股权转让程序,同时,赋予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更多的公司自治权,以维护有限公司的人合性。
三、认定路径
隐名出资关系下,股东资格的认定应从维护公司独立性,塑造公司法人独立意志入手,更要基于有限责任公司对股东人合性的要求作考量。本文认为在隐名出资中,不同主体的法律地位认定应遵循这样一种逻辑进路:首先按照形式标准认定名义出资人具有股东资格,隐名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的法律关系则通过他们相互间的协议进行界定。
(一)股东资格的确定
承认名义出资人在公司的股东地位,是对公司独立人格的坚持。公司作为独立的市场交易主体毫无疑问要遵从“自己行为,自己责任”这一朴素的民法学理。名义出资人股东地位的确立使得公司内部结构得以稳定下来,公司所进行的交易活动便不会因为交易主体的任意变更而受到不利影响。真意主义是适合于民法等个人法的立法理念,而表示主义则与商法等团体法的立法观念相吻合。公司法属于典型的团体法,自应优先适用团体法的一般规则。[16]实际出资人对其出资享有受限制的财产权(主要是收益权),但形式要件才是股东在公司行使完全股权的推定依据,特别是管理和控制权利、获得信息和查询公司帐薄的权利、提起派生诉讼的权利等。[17]有限责任公司是虽然是中间公司,但是其人合性显然较资合性更强。有限责任公司的发起设立是各股东基于对彼此的相互了解和相互信任而为的法律行为。而且《公司法》赋予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更多的自治权。有限公司具有的人合性是其区别于股份公司的根本特征,是体现有限公司自身价值的属性。如果因为没有实际出资而径直否认名义出资人的股东地位也就不利于有限公司自身价值目标的实现,违背了企业维持理论。在公司内部,名义股东的地位虽然得到承认,但是由于并没有对公司出资,没有履行出资义务,其股权的行使应受到相应限制,甚至可以引进股东除名制度对该股东予以除名。
从形式条件认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标准通常有三种情况:工商登记、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我国股东资格的认定标准是根据公司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公司工商登记材料等显性证据的记载。[18]当上述三种记载一致时,股东资格是显而易见的。现实情况是,当出现三者记载并不一致时,应该参照何种标准进行判断呢?此三种记载均属形式标准,均体现商事法律所追求的外观法理。因此,本文认为应该从外观主义所产生的公信力强弱作为标准。公信力最强的形式标准优先适用,公信力强度逐次降低,作为标准的顺序也越靠后。公司的成立需要办理公司设立登记。虽然登记机关对公司股东的登记并不能直接创设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登记机关所作登记会产生公示公信力,善意第三人因信赖公司登记而与公司进行交易的行为值得法律保护。这是商法外观主义的要求。
根据股东名册所记载,名义出资人成为公司股东,具有股东资格。登记于股东名册的股东或者经过变更登记的股东,可以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但是,公司不履行登记义务等原因导致股东名册未予记载的,可以通过股东资格确认之诉进行更正。在更正之前,公司只对现已记载于股东名册上的股东给予股东待遇,履行公告等义务。若存在隐名股东,只有通过股东身份确认程序,才能具有股东资格,从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19]
公司章程作为公司的自治法,是股东共同签署的,说明行为人有作为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20]公司章程不仅确定了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且作为公司必备事项,在对外交易时为交易相对人查阅,具有公示效力。公司章程可以成为判断股东资格的形式条件,但是其生效或者变更股东通常需要经工商登记机关予以登记,因此,其公信力较工商登记弱。
(二)名义出资人与实际出资人的法律关系
在确定公司股东之后,接下来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明确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的法律关系。实际出资人通过投资公司获取利润,最好的办法是由自己直接行使股东权利,影响公司经营策略的制定,以期减少代理成本,实现利益最大化。现实状况却与出资人的愿望背道而驰。用隐名出资的方式进行投资使得自己失去了亲自掌控公司的主动权。况且,名义出资人作为一个经济人,难免不为自己的利益而计算。在这种情形下,实际出资人的权益被损害了,需要通过法律途径寻求公平正义的实现。为了保障出资人的合法权益,法律应对隐名出资人和名义出资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进行调整。隐名出资人可以要求名义出资人按照双方之间的协议履行义务,也可以通过股权转让程序使自己从幕后走向前台,让自己显名化。需要注意的是当事人的协议是否有效,应结合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并按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判断协议效力。
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公司法(解释三)》认可了名义出资人与实际出资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合同的成立是双方当事人对合同内容意思表示合致的结果,合同是私法自治精神的体现。分析隐名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该从他们达成的协议入手。双方当事人将自己的内心意思用合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达成一致,并利用合同划分了各自权利义务的范围和责任。首先需要讨论的是合同是否存在无效的情形。出资人向公司出资后却不让自己显名是有多种原因。例如,根据《公务员法》公务员不得从事或参与营利性活动的规定,公务员不能成为公司股东。于是,某公务员另辟蹊径地用隐名出资的方式逃避公司登记时的股东资格审查,从公司经营中获取财产利益。对于前述行为,出资主体因为违反了行政法的强制性规定,宜认定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指出:“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法律法规的意旨,权衡相互冲突的权益,诸如权益的种类、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规制的对象等,综合认定强制性规定的类型……”。从《公务员法》法条来看,并不能直接发现对公务员参与经营行为的效力持否定态度。但是结合法律条文本身的目的和所保护的法益内容,可以认定该类合同属于违反了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诸如此类,在确定了合同效力之后,具体分析合同内容,判断具体权利义务的归属。投资协议是隐名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的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隐名出资人可以要求名义出资人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其合同义务。公司并不应该参与到隐名出资人和名义出资人的合同关系中,公司关注的焦点应在于公司股东是否完全履行了自己的出资义务。
(三)股权处分的效力
在隐名出资引起的法律关系中,往往牵涉到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问题。这部分股权转让的效力如何,值得探究。《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六条针对名义股东处分股份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作了回应。该条文规定:名义股东处分股权而引起纠纷的,参照民法善意取得制度解决。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一个前提是基于行为人的无权处分行为。公司法解释也就暗含了一个结论:名义股东转让股权的行为是无权处分。进一步言之,隐名股东才是该股权的真正权利人。对公司而言,既然隐名股东是股权的真正权利人,那么在股东资格的认定上,司法解释坚持了实质要件的判断标准。然而,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在立法态度上,似乎偏向以形式要件说作为判断股东资格的标准。尽管第二十四条也包含了实质要件说的内容,但更多体现了形式要件说的内容。司法解释这种暧昧不明的态度也为学界提供了一个争议点。
本文认为,名义股东转让股权的行为应属于有权处分。其理由如下:界分处分权之有无,实质上是考量相对于权利客体的主体是谁。在实际出资与取得股东资格相分离的现实条件下,实际出资人与公司的关系是一种外部关系。然而,享有股权,行使股权均需依赖于公司股东这一特殊身份。如果公司没有拒绝股东登记或者登记错误,公司只对已经登记或者记载的股东履行义务。即使第三人是善意的,是否为善意取得,取决于公司是否为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21]如果认为名义股东处分股权的行为系无权处分,实际出资人作为权利人有权转让股权,这会造成以公司为节点的法律关系的混乱,而且这种观点也有悖于公司法法理,损害了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
当名义股东向第三人转让股权后,该第三人成为公司股东,享有股东权利。通过确认转让行为的有效性,公司股权结构得以确定,公司的独立性得以维护;第三人所受让股权的效力也被肯定。细心观察会发现,在这种情况下,实际出资人的利益并没有受到全面的维护,即使可以通过对其与名义股东的合同关系进行矫正,但是,从利益实现的实然层面看,法律还可以做得更好。尤其是为了保护实际出资人的利益,可以规定名义股东转让其股权后,实际出资人可以从受让人处取得股权转让合同的利益。需要注意的是,由实际出资人取得该股权转让的利益与名义出资人的有权处分并不冲突。属于有权处分是基于公司经营之稳定、连续和公司人合性的需要,同时也应考虑交易安全性,有权处分所获取的利益也并不必然归属于同一主体,即名义出资人。这一点可以从对非法获取的现金出资的处理上找到答案。对于货币,民法理论坚持占有即所有的原理,承认以非法获取的货币出资属于有权处分,作为出资的货币来源的非法性并不影响出资的效力。[22]这和本文所讨论的名义出资人的有权处分有着逻辑结果的一致性。所以,为了平衡实际出资人的利益,由其享有转让合同之利益是实质正义的体现。接下来,应该思考的是如何保障这部分利益的实现。可以考虑规定名义股东的通知义务,在合理期限内通知实际出资人。实际出资人同意,则在转让股权合同时类似订立了一份利益第三人(实际出资人)合同;如果实际出资人表示反对,则应由名义出资人将该部分出资的相应对价支付给实际出资人,以保证股权的流通性;如果实际出资人在合理期限内未作表示,可以认为其默示同意。要注意的是,上述三种情况并不妨碍实际出资人可以依照其先前与名义股东签订的合同追究其违约责任,如此,实际出资人的利益便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维护,同时也有利于公司独立性之保护,又兼顾了股权基于其财产权性质的流通性。
作为民事法律特别法,商法除了具有民法注重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等价有偿的基本精神外,还洋溢着有别于民法精神的独特的商事法精神,如商事法更加注重行为外观,相比内心真意,更加强调真意的外部表示。这种信赖的根据并不是或不仅仅是某项可归责的意思表示,其所根据的只是由其他方式产生的、存在某种相应的权利状态的表象。[23]商事法对外观主义的坚持是对商事交易现实需要的必然反应,是维护商事交易关系稳定,提高交易效率的重要手段。商法对外观主义的坚持甚至超过传统民法理论对当事人真实意思探究。股东资格应考量表示主义的运用,赋予股东名册、公司登记材料等表示行为优于内心意思的效力。[16]
结语
关于隐名出资人资格认定的标准,也可以说是一个价值取向问题。登记、记载的主体与实际出资主体的不一致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认定的表面原因,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具有财产权色彩的股权嵌入了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制度结构中。认定谁是公司股东,需要从维护有限公司人合性的特征出发,同时,也要尊重公司独立的法人人格,并稳定以公司为中心的交易网络的法律关系。现代商法精神倡导的外观主义是保证交易安全的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商法理念也要求我们将外观表示置于比内心意思更靠前的位置。相对人与公司进行交易,凭借对该公司登记公示的材料的查阅,可以获得对公司财务状况、交易能力、信用度的一个直观了解。公司的前述能力需要通过公示于外表的事实获取相对人的信任,从而推动交易的达成。
参考文献
[1]赵旭东,顾东伟.隐名出资的法律关系及其效力认定[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19):141.
[2]周友苏.试析股东资格认定中的若干法律问题[J].法学,2006(12):80.
[3]罗晋京.试论公司股东资格、股权、股东[J].特区经济,2008(2):99.
[4]前田庸.公司法入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9.
[5]左传卫.股东出资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13.
[6]赵万一.商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6.
[7]江平.论股权[J].中国法学,1994(1):76
[8]吴高臣.有限责任公司法论[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7.
[9]冯果.公司法要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83.
[10] 朱慈蕴.公司法原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134.
[11] 王岩.隐名股东确认之诉的几个问题研究[J].法律适用,2007(12):41.
[12] 史际春.企业和公司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17.
[13] 石少侠.公司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29。
[14] 胡晓静,崔志伟.有限责任公司隐名出资法律问题研究[J].当代法学,2012(4):35.
[15] 刘凯湘,张海峡.论商法中的人合性[A].商事法论集[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2):26.
[16][24] 蒋大兴.公司法的展开与评判[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497.
[17] 甘培忠,周淳.隐名出资纠纷司法审裁若干问题探讨[J].法律适用,2013(5):20.
[18] 吕召,高雁.公司隐名出资人股东资格确认的相关问题[J].中国审判新闻月刊,2008(7):71.
[19] 华小鹏.有限责任公司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认定[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8(4):116.
[20] 范健.论股东资格认定的判断标准[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6(02):67.
[21] 王涌.股权如何善意取得[J].暨南学报,2012(34):33.
[22] 胡晓静.公司法专题研究:文本·判例·问题[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214
[23] 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886.
Analysis on Legal Status of Dormant Investors
DENG Peng
(School of Law,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In a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property rights in stock rights was influenced by characters based on shareholders, it conducts the complex of cognizance of shareholder qualification in dormant capital subscription. To affirm shareholder qualification, we should sustain the independency of company, and comply the way from inner relationship to outside. Formal elements should be considered firstly in inner relationship of company. As a special law of civil law, a commercial law is not only explore a litigant' inner meaning, but also lay concer on the expression of it, to protect the benefits of the third party and transaction security. It is valid that nominee shareholder transfer the shares, and cannot judge its validity refer to goodwill get system.
Key words:Dormant capital subscription; Equity ownership; Characters based on shareholders; Entitled to dispose.
【中图分类号】DF411.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4860(2015)05-0081-07
作者简介:邓鹏(1989—),男,汉族,四川达州人,硕士。研究方向:刑法学、商法学。
收稿日期:2015-06-14 2015-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