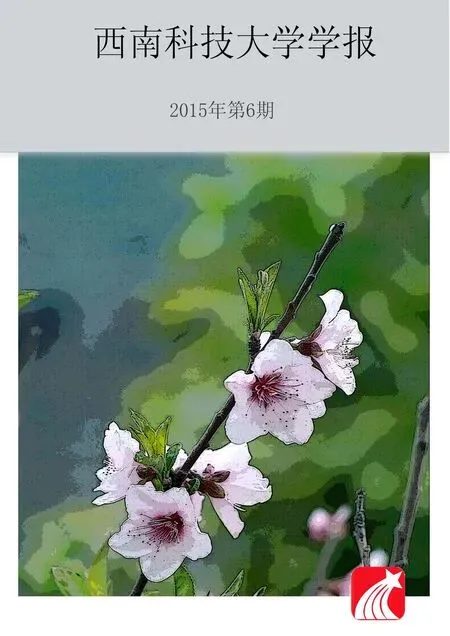儒家中庸尚和与基督教崇力尚争之比较
靳浩辉
(中共中央党校 北京 100091)
儒家中庸尚和与基督教崇力尚争之比较
靳浩辉
(中共中央党校北京100091)
【摘要】儒家与基督教作为中西方文化的代表,分别彰显出中庸尚和与崇力尚争的精神气象。对儒家的中庸尚和与基督教的崇力尚争进行比较,在透析两者差异与区别的同时,有利于增进儒家与基督教之间的了解,也有益于中西方文化的深层对话。
【关键词】儒家;中庸尚和;基督教;崇力尚争
儒家与基督教作为中西方文化的代表,在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具有鲜明的差异,儒家崇尚中庸,不走极端,追求和谐与稳定,对外来文化比较包容。而基督教崇尚竞争,易走极端,追求力量与对抗,对异己文化比较排斥。儒家中庸尚和与基督教崇力尚争的思想分野,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中西方文明的迥异。
一、儒家中庸思想的历史嬗变
孔子认为中庸是最高的道德境界:“中庸之谓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多次论及中庸,如赞美《诗经》的《关雎》篇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又说一个人的性格风度,“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崇尚“中庸”,提出了处理问题的尺度,主张执两用中,强调“过犹不及”。“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在他看来,狂、狷都是不可取的,依中道而行方能有所作为。《论语·先进》记载了孔子对学生的评价。孔子认为子张和子夏,一个太过,一个不及,两人各走一端,都有偏激之处,所以说他们“过犹不及”。在孔子看来,事物都应以中庸为标准,这就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论语·尧曰》)孔子主张凡事应“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因此“允执其中”就成了孔子倡导的处理问题的方法与理念。
《中庸》是我国古代第一篇专门阐述中庸学说的文章,相传为孔子之孙子思所著,它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中庸理论,从而成为儒家学说中至关重要的经典著作。《中庸》第一章提纲挈领地阐释:“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庸,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首次把“中”与天道、人性联系起来,以调节人性固有的喜怒哀乐等感情为根据来阐明中和之道。首先提出了“未发之中”和“中节之和”两个命题,然后断言“中”是大本,“和”是达道,最后极力描述“致中和”的功效以及所达到的最高境界。
孟子作为孔子的“私淑弟子”,并直接受业于子思,自然继承了他们中庸的思想。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在孟子看来,杨朱为我,墨子兼爱,前者无君无夫,后者爱无差等,孟子认为他们俩都过于极端,不符合“执中”之道。
由此可知,儒家中庸的核心理念便是思想行为的适度和守常。反映在事物中,要求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既反对没有灵活性的固步自封,也反对没有原则性的见风使舵。
二、儒家尚和思想的四维体现
(一)儒家尚和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其重教化,轻战争和刑罚态度上
《论语》记载,“子之所慎:斋,战,疾。”(《论语·述而》)战争是生死所关的大事,孔子非常谨慎。孔子认为,“足食”、“足兵”和“民信”是为政的3件大事,而3者又各有轻重缓急,若要去掉一个,孔子首先主张“去兵”。当卫灵公询问孔子军队列阵之法时,孔子毫不犹豫地反驳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论语·卫灵公》) 并且第二天就离开了卫国。其对战争的审慎态度可见一斑。另外,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人小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孔子反对嗜杀,主张“为政以德”。在上位的人只要以身作则,善理国政,百姓就会纷纷效法顺从,如同风吹到草上,草必定顺着风倒一样。
相对于孔子,孟子崇尚和平,反对战争的倾向更加鲜明。孟子崇尚民本,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施行民本就要重视和珍惜民众的生命,统治者绝不能轻易剥夺民众的生命。基于民本原则,孟子认为“春秋无义战”。春秋时期的战争,目的在于争夺城池,拓展疆域,常常导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为此孟子愤然谴责道:“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离娄上》)孟子反对“以力服人”,主张“以德服人”,并以“以德服人”与“以力服人”作为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在战国群雄争霸,兼并战争频繁的背景下,孟子推崇仁政与王道,反对不义之战的思想可谓是弥足珍贵。
(二)“协和万邦”是儒家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
儒家崇尚“和”是解决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主张“协和万邦”。“协和万邦”最早见于《尚书·尧典》,“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俊德”指才德兼备的人,“钦”指恭谨严肃,“明”指明察,“恭”指谨慎,“让”即不骄,这些都是“俊德”的具体德目。“明德”的社会功能是亲睦九族、协和万邦,求得世界的普遍和谐。[1]317-318内圣的明德鲜明地指向外王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治国就是“九族既睦,平章百姓”,以求得内部的和平与和谐,平天下就是“协和万邦”,以达到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与和谐。随着《尚书》被尊为儒家的“五经”之一,其所主张的处理国家关系的原则也逐渐被统治者所采纳。儒家“协和万邦”的理念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国与国之间的和谐交流。
儒家协和万邦的思想,最鲜明地体现在朝贡体系的构建上。对于周边国家,只要承认中原王国的权威并向其朝贡,中原王国并不武力直接统其国土,对于前来的各国进贡使臣及其国王,中原王国赏赐的物品较贡品多以数倍,可谓是“厚往而薄来”(《礼记·中庸》)。另外在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开展国际贸易时则采取互利互惠、公平交易的原则,并不是借武力以大欺小,以强凌弱。这也彰显出儒家“柔远人”(《礼记·中庸》)的和平理念。
(三)“贵和”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法则
儒家“贵和”思想体现在人与自然关系层面,主要是指“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融合性与统一性,“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孔子曰:“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天地的运行和万物的生长都是自然而然的,人类应该承认并遵循这种自然规律,而不能贸然违背。《论语·述而》载:“子钓而不纲,戈不射宿。”《论语·雍也》载:“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孔子甚至认为“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祭义》)将对待生物的态度提高到孝道的程度。曾子亦言“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礼记·祭仪》)孟子继承了孔子“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的仁爱理念,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将仁爱之心推己及人,进而推己及物,“恩,足以及禽兽”(《孟子·梁惠王上》),要求统治者合理利用资源:“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慧王上》)。荀子也认为:“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荀子·礼论》), 将人的怜悯同情之心辐射到生物身上,从而使人生发出尊重并保护生物的情感。后来宋儒张载提倡“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也是遵循了“天人合一”的理念。
(四)“贵和”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法则
儒家认为,“和”不仅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一种有效调解人与人之间利益冲突的方式。孔子积极倡导“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和为贵”的理念是从礼中彰显出来的。孔子以射箭作喻:“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认为君子在竞争激烈的射箭当中可以以礼相待,和睦相处,这种争也是君子之争。孔子还提出了人际关系和谐的具体方法,就是其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能依忠恕之道而行,方能实现“均无贫,和无寡”(《论语·季氏》)的理想境界。当樊迟问仁时,孔子回答:“爱人”(《论语·颜渊》)。孟子后来发展为:“仁者爱人”,孟子强调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仁者以关爱他人为出发点,推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进而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和谐,故而有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说。总而言之,儒家以“和”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则,其最终理想是实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的大同理想。
需要强调的是,儒家的“中庸”思想往往与“尚和”思想紧密相连,从而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儒家“中庸尚和”的价值深蕴,并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国人的精神气象。
三、基督教的崇力尚争
(一)基督教崇力尚争的思想根源
基督教崇力尚争的思想具有深厚的思想根源。基督教认为灵肉是二元对立的,而灵肉的二元对立使得基督徒肉身与心灵产生强烈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使得人的灵与肉难以达到和谐,对基督教“崇力尚争”特征的形成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基督教推崇人性本罪,背负原罪的人只有依靠上帝的恩典才能得到拯救,因此基督徒冀求通过“崇力尚争”的现世努力来获得上帝的恩典。另外,基督教是一神教的典范,而一神教极端敌视异端,其显示出来的傲慢与独尊也折射出“崇力尚争”特征。同时,基督徒具有极端强烈和狂热的传教精神,这种传教精神需要“崇力尚争”才得以实现。
(二)基督教“崇力尚争”的四维体现
1.基督教的“崇力尚争”体现在对外异端宗教的战争上
在对外异端宗教的战争上,基督教“崇力尚争”的本性表现最为经典的莫过于“十字军东征”。由于基督教圣城耶路撒冷落入伊斯兰教徒手中,为了从伊斯兰世界夺回耶路撒冷,罗马教皇以捍卫宗教、解放圣地为名,组织西欧的封建领主和骑士,对他们认为是异教徒的国家发动了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十字军东征”从11世纪到13世纪,历时近200年,前后共进行了9次东征,参战人数达200多万人之多。令人惊愕、不解的是,“十字军东征”展现了崇高、神圣目的与残忍嗜杀手段的奇妙结合。一方面,基督徒满怀着圣战的热情和目的走向战争,他们相信为圣战而死灵魂就会升入天堂,为此他们并不畏惧死亡;另一方面,他们为了实现崇高圣战理想,在其过程中所采取的手段极其残忍野蛮,无论男女老少,逢穆斯林便杀戮,杀完之后还把财物抢劫一空。事实告诉人们,“十字军东征”看似目的崇尚而神圣,本质上却是野蛮暴行,其大大深化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上世纪90年代初,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也无不折射出东西方冲突之后的宗教根源。随着“9·11事件”的发生,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矛盾进一步激化,其后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甚至一触即发的叙利亚战争,都表现出基督教对异端宗教“崇力尚争”的本性。
2.基督教的“崇力尚争”体现在对内教派的战争上
在对内教派的战争上,基督教“崇力尚争”的本性表现得最为明显的莫过于惨烈的“30年战争”。1618年到1648年间,在四分五裂的德国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宗教战争。战争最初是在德国的新教诸侯与天主教诸侯之间展开,随后逐渐演变为西欧各国参加的宗教战争。后来这场战争甚至被认为是世界近代史上的第一场国际战争。战场的双方泾渭分明,英国、瑞典、丹麦、瑞士和荷兰支持德国的新教诸侯,而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和罗马天主教会支持德国的天主教诸侯,这场战争持续了30年,前后打了4个回合,但最终没有任何一方取得决定性胜利。直到1648年,势均力敌的双方不得不相互妥协,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该和约以中欧为界,划定了新教与天主教的势力范围。这场历时30年的战争使德国各邦国大约丧失了60%的人口,各参战国亦伤亡惨重,基督教的“崇力尚争”的本性在这场宗教战争中表露无遗。
3.基督教的“崇力尚争”体现在对外殖民扩张上
欧洲基督教世界的殖民扩张,在追求财富,开拓疆域的同时,也传播基督教。殖民者大都肩负着传播福音的使命。在他们看来,殖民地民众是野蛮的、未开化的,而基督徒则是文明的、有教养的。基督徒自身的使命就是教化、洗涤异教徒和野蛮人。于是他们一手端着抢,一手拿着《圣经》,在用坚船利炮轰开殖民地国门的同时,也敲开了殖民地民众的心门。他们的到来,不仅意味着殖民地原住民领土和财富的丧失,更是导致了殖民地民族文化的衰落。可见,基督教世界的殖民扩张始终是与基督教的传播紧密相连的。在基督教传教精神等因素推动下,西欧各国纷纷走上了殖民扩张的道路。基督教“崇力尚争”的本性在对外殖民扩张中可见一斑。
4.新教伦理在商业贸易层面凸显了基督教的“崇力尚争”
新教之一的加尔文宗推崇“天职”观念,抛弃了天主教禁欲主义式的修行,希冀将上帝赋予个人的天职在尘世活动中彰显出来。加尔文宗也提倡预定论,认为人在其出生之前就已经被上帝注定了来世的命运,尘世中的人无法得知上帝的旨意;人们在尘世的工作就是为了荣耀上帝;争取职业上的成功,是成为建立获救信心的惟一手段。新教徒为了获得职业的成功,在商业贸易上相互竞争,拼命创造并积累财富。加尔文宗在鼓励信徒注重生产和竞争的同时,禁止奢侈性挥霍,从而渐渐形成了一种多创造、多生产、少挥霍、少浪费的新教伦理。马克斯·韦伯说“假如对生活的禁欲态度经得起考验,则财产越多,就越感到有责任为上帝的荣耀保持不使财产减少,并通过不懈的努力使其增多。”[2]160这种“崇尚竞争,勤于工作”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有着很强的亲和力,成为了促进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精神杠杆。英国和荷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达,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新教伦理的优越性。后来新教徒来到美国,在那里开疆拓土,艰苦奋斗,大力发展商业贸易,为美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儒家中庸尚和与基督教崇力尚争之比较
(一)儒家的内向心态与基督教的开放心态
儒家文化在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中孕育而生。中国的西南面和西面是高耸的青藏高原,东面是难以逾越的太平洋,北面和西北面是贫瘠而荒芜的蒙古高原。儒家囿于血缘宗族的藩篱,加之自身重农抑商,商品经济发展缓慢,这些地理和文化因素致使儒家散发出内向的、崇尚中庸尚和的心态。这种内心的心态也导致其重自我保护而轻外部拓展,并不提倡对外战争。在儒家看来,穷兵黩武式的向外征服是不义的。在对外关系中,儒家主张“协和万邦”,“厚往薄来”,主要以和平的方式开展对外关系,并不力求外部扩张,也并不追求将其制度或意识形态强加于人,希冀用“中庸尚和”的理念实现“平天下”的鸿鹄之志。我们看到,推崇“中庸尚和”的儒家充分展现出一种内向的心态。
与儒家封闭的地理形态相反,基督教产生于开放性的海洋文明,其中心为浩淼的地中海,西面是无尽的大西洋,其他3面则是广袤的陆地,这样的地理条件为基督教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另外,海洋文明致使基督教世界商品经济相对发达,其对外拓展的欲望强烈,加之基督教具有的普世性促使教徒们积极向外传福音:“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马太福音》28∶19),“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马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使徒行传》1∶8)。在上帝的呼召下,基督徒不畏艰难困苦地走上了传教之路。于是,基督教从一个犹太教的异端,突破犹太地,绵延至地中海西岸,进而发展到罗马帝国全境,后来伴随着殖民活动真正走向世界,成为名副其实的普世宗教。其波澜壮阔的嬗变历程,充分展现出开放性的特征。
(二)儒家对异端的包容与基督教对异端的排斥
与西方人认为“一切作用在其敌对上”不同,中国人认为“一切作用在其和通上”[3]454。儒家宽宏通达且开明仁爱,崇尚中庸和平,对待异质文化,虽然也有批判异端的言论(如孟子辟杨墨),但总体上坚持了“和而不同”、“和为贵”的理念,认为各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于是出现了儒道互补、儒法结合、援佛入儒、儒释道合一,甚至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共存,这就构成了儒家文化兼容并包的特色。儒释道3家在历史上长期共存,相互吸收,最终走向“三教合一”,而没有出现西方国家的各宗教教派之间尖锐而残酷的斗争,这和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坚持宽容与合、求同存异的态度紧密相关。其次,作为异族的蒙古人与满人先后入主中原,建立王朝,但其文化后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中和与融通,并最终奉儒家文化为圭臬。同时,儒家文化反对“以力服人”,其对外传播也是和平的,正因为能“以德服人”,很多国家的使臣便都慕名而来,主动接受其教化,并不像基督教的传播那样,经历了剑与火的洗礼。
基督教一神教的傲慢致使其产生一种非此即彼、非敌即友的思维模式。基督教对于异端没有包容性,好于走极端,“义人见仇敌遭报就欢喜”(《圣经·诗篇》),这就引发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及其他宗教之间的残酷战争(如十字军东征,残杀犹太人)。基督教不仅排斥外部异端,对其内部的派别之争也多诉诸于武力解决,基督教内部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之间的宗教战争在历史上连绵不绝,非此即彼的二元对抗思维已经深入基督教世界的骨髓,对异端的排斥充分展现了其“崇力尚争”的本性。
(三)儒家的“天人合一”与基督教的“天人二分”
儒家的“中庸尚和”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即为推崇“天人合一”,认为人与自然相依相存,人类应从内心深处敬畏和尊重大自然,力求“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从而“与天地参”。相反,基督教却有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推崇“天人二分”,强调对自然的征服,充分彰显出其“崇力尚争”的本性。根据《圣经·创世记》的论述,上帝创造了世间万物,但在所造之物中,只有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人可以说是“万物之灵长”,最得上帝的欢喜。在基督教看来,人是自然界的主人,自然界是上帝创造出来为人服务的,人对自然的统治是神圣的、绝对的。莫尔特曼认为“因为只有通过人对大地的统领,人才能够和上帝即世界的主相似。正像上帝是整个世界的主和所有者那样,人也必须工作,以变成大地的主和所有者,以证实人与其上帝酷似。”[4]所以梁漱溟认为“自然界的独立分出是西洋文化上一大特色。”[5]335所以说基督教“划出一个自然界,而人与之相抗。”[5]319另外基督教认为只有上帝才具有神性,反对万物有灵论,既然自然万物没有神圣性,人类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征服自然为自己服务。正如莫尔特曼所言,基督教通过“自然无灵魂概念把上帝从世界上牵走,并且让世界受到人类无情的摆布。”[4]
(四)儒家“道德人”的气象与基督教“经济人”的气象
受儒家“中庸尚和”思想的影响,人与人之间保持和谐的关系,体现在经商活动中就是人们普遍崇尚“和气生财”,以和为贵,不强调过多的竞争。为了抑制过度的利欲,儒家主张“以义制利”,“见利思义”,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些理念在成功塑造了儒家“道德人”的风范的同时,也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活动重和谐、轻竞争的思想文化根基。
在新教看来,人类中的一部分是可以得救的,而另外一部分是无法得救的,人的得救与否在“因信称义”的同时,也取决于在世间是否取得相应的成就,以充分地荣耀上帝。人对上帝的虔诚与荣耀上帝的期望汇聚在一起,便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只要在形式上正确的界限之内,只要道德品行白璧无瑕而且在财富的使用上无可指责,资产阶级实业家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追求金钱利益,同时感到这是必须完成的一项义务。”[2]166这样,人们为了创造更多的财富,以更大程度上荣耀上帝,人与人之间关系普遍紧张,彼此之间相互激烈竞争,从而成功形成了基督教“经济人”的气象,彰显出基督教“崇力尚争”的本性。
结语
儒家“中庸尚和”和基督教“崇力尚争”充分彰显了两者精神气象的不同特征,揭橥了彼此价值追求的分野。通过剖析儒家中庸思想的历史嬗变与儒家的尚和思想在4个维度的体现,可以触摸到儒家“中庸尚和”的深层精神蕴藏;解析基督教“崇力尚争”的思想根源与其在4个维度的体现,可以充分洞察到基督教“崇力尚争”的脉络谱系;将儒家“中庸尚和”和基督教“崇力尚争”在4个向度进行系统比较,可以充分管窥两者的差异甚至冲突。不过,相信儒家与基督教如果本着“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海纳百川”的包容姿态进行对话,相互的了解与认知将会进一步深化,从而为中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奠定精神基础。
参考文献
[1]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2]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3]钱穆.晚学盲言[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4]莫尔特曼.生态危机:自然界享有和平吗?[M]//刘小枫,主编.二十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下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1.
[5]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nfucian “Advocating Moderation and Harmony” and
Christian“Advocating Power and Competition”
JIN Hao-hui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respectively reflect the spirit of advocating moderation and harmony and advocating power and competition. Comparing with the Confucian the spirit of “advocating moderation and harmony” and Christian the spirit of “advocating power and competition”. Exploring their difference at the same time, is conducive to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also conducive to the deep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Key words:Confucianism; Christianity; Advocating moderation and harmony; Advocating power and competition
【中图分类号】B9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4860(2015)06-0046-06
作者简介:靳浩辉(1987—),男,山西运城人,博士在读。研究方向:中西比较伦理、政治伦理。
收稿日期:2015-05-10 2015-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