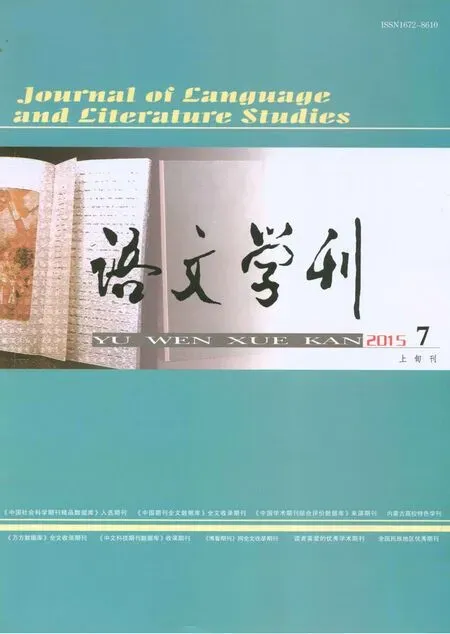张爱玲自译小说与文本的“生命存续”
——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新视角
○ 张敏
(中山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张爱玲自译小说与文本的“生命存续”
——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新视角
○ 张敏
(中山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张爱玲的作品自译一直是广大学者研究的对象,多侧重于用张爱玲的自译时的创造性及译者主体性研究,鲜有涉及翻译的哲学领域。由德里达为首的解构主义翻译观,提出语义链条的递归性,文本的生命存续,语言的多义性和差异性等概念。文章从解构主义的翻译观点来看张爱玲的《金锁记》系列文本所体现的意义链条的延续与升华;通过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观点对张同一部作品,不同的译本和改写本,进而分析《金锁记》文本是互相补充发展的递归性语义链以及文本的“生命存续”。
解构主义翻译观; 德里达; 张爱玲; 语义链; 命名; 生命存续
一、引 言
国内外对张爱玲的研究多集中于比较文学与自译研究,但并未涉及其作品与当代翻译理论的关系。
本文旨在从解构主义的翻译观来研究张爱玲小说的个案:《金锁记》,《怨女》,TheRougeoftheNorth和TheGoldenCangue等四部小说文本。《金锁记》是张爱玲于1943年发表在上海《杂志》的一篇中篇小说。在此后的二十余年多次进行翻译和修改。于1967年,张以《金锁记》为基础,改写成TheRougeoftheNorth,(有汉语译名:《北地胭脂》),最后译为《怨女》,经过一系列的改写与翻译,最终张爱玲直译了其第一文本《金锁记》为The Cangue,实现了意义链条的完成。
从这四个有着特殊联系的文本出发,从解构主义翻译观的视角进行分析。这些哲学领域的翻译观点给了我们许多新的启示。
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观综述
解构主义的翻译观代表人物德里达,德里达是解构主义的先行者。
德里达在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中曾经指出翻译的不可能性就如同翻译的必要性一般:
“在任何一个时刻,翻译都是不可能而且必要的。”[1]183
德里达在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中,用夏洛克的一磅肉和一笔钱作比喻,来验证翻译的不能性,但由于“债务关系”不得不进行交换,正如翻译的不可能性以及必要性。因此德里达认为绝对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不存在的。
“完全可译的文本最总会归于书写和言语,作为一种文本消失意义。完全不可译的文本根本不存在,即使是在同一种语言内,完全可译是不可能的。”[2]102
这句话对文本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进行了阐释。德里达是指如果一个文本全完可译,它就失去了自身的特点和特性,就是对已在文本进行简单绝对的重复。当然这样的文本是不存在的,就算是逐字重复,因为语境的变化,意义也会有所不同。如果文本是完全不可译的,它就失去了与意义系统间的联系独立封闭,最终枯竭而死。这种文本也是不存在的,如果是这样自给自足的话,就不能称之其为文本。因此德里达认为,由于不同的语言内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差异性导致绝对可以性的不可能。然而德里达又指出“翻译就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或可能的范围内传达能指与所指的差异性”[3]20。本雅明曾说过:“如果翻译的终极本质是努力达到与原作的相似性,那么任何翻译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其来世的生命中——如果不是对活的东西的某种改造和更新的话就不能称呼之——原文经历了一次变化”。[4]282因此翻译不是翻译相似性,而是德里达所提出的差异性,即语义的细微差异。在翻译这种差异性的时候,德里达认为命名是体现差异性的源头。
根茨勒曾指出,德里达对于翻译的兴趣,在于翻译过程发生于事物存在之前,未被命名的时刻。因此翻译的过程解构了文本的存在,重新回到事物未被命名之前,因此是意义转变的过程清晰可见。[6]
总的来说,对于解构主义,翻译的地位有了本质的变化,翻译已经不再是原作的附属品,它解构了原作与译作间的二元对立。“德里达质疑任何一种将翻译说成是对原作“意义”的传输、再造、重现或传达的定义。”[5]169认为最好将翻译看成一种实例,即语言可被看做总是处于修正原作文本的过程,亦即永远都处于延迟并替代任何一种可能把握原作文本曾渴望命名的事物的过程当中。[5]169因此翻译是持续的生命,是递归的延续,是永不止息的意义链条。
三、连环文本之《金锁记》②的文本分析
(一)命名的语言
张爱玲小说的背景是传统的旧上海,因此必然有很多专属于汉语的专有名词。对专有名词德里达曾经做过这样的描述:“对于每个专有名词都会有这样的渴望:翻译我吧,同时也不要翻译我!一方面,不要翻译我,因为我独立于其他语言,我不能被翻译,遵守我作为专有名词的规则。翻译我,遵循我的规则,让我变成普世语言的一部分。”[7]102我们通过几组例子来看张爱玲对此是如何处理的,如何让专有名词保留其特性,有融入普世语言之中。
InTheRougeoftheNorth:
Shepushedbackherwetbangsandopenedherhighcollar,highestinfrontjustunderthecheekbonesforahollow-cheekedeffect,withabroadblacktrimminggreasyandfrayedaroundtheedges.[8]4
《怨女》:
她把汗湿的前刘海往后一掠,解开元宝领,领口的黑缎阔滚 条洗得快破了,边上毛茸茸的。[9]4
这两段话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和译者对“元宝领”的处理。对于张爱玲来说,元宝领是其意识里的原文,这里英文先创作发表,汉语随后才被张翻译过来。张爱玲在处理英文时,用了德里达所提倡的注释,在解释中体现差异性。通过做注解来追溯命名时所忽略的细微差别的意义。汉语中三个字的词“元宝领”,张爱玲在英文中用了一行“high collar, highest in front just under the cheekbones for a hollow-cheeked effect”来进行解释。这种现象在其文本《怨女》和The Rouge of the North中有很多。比如:对“方步”,“高升点”,“万福”等用英语的描绘。[9]
“万福”是中国人恭喜别人的一种肢体表达方式,在英语中祝贺“congraduation”并没有汉语“万福”的肢体动作的表现。很难找个一个同等概念来表达相同的意义。因此张爱玲用具体的描写:“placing one hand on top of the other over her right ribs and moving the hands up and down a bit”[8]16——将一只手放在另一只手上,微微拱起,在胸前前后摆动。这样对母语不是汉语的人,也能理解“万福”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表达方式。
每一次的命名,都是一次差异性的体现。不同的所指,不可能表达同样的能指。但是,这种命名的语言等待被翻译。本雅明认为语言的不可译性在于命名的语言。德里达认为,专有名词等待被翻译,又具有本能的不可译性。这种方式使汉英之间的差异性表现得很到位,是读者一目了然。这种命名加注释的方式无论对原文或是译文都是文本意义的升华,使得译文语言更加丰富,同时原文的意义也得到了完善。
(二)意义链条与意义的升华——(sur-vive)文本生命的存续(living-on)
德里达认为意义没有绝对的源初,一切文本的意义都是能指链条的递归性循环。翻译就是因为差异性的存在,而不是翻译其相似性来实现对原作的忠实。张爱玲的 《金锁记》系列就与德里达所提出的翻译观贴合。每一次翻译都是一次新的生命。就像张爱玲同时作为译者和作者,已经无法辨别其作品和译品,无论是哪个文本都是张爱玲作品意义的升华。《怨女》与《金锁记》拥有共同的一条主线,就是七巧/银娣的走向堕落的一生。王德威(2003)认为张爱玲不断重写与翻译的原因,是她的原始创伤促使她找寻一种更加铁切的解释。张的重写不仅用中文而且用英文。张爱玲不断地“回归过去,重复自己,一再拆解记忆,重新拼凑。”[10]194但同时正如德里达所说的能指与所指二元对立的消解,因此这两部作品已经不能在完全意义上与对方等同。这两个文本拥有不同的能指,因此其所指意义也是不同的。比如《怨女》删掉了七巧之女长安的那一条线索,却对银娣的一生做了更细致全面的展现。因此,这两个文本就具有共性(generality,可译性的基础),又具有各自的特性(singularity,不可译性的原因)。
下面是从《金锁记》和《怨女》中的节选片段内容:
《金锁记》:
风从窗子里进来(……)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退了色,金绿山水换为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
去年她戴了丈夫的孝,今年婆婆又过世了。[11]14
TheRougeoftheNorth:
Thegreenbambooblindkeptmovinginthesummerbreezecominginthewindow.Sunlighttiger-stripedtheroomandswayedbackandforth(...)Heavymourningwouldhavebeenabadomenpointingtotheheadofthehouse.NowsheworemourningforOldMistress.
…
Thathadbeensixteenyearsago.[8]67
《怨女》:
绿竹帘子映在梳妆台镜子里,风吹着直动,筛进一条条阳光,(……)那回是他叫起来,把她救下来的。他死了,她也没穿孝,因为老太太还在,现在是戴老太太的孝。(……)
十六年了。[9]67-68
TheGoldenCangue:
(…)Whenshelookedagainthegreenbamboocurtainhadfaded,thegreenandgoldlandscapewasreplacedbyaphotographofherdeceasedhusband(…)
Lastyearsheworemourningforherhusbandandthisyearhermother-in-lawhadpassedaway.[12]540
这是张爱玲用不同的语言,同种语言的不同的表达方式对同一场景进行了描绘。我们可以看到张爱玲在进行“有调节的转换”(regulated transformation)(Derrida,2002:20)的时候,意义系统已经发生了转变。翠竹帘已经不再是当年的翠竹帘。我们按照时间顺序对四个文本进行排序,《金锁记》是第一文本,The Rouge of the North是第二文本,《怨女》是第三文本,The Golden Cangue是第四文本。我们对其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张爱玲的翻译已经超出了翻译本身,因为语言系统的多样性,因为这种“巴别塔处境”(Babelian situation,②Derrida, 1985a:103), 使语言的翻译具有不可能性和必要性。在《巴别塔》一文中,德里达采用了沃尔特·本雅明的生存观(berleben)——语言的生存——来解释翻译是如何对原作的意义进行转换升华。[13]但德里达认为文本是一种living on③的文本,我们可以将其看做文本的生命存续。我们可以从张爱玲对《金锁记》到The Rouge of The North 这四个文本中看到她如何用翻译对原作进行修订和补充。这四个文本的意义变化不仅是从汉语到英语的转换,其情节和意义已经被升华。首先是时间上比较明显的由十年变成了十六年。翠竹帘和相框未变,丈夫的遗照未变,读起来确实另外一种感觉。“德里达认为最好将翻译看成一种实例,即语言可被看做总是处于修正原作文本的过程,亦即永远都处于延迟并替代任何一种可能握原作文本曾渴望命名的事物的过程当中。”[5]169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德里达对翻译的观点已经消解了以前那种翻译隶属于原文的二元对立观念。翻译成为原文的先在,等待译文对其进行完善。德里达(1985b)采用了本雅明的生存观——语言的生存——来解释翻译究竟是如何修订并补充原作。[13]他认为,“译者的任务”并不只是确保语言的生存,实则是确保生命的存活。通过“有调节的转换”使文本的意义得到升华。
通过与张爱玲自译小说的解构主义分析,为我们在以后翻译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把翻译当做是对文本的解读,赋予文本以新的生命。对现在双语写作的作家的翻译提供一条新的研究线索。张爱玲在自译时采用的自译策略的确体现了许多解构主义的翻译观点,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探讨。希望可以为广大读者,作者和译者提供一个新的思路来重新审视译者与作者的身份,译文与原文的关系。在翻译和创作实践中实现文本意义的“生命存续”。
【 注 释 】
①之所以称其为连环文本是因为张爱玲对自己同一题材的小说进行了多次改写和翻译,形成了一条文本链条:《金锁记》-The Rouge of the North-《怨女》-The Golden Cangue.
②引自Derrida J. The Ear of the Other: Otobiography, Transference, Translation: Texts and Discussions with Jacques Derrida[M].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5a,代表了一种语言的存在状态,此外德里达有一文为Des tours de Babel 《巴别塔》。
③出自德里达的文章Living on /Borderlines. 收录在Derrida J, Hulbert J, Bloom H, et al. De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J].New York: Continuum, 1979.
[1]Derrida J. 2001. 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J].Venuti L. trans. Critical Inquiry.
[2]Derrida J, Hulbert J, Bloom H, et al. 1979. De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J].New York: Continuum.
[3]Derrida J. 2002. Positions[M].(English version). trans.Alan Bass. New York: Continuum.
[4]本雅明. 译者的任务[C]//陈永国,马海良.本雅明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5]根茨勒. 汪敬钦译. 当代翻译理论纵横[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6]Gentzler E. 1993.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London: Routledge.
[7]Derrida J. 1985a. The Ear of the Other: Otobiography, Transference, Translation: Texts and Discussions with Jacques Derrida[M].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8]Chang E. 1998. The Rouge of the North[M].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9]张爱玲. 张爱玲典藏全集:怨女[M].哈尓滨出版社,2003.
[10]王德威. 现代中国小说十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11]张爱玲. 张爱玲经典作品选: 金锁记[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
[12]Chang E. 1981. The Golden Cangue[C]//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as, 1919-1949. Eds by S.M. Lau, C. T. Hsia, and Ou-Fan Le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3]Derrida J. 2002. Des tours de Babel[J].(English trans.1985b.) Acts of Religion(C). eds. Gil Anidjar. New York: Routledge.
张敏,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双语创意写作,自译及外国语言学。
I206.6
A
1672-8610(2015)07-001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