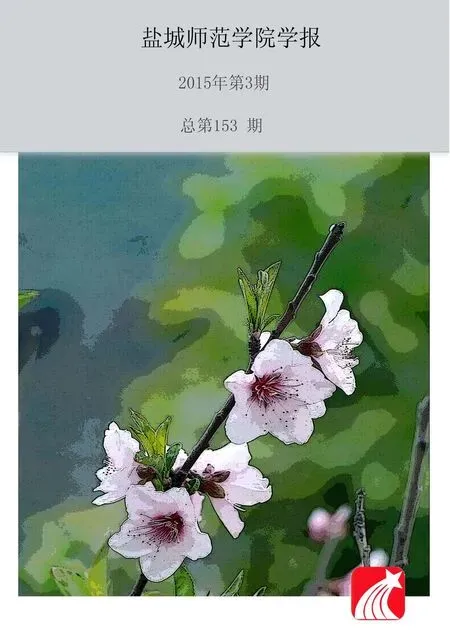创伤与抗争
——《宠儿》中三位非裔母亲身份构建
朱晓丽
(盐城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创伤与抗争
——《宠儿》中三位非裔母亲身份构建
朱晓丽
(盐城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非裔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宠儿》以“弑婴”为中心事件,以一种残忍的方式诠释了奴隶制摧残下的三位女黑奴畸形的母爱。分析非裔母亲身份的构建过程,可突现母爱的缺失和变异并不是非裔母亲自身母性的沦丧,而是万恶的奴隶制所造成的伤痛。作品褒扬了非裔母亲自我意识的觉醒及其为追求自我主体性所表现出的抗争精神。
托妮·莫里森;《宠儿》;非裔母亲;身份构建;创伤;畸形母爱
托妮·莫里森199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美国文坛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而让读者印象极其深刻的是她成功塑造了一群奋起抗争的黑人母亲形象的九部小说。其中第五部小说《宠儿》因为其独特的文学价值而被誉为当今美国文坛不可多得的巨作。小说内容独树一帜:一方面深深聚焦于非裔传统文化和奴隶制历史对黑奴的影响,同时也关注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下黑人女性悲惨的历史遭遇和创伤;小说形式也与众不同:采用了历史与现实交替、时空颠倒的叙事顺序,并巧妙融入魔幻与荒诞的手法,再现了黑奴的苦难史。莫里森深切感受到黑人女性在奴隶制下所遭受的创伤,小说通过重塑非传统的非裔母亲形象来激励黑人女性群体的自我觉醒和主动反抗。
黑人母亲和黑人女作家的双重身份让莫里森认识到:“身为黑人和女性,我能进入到那些不是黑人、不是女性的人所不能进入的一个感情、感受的宽广领域。”[1]芭芭拉·韦尔特也认为女人应该是母亲、女儿、姐妹、妻子各种身份的承载者。没有这些身份,女人无疑会失去自我存在的价值;有了它们,女人就能获得无穷力量和自我[2]。弱势群体黑人女性更是一群特殊的非裔美国人,而无情的奴隶制残忍地剥夺了她们获得这些身份的权利,让她们集体得了失语症,丧失了自我主体性。作为生命和创造的源泉,母亲的生殖和哺育能力以及对苦难的忍受力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宠儿》以“弑婴”为中心事件,以一种残忍的方式诠释了奴隶制摧残下的三位女黑奴畸形的母爱以及各自非裔母亲身份的构建过程:塞丝的生母爱得隐蔽而平实,精神上独立坚强,努力在塞丝面前捍卫自己的母亲身份,最终虽难逃毁灭的命运,但却在塞丝心中保存了自己的母亲形象;塞丝爱得浓烈而颠覆,精神上从自发到自主,行动上从积极出逃到暴力“弑婴”,以极端疯狂的方式构建了自我主体性和母亲身份;贝比·萨格斯爱得博大而成熟,她在自爱和互爱过程中确定了其作为精神领袖的母亲身份。小说旨在突出母爱的缺失和变异并不是非裔母亲自身母性的沦丧,而是万恶的奴隶制所造成的伤痛,褒扬了非裔母亲自我意识的觉醒及其为追求自我主体性所表现出的抗争精神。
一、塞丝生母的非裔母亲身份建构:名字和身体标记
在非人道的奴隶制下,女黑奴不仅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和自由,人格更是遭到无情的侮辱和践踏。她们不仅要像男黑奴一样辛勤劳作,而且还沦为白人男性的泄欲工具和生育机器;她们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可以被随意买卖和处置并且无权选择自己的配偶。奴隶主随意践踏女黑奴天然的母性,残忍割断她们与孩子的母子(女)关系,致使黑奴母亲们失去拥有自主的家庭和做母亲的权利。身为黑奴,塞丝的生母就遭遇了这样的悲惨命运。
小说中,塞丝的生母没有自己的名字,只是以“塞丝的太太”这样的身份出现,这就意味着奴隶主意图通过剥夺她为自己命名的权利而让她失去自我。和其他黑奴一样,她是“从海上来的”[3]74,多次被白人强奸,并被迫与男黑奴“配种”来帮助奴隶主繁殖劳动力。处于边缘的她无法改变命运,她所能做出的抗争就是把与白人生的孩子全都扔掉来努力涂抹白人强权的印记,唯独留下与黑人生的孩子并赋予其名字塞丝,目的是向奴隶主宣称自己只承认自己的黑人母亲身份,而名字恰恰是确立一个人个体身份的关键,也是她努力构建自己作为黑人母亲身份的最初体现。
在奴隶主庄园里,塞丝生母的黑奴身份迫使她日夜在田间劳作而无暇照看自己的孩子,只得把塞丝交给专门照顾小黑奴的女黑奴楠看管。她被迫丧失了哺育孩子的天然母亲身份,也就丧失了自我的社会价值和身份。当她潜意识里想要恢复作为母亲的权利和自由时,她便找机会偷偷把塞丝带到熏肉房后面,向塞丝展示了自己乳房下面的一个十字和一个圆圈的印记。“‘这是你的太太。这个,’她指着说,‘现在我是唯一有这个记号的。其他人都死了。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你又认不出我的脸,你会凭这个记号认得我。’”[3]72塞丝生母旨在让女儿牢记这是她作为母亲特有的标志,从而确认自己在塞丝心中神圣的母亲身份。正如莫里森在访谈中所说:“在奴隶制存在的这么一种戏剧性氛围里,如果你做出了某种声明,某种不会被人听到的声明,即你是那些孩子的母亲。对于一位奴隶母亲来说,这种声明是令人吃惊的。一旦她敢确定自己是一位母亲,这就意味着她在一个本来自己不被当做人的环境下确定自己是一个人。”[4]乳房下的标志本是她沦为奴隶的耻辱印记,她却勇敢地把它重新界定为自我个体母亲身份的象征,因为母亲乳房是哺育孩子的重要器官,也奠定了母亲不可替代的地位,从而挑战了奴隶主对她的占有关系。虽然后来她被奴隶主残忍吊死,但她却通过实际的反抗行动确立了自己的非裔母亲身份。
二、塞丝的非裔母亲身份建构:出逃和弑婴
在奴隶主庄园长大的塞丝同样与自己奴隶的悲惨命运进行了抗争。在她的记忆中,白人奴隶主加纳先生的农场被称为“甜蜜之家”。在那里,塞丝曾经和五个男黑奴自由地劳动生活了数年,加纳先生对他们很“民主”,不仅与他们交流,还给他们选择配偶的自主权。这一阶段,塞丝的精神和行为还处于一个模糊的自发状态中,她甚至默认了“甜蜜之家”的说法。作为庄园里唯一的女黑奴,塞丝受到了所有男黑奴的垂青。经过慎重考虑,塞丝选择了黑尔做丈夫,这是塞丝自爱的一种体现,她开始把自己看做一个有主权和尊严的人,大胆地向加纳太太要求一个像样的婚礼,并给自己缝了件裙子。奴隶制的实质让奴隶主太太无情地拒绝了她的要求,但塞丝对人权和自由的自发的向往为其自我意识的觉醒孕育了可能性。
塞丝自我意识苏醒的诱因就是“属性”事件。白人“学校老师”接管“甜蜜之家”后赤裸裸地主张进行毫无人性的实验:把奴隶们看作牲畜,分别列举他们人的属性和动物的属性。无意中听到奴隶主这一罪恶计划后,塞丝意识到:加纳先生的民主管理和“学校老师”的科学实验实质都是把黑奴当做能带来超额利润的牲畜来对待,黑奴根本没有人权和尊严,“甜蜜之家”实质只是个美丽的谎言。作为母亲,她为自己孩子的命运感到深深担忧。于是,在强烈的母爱驱使下,她勇敢地计划着把孩子都送出去后自己也逃跑,尽管当时她即将面临分娩。抢奶事件激发了她强烈的反抗意识,因为奶水昭示着母亲价值的存在和权力。当奶水被抢时,她感到自己的黑人母亲权利遭受了严重的侵犯,她奋起反抗并发誓:“(今后)除了我自己的孩子,谁也不能再得到我的奶水。我再也不必给别的人了——那唯一的一次是被人抢走的——他们按倒我抢走的。属于我的宝贝的奶水。”[3]239正是坚强的母性支撑着塞丝身怀六甲时只身出逃并中途成功产子。
逃到婆婆家后,塞丝和自己的孩子确实过了段自由的日子,然而奴隶力求脱离残忍的奴隶制成为自由人谈何容易。她自主抗争意识爆发的直接导火索就是“弑婴”事件。当“学校老师”追来时,自身的悲惨遭遇让塞丝决意“弑婴”以避免她的孩子们重蹈覆辙。塞丝用一种疯狂的方式宣告了她的母亲身份,昭示了她所生的孩子是自由人,而不再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作为母亲,她行使了决定孩子的生死的自主权,正如她后来所说:“宠儿,她是我的女儿。她是我的。”[3]239她的自主逃亡和弑婴行为是对“学校老师”的抵抗和对奴隶制的宣战,是残酷的奴隶制下浓厚的母爱异化的表现,也凸显了新一代非裔母亲勇敢捍卫其母亲身份的义无反顾的精神。
三、贝比·萨格斯的非裔母亲身份建构:自爱和博爱
塞丝的黑人婆婆贝比·萨格斯在摆脱奴隶身份前同样命运悲惨:她长期被看作是可繁殖的廉价牲畜,以致“奴隶生活摧毁了她的双腿、后背、脑袋、眼睛、双手、肾脏、子宫和舌头,她什么都不剩了”[3]103。作为女黑奴,她被迫和六个不同肤色的男人生了八个孩子,但最后只剩下肤色黝黑的黑尔,其他的被抓走或被卖掉。与成千上万遭受奴隶主终身奴役的黑奴相比,贝比·萨格斯是相对幸运的,因为儿子黑尔通过长期劳作帮她赎身,最终让她在年老时获得了身体的自由。在盛行的奴隶制下,奴隶主掌握着对黑奴的生杀大权,可以任意处置黑奴。奴隶制无情抹杀了黑奴作为人的价值,因此,黑人要独立自主,成为自由人,就首先必须意识到自我价值,学会自爱[5]。所以,贝比自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替自己重新命名来宣称自我主体性,感受自己作为人的心跳,因为要重构自我,首先要珍爱自己的身体,即自爱,而自爱是黑人获得自我的关键一步。
贝比认为自爱与爱他人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她追求的真正自由是所有黑人身心的自由,她的爱也是作为一个领袖母亲广博的爱,这首先体现在对儿媳塞丝的帮助和精心呵护上。当遍体鳞伤的塞丝逃到124号时,贝比看见儿媳的伤时,心里充满了母亲般的怜爱,于是她立刻细心地帮塞丝从头到脚洗干净并替她换上干净衣服。这样的洗礼不仅让塞丝获得了重生,也让贝比通过照顾和帮助儿媳重构了丧失已久的母亲身份。此外,贝比在社区里还充当了领袖母亲的角色,作为一名不入教的牧师,她用母亲般广博的爱鼓励饱受创伤的黑人男女们学会热爱自己的身体,理解自爱的价值,并带领大家来到林间空地,在那里尽情地跳舞唱歌,从而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另外,贝比深切体会到黑人母亲失去主权和地位的痛苦,她大声鼓励黑人女性们热爱自己的母亲身份:“比眼睛比脚更热爱。比呼吸自由空气的肺更热爱。比你保存生命的子宫和你创造生命的私处更热爱,现在听我说,爱你的心。因为这才是价值所在”[3]105。在她的感召下,黑人母亲们团结一致,积极地为重构自我非裔身份而抗争,而她的领袖母亲身份再次得到了巩固,最终成功获得黑人们的敬重,成功重构了其非裔母亲身份。
传统“母爱产生于一种强烈的感情,它不受那种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和愤怒所左右。许多母亲养成了一种母性的意识——一种她们愿意为孩子们付出所有心血的意识”[6]。然而,三位黑奴母亲因为奴隶制的摧残而颠覆了传统的母亲形象,要么无法真正去爱,要么爱得太浓太壮烈。尽管爱得迥异,但为了确立各自的非裔母亲身份,她们都做出了抗争:塞丝生母有意只留下黑人孩子并为其取名塞丝,从而宣称自己只是黑人母亲。此外,她还通过重新定义乳房下的身体标记来确立自己在塞丝心里不可取代的母亲地位;塞丝出逃过程宣告了自己作为母亲的本能,而“弑婴”的极端行为则确立了自己作为非裔母亲的主权和地位;贝比·萨格斯作为一位精神领袖,她自爱和爱他人的精神和行为让她真正意义上确立了黑人女性作为非裔母亲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地位。非裔母亲们在种族、性别等多重压迫下从失语到觉醒和抗争的艰辛的自我身份认同之路,不仅为黑人女性指明了方向,也有助于促进整个非裔群体的身份重构过程,并赋予其新的活力。
[1] Guthrie T,Danile.Conversations with Toni Morrison[M].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4:243.
[2] Welter B.Dimity Convictions[M].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1976.
[3] 托妮·莫里森.宠儿[M].潘岳,雷格,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6.
[4] Bernard C.Passing the Torch:A Mother and Daughter Reflect on their Experiences Across Generations[J].Canadian Women’s Studies Journal,1998,18(2/3):46-50.
[5] 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 Ruddick S.Talking About Mother[M].Tianjin:Nankai University Press,1994:125.
〔责任编辑:朱莉莉〕
I106.4
A
1003-6873(2015)03-0095-03
2015-02-20
盐城师范学院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托尼·莫里森《宠儿》、《爵士乐》、《天堂》三部曲中的非裔身份认同研究”(14YCKW018)。
朱晓丽(1979-- ),女,盐城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15.03.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