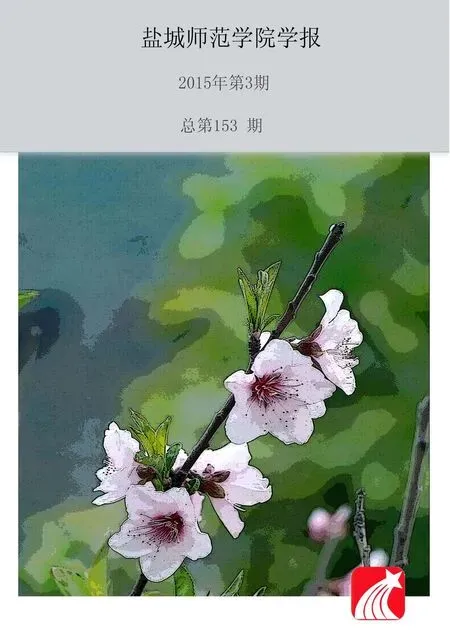从自然风景体验看穆旦诗歌的现代性
程振兰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从自然风景体验看穆旦诗歌的现代性
程振兰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如果从自然风景体验去切入穆旦诗歌,可以发现穆旦诗歌具有本土化的现代性体验,这样可以拓宽穆旦诗歌研究的视野。穆旦随学校迁徙过程中的自然风景体验,带给诗人独有的土地体验,其中包含了对国家与民族的深厚感情,对人民以及自身的生命关切和思考,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反思。野人山的自然风景体验给诗人带来了恐惧体验,这就促使诗人去思考战争、自然和人的生命之间的关系。穆旦在1940年代的诗歌指向始终是物质层面上的,而晚年的四季体验让诗人一直在寻找灵魂的栖居地。从这些可以看出,自然风景体验是参与了穆旦诗歌的现代性生成的。
自然风景;体验;穆旦;诗歌;现代性
穆旦诗歌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其诗歌的现代性特征也是众多研究者讨论的焦点。而对穆旦诗歌中的现代性特征的研究,多数研究者关注的是西方现代诗派诗人艾略特,奥登、叶芝等人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但是,过度关注穆旦诗歌跟西方现代派的联系似乎就会忽略或者有意无意的摒除穆旦在中国本土的生活经验以及在这种经验下形成的艺术感受。“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1]似乎会被过于放大,这样对于穆旦诗歌的研究就会难以突破西方诗歌的框架,所以才会出现江弱水对穆旦诗歌的不满的声音,认为其诗歌创作就是一种伪奥登风。
如果暂时摒弃英国现代派对穆旦诗歌的影响,暂时搁置穆旦在诗歌技术上对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借鉴,将穆旦研究目光由西方空间转移到本土空间上来会不会提供另一条穆旦诗歌研究的路径呢?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摒弃和搁置并不是否认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影响,而恰恰是在承认穆旦所受到的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影响,并在尊重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本土经验来进入穆旦的诗歌。联系穆旦生活经验以及穆旦的诗歌可以发现,自然风景体验是贯穿穆旦诗歌的,本文欲从风景视角切入穆旦诗歌,以此来观察穆旦诗歌与穆旦生活体验之间内在关系,从而去深入探究穆旦诗歌。
一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站在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2]成为当时学生状况的真实写照。战争给众多的学子带来的似乎是灾难,但对于联大的学生来说也是另一种契机,也许没有战争就不会有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为了保持教育的不中断而进行迁徙,两次迁校活动让学生们离开了自己所熟悉的北方城市,绕过大半个中国徒步来到西南联大。期间师生们尽览了中国的河山风光和当地的风土人情,很多学生对这一过程进行了记录和回忆,如林蒲、向长清、刘兆吉、蔡孝敏等。穆旦作为其中的一员,跟随着迁移队伍“从熟悉的‘平原文明’进入了相对陌生的‘山地文明’”[3]。穆旦关于这次经历最早呈现出来的是1940年10月发表的《出发——三千里步行之一》《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之二》两篇诗歌。《出发——三千里步行之一》中诗人始终带着一种激扬的情绪用现代人独有的感觉去描写中国的江河和土地。“而江水滔滔流去了,割进幽暗的夜/一条抖动的银链振鸣着大地的欢欣”,其中“割”“抖动的银链”是现代人一种独有的体验方式,这里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穆旦对自然和大地的那种带着痛感的爱。当然,我们无法判定这次经历是否对穆旦诗歌有直接影响或者是直接参与了穆旦40年代诗歌的现代性的生成。但无法否认的是穆旦诗歌中那种对于广阔和厚重的土地的热爱和依恋,正如他评价诗人艾青那样:“作为一个土地的爱好者……没有一个新诗人比艾青更‘中国的’了。”[4]这其中也蕴含了穆旦对祖国的热切的期望。在《合唱二章》中诗人将自然原野放在广阔的历史空间上,自然风景成为了一种激烈的催化剂,催着人们去进入历史的原野,去开拓宇宙的洪荒,“像大旗飘进宇宙的洪荒/看怎样的勇敢,虔敬,坚忍/辟出了华夏辽阔的神州”。诗人加入到祖国的大合唱,对华夏神州的新生热切期望,这样原野上的自然风景也就催生了民族精神。这种感情在《赞美》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诗歌写作的背景正是中国全面抗战时期,在中国的“山峦、河流和草原”上,“接连在原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穆旦铺陈了一幅受难和耻辱的中国历史图像,诗人将全诗的情绪定位于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悲壮与坚决,在那里自然的景物被诗人赋予了民族性,这是诗人面对着国破家亡而独有的现代性的体验。这种体验中蕴含的是一种对于新生的渴望,在《在旷野上》中由于强烈的新生的渴求,荒野风景的体验显示出了破坏力。“在旷野上,在无边的肃杀里/谁知道暖风和花草飘向何方/残酷的春天使它们伸展又伸展/用了碧洁的泉水和崇高的阳光/挽来绝望的彩色和无助的夭亡”,在这里春天成为了残酷的,可以用泉水和阳光挽来绝望和无助的夭亡,这是一种有着强烈破坏性的力量,是野性的力量,是具有破坏性和突破性的荒原般的现代性的体验的。同样,《神魔之争》中,诗人用一种现代人的感触,让东风、神、魔、林妖集合起来进行对话,这里的自然风景体验也带有一种破坏性,有着野性的突破,这种破坏性也正是另一种新生和蜕变,这是穆旦带着独有的现代性体验而对祖国的土地体验表达出的民族情感以及对新生的渴望。
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在激动地表达着对土地的痛苦的爱,在热情的呼唤着新生的同时,并没有失去理性,这也就是所谓的“欢呼着又沉默着”。那么是什么让诗人沉默?诗人自己没有言说,但是从其诗歌中或许可以找出其中的些许缘由。《出发——三千里步行之一》中在自然景物激发的民族情感之外,诗人也将关注点放在了扎根在中国的土里的人民身上。“他们流着汗挣扎,繁殖”,在这里穆旦对中国大地上的农民有了一定的认识,看到了那苦难的人民,这样在合唱里就出现了个人的面孔,这种个人的面孔还出现在《赞美》中。诗人塑造了一个受难的农夫的形象,农夫不仅仅是中国人民中的一员,“他是一个女人的孩子,许多孩子的父亲”,他在人民中是无言的,是融进了大众里的,但是在那个女人和许多孩子的眼中,他是独特的,是无法代替的,这样就显示出诗人是充分尊重了个人的存在的。农夫并不像大路上的人们一样演说,叫嚣,欢快,他只是默默将自己融进大众,融进死亡,融进这中国的土地上,也许他的融进很简单,单单是为了期盼着他的老妇和孩子。这是在面对现代战争的背景下,穆旦独有的观察。穆旦用第三种抒情的方式创造了独特的具有个人面孔的旷野上流亡者的形象,这是不同于当时时代背景下的将个人融进大众合唱团取消个人性的诗歌的方法,这也体现出了穆旦对个人生存以及生命的独特思考。这种对个人的生存状况的观看最后发展成为对自我的认知,《玫瑰之歌》中自我由“我长大在古诗词的山水里”到“我要去寻找异方的梦”,同时将自我作为“一颗冬日的种子期待着新生”,这是一种对旧的自我的否定,期待着新的自我的出现,但是自我的处境却依旧是“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我》)这表现了一种“我”的分裂,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导致了的“我”的分裂。
穆旦诗歌中的原野体验不仅仅表达了诗人对原野自然风景的热爱和赞美,以及原野风景背后所蕴含的爱国情怀和对祖国新生的热切期望,与这种感情形成强烈对比的却是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厌倦与反感。“我们终于离开了渔网似的城市/那以窒息的、干燥的、空虚的格子/不断地捞我们到绝望去的城市呵”,这里对于城市的感知“渔网”“格子”“捞”都是现代人对现代城市的感知方式。类似这样的表述在《黄昏》中也有出现,“一天的侵蚀也停止了,像惊骇的鸟/欢笑从门口逃出来,从化学原料/从电报条的紧张和它拼凑的意义”。这里看到的是现代文明物化的生活方式,而与之对应的则是静谧的自然风景的氛围“突立的树和高山,淡蓝的空气和炊烟/是上帝的建筑在刹那中显现/这里,生命另有它的意义等你揉圆”。
二
土地体验带给穆旦的不仅是对自然风景的热爱,对土地上的人民以及自身的生命关切和思考,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反思,还给诗人带来了另一种相反的体验感受——恐惧。诗人在1942年辞去联大助教参加中国远征军做随军翻译,期间经历了野人山战役,这是一场自杀性的殿后战,这里笔者将立足点放在战争、人、自然风景三者之间的关系来探讨穆旦诗歌的独特性。
对于野人山战役,王佐良在《一个中国诗人》中说:“他本人对这一切淡漠而又随便,或者便连这样也觉得不好意思。只有一次,被朋友们逼得没有办法了,他才说一点。”[5]穆旦有关野人山的文字也只有1945年9月以诗歌形式写出的《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诗中穆旦用他现代人独有的现代感知将森林和人放在同一物类之上进行对话。这种现代性的特征恰恰跟西方的绝对隐喻不谋而合,这是一种现代性的体验,相较于“曾经迷误在自然底梦中/我底身体由白云和花草做成”(《自然底梦》)的“我”来说,这里的风景带来的已经不再是拥抱、抚摸,这种模式已经区别于中国古典诗歌中自然风景是生命的滋养,是创伤的抚慰的表达,这里的自然风景似乎具有了狰狞的面孔,自然和人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这里森林代表的是原始的、能将人领过黑暗的力量。这种力量令人“畏惧”“窒息”“血肉脱尽”,这种力量威胁着人的生命,给人造成巨大的恐惧,这样的自然风景体验感受是同时代诗人所没有的,这是穆旦的独特的现代性的自然风景体验,这不同于郑敏的痛苦的承载者“阴郁的森林”[6](《诗人的奉献》),也不同于杜运燮的“高寿的森林”[7](《滇缅公路》),这也不同于穆旦曾经的“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春》)的希望和新生,这里自然风景带来的是“疾病和绝望”,让人发出绝望的呼声“绿色的毒,你瘫痪了我的血肉和深心”。
诗人由对自然的热爱,与自然的和谐体验是如何急转为对自然风景的恐惧以及不和谐体验呢?从《森林之魅》中可以看出这种转变,这种转变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这体现出了战争,自然风景体验以及人的生存三者之间的关系,“离开文明,是离开了众多的敌人/在青苔藤蔓间,在百年的枯叶上/死去了世间的声音。这青青杂草”文明让人有很多的敌人,将人异化,自然风景在这里依然得到崇奉,这里人为了摆脱现代文明,为了摆脱现代战争,来到了崇奉的自然,但是遇到的却是另外一番境界“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此时的自然给予的不再是安抚,不再是温柔的拥抱,而是进一步的死亡。“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在这里,自然风景那强大的力量已经超越了战争的意义,历史、战争和人都将被遗忘在那“静静的山坡上”,被遗忘在那“欣欣的林木”里。
三
1940年代穆旦对自然风景的体验是多样的,无论是三千里步行所带来的对自然的热爱,对个体的关怀以及对自我的认知,还是在野人山战役之后,对自然风景的体验由崇奉转变为恐惧,进而认识到自然的强大,这些都是穆旦作为一个现代人独有的现代性的体验。然而穆旦晚年并没有将身体融进大自然的经历,却写出了以四季命名的诗歌,这里的四季并不是单纯的物理时间的流转循环,轮回,而是饱含着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的灵魂寄托点。关于四季体验的诗歌是从春之体验开始的。穆旦在西南联大时期就写了三首以春为标题的诗歌《春底降临》《春》《春天和蜜蜂》。诗歌中春天的自然风景带给诗人的是一种复杂的体验。生命在春天中渴望、反抗、烦恼、欢乐和痛苦,给“我们二十岁紧闭的肉体”带来希望,带来新生和蜕变。穆旦用现代人的感受将春之体验表达出来,用现代人的思辨的色彩表达出了现代人的复杂的感受,正如王佐良所说的“截然不同于千百首一般伤春咏怀的作品”[8]。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诗人在表达春天作为希望的引领者之时,并没有将春天作为万物的神“春天的邀请,万物都答应/说不得的只有我的爱情”(《春天与蜜蜂》),而爱情却是在冬天得到了收获,这就表明诗人对春之体验的另一层复杂的表达,正是这层复杂的表达为穆旦晚年诗歌中的四季体验提供了另一种新的可能。
在晚年的同题诗歌《春》里,春之体验带来的新生和蜕变的急剧膨胀,最终成为一种强大的催化力,“带来了一场不意的暴乱/把我流放到……一片破碎的梦”,梦也被这种蜕变的暴乱所破碎。从穆旦一生的经历来看,这无不对现实社会状况有所映射,穆旦早期对新生中国的期待与希望建筑了诗人的梦,终于在以为梦即将实现之际,看到的却是“春”带来的一场暴乱,此时的“春”已经不再是新生和希望,而似乎是历史的轮回,“春”的强暴依旧会让梦成为碎片,那么这个梦是什么呢?从《春》中可以看出诗人在这时已经转变了自己的立场,将“我”和“我们”分离开,在面对另一种境地的春天之时,诗人表现的不再是对环境的激扬,而是关注“我的心”,而是“筑起寒冷的城”,“把一切轻浮的欢乐关在城外”。联系当时的时代环境,暴乱意指文革,在现实失落之后,诗人将眼光聚焦在内心。同时也说明自然的“春”永远是以自身的力量来轮回,而人所造就的“春”,在人失去理性节制之时会演变成一种过分的激扬,就会“是太阳的感情在大地上迸发”(《夏》)。“夏”已经达到了一种似乎将要爆发的阶段,面对这样的情形而“我”只能躲进冥想之中去,这样诗歌就带有了现代人的思辨的色彩。“四人帮”倒台后,当时的环境似乎是有些改变,穆旦也终于等到“天空呈现着深邃的蔚蓝”(《秋》)的时候,诗人的诗情和笔触就来到了“秋”,这时的“秋”不再是承载着古人的哀思愁怨和收获喜悦的季节,此时的“秋”拥有了理性和哲思,“秋”使“夏”的狂热和喧嚣得到了冷却和肃静,此时的太阳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将要迸发,“如今他已是和煦的老人”(《秋》)。“秋”将情感、生命和历史都融入到了自然之中,这也映射了当时的时代变化,“四人帮”倒台,国内形势有所缓和,仿佛是进入沉思的秋,去反思那狂热的时代,去理性评判曾经将要爆炸的时代,这是诗人在经历了众多历史苦难和个人的情感变化与反思之后独特的体验。当这种秋的反思变为人生哲理性的思辨之时,诗人却迎来了人生的冬季。“冬”似乎是对春夏秋的回忆与总结,其中有对“枯草的山坡,死寂的原野”(《冬》)的过往经历的回忆,有对“听着北风吹得门窗沙沙地响/而我们回忆着快乐无忧的往年”的美好友谊的怀念,有对理想和感情的思考。冬天是沉思的季节,“盛夏的蝉鸣和蛙声都沉寂/大地一笔勾销它美丽的蓬勃”。冬天体现的是一种沉稳,沉静,同时也能将一种情感扼杀。“冬天是感情的刽子手”能够使“心灵枯瘦”。同时冬天也是“好梦的刽子手”,这样就会产生一种后果,“年轻的灵魂裹进老年的硬壳”,灵魂陷入了僵化的境地,那么只能在历史的车轮的转动中过着近乎惯性的生活,日益淡化了感知,“吃着,哼着小曲,还谈着/枯燥的原野上枯燥的事物”,这样就在历史和自然的惯常下,人就丧失了感知,丧失了灵魂。
综上所述,自然风景体验参与了穆旦诗歌现代性的生成,并且一直贯穿着穆旦诗歌的写作。只是,1940年代抗战环境下的自然风景体验激发的是诗人对祖国大地深沉的爱,进而是对大地上的人民与自身的发展状况的关注。这些关注点指向了物质的层面,贫苦的农民、陷入“污泥里的猪”的境况,既是广大青年的现状,也是诗人自身的状况。而在《森林之魅》之后,诗人看到了自然的强力,既感受到自然风光的生命因素,同时也承受着自然风景带来的对生命的威胁与挤压,诗人不知如何去表达当时自然给他的那种触动,这样诗人的关注点也在逐步地转移。新中国成立之后,诗人带着极大的热情投向祖国母亲的怀抱,但是在这里诗人不安定的内心并没有得到安放,尤其是经历过文革之后,诗人变得越来越沉默、痛苦。从他晚年的四季体验诗歌可以看出,穆旦晚年将自我肉体与灵魂割裂,诗人越来越蜷缩于自己的灵魂深处,一直在寻找灵魂的栖息地,也许对穆旦来说,“人生中游牧与栖居、变迁与凝固不断变奏的乐曲,静止与变迁都将是流逝的风景与乐调”[9]。
[1] 穆旦.穆旦诗文集1[M].增订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2] 易彬.穆旦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52.
[3] 马绍玺.边地风景体验与西南联大诗歌[J].文学评论,2015(1):88-91.
[4] 穆旦.穆旦诗文集2[M].增订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54.
[5] 杜运燮,张同道.西南联大现代诗钞[M].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7.
[6] 欧宗耀.时间、人生、历史四部曲:解读穆旦1976年诗作《春》《夏》《秋》《冬》[J].时代文学,2007(6):109-112.
[7] 孙玉石.中国现代诗歌导读:穆旦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王建霞〕
I206.6
A
1003-6873(2015)03-0087-04
2015-03-10
程振兰(1989-- ),女,河南濮阳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15.03.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