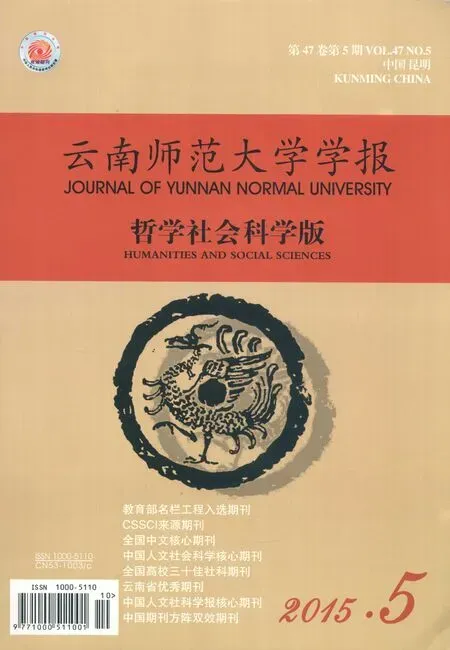云南新平傣族生计模式及其变迁的生态人类学研究*
崔明昆, 杨 索, 赵文娟, 周晓红
(1.云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云南昆明650092;2.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云南昆明650091; 3.云南大学资源环境与地球科学学院,云南昆明650091)
云南新平傣族生计模式及其变迁的生态人类学研究*
崔明昆1,2, 杨 索2, 赵文娟3, 周晓红2
(1.云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云南昆明650092;2.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云南昆明650091; 3.云南大学资源环境与地球科学学院,云南昆明650091)
云南新平县戛洒镇大槟榔园是一个典型的傣族聚居村落,也是当地重点发展的特色乡村旅游村寨之一。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应用生态人类学的文化适应理论分析了大槟榔园的传统生计模式及其变迁,以及生计变迁对生态文化的影响等问题。研究表明,大槟榔园村民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传统生计模式是一种适应于当地自然环境的文化机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村民的生计模式正发生着深刻而剧烈的变革,村民以一种较为主动的方式融入开放的市场中,体现出对社会文化环境变化的适应性,但又不得不受限于一些限制性因素的影响。
大槟榔园;适应;花腰傣;生计模式
生计模式(livelihood modes)是指“特定族群在与周围自然环境长期互动的过程中,逐步构建和完善的各种谋生手段和谋生方式的总和”。①赵文娟,崔明昆,等.工程移民的生计变迁与文化适应——以泸沽湖机场移民为例[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11,(3).关于人类生计和生计模式的探讨,一直是生态人类学(Ecological Anthropology)的研究重点。生态人类学是“生态学方面的人类学,是人类学中分担生态学层面的领域,是研究人类生存方式的学问”,是一门“以文化解读生态环境或以生态环境解读文化”的学科。②秋道智弥,市川光雄,大塚柳太郎.生态人类学[M].范广融,尹绍亭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1.20世纪50年代,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在其《文化变迁的理论》一书中提出了“生态文化适应”(ecological cultural adaptation)的概念,其含义指“一个在历史上发展出来的文化在特殊的环境中得到改造的适应过程”。③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理论探索与实践[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72.尔后,“适应”(adaptation)和“文化适应”(cultural adaptation)概念随即成为生态人类学研究中的核心关键词之一。适应是指“地球上的生物种群通过自身变化与周围环境达成协调并繁衍下去的过程,人类的适应包括生物性适应和文化适应”,文化适应则是“通过改变生活方式的策略达成和自然与社会环境之和谐”。④庄孔韶.人类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97.本文以文化适应理论为基础,应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于2014年1月对云南新平县戛洒镇大槟榔园花腰傣传统生计模式及其变迁展开调查,试图梳理出花腰傣生计变迁的过程与脉络,并探讨生计变迁对民族生态文化所造成的影响。
一、田野调查点概况
新平傣族又称花腰傣,是人们对分布于红河流域傣族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学术界第一次使用“花腰傣”这一名称的是美国传教士W.C都德(William Clifton Dodd,D.D),⑤邢公畹.红河上游傣雅语[M].北京:语文出版社,1989:1.其原因是这里的傣族妇女腰间围系着一至多条长长的彩色腰带。有学者认为,傣族先民是亚洲及世界最早驯化野生稻并种植稻谷的族群。⑥高立士.傣族悠久的稻文化[J].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1).不同于生活在其他地区的傣族,花腰傣最显著的特征是尚未受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影响,至今仍保持着浓厚的万物有灵信仰,具体表现为对“竜树神林”的植物崇拜与原始宗教祭祀活动。每个花腰傣村寨均有数棵掌管各自村寨的“竜树”,每年由专门的神职人员“竜头”负责对不同“竜树”举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祭祀,以祈求人畜平安,五谷丰登。
居住于红河流域的花腰傣以新平县人口最为集中,有4万余人,其中尤以戛洒、漠沙、水塘等乡镇为主要分布地,因而新平又有“花腰傣之乡”的美誉。戛洒镇位于云南新平县西部哀牢山脉中段东麓红河上游的戛洒江畔,距新平县城约65千米。镇域内既有高海拔的高寒山区,又有低海拔的河谷热坝,呈现明显的立体气候特征。花腰傣居住在海拔500米左右的河谷热坝区,其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盛产稻谷、甘蔗、香蕉、芒果、荔枝、火龙果、木瓜等粮经作物,物产丰饶,风景旖旎。2011年岁末,戛洒镇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为中国十大“最浪漫栖居地”之首。①新平县广电局.新平县戛洒镇跃居中国十大“最浪漫栖居地”之首(2012-1-17)[EB/OL].http://www.ynagri.gov.cn/yx/xp/news4246/20120117/1365210.shtml.
大槟榔园坐落于戛洒镇南蚌村东侧的戛洒江畔,是一个传统民族文化保存比较完好的花腰傣村落,距镇政府所在地约3千米,现作为当地重点开发的特色乡村旅游村寨之一。大槟榔园现有村民68户,人口332人,村民皆属于花腰傣中的“傣洒”支系。傣语“洒”为“沙”之意,傣洒意为“居住在沙滩边的傣家人”。田野调查中,常听到村民说起一句流行于花腰傣地区脍炙人口的俗语——“糯米饭、腌鸭蛋、干黄鳝,二两小酒天天干”,这既是花腰傣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对花腰傣传统生计模式的精炼总结。然而,2000年以来,作为特色乡村旅游村寨的大槟榔园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生计模式逐渐消亡,新的生计模式正在形成或已经形成。
二、传统生计模式
背山面水是傣族人认为的最佳居所环境,花腰傣聚居的河谷热坝,背靠哀牢山,面临戛洒江。当地气候干热,终年无霜,河流密布,土壤肥沃,良好的自然条件适宜于发展水稻种植业,是极其理想的水田农业区。日本学者渡部忠世在《稻米之路》一书中提出“阿萨姆—云南稻作起源说”,认为云南是水稻驯化和栽培的发源地,水稻种植沿着河流向外传播,其中一条“稻米之路”经由红河南下,②渡部忠世.稻米之路[M].尹绍亭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96~98.大槟榔园正好处于这一条水稻种植的传播路线上。在这条“稻米之路”上如今仍有野生稻的分布,说明该区域极有可能是较早驯化和栽培稻作的地方之一。
历史上大槟榔园的水稻种植为一年两季,一般农历正月至六月种植早稻,七月耙田撒秧,八月至冬月种植晚稻,腊月放水犁田,完成一年的农业耕作周期。稻作生产过程可以简单分为放水泡田、犁田耙田、撒秧育秧、插秧薅秧、施肥育土、排灌收割、打谷入仓等一系列生产环节。村民生产生活的中心,都围绕着水田和稻谷展开。水稻的收成是村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稻谷作为商品交换的重要产品,为村民换取生产生活的其他必需品。
村民种植水稻的同时,也兼事养殖业,养殖的家畜家禽主要有牛、猪、鸡、鸭等。牛是重要的生产工具,是水稻耕作必不可少的劳力输出。通常,村民以木材搭建牛棚,饲料主要来自水稻收割后的秸秆。猪是养殖的另一重要牲畜,是村民肉食的主要来源。春节前夕,当地有“杀年猪”的风俗,以备制作风味独特又易贮藏的腌肉。鸡、鸭是养殖的常见家禽品种,鸭蛋常被腌制食用。同时,牛、猪等大牲畜的粪便作为重要的农家肥来源,保持并增长着水田肥力,促进稻作农业的稳定与发展。
花腰傣生活的区域,地处哀牢山腹地,自然条件优越,有着极其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村民对野生动植物资源,尤其是植物资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利用体系。“新平花腰傣食用的野生蔬菜种类较为丰富,按植物的食用部位,可以将野菜分为花类、茎叶类、果实类、块茎(根)类和竹笋类等”,多种野菜生长在村民耕作的田间地头,野菜采集“不仅可以节约土地与劳动力,还使得花腰傣的食物种类丰富多彩”。③崔明昆.云南新平花腰傣野菜采集的生态人类学研究[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花腰傣傍水而居,河流与稻田出产的鱼、虾、田螺、黄鳝等水产资源丰富。村民在劳作与闲暇之余将其捕获食用,其中干黄鳝是一道颇具特色的风味菜肴。哀牢山茂密的原始森林是众多飞禽走兽出没之地,花腰傣的传统狩猎活动主要包括“撵麂子”(“撵山”)、“捕野猪、打刺猬”、“捕火雀”等,①朱慧贤.云南新平花腰傣的狩猎习俗和动物保护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08,(16).狩猎活动通常由男子在农闲时节举行。
由上可知,花腰傣是一个典型的稻作民族,以稻作农业为根本,养殖业与采集渔猎业作为重要补充,为村民提供着肉食、蔬菜、水果等产品;稻作农业、养殖业、采集渔猎业三者相互补充又相互完善,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共同构成当地以稻作农业为中心的传统生计模式。
三、变迁中的生计模式
2000年以前,大槟榔园的传统生计模式保存较为完好,村民一直较完整地维系着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原因在于村民的居住地域相对封闭,人们难以走出深山,外部事物也难以进入。历史上,哀牢山下的花腰傣村民都只能依靠马帮和河运与外界保持着商品的交换与信息的传递。同时,正是由于这种自然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封闭性导致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滞后性,花腰傣的社会经济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时代。2000年以来,戛洒镇的社会经济步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由于现代农业的进入,工矿企业的发展,以及民族文化旅游的兴起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以“糯米饭、腌鸭蛋、干黄鳝”为代表的花腰傣传统生计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大槟榔园处于各种变迁因子的环绕之下,往昔平静而安逸的乡村生活被打破,生计变迁彻底改变了村寨的面貌,传统生计模式逐渐湮没在发展的市场经济浪潮中。
(一)第一产业的变化
大槟榔园经历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土地征用(一次是修建新平至三江口的二级公路,另一次是修建戛洒镇的污水处理厂,两次共征用农田60余亩)后现有农田285亩,其中约200亩已被租赁。租赁的土地大部分用于香蕉种植,租期一般为5至6年。2013年,部分村民的土地又完成一次续签。随着土地租赁价格的上涨,每亩土地的年租金已从800至1000元增长到1500至1600元。土地的承租者之一是新平县天惠农业发展公司,该公司是一家专业化与市场化的现代农业企业,主要经营项目是以香蕉为代表的热带水果种植及销售。另一承租者是一位外地个体经营户,同样租赁土地来种植香蕉,其租种面积约100亩,与天惠公司大体相当。香蕉种植采用现代化与产业化的生产模式,雇佣专门的种植工人负责香蕉的耕种、施肥、浇水、杀虫、除草等田间管理事项。香蕉种植过程中,需要使用大量的化肥农药。以外地个体经营户租种的香蕉地为例,每年化肥至少投放4次,每亩土地的年投放总量达400公斤左右,农药亦要播撒2至3次。土地流转前,村民还经历过短暂的甘蔗种植阶段,但持续时间不长。由于甘蔗价格的下降,劳动投入与实际收入的不对等,使得村民放弃甘蔗种植,进而转向出租土地来获取固定地租。
村里仅有余下的少部分水田继续耕种水稻。与传统的水稻种植相比,目前的耕作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一是水稻种植主要由中年女性与老年人完成,中年男性与青年人只在农忙时节才会参与到水稻劳作当中;二是在长期劳动实践中所培育的大部分传统稻米品种已经不再种植,取而代之的是杂交稻品种,稻米品种的生物多样性在减少;三是大部分村民已引进机械化的农业生产工具,如用手扶式拖拉机来替代传统人力与畜力的使用,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2013年8月,镇政府为实施“美丽乡村”的乡村美化建设项目,打造大槟榔园良好的新农村面貌和旅游目的地形象,规定村寨内禁止养殖家禽家畜。村寨内的牛棚、猪圈、鸡舍等一律拆除,以免影响环境卫生和村容村貌。这一规定的实施未能得到村民的理解与支持,认为这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不利的影响。最主要是人们不得不花费更多金钱在市场上购买各种肉类和禽蛋,这无疑加重了他们生活的负担。但是,村民又不得不遵守这一规定,进而只能采取一些消极方式进行抵抗。例如部分村民选择将家禽家畜寄养于其他村寨的亲戚和朋友处,部分村民则选择在离村寨较远的江边修筑棚舍继续从事养殖,但养殖业规模已大不如前。由于20世纪80年代哀牢山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以及90年代起国家对民间枪支弹药的管制,村民的狩猎活动已成为过去。土地流转后,大部分水田变成香蕉种植地,以及受到工农业与生活污水排放的影响,原有的水田与河流生态环境出现退化迹象,水产鱼虾逐渐减少。香蕉种植中大量使用化肥农药,使田间地头的野菜数量与质量下降。由于封闭的自然与社会文化环境被打破,可选择的食品种类日益多样化,村民在日常饮食中很少见到鱼虾和野菜的踪迹,传统的采集生计已基本消失。
(二)工矿企业与生计变化
戛洒镇境内矿产资源十分丰富,铜、铁等矿藏储量在云南省居于前列,被誉为新平的“聚宝盆”之一。依托矿产资源优势与先进技术的引进,以戛洒镇大红山铜矿为代表的工矿企业获得了巨大发展,成为推动当地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大红山铜矿距离镇政府所在地约6千米,为国内高品位的富铜、富铁共生矿床。一、二期建设工程分别于1997年与2003年建成投产,设计生产能力为日产原矿4800吨,是国家“八五”重点建设项目。经过多次技术改进,目前日采原矿15000吨,年产铜精矿2万吨以上,铁精矿6万吨,是云南铜业与昆明钢铁集团公司的主要原料基地之一。①玉溪矿业公司大红山铜矿简介(2011-11-22)[EB/OL].http://www.yths.com/info/1010/2350.htm.土地流转后,水稻种植不再需要过多的劳力,大槟榔园的富余劳动力开始转移。由于工矿企业用工需求大,经济效益好,工资待遇高,且矿山距离村寨较近,村民可以不用背井离乡即可务工赚钱,故而以大红山铜矿为代表的工矿企业就成为村民就业的首选目标之一。受工矿企业高强度劳动作业性质的影响,在矿山工作的村民基本上都是中青年男性,工作岗位有保安、司机、矿工等。工作期间,村民一般选择在矿上居住,休息日再回到家中,亦有少部分村民选择驾驶摩托车或乘车当日往返村寨。目前,大槟榔园几乎每户家庭都有男性家庭成员在矿山企业工作,他们的工资收入是家庭最为重要的经济来源。相比传统的水稻种植,村民的收入显得更加稳定,现金收入也呈现出明显增长的趋势。此外,戛洒江边建有采砂场,采砂场在与大槟榔园对应的江段进行采砂作业时需支付给村寨一定数额的现金,收入由全村共有,村民按户数共同分配。
(三)旅游业与生计变化
作为特色乡村旅游村寨的大槟榔园,旅游业一直是镇政府优先倡导的发展项目。依托大槟榔园浓郁的民族文化和优美的田园风光,政府试图将其打造成为一个代表花腰傣与当地旅游形象的旅游目的地。大槟榔园村寨旁的“曼理圣林”是花腰傣传统节日“赶花街”的场所。“赶花街”被誉为花腰傣的情人节,是青年男女相互结识、谈情说爱的日子,传统上在每年农历二月的第一个属牛日举行。节日期间,来自不同村寨的乡民与各地游客汇集于“曼理圣林”赶花街,显得格外的喜庆与热闹。大槟榔园的村民销售各种具有民族特色的产品,如花腰傣的服饰、银镯、银链、银枷、篾帽、秧箩及食品等,部分村民一天销售的腌鸭蛋数量可达上百个。花腰傣妇女的民族服饰做工优良、精致秀美,很受游客青睐,但价格昂贵(每套衣服价格在3000~4000元),许多游客则通过租借自己穿着或邀请身着民族服饰的村民与其拍照留念,村民会收取一定费用。亦有不少游客食宿于大槟榔园,村民提供服务来获取报酬。村中有3户村民经营“傣家乐”,为游人提供吃住“一条龙”服务。
2011年后,大槟榔园的旅游热潮开始消退,村寨中用来展示花腰傣文化及生活的水碾、水磨等展示设施基本废弃,游客数量锐减。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引入新平县中恒旅游开发公司共同对戛洒镇进行专业化的旅游开发。旅游开发项目有二:一是在镇上兴建“花街”步行商业街;二是在大槟榔园举办“花腰宴舞”。“花街”建成后,政府将“赶花街”的场所搬移到镇上,大槟榔园不再作为“赶花街”的中心而存在,这一结果直接导致游客的分流。村民认为专业化的旅游开发并没有让他们得到经济收入的实际增长,相反还减少了以往可观的旅游业收入。“花腰宴舞”是一台结合花腰傣传统饮食与艺术的歌舞宴会,游客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原生态的风情歌舞表演。“花腰宴舞”的举办,吸引部分大槟榔园的村民到此工作,其中多为年轻女性,主要从事餐饮服务,这为土地流转后女性村民的就业选择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四)变迁中的生计模式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受到开放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变迁因子的共同作用,大槟榔园的传统生计模式已发生深刻而剧烈的变化,而且目前仍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土地流转后,村民由土地的耕种者变为出租者,获取固定的土地租金;稻作农业虽有所保留,但重要性不如往昔,同时也反映出一些新特点;养殖业与采集渔猎业受到政府政策与生态环境退化的影响,呈现出消亡的趋势或基本消失;从种植业中释放的富余劳动力开始从事其他产业的工作,经济重心发生转移;由性别与年龄的差异决定,中青年男性主要面向工矿企业,青年女性则向以旅游业为代表的服务业转移。新的生计模式形成并发展,大槟榔园村民的经济收入构成呈现多元化结构。
四、生计变迁对生态文化的影响
地球上自然环境和生物种群的多样性造就了人类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不同生境下的族群在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的过程中产生了多样化的生计及生计模式,如采集狩猎、“刀耕火种”、畜牧与定居农业等。人类与其他生物物种之间的最大差异在于人类主要通过文化手段,而非生物手段来适应外部的环境变化。因而人类的生计模式是适应自然环境与利用自然资源的一种文化机制。在对不同自然环境的文化适应过程中,不同生境下的族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性与多样性的生态文化。“生态文化是以调适生态与文化的关系、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为落脚点和归宿的文化”,是一种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化。①黄绍文,廖国强,等.云南哈尼族传统生态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9~12.
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花腰傣以一种适应于当地自然环境的耕种方式,形成并拥有着发达的水稻栽培和水利灌溉技术。其修筑水沟、放水泡田、犁田耙田、护林保水、施肥保田等水田管理经验正是花腰傣生态文化的集中展示,从而创造出一个良性的农业生态系统,将人、水田、稻谷、森林、河流等都容纳于一个完整而平衡的生态系统中,形成并发展出具有民族特色的稻作文化类型。例如,花腰傣的生态文化通过稻谷,特别是糯米这一物质载体而得到较好的体现:一方面,村民喜食糯米,将糯米制成粽子、汤圆、糯米粑粑等特色食品,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饮食文化;另一方面,糯米在花腰傣的宗教仪式与人生礼仪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具有特殊的象征与寓意。“祭竜”仪式中,会应用到由密蒙花染制的金黄色糯米饭,以祈求风调雨顺、粮食丰收;婚礼仪式中新郎与新娘食用的“交心饭”,其糯米的黏性象征着夫妻恩爱、儿孙满堂。②崔明昆.象征与思维——新平傣族的植物世界[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58~59,110.显然,稻米已超越提供物质能量的一种普通食物的范畴,更彰显出植根于稻作农业类型中生态文化的丰富性。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花腰傣原有的传统生计模式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改变,从而对民族生态文化产生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土地流转后,大量束缚于水稻耕作的劳动力向其他产业转移,造成了民族文化传承的断裂。由于学习接受能力和流动性较强,年轻村民首先选择离开土地。外出打工后,他们便不再直接从事与水稻劳作相关的农业活动。他们往往对传统稻作农业的生产技能技术都比较陌生,对农业生产的态度也较为冷淡。他们认为水稻种植属于过去时代的产物,没有太多的经济收益,所以不愿再从事稻作生产。长期历史进程中,村民创造出的众多蕴藏于水稻种植中的传统生态智慧与生态知识,正在由于传承人的缺失而逐渐衰落。由于现代农业的进入,化肥农药使用量的急剧增加,土壤肥力的退化与河流水源的污染,直接改变了原本良性的农业生态系统,进一步加重了传统稻作农业及其生态文化的衰落趋势。
其次,当地人崇尚的万物有灵宗教信仰逐渐淡化,其中蕴含的崇拜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化正在消失,颇有代表性的是村寨中祭祀“竜树神林”宗教仪式的变迁。花腰傣传统文化将树木神圣化,并以各种宗教仪式对其加以祭拜,其意义不仅仅局限于人们企盼理想生活的信仰层面,还具有保护自然环境的现实作用,显示出蕴藏于传统信仰体系中的科学性。水源是水稻种植中必不可少的自然条件因素,水源的多少与优劣直接影响到水稻收成的好坏。树木森林具有涵养水源、调节水源分配、防止水土流失等多种生态功能。因而,对树木森林的管理和保护是关乎稻作民族生存与繁衍的头等大事。“竜树神林”的植物崇拜将保护森林、保护水源、保护自然等环境的保护意识,通过对自然与鬼神的崇敬内化于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中,成为生态文化的鲜活再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生态意义。由于现代信息的散播及当代价值取向逐步深入人心,传统价值观在年轻人中受到了挑战。对于传统的宗教信仰,年轻村民往往持一种不置可否的态度,传统文化的吸引力逐渐丧失,造成了不同代际间的文化断层。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传统的宗教祭祀及节日、节庆活动也不得不做出调整以适应旅游业的发展。例如,当地最隆重的一次“祭竜”(亦称“祭大竜”),即祭祀“牛竜树”与“花街节”传统上都在每年农历二月的第一个属牛日举行。旅游开发中,“祭竜”与“花街节”的内在价值与外在形式都在发生着改变,皆被开发成一种观光游览与旅游体验项目。为了增加旅游收入,迎合市场需求,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将“花街节”的举办时间由传统的农历二月的第一个属牛日更改为每年正月初三至初六;在大槟榔园,“花腰宴舞”被安排在村寨的“竜树林”旁,以便于游人观看“祭竜”仪式,可见该“仪式”已具有明显的表演性质。随着“祭竜”仪式表演成分的增加,村民对其仪式的庄重与神圣感正在消失。例如,“祭竜”仪式由专门的神职人员“竜头”主持,“竜头”的产生则是通过“称衣择重”来选取,具有神判的性质。然而,2013年大槟榔园两次通过传统仪式所选出的“竜头”都不愿担当这种费力费时且没有什么经济效益的差事,人与鬼神的意志出现相左,“鬼神”的意志最终让位于村民的“经济”意识。其实,村民追求经济效益,向往富裕生活是人之常情。但问题是,村民在关注传统文化表演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忽视了蕴含在其宗教仪式、传统节日中的民族文化价值及其生态效益。
五、结 语
花腰傣的传统生计模式是适应于当地自然环境,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一种文化机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谋生方式与生存策略,是传统生态智慧和生态知识的结晶。
大槟榔园村民的生计变迁,显示出一种有别于自然环境因素发生变化的变迁方式,更彰显一种在激烈的社会文化变革中,人们对于社会文化环境变化的适应性。面对不同于以往的社会文化环境,村民以一种积极主动的态度接受这种变化:以土地流转、外出务工、旅游服务等多种回应方式进行着文化适应,采取一种较主动的方式融入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但是,这种适应性又不得不受限于社会文化环境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变迁因子,尤其是受政府政策与市场经济的影响,使村民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某些方面处于一种相对被动的适应地位。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大槟榔园传统生计模式的变迁使得植根于其上的生态文化也必然会受到影响。文化虽在不断变化中,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保守性,因而花腰傣的生态文化不会立即消失。但由于文化传承人的缺失,使得生态文化的保护刻不容缓,对此必须加以重视。根据大槟榔园旅游业的发展已有相当良好基础的实际情况,在进一步的旅游开发中,发展观光农业不失为一种保护与开发并举的解决方案。这一举措的实施,既可使村民在水稻种植中直接获益,又能让年轻人体会到传统农业的深层价值,激发他们自觉保护与传承本民族生态文化的自我意识。在民族自豪感与民族自信心的形塑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完成对生态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同时,政府在旅游开发中应发挥更积极的引导作用,优先考虑村民的切身利益,正确处理发展中的利益共享问题,采取适宜于当地实际的举措,做到既能改善村民的生活水平,又能避免优秀民族文化的消失。
A study of the livelihood mode and changes of the Dai people in Dabinglangyuan Village of Xinping Coun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eco-anthropology
CUl Ming-kun1,2, YANG Suo2, ZHAO Wen-juan3&ZHOU Xiao-hong2
(1.School of Life Sciences,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650092,China; 2.Institute of Ethnic Studies,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091,China; 3.School of Resources,Environment and Earth Science,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091,China)
Dabinglangyuan Village of Xinping County in Yunnan Province is a typical Dai village specially select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for rural tourism.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the paper adopts the cultural adaptation theory of eco-anthropology to analyze the livelihood mode and changes of the Dai people in this village as well as the impacts of livelihood changes on its eco-culture.It concludes that their traditional livelihood mode formed in the long history was a cultural mechanism that can adapt to the local natural environmen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society and economy,the traditional livelihood mode of these villagers has experienced dramatic changes,and they are somewhat willing to adapt to the open market,a kind of adaptation to the changes in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but are also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ome restrictive factors.
Dabinglangyuan Village;adaptation;Dai people;livelihood mode
王德明]
C912.4
A
1000-5110(2015)05-0030-06
崔明昆,男,河南辉县人,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外聘教授,研究方向为生态学人类学。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元江干热河谷的傣族地区土地退化的生态人类学研究”(13BMZ05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363O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