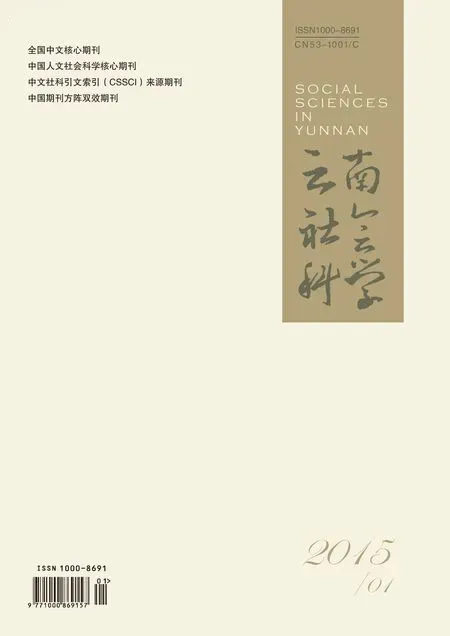从西双版纳的内外之分看早期国家的统治基础
卢中阳
在西双版纳的历史上,内、外区分具有普遍性。“内”被称为“乃”,“外”被称为“诺”。如“内议事庭”(“司廊乃”)与“外议事庭”(“司廊诺”)、“内领囡”(“领囡乃”)与“外领囡”(“领囡诺”)、“内冒宰”(“冒宰乃”)与“外冒宰”(“冒宰诺”)、“内滚乃”(“滚乃乃”)与“外滚乃”(“滚乃诺”)、“内洪海”(“洪海乃”)与“外洪海”(“洪海诺”)等。这种内、外之分还见于其他社会当中,如《尚书·酒诰》中提到商代的“内服”和“外服”,1949年以前藏族的“乌拉差”分为“内差”(“囊差”)和“外差”(“期差”),永宁纳西族在土司统治时期的“责卡”分为“内责卡”和“外责卡”,四川甘孜藏族土司家的娃子分为“内娃子”和“外娃子”等,这些社会的共同特点是都尚处在国家不甚发达的早期国家阶段。通过对西双版纳内、外之分的研究,既有利于掌握内、外区分的标准,又有利于了解这种内、外之分在早期国家统治中所占的地位。
一、地域不能作为区分内、外的唯一标准
这种内、外之分,学术界一般认为是以一定的地域为划分标准的。在西双版纳,有学者认为以城子为划分依据,住在城子的为“内”,住在城外乡下的为“外”[1](P223)。即“内领囡”“内冒宰”“内滚乃”都是住在城子,而“外领囡”“外冒宰”“外滚乃”都是分出去建寨住在城外[2](P7)。还有人进一步解释说,城子的“滚乃”“领囡”“冒宰”,称呼上都加上“乃”,“乃”是“内”之意,也含有“大”“上”“头”的意思;城子外的“滚乃”“领囡”“冒宰”,称呼上加“诺”,意思是“外”或“小”的意思[2](P36~37)。此外他们还认为,城内和城外之人社会地位和负担也是不同的,城子的“滚乃”“领囡”“冒宰”可当波郎,管辖城外的人,而城外“滚乃”“领囡”“冒宰”不能当波郎。城内负担土司的劳役较轻,而城外负担的劳役较重[2](P36~37)。同样的区分还见于云南宁蒗县永宁纳西族的“责卡”等级,有学者认为居住盆地中心的称为“内责卡”,居住边缘地区的称“外责卡”。关于商代的内、外服,也有学者认为是以“王畿”为划分标准,“王畿”以内的为“内服”,“王畿”以外的为“外服”*《尚书·酒诰》孔颖达《正义》:“畿外有服数,畿内无服数”,文中“畿外”即外服,“畿内”即内服;“所谓‘内’与‘外’,是以王畿为限。王畿以内为内服,王畿以外为外服”,见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8页;“商朝王畿在古文献中称为‘内’,于此相对的诸侯国称为‘外’”,见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514页;“所谓的‘内’、‘外’是指天子所直接统治地区和诸侯国地区。”见李学勤主编,王宇信等著:《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21页。。由此可见,在以往的研究中,无论是在西双版纳,还是在永宁纳西族和商代社会中,这种内、外之分都是以一定地域作为划分标准的。
但实际上,按地域作为划分内、外的标准不完全成立。以西双版纳为例,在景洪市的曼沙和曼令两村,他们属于“滚很召”等级的“领囡”阶层,两村的劳役是各户轮流给“召片领”(宣慰使)炒菜。曼沙是“内领囡”,称为“乃”,是专司掌锅炒菜的大师傅。曼令是“外领囡”,称“鲁农”,即小辈或仆从,职掌洗菜打杂[1](P222~223)。曼沙和曼令位于今天景洪市的嘎栋乡,两村隔河相望,至今两村的老人还说他们是负责炒菜劳役之人的后裔*据笔者2013年11月4日对曼沙和曼令两村的调查。。据西双版纳贝叶文化研究中心所长介绍,当时的城子在景洪城区东南的猴山*据笔者2013年11月4日对西双版纳贝叶文化研究中心的访谈。猴山位于澜沧江与流沙河的交汇处,以前曾是一个旅游区,现在已经废弃。笔者曾于2013年11月3日到过猴山,目前许多历史遗迹都被澜沧江和流沙河冲毁,仅存塔庄董、塔庄孟两座佛塔和一个圣泉。傣王宫早在“文革”时期就被拆毁,现在变成了农场的一个生产队。以前猴山上有8个寨子拱卫王宫,即曼岗景、曼龙东、曼控章、曼帕萨、曼勒、曼瓦、曼嘎、空柯。后来这些寨子被当作“召片领”(宣慰使)的“孝子贤孙”,强迫分散到十几个村寨安家。。而猴山距离两村直线距离有十多公里,所以他们都不属于城子。拱卫城子的“三佬四练”村寨,一般被认为是“内”[3](P84)。但他们并不全都住在城子,如景洪的“三佬四练”寨有曼勒、曼控章、曼帕萨、曼岗景、曼龙冬、曼贺蚌、曼贺纳、曼景法、曼苏供、曼龙枫等十几个寨子[4](P60),其中只有曼勒、曼控章、曼帕萨、曼岗景、曼龙冬属于城子。在勐景真,据土司后人刀波罕说,当时城子在(母)乌龟山上,就是景迈、曼海和“召庄”的范围,现在则被划分为景迈和曼海两个自然村*笔者于2013年11月5日到过位于曼海村的刀波罕家,他家仍保留着以前土司的老房子,并有鱼塘和两栋小楼。刀波罕经营茶叶生意,经常去泰国和缅甸,家境殷实。他所说的乌龟山,当地人称为母乌龟山。。勐景真的“三佬四练”寨,有景迈、曼拉闷、曼养、曼赛、曼海、景代、曼养六个寨子[3](P85),只有景迈和曼海属于城子,其他都在城外。在勐遮,据岩香瓦和岩章满两位老人介绍,当时城子主要在(公)乌龟山上,包括现在的召庄、曼吕、曼宰竜、曼章领、曼磨中、凤凰和曼别这7个村子*据笔者2013年11月5日在勐遮的调查。岩香瓦和岩章满所说的乌龟山属于公乌龟山。。有人认为“三佬四练”村寨指的是曼宰竜、曼吕、曼宰令、曼别、曼凤凰、曼磨中6个寨子[3](P84)。也有人认为所谓“三佬”是指曼贵、曼遮龙和曼章领,所谓“四练”是指曼别特、曼洪换、曼保中和曼侬卫[5](P32)。不管怎样,它们并不都在城内是肯定的。在勐往,“四卡真乃”,直译为“内四大臣”。在“内四大臣”之外,还有“四卡真乃景”,“乃景”有“城内”之意,即“城内的四大臣”。可见“四卡真乃”即“内四大臣”,应该并不住在城内。此外,“郎目乃”寨,也有人称之为“郎乃”寨,“乃”为“内”,是直属于“召片领”(宣慰使)的寨子。他们往往作为“召片领”的政治“陇达”被安插在各勐,目的是对各勐土司进行监控,这样的寨子总共有一百多个,这些“郎目乃”寨也并不住在“召片领”的城子[6](P8)。
住在城内的人在社会地位上也不完全比住在城外的人高。比如勐往的“四卡真乃”和“四卡真乃景”,其中“四卡真乃景”住在城子内,但政治地位略低于“四卡真乃”,在许多方面受到“四卡真乃”的节制[6](P152)。同时,城内负担土司的劳役也不比城外轻。因为许多在城子为土司服劳役者,随着人口增加被分出去建寨,却仍然定期轮流提供他们原来负担的那些家内劳役,其所承担劳役的内容和数量并无变化[1](P206)。如滚莫寨最初住在城子,后来人口增多容纳不下,他们便问土司要到哪里去住,土司说:“随便”。于是他们就选定寨址,经土司同意后分出去建寨,但仍然负责原来的祭竜事务[6](P56)。这样既降低了土司为服役者提供生活所需的成本,又使服役者获得了更多的土地,经济和社会地位都有提高。
此外,以地域作为区别内、外的标准,在永宁纳西族和商代社会中也是行不通的。如居住宁蒗县永宁坝子中心的并不完全是“内责卡”,还包括温泉乡西部瓦拉片、八瓦等纳西村以及拖七、比七、瓦都等普米村,而他们都不属于“内责卡”[7](P34)。在商代所谓的“王畿”之外,还存在着明确被称为内服的“亚某”,所以用“王畿”内、外来划分内、外服也是不成立的[8](P40)。
二、内、外区分的复杂性
在早期国家阶段,内、外之分,虽然偶有与地域相重合的情况,但绝不是以地域为划分依据。西双版纳傣族的材料表明,这种内、外之分是十分复杂的。
首先是服务对象的区分。这一点主要表现在直接为统治者自身服役的为“内”,为他人或国家服役的为“外”。如“召片领”(宣慰使)和各“召勐”都有“议事庭”,直接归“召片领”和“召勐”管辖的,称为“内议事庭”。而作为负责全区和全勐事务的最高议事和行政机关,则称为“外议事庭”*“外议事庭”由部落议事会发展而成,是部落的最高权力机关,可以对“召片领”或各勐土司的交议事项进行否决,进而实现权力制衡。见《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综合调查二》(修订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4页。。对于“滚很召”等级的“领囡”阶层而言,为“召片领”直接服务的称“领囡乃”(内),为波朗和召竜帕萨服务的称“领囡诺”(外)[9](P103)。而对于各勐土司而言,“滚很召”是“召勐”自己的,称为“内”。“郎目乃”是“召片领”的,称为“外”[2](P8)。这种区分还见于其他民族当中,如在永宁纳西族,由土司直接控制的称为“内责卡”,由土司下属管理的称为“外责卡”[10](P84)。藏族的“乌拉差”也体现为给直属的统治者服役和缴纳的差称为“内差”,给地方政权第巴政府及其下属机构缴纳和支应的差称为“外差”[11](P92)。按照服务对象不同区分内、外,构成了早期国家阶段内、外之分的基础。
其次是亲疏远近的区分。从内、外议事庭和“召片领”(宣慰使)的亲疏来看,内议事庭为亲,外议事庭为疏。内议事庭的组成人员都是直接为“召片领”宫廷服务的亲近家臣,而外议事庭则关系相对疏远[4](P17)。对于同一服务对象,根据亲疏远近的不同也存在内、外之分。“召庄”是土司的远亲,“召”是“主”,引申为“官家”,与其他等级相比,他们往往被看作“内”。如勐往的“内四大臣”(四卡真乃)和“城内的四大臣”(四卡真乃景)合称“别卡真”(即八大臣)。与“外四大臣”(四卡真诺)相对,他们都属于“内”。但因为“内四大臣”的官员限定由官亲“召庄”担任,政治地位高于“城内的四大臣”,所以在“别卡真”中又分内、外,即“四卡真乃”为内,“四卡真乃景”为外[6](P152)。“滚很召”是土司的家臣,“滚”意为“人”,“很”为“家内的”或“自己的”,“召”为“主”或“官家”,合起来是“主子的人”或“官家的人”。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于官家的亲戚“召庄”,所以相对于“召庄”而言,“滚很召”是“外”,“召庄”为“内”。而对于被征服者“傣勐”来说,则“滚很召”是“内”,“傣勐”为“外”[3](P12)。这种按照亲疏远近关系区分内、外,在商周时期也非常普遍,当时“亲不在外,羁不在内”被认为是各国任官制度的通则*见《左传》昭公十一年。。
再次是臣服先后的区分。在西双版纳,“老傣勐”和“新傣勐”之间也存在着内、外之分。“老傣勐”寨由于建寨较早,为“内”。它们一般集中居住在坝子的中心,耕地也靠近水源。“新傣勐”寨由于迁来建寨较晚,为“外”。主要分布在澜沧江沿岸,那一带地高水低,江水无法利用,多是荒草野林,村民到坝子去种田,一般要走十几里路。所以人们称“老傣勐”寨为“陇咚”,即坝心的寨子;称“新傣勐”寨为“陇厅”,即江边的寨子。“老傣勐”寨由于建寨较早,所以臣服也较早;“新傣勐”寨建寨较晚,所以臣服也较晚。臣服较早的为“内”,臣服较晚的为“外”。新、老“傣勐”之间的内、外之分还表现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异,如“老傣勐”寨说自己的“鬼大”,不能和“新傣勐”寨子通婚。“新傣勐”的人由于社会地位低,很少去“老傣勐”的街子赶街[12](P5~6)。
三、内、外之分与早期国家的统治基础
内、外区分,主要是为了通过“以内御外”的统治方式,在社会上形成层层控制。如景洪和各勐的内、外“议事庭”之间关系就十分微妙,“内议事庭”成员主要是直接服务于“召片领”(宣慰使)的亲戚或家臣,而“外议事庭”成员主要由坝区四“火西”的叭、鲊、先及山区头人组成。从两者官员的等级看,“内议事庭”低于“外议事庭”,但“内议事庭”官员可以参加“外议事庭”会议,“外议事庭”官员不能参加“内议事庭”的会议。“召片领”下达事项是由“内议事庭”商议后,再通知“外议事庭”去下达处理。各勐要禀报事宜,也是先报“外议事庭”,处理不了,才交“内议事庭”商议,再解决不了,便由“内议事庭”呈报“召片领”[13](P89)。可见“内议事庭”的实际权力要高于“外议事庭”。所以有人认为“外议事庭”和“内议事庭”之间存在附属关系,也就是说“外议事庭”是“内议事庭”的外围组织[5](P91)。这一点在其他事项上也得到印证,在勐往就存在着以官亲“召庄”担任的“四卡真乃”,比以“城子头人”担任的“四卡真乃景”高,“四卡真乃景”比以“叭火西”担任的“四卡真诺”高的政治格局[6](P152)。为了加强对各勐的控制,防止土司叛乱和人民造反,“召片领”还派自己的亲信到各勐建立“郎目乃”寨,这些村寨不受当地土司管辖,直接隶属“召片领”。“郎目乃”负责监视各地“召勐”、头人和百姓[4](P212)。这种情况在各勐也存在,当勐遮“傣勐”反抗土司被镇压后,土司为便于管控“傣勐”的叛乱,便把自己的亲近奴仆“滚很召”安插到“傣勐”中去建寨。据说,“滚很召”最初被分出去建寨时,每天都要回到土司家里。有人说,他们是为了给土司报告“傣勐”的消息[6](P7)。同时,即使是在同一个等级内部,也要区分内、外。如同为“领囡”等级的曼沙和曼令两寨,因为曼沙是专司掌锅炒菜的大师傅,所以被划分为“内”,而职掌洗菜打杂的曼令被划分为“外”,由曼沙的头人“叭炸”管理和监视[1](P222~223)。由上可知,不仅各个等级之间区分内、外,而且同一等级内部也有内、外之分。通过“内”来控制“外”,这样便在整个社会中形成层层控制,并以此维护土司的统治。
为了实现以内驭外的目的,还规定了内、外之分在负担上的差异,与“外”相比,“内”往往享有一定的优待和特权。如作为官家亲戚的“召庄”,他们构成了土司武力统治的基石,属于国家结构中的“内”,他们除负担警卫外,并不承担其他义务。“滚很召”阶层的负担虽然比“召庄”重,但与“傣勐”侧重于经济方面的榨取相比,“滚很召”认为自己承担的劳役负担比“傣勐”要轻[2](P10)。此外“滚很召”相比“傣勐”还有许多特权,他们犯了罪可以罪减一等。“滚很召”去土司家服役,有事可请假回家。可“傣勐”要请事假,土司是不允许的。“滚很召”在土司家可以靠近土司身边,睡在土司家的门楼里,还可以吃土司剩下来的饭菜,这些“傣勐”都是办不到的[6](P7)。值得注意的是,“召庄”“领囡”“冒宰”“滚乃”等村寨,在1936年以前尚未列入“火西”的编制,也就是说派给其他村寨的负担他们可以免除。直到1936年,土司合并内、外议事庭,把“外领囡”“外滚乃”“内、外冒宰”编入“火西”,他们才被正式列入负担系统。至于“召庄”和“内领囡”“内滚乃”等仍未编入。“外领囡”“外滚乃”和“内、外冒宰”虽然被编入“火西”,但在一般负担上仍有所不同,据“领囡”和“冒宰”说,“傣勐”出夫3次他们出1次,“傣勐”出钱3块他们出1块[2](P9)。山区“郎目乃”寨的头人与其他头人相比享有一定的特权,他们可以骑着高头大马,打着“金伞”,敲着锣鼓,大摇大摆地径直来到“召片领”房前才下马。“召片领”(宣慰使)给“朗目乃”的委任状上明白宣谕:“如有任何人敢于压迫你们,就要遭到灭亡,你们可把情况报来宣慰使予以处理。”[4](P212)对于新、老“傣勐”之间形成的内、外关系,在负担上也是有差别的。“新傣勐”被编为五个“扫”,“老傣勐”只是一个“播”,而在负担分配数量上“播”和“扫”是相等的,但自然户却不相等,这样自然户的负担数额则差异很大。如缴纳给“召勐”的“考汗”,“播”内每户只合2挑,“扫”内每户要合5挑[12](5~6)。这种负担方面的差异,其实正是维护内、外之分的需要。
余 论
内、外之分在维护早期国家的统治中占有重要地位,统治者根据服务对象不同以及亲疏远近和臣服先后的差异区分内、外,通过“以内驭外”在社会上形成层层控制,从而强化国家统治。纵观中国古代的历史,即使国家在进入成熟时期后,这种内、外之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以内驭外”的政治格局都还一直存在。战国时期,各国国君的家臣、奴仆,一跃而成为国家的要员。如“宰”原本是负责宰杀牲畜的臣仆,后来则摇身一变成为了总理天下事务的宰相。汉武帝以后,为削弱丞相的职权,不断扩大内朝(中朝)的权力,提高少府属官尚书令和仆射等地位,赋予其参决机务的职能,最终使尚书台成为中枢决策机构。尚书台(省)事权膨胀,逐渐走向外朝,中书、门下即取代尚书在内朝的作用,掌诏命之事的参与决策。经魏晋南北朝,中书省、门下省也最终走向前台。隋唐时期,便形成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并立朝廷和共参国政的新格局。中唐以后,皇帝的秘书班子介入决策,翰林学士被视为“内相”。宦官充任枢密使,枢密、宰相共参国政。于是,又出现新的“以内驭外”之势。五代之际,枢密使改用士人,枢密院便转而成为外朝高级军事机构。明朝的内阁继承宋朝翰林学士院之制,由后台走向前台,成为相当于宰辅的中枢机构。总之,朝廷设官,既需要有一个替皇帝处理政务的宰辅,又担心其事权过大,威胁皇权。于是,便设计出一个“以内驭外”的格局,由内廷控制外朝。内朝事权扩大,必然取代外朝,便再设置新的内廷,控制被取代后的新外朝。这种“以内驭外”的政治格局,虽已经不可与早期国家阶段的内、外之分同日而语,但由于中国古代长期存在“家国一体”的政治体制,所以基于亲疏关系的内、外之分才会长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