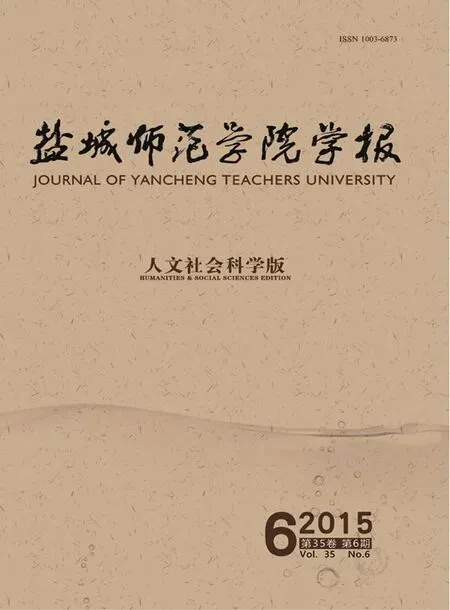儒家“内圣外王”与柏拉图“哲学王”之比较——兼论中西方传统政治思想的异同
恽彩锋
(南京艺术学院 传媒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内圣外王”与“哲学王”分别作为中国儒家与西方柏拉图时代的政治吁求与政治理念,反映了两千多年前中西方政治思想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但两者并不等同。本文将对这两种思想进行比较。比较的方式不是简单列举出它们语言形式上的区别,而是努力深入各自思想的本质层面进行分析和对比;比较的目的不是为了分出高低和优劣,而是试图跨过中西方的话语壁垒,认识中西方传统政治思想中某些实质性的异同。
一、中西方传统政治思想的核心要义
“内圣外王”一词并非源自儒家经典,而是从道家著作《庄子·天下》中移植而来。庄子有感于“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以及“道术将为天下裂”,提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1]228,并将“内圣外王”的精神概括为“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1]228。
其实,早在先秦儒家思想中就已经包含有“内圣外王”的观念。孔子曾把尧舜视为“圣王”,认为他们所行的就是内圣外王之道。荀子也认为天下至大,“非圣人莫之为王”[2]227,他还给“圣王”下了一定义:“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2]296可以说,内圣外王体现了儒家成圣成仁和仁民爱物的统一,人格理想与现实政治要求的统一,自身关怀与现实关怀的统一,从而构成了儒家政治学最核心内容。当然其正式使用这一术语是从宋代开始的。北宋理学大师程颢把他同时代学者邵雍的学说称作“内圣外王之学”。现代新儒家更是喜欢用“内圣外王”来概括儒学。熊十力在其《原儒》一书的序言中指出,孔子“承乎泰古以来圣明之绪,而集大成,开内圣外王一贯之鸿宗”。冯友兰在其《新原道》序中指出,中国古代哲学无论哪派哪家,都自以为是讲“内圣外王之道”,中国哲学家都把哲学看作是成就内圣外王人格的学问。
柏拉图政治哲学中最为核心的理论之一便是“哲学王”的思想。《理想国》一书从第五卷到第七卷后半部分对哲学的论述中,对该思想作了充分的阐述。“只有在某些必然性碰巧迫使当前被称为无用的那些极少数的未腐败的哲学家,出来主管城邦(无论他们出于自愿与否),并使得公民服从他们管理时,或者,只有在正当权的那些人的儿子、国王的儿子或当权者本人、国王本人,受到神的感化,真正爱上了真哲学时——只有这时,无论城市、国家还是个人才能达到完善。”[3]251作为一种智慧之学,柏拉图认为,哲学是通过研究辩证法和探寻事物的本质并在善的理念的指引下进行的。“哲学王”的政治主张认为,哲学家并不热爱权力,但他们是真理的追求者和知识的拥有者,出于对城邦的责任,哲学家应当作是这个城邦事务的管理者和建设者。换言之,统治国家、城邦的人应当是哲学家,也只有哲学家才能统治这个国家、城邦。这一思想是对柏拉图“理想国家如何实现”的现实回答。
二、中西方传统政治思想的相互关联
“内圣外王”和“哲学王”并非两个互无关联的概念。如果以现代人的思维来认识这两者,便会发现它们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而这些相似又反映出中西方传统政治思想一定程度上的呼应。
首先,两者都体现了王者之治的政治思想。
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存在着两种治国之道:一是“王”道;二是“霸”道。王道主要是通过道德指示和教育来实现;霸道则是通过暴力的强迫来实现[4]65。在柏拉图那里,政体被分为五类:一是王国或贵族制;二是荣誉至上的政体;三是寡头政体;四是民主政体;五是僭主制。理想国中的哲学王所对应的是第一种政体,这种贵族制政体是由最优秀的人或人们进行统治的,它所追求的是善或美德,是正义城邦的政体[5]59。跨过中西方文字表达上的差异,圣王的治道与哲学王的贵族统治所体现的实际上都是一种王者之治。这种王者之治的政治思想,实际上同时也表明了社会对统治者个人素质的更高要求。因而柏拉图认为只有微乎其微的人能配得上研究哲学,进而成为统治者[3]247。在成王的过程中,圣人和哲学家都表现出一定的个人自制。只不过,哲学王是通过理性引导达致自制,而圣王是通过克已遵礼来实现个人自律的。
如果援用马克斯·韦伯的三种统治类型的范式(即传统型、魅力型和合法型)[6]来分析,这种王者之治也就是一种个人魅力型的统治方式。魅力型统治者的权力是建立在被统治者对他个人使命的纯粹实际承认的基础上的,这种承认的渊源在于信仰上倾心于不同寻常的和闻所未闻的、被视为神圣的东西[7]。其实圣人或哲学家之所以能够成王主要源于他们自身非凡的品质和超人的智慧。当他们成为统治者后,不需要借助神权、暴力等外力手段便可获得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被统治者对他们的服从和支持也是自然而然的。如果统治者刻意去要求被统治者接受其统治,那反而是不自然的,这也不是一个有用统治者的所为[3]236。当然纯粹魅力型的统治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存在的,它总是或多或少地夹杂着一些其它的成份,但是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它是有着清晰的界定的,儒家和柏拉图思想中的统治者也是一样。
第二,两者都介于有为与无为之间。
这里的“有为”主要取义于中国传统哲学,而非指现代意义上的那种把人看成自己生活世界的积极塑造者和支配者的功能主义的意识倾向。在中国思想中,有为主要指的是个体基于对他人、自然和社会关注之上的有所作为;无为指的是摆脱一切现实制约、不断走向自我的自由超然状态。这两者大体上类似于“入世”与“出世”的差别,也常常成为人们评判某种政治思想的简洁结论。但是如果我们分别用“有为”和“无为”对圣王和哲学王加以定性和区别,那么理解上的歧义就会出现,因为在圣王和哲学王身上这两者并不是相对立的。
不管是圣王还是哲学王,都是先有前方修饰语的存在,才有后面“王”的出现的。但内圣与外王之间、哲学与王之间并不是一种必然关系,前者只是后者的必备条件。也就是说圣者不一定必然为王,哲学家也不一定都成为统治者,但是要成为王,一定得先是圣人或哲学家。所谓“内圣外王”,简言之就是说,最适合为王的一般来讲应该是在思想上、在精神上最富有成就;但事实上是否如此,就另当别论了[4]8。在理想国中,哲学作为最高的学问,哲学家学习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去从事政治活动,而是为了追寻至高的善的理念,从而使自身的灵魂达致一种理性状态。哲学家一旦成王,这是违反他本人的意志的,他最终的成王是被迫的,并且其本人将为此作出牺牲。因而可以说,圣王和哲学王都是偶然成王的。这种偶然性毫无疑问地体现了他们无为的思想情怀。
然而,无论是圣人还是哲学家,他们的内心都存有一份责任意识。柏拉图关于正义的阐述不仅意味着只有哲学家才真正是正义的,而且还意味着正义城邦的所有成员以及某种意义上任何城邦的正义成员,不管他们是不是哲学家都应该是正义的[5]57。这就使得哲学家不管是出于内在的兴趣,还是出于义务或被迫都必须为城邦服务,进而哲学家出于自己的爱国主义之爱而参与政治活动也就成为理所当然[5]58。对于儒家的圣王而言,有为的意识是横贯一生的。因而圣人是既入世也出世的[4]7。他们的“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以其廓然大公之心包举众流,无为而无不为。也可以说,正是一种责任意识和义务感驱使圣人和哲学家最终成王,实现了有为与无为的统一。
第三,两者都实现了个人与社会的统一。
这一点理论界的认识并不统一。一般认为理想国中的哲学家们长于远离现实的抽象理性思考,他们轻视可见世界的认知而执着于可知世界的探寻,因而个人与社会之间呈现出的是一种二元状态。柏拉图本人也认为哲学家的注意力永远在永恒不变的事物上,对于琐碎人事是无暇关注的[3]252。但如果据此便认为柏拉图的哲学王是完全超脱于社会现实的,个人与社会之间是完全割裂的,这也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主客体的二分对立是西方近代以后才开始确立的,在柏拉图那里整体的善才是最终的善,这种善包容着所有不完全的善[8]。并且他认为,哲学王的成长与城邦共同体的状况是紧密相连的,因为只有在一个合适的国家里,哲学家本人才能得到充分的成长,才能去保卫自己的和公共的利益[3]248。而城邦的立法也不是为某一个阶级的特殊幸福,而是为了造成全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幸福[3]279。这样看来,个人与社会的统一在哲学家那里是不言而喻的。
至于儒家圣王,这一点是不存在异议的,因为内圣外王思想本身便集中体现了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高度统一。中国人向来强调天地一体,认为具有肉体生命的个人是家族、社会乃至天下的一员。儒家更是注重内与外、圣与王、心情修养与经世致用、精神境界与建功立业的贯通,立己、达己是起点,立人、达人是终点。
第四,两者都体现了知识与权力的统一。
这种圣与王、哲学与王的结合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西方传统政治哲学中知识与权力的统一性。知识和权力都是现代话语,如果以现代人的视角审视两千多年前的古代社会,我们会发现他们对于知的承认,包括德性和智慧的至高地位的确立最终往往是通过赋予其政治权力来体现的。当一个人达到了“人伦之至”,修炼到了圣人的境界,那么社会便可以给予其王者的地位。同样当一个人经过音乐、体操、数学及辩证法的训练,具有了超凡的理性,那么他就可以被确定为城邦的“最完美的护卫者”[3]257。如果两者不能统一,即哲学家成不了国王,或已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不能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那么对国家甚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3]215。
由此来看,知识与权力的结合并非完全是现代启蒙的产物,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对于知识权力体系的现代性批判实际上一直可上溯至此。但是它们的那种结合与当代的知识霸权还是有差别的。在当代社会知识往往被作为获取权力目的的一种手段和工具,造成物对人的操纵和控制。在古代社会对知识的追求和自我的提高是人的终级目的,古人并不是为了成王才去学习修炼,而主要是为了获致一种圣人之境或至善理念,因而虽然同是知识与权力的结合,其后果却是不同的。
三、中西方传统政治思想的主要差别
圣王与哲学王虽然有许多一致性,但它们毕竟产生于不同的历史语境,是由不同国家的不同思想家提出的,因而两者的差异也是必然的,透过这些差异我们可以窥探到中西方政治思想中某些根本性的差别。
第一,“为道”与“为学”之别。
一般来说,中国哲学重“为道”,轻“为学”,而古希腊哲学一开始便以“爱智”——求知为目标[9]。“为道”所采取的途径是直接体验,其结果是一种非理性的境界;“为学”所采取的途径是逻辑推理的思维方式,结果是理性的普及[9]139。这种差异也或多或少地表现在圣王与哲学王身上。
从“二王”学习的内容上看,中国的圣王主要是以“修身”为本,以“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为“内圣”功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外王”功夫。学习的内容主要取自《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四书五经”经典著作。其中述及较多的是各种关于“道”的学说,它所强调的是个人内在德性的提升。古希腊哲学王的学习是分阶段进行并且伴有淘汰制。先是进行体操教育,“因为它影响身体的增强与衰弱”;接着是音乐,它通过习惯、音调、韵律、故事的语言等教育护卫者;然后是计算和数数,其目的是“为了用于战争以及便于将灵魂从变化世界转向真理和实在”[3]288;再下面是几何学、天文学;最后也是最高点是辩证法的学习,因为“当一个人企图靠辩证法通过推理而不管感官的知觉,以求达到每一事物的本质,并且一直坚持到靠思想本身理解到善者的本质时,他就达到了可理知事物的顶峰了”[3]298。经过这一系列长期的学习训练之后,哲学家便应运而生。从两者的培养过程可以看出,圣王的培养注重的是“道”的修炼,哲学王的学习注重的则是“知”的获得和“理”的领悟。
第二,伦理的自觉和法律的完善。
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只要承认“王”的存在,便同时认可了一种人为秩序存在的必要性。这种对圣哲王者的需求,反映出人们对自由无序状态的担忧和对合理管制的渴望。这一点不论是在有着自由主义思想传统的西方,还是在有着专制主义思想传统的中国,都是没有争议的。
但同样是统治者,他们在治理方式上却是有差异的。儒家圣王依靠的主要是伦理道德的自觉,在政治实践中注重对人性的挖掘和政治伦理的运用,逐渐实现由心性伦理向政治治理的推进。他们认为“君若没有圣君必备的道德条件,人民在道德上就有革命的权利”[4]65。也就是说,这种“内圣”的要求已转化为对统治者理想人格的要求。因而孔子坚信,“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0];孟子认为“其身正而天下归之”[11]。其实,不论是孔孟的仁政德治,荀子的以推行仁义为目的的“王制”,或是董仲舒的行教化的“圣人之政”,他们都把道德修养与政治治理过程揉合在一起加以考虑的,并将一切问题都化约为道德问题。这样,道德便具有了无所不能的普适性,进而出现了政治道德化的倾向和泛道德主义,这一点使得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受挫。
柏拉图的哲学王则倾向于通过思辩科学或实证性的手段,实现对社会的统治。在《政治家篇》中他从理想国回到了现实社会,提出了依据法律的治理形式,也即第二国家形式,并在接下来的《法篇》中用了大量篇幅阐述了其法治思想。因而《法篇》的写作既是对科学理性的一个回应,也是对哲学王的必要补充。这种法律意识的兴起无疑是意义重大的,它开启了西方政治思想中法治意识的先河,后来亚里士多德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这也是为何中国的德政思想源远流长,而西方的法制思想较健全的原因之一。
第三,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不同选择。
圣王在中国是被作为一个历史存在来看待的。夏商周三代之王已成为内圣外王的直接取法对象,并且儒家思想家们常常以一些历史人物作为典范来教化民众,如孟子说:“伊尹,圣之任者也。伯夷,圣之清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12]《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中庸》的“治国九经”也为这一政治理念提供了经典诠释。因而行内圣外王之道的社会并不要在超现实世界中实现,“圣王”也不需要离开世间,而是“游内以弘外”者。
而哲学王在西方则是被视为一个从未实现过的理念来追求的。柏拉图并没能给人们一个现实的哲学王的范例,他要告诉世人的只是一个关于正义城邦的理念,甚至他自己也认为“这种城邦在地球上是找不到的”,“或许天上建有它的一个原型”[3]386。他论述的真正意义只是在于其所表达的美好的政治愿望和深刻的政治哲学思想。因而后来的西方人把哲学王作为一个目标来追求,把希望寄托于未来;而后来的中国人则把圣王作为一种经验来学习和效仿,这恐怕也是中国人喜欢溯古,而西方人更乐意瞻后的原由之一。当然今天许多学人以“乌托邦”或“空想”来评判柏拉图的这一思想,或者认为哲学王就是柏拉图本人,这些都是有失偏颇的。正如柏拉图洞穴之喻中象征至善的“太阳”,尽管在一般人眼里哲学王并不是一个现实存在,但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它可以使人们在理性思考中获得提升,因而它对于现实政治的意义也是不可忽视的。
[1]柴华.中国文化典籍精华[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2]荀况.荀子[M].王学典,编译.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
[3]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5]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M].李天然,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
[6]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41.
[7]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49.
[8]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韩震,等,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1:181.
[9]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8.
[10]李浴华.《论语》《大学》《中庸》[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9.
[11]朱祖延.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诵读[M].武汉:崇文书局,2004:117.
[12]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M].北京:三联书店,200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