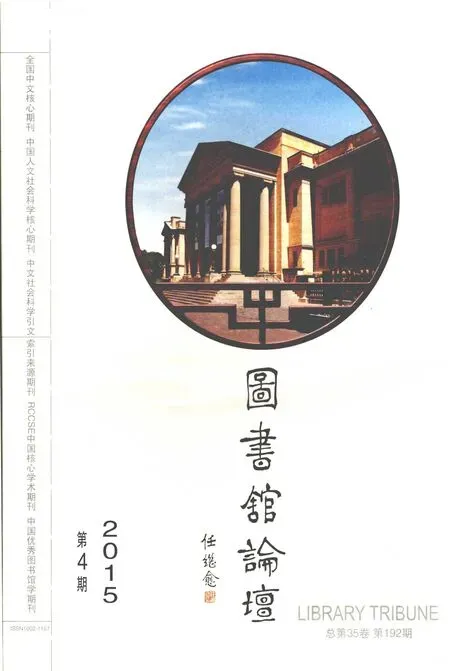张舜徽先生学术思想对图书馆学的影响*
王余光,钱 昆
0 引言
张舜徽(1911.8.24-1992.11.27),湖南沅江人,出生于书香之家,自学成才,治学广博,在文史哲领域均有创见,尤以文献学研究见长,代表作有《广校雠略》《中国文献学》《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汉书艺文志通释》《中国古代史籍举要》等[1]。
在现有学科体系中,文献学与图书馆学有着紧密的联系,文献学亦是图书馆学专业的重要课程,因此张先生的学术思想与治学轨迹难免与图书馆、图书馆学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张先生在自学与治学的漫长岁月里,与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不仅早年自学得益于图书馆,在他后来治学的几十年里,也无处不利用图书馆,因而他熟悉了解图书馆,关心图书馆的建设发展,并身体力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图书馆的工作。”[2]张先生的藏书在其去世后送藏湖南图书馆。1947年张先生致刘国钧先生的一封信中可略见其与图书馆学人的学术交流与互动:“衡如先生左右,昨接清谈,弥钦通核。承索拙著《广校雠略》。兹奉上一本,敬求教正。”[3]
张舜徽先生的学术思想对图书馆学的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 治书之学
文献是记录知识的一切载体,广义的图书等同于文献。对图书与图书馆史的研究历来是图书馆学研究的重点。张先生在文献学研究过程中对书籍制度和古书的散亡(即“书厄”)等问题颇有研究,形成独到的治书之学。张先生的治书之学发轫于1945年出版的《广校雠略》,而在1982年出版的《中国文献学》中得到进一步完善。
《广校雠略》共5卷100篇。卷一讨论校雠学及相关名称,20世纪初期普遍被人接受的名称是“校雠学”而非“文献学”。从校雠学讨论范围看,有狭、广之分,狭义的校雠学即今日所说的校勘学;广义的校雠学即今日所说的文献学。20世纪出版的校雠学著作几乎都是广义的校雠学,张先生在《广校雠略》中主张的也是广义的校雠学。20世纪后期校雠学被文献学取代。卷二讨论古代书籍流传问题,主要包括著述体例、著述标题、关于作者、称引体例、序书体例和注书流别。卷三讨论古代书籍流传问题,包括简纸与书籍的篇卷以及书籍之散亡。卷四讨论校雠学的各种方法,如目录、分类、校勘、辨伪、辑佚。卷五讨论汉唐宋清学术成就,重点放在校雠学方面,如辨章学术始于太史公、郑玄注群经[4]。
《中国文献学》 共12编。第1-2编沿袭《广校雠略》卷一、卷二体例,讨论文献学的范围与任务、古代文献的散亡和编述体例等;第3-5编依次阐述古代文献整理的三项主要工作,即版本、校勘和目录;第7-10编阐述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丰硕成果、业绩和贡献等;第11编指明今后整理文献的重要工作;第12编重申整理文献的主要目的和重大任务[5]。
此二书皆体现了张先生在治书之学方面的会通思想。他在《广校雠略》中说:“近世学者于审定书籍,约分三途:奉正史艺文、经籍志及私家簿录数部,号为目录之学;强记宋、元行格,断断于刻印早晚,号为板本之学;罗致副本,汲汲于考订文字异同,号校勘之学。然揆之古初,实不然也。盖三者俱校雠之事,必相辅为用,其效始著。否则析之愈精,逃之愈巧,亦无贵乎斯役矣。”[6]他在《中国文献学》中进一步总结章学诚的见解:“古人只有校雠之学,别无所谓目录之学。”[7]该观点虽非张先生首创,然张先生始终坚持这一观点,引起图书馆界对此问题的争论。
2 目录之学
张先生治学讲求“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因此极其重视“提要”与“别录”文献研究方法,有《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两部力作问世。张先生亦重视注释实践工作,继《说文解字约注》,更在晚年完成《汉书艺文志通释》这部力作,对文献学研究贡献巨大,尤其在目录学研究领域。由于图书馆学界普遍认为目录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也是图书馆学的必修课程,所以张先生在目录学领域对图书馆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鸿篇巨制的学术著作里,更表现在学术观点对图书馆学人的影响,这种影响当然也包括某种观点引起的争论。
张先生本着郑樵、章学诚的观点,强调目录、版本、校勘皆校雠之事,校雠学之外,不应另有目录学。关于目录学的名实争论由来已久,在张先生继郑樵、章学诚二人之后再次重申这一观点时,引发图书馆界更为激烈的争论。比如,彭斐章、谢灼华两位先生在探讨目录学研究对象时,指出持“否定说”的人认为:“目录、版本、校勘三者是校雠学的组成部分,目录不能自成为学科,但举校雠足以包举无遗。这并非什么新观点,早在清代,章学诚就不承认有目录学,而欲以校雠学包举之。从那时起直到今天,还有人不断地否定目录学的独立存在,这种观点既不符合现代科学的发展,又不能反映目录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文化科学的进步,以及知识的不断分化,从而导致目录学与版本学、校雠学划分了界限。它们各自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分别发展成独立的学科。这也是人类对于客观世界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8]
董慧敏认为校雠学与目录学“这二者之间虽然还有某种必要联系,但作为两门学科,其性质、研究对象及任务不能混淆”[9]。柯平在对张先生否定目录学的观点提出质疑时,进一步总结校雠学与目录学之争主要有三派观点:一是否定目录学的存在,用校雠学包举目录学;二是认为校雠学即目录学,用校雠目录学之名替换;三是目录学与校雠学是两个独立学科。柯平认为章学诚、杜定友、张先生同属一派,观点都是用校雠学包举目录学,而今仔细推敲,这样归纳未必妥当。他进一步强调,现在目录学与校雠学是两门独立的学科,古典目录学是文献学的组成部分,而现代目录学则冲出了文史目录学、校雠目录学、版本目录学的范围,内容更丰富,并日趋走向新的时代,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点[10]。柯平说:“三十年代著作中否认目录学,五十年代著作中承认目录学,七十年代文章中又否认目录之学。前后矛盾,使人难得其解。”[11]
其实这是误解,张先生在著作中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正如李勤合所说:“张先生有时著书论文之所以用“目录学”之名,多因涉及之人自称目录学家,而求行文方便,非真骑墙之论也。”[12]
当然,也有人支持张先生的观点。比如,李华斌、鲁毅认为:“从张氏《广校雠略》《中国文献学》等来看,不承认目录学、反对单立目录学的观点可能有些偏激,与主流看法不合,难被学者接受……但籀绎其理,则发现其确立的为会通的校雠学……会通的校雠学作为一种代表的学术观点,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步被学术界理解、认可和接受,例如程千帆、徐有富编写《校雠广义》,分版本、校勘、目录、典藏四篇,继续沿用广义校雠学的概念。”[13]
李勤合指出:“张舜徽于1945年提出用校雠学包举目录、板本、校勘,而否定目录学的意见。这是由他通人之学、反对狭隘、由博返约的学术风格决定的。”[14]他进一步指出:“对于学者之观点论说,不能简单地仅从逻辑上去判断,还须从学者所处之环境、人生之经历、为学之风格考量,这是从孟夫子‘知人论世’说到近代陈寅恪‘了解之同情’说传下来的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可惜,学界在批评张舜徽先生有关目录学的观点时,少有从此入手者。”[15]这是对张先生目录之学最好的注解。结合张先生所处环境、人生经历以及为学风格,可以进一步理解张先生的文献学观,从而理解他的目录之学。
3 阅读指导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先生给学生开书目的传统,以达到指导后生治学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图书馆学界,不管是对目录学的理论研究,还是对阅读推广工作的实践研究,阅读指导一直是研究重点,尤其在经典阅读方面,张先生的阅读指导思想亦可为今日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工作和目录学理论研究提供借鉴。
张先生自1941年起,先后在湖南国立师范学院、北平民国大学、兰州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校任教,博览群书,走通博之路,对小学、经学、史学、文献学都有精深研究,因此张先生的阅读指导主要以继承传统学术、经典阅读为核心内容,而研究并继承传统学术的前提是通识古文字。张先生强调:“阅读旧籍,必识古字古义。士而有志习本国文史,则日接于目者,皆古书也。苟不识其文字,何其通其语义,故读书必以识字为先。”[16]为此,1947年张先生在兰州任教期间,曾给学生开列了《初学求书简目》。张先生认为:“读书以识字为先,学文以多读为本。必于二者深造有得,而后可以理解群书。”[17]意即通识古文字是读书的基础,通而不读始终会立于学术之门外,因此,识字必须与读书相联系,并以读书为归宿。他在《初学求书简目》中首列“识字”“读文”两类,其中“识字”类下细分为字形、字音、字义三小类,字形类开列的书目包括《文字蒙求》《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注》等8种,字音类开列的书目包括《广韵》《说音》《切韵考》等8种,字义类开列的书目包括《尔雅义疏》《广雅疏证》《释大》等6种。凡此20余种,作为识字的入门书,以为阅读旧籍的基础。在21世纪的今天,大学生阅读不再以识字为先,一些大学生阅读书目中不再收录《说文解字》,但笔者认为在研习传统学术、阅读古代经典文献方面,张先生在“识字”方面开列的书目仍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除列“识字”类外,张先生另在“读文”类收录选本三种,包括《古文辞类纂》《续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在“识字”和“读文”之后,又列经传、史籍、百家言、诗文集、综合论述五类,其中经传类包括《诗》《尚书》《左传》《国语》《论语》《孟子》等19种;史籍类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文献通考》等32种;百家言类包括《管子》《老子》《庄子》《墨子》《孙子》《荀子》等24种;诗文集类包括《楚辞》《文选》《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杜工部集》《白氏长庆集》《欧阳文忠集》等19种;综合论述类包括《梦溪笔谈》《容斋五笔》 《日知录》《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31种。所录各书,张先生皆作版本或作者提示,或作书中提要,或品评得失,有利于初学。
张先生在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讲授过《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1983年主持编撰《中国史学名著题解》,再次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走博通之路,方能“由浅入深,自近及远,有自得之乐”[18]。
4 结语
张舜徽先生治学走博通之路,成就斐然,在治书之学、目录之学和阅读指导三个方面对图书馆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笔者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图书馆学史”也体现了“会通”的思想,这也是张先生对笔者潜移默化的影响。
[1][5][7]张舜徽.中国文献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 刘雪莱.张舜徽先生与图书馆[J].图书馆,1993(3):51-53,39.
[3] 王余光.张舜徽致刘国钧的一封信[J].图书与情报,2011(6):136-137.
[4] 王余光.张舜徽先生的文献学成就[J].图书与情报,2002(4):15-19.
[6] 张舜徽.广校雠略:汉书艺文志通释[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7.
[8] 彭斐章,谢灼华.目录学文献学论文选[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2-3.
[9] 董慧敏.从古今校雠学与目录学的分合看目录学独立之可成立性——兼与张舜徽同志商榷[J].图书馆建设,1982(S2):267-271.
[10][11]柯平.目录学札记——校雠学与目录学[J].赣图通讯,1986(1):23-24.
[12][14][15]李勤合.张舜徽目录观发微[J].九江学院学报,2007(5):123-125.
[13]李华斌,鲁毅.张舜徽会通校雠学发微[J].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9(1):17-20.
[16][17][18]王余光.文献学与文献学家[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122-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