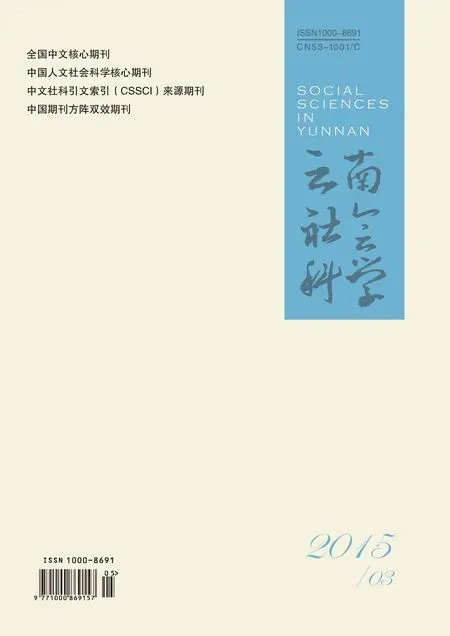定义、对象与案例:环境史基础问题再探讨
环境史作为一门兼具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的历史学新兴分支学科,受到了学术界及现实社会的极大关注。因其研究对象与内涵、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研究范式均迥异于传统史学,对其定义、研究对象等基础问题的探讨就长期处于争议但依旧模糊、混乱的状态中,这与学科蓬勃发展的态势及其学术、现实使命的需求极不相符。重新思考及厘定环境史的定义及研究对象,对进一步推动学科的发展及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明义彰远:环境史研究定义与对象的再思考
环境史定义及研究对象的准确界定是个长期困扰着环境史学者的主要问题,学界的观点纷繁复杂,很难统一。美国著名环境史学者唐纳德·沃斯特认为,“在环境史领域,有多少学者就有多少环境史的定义”①包茂红:《解释中国历史的新思维:环境史》,《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3期。。事实确实如此。西方学者从不同学科及视角出发作出了类型及内涵各异的界定,部分观点经侯文惠、包茂宏、梅雪芹、高国荣、雷洪德等学者翻译介绍到中国,对中国环境史学的产生及理论思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中国环境史研究起步阶段重要的理论源泉。但历史及文化、制度及思想差异极大的中国与西方,在具体问题及其内涵的思考上存在着极大的不同,环境史定义及其研究对象的界定就是较突出的实例。
1.确立环境史定义及研究对象应注意的问题
综观中西方学者的界定,其差异极大、表述不一,但从其核心主旨看,多认为环境史是一门研究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研究自然发展史及人类的干扰作用的学科,主要探讨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影响及自然对人类社会反作用的历史。即在关注人与自然这两个中心点相互制约、影响的同时,虽然强调自然的作用及变迁,但多是站在本位立场上,不自觉地将自然与人并列并作为两个独立的主体进行考量。虽然也有学者从自然科学视角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但也只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扩展及延伸。学界对环境史研究对象及定义的各种解读及阐释,与环境史本身所具有的内涵还有很多差距,存在着极大的补充、完善及拓展的空间。作为正在蓬勃发展,属性及内涵、外延不断调整但逐渐在发展中明确的学科,其定义及研究对象的界定亟需明确,使其主旨内容与表述更加贴合。这就应当注意以下四个层面的问题。
首先,应该厘清自然界整体与个体的关系,彻底摒弃不自觉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人与自然的关系无疑是环境史研究的核心,但这两个核心体只是地球进化及环境发展的整体史上的阶段性部分,人也只是自然界中的一个组成要素,只因其社会化及文明程度较高位居生物界顶端,在某些历史阶段被认为是自然的主人。但人类并非自然界的主体及核心,作为整体的自然和作为自然界个体之一的人的关系,是整体和作为组成部分的个体的关系。
目前的环境史定义将人与自然作为并列的独立个体看待,研究二者相互影响、制约等关系的论点显然是有局限性的,实质上依然停留在不自觉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层面上。即便要研究二者的关系,也应该是从研究自然这个整体中不同物类、不同要素及系统相互影响、制约的关系出发,看到人与自然整体中其他物种、类群及要素的相互关系只是自然界不同要素相互关系中很小的一部分,远未囊括自然界的全部组成要素及关系。因为自然界还有很多人力及人类认知所不及的领域及层面,也有很多与人类尚未发生关系的部分,很多已知或未知部分之间也存在不同的制约及影响关系。
因此,确定环境史的定义及研究对象,应该摆对人类的位置,真正把人作为自然界的个体、组成部分来思考,看到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只是环境史一个侧面的事实。环境史包含的内容远远突破了人与自然关系史这个简单的范畴,其研究对象应该是自然界这个大整体中单个的个体及群体、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独立存在、发展及相互依赖、影响的历史。
其次,正确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摆脱自然中心论的影响。环境史近年来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误区,即看重自然某些因素的变迁及其人为动因而一味指责人类及其活动,甚至认为人的存在及其活动都构成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这种思考视角无疑陷入了自然中心主义的泥沼,将人类置于自然环境的对立面,不自觉地认为二者是你存我亡、我存你伤的关系。这种非此即彼的观念导致了错误的认知结果,即要保持自然环境的良好及发展,人类就不能有任何的活动及开发,这无疑剥夺了人类作为自然界组成部分的生存发展权,也剥夺了其在环境中应有的生态位。
人既然是自然生物中的一个组成要素,与其他要素的关系就是自然界众多关系中的一个或几个侧面,与其他生物、非生物要素就是平等、并列的关系。这类关系必然存在良性或破坏性的一面,但不能因为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一些要素造成的破坏性影响而否定其存在价值。因此,环境史不仅要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桎梏,更要摆脱自然中心主义的束缚,学科定义及其研究结论才能更趋全面、客观和理性。只有将人类作为一种生物个体,通过自身努力,调适、改良生存及发展模式,改变自身生态位的作用方式及其效果,利用人类的科技及能动性,降低对其他环境因素的不良影响,与其他环境要素平等、协调发展,使环境史的发展方向日益向着对自然环境中每个要素都有利的良性方向进展,其定义的客观性才会凸显出来。
再次,应该重新思考及界定环境的内涵及其组成要素。地球生物及非生物都在环境发展变迁史上扮演了重要且不能缺失的角色,那么,除了动物、植物及微生物等生物与人类关系存在历时性的发展及变迁是环境史研究的内容外,生物个体、群体的发展史及其相互影响的关系史,也应当是环境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内容。除此以外,大气、水、阳光、岩石、土壤、气候等非生物也是重要的环境组成要素,其对包含人类在内的生物存在、发展的作用也不能小觑,其各个体及群体不仅有其发展、变迁的历史,也有相互依赖及影响的关系史,还与人类及其他生物存在着无我即无他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史,这无疑是环境变迁史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的内容。没有非生物要素,人类及其他生物都不可能存在发展,遑论环境的历史?因此,非生物要素的发展史及其相互关系史、与生物的关系史,应该成为环境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因而,环境史不仅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密切相联,也与自然环境其他要素的存在、变迁及其关系史状况密切相关,一部客观及完整意义上的环境史,应该是自然界各要素产生、发展、变迁及其相互影响、促动而共同谱写的历史,其定义及研究对象也应从非生物、生物各要素存在及其相互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这个视角进行界定。
第四,既要具有区域性的思维,更要具有全球的视野及胸怀。环境史不仅具有区域性,也具有国家、民族及全球性的整体性。因此,环境史既具有整体史的共性,也具有区域史的个性,其定义及研究对象从理论上说,应该具有广义、狭义之分。作为学科发展的基础性命题,环境史学者探索广义、狭义层面上的环境史定义的责任及义务尤显重大。
广义的环境史是宏观的、整体的,具有普遍性、广泛性的特点,即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生态系统等的发展变迁在一定层面、一些要素上具有共性。任何国家、地区的环境史,不可能独立于世界、全球环境史之外,而是全球环境整体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环境史定义的界定,应具有全球的视野及胸怀,关注到全球环境共性、普遍性的内容。
狭义的环境史是微观的、区域的,个性特点突出,在具有普遍性特点的基础上,应凸显各地自然要素及环境状况的的差异性及多样性。目前,很多学者在中国环境史的定义及研究对象研究上做了积极有益的探索。而在西方环境史学及语境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早期中国环境史学,对环境及其历史的思考及界定带有西方史学及现实的浓重色彩,并不完全适用于自然及社会历史发展途径迥异的中国。其他国家及地区套用其定义及理论后,也出现了同样的不适用性,这是各国本土环境史研究兴起的原因之一。中国的地理位置、土壤、气候、水域、生物种类及其生态系统都有其独特之处,人类作为生物个体的起源及发展史也独具特点,与欧美国家的历史发展、社会文化、思想意识、政治制度、民族、宗教等均有极大差异,欧美环境史学者的定义及研究对象是全球环境史定义界定及研究的重要基础,不是唯一标准,只是环境史狭义定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确了环境史定义及研究对象界定时应注意的问题后,其具体内容已可呼之欲出了。
2.环境史研究对象及定义的新思考
环境史学界积累了很多对此进行探讨的前期思考及研究成果,虽然大部分论述及阐释多集中在人与自然关系史的范畴内,但也有很多研究涉及到自然史的范畴①详见包茂宏:《环境史学的起源与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王利华:《徘徊在人与自然之间——中国生态环境史探索》,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田丰、李旭明等主编:《环境史: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叙述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尽管其对自然史的表述还较为模糊、笼统甚至偏重生物史层面,但却对环境史定义及研究对象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以梅雪芹的阐述最全面、深入,他认为环境史是以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发展、变迁为基本研究对象,构建人与自然、自然史与社会历史相关联的历史叙述的新模式,包括三类:一是“自然的历史”,侧重于研究自然环境自身的演变过程;二是“社会的历史”,将环境视为人类活动的背景与可资利用的资源;三是“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历史”,致力于以自然环境、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结合的宏观视野,研究人及其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程。②梅雪芹:《从环境的历史到环境史——关于环境史研究的一种认识》,《学术研究》2006年第9期;《环境史研究叙论》,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1年。
但一些即便涉及自然史的相关讨论中,关注的自然多是生物,以生物发展演变的历史涵盖了自然界其他要素的发展演变史,忽视了非生物环境的历史,也忽视了非生物环境的基础性作用尤其是其无时无刻不对生物界各要素发挥影响的历史。因此,环境史的研究对象及定义应进行必要的拓展、修改及完善,应包含以下三个既独立但不能割裂且彼此联系的内容。
一是自然史层面的环境史,包括自然环境各要素暨各个体及群落、各类群本身发展、变迁及其相互影响的历史。自然环境要素既包括动植物、微生物等生物要素,也包括地球及环地球生物存在的各类非生物要素存在、发展、变迁及其相互影响的历史,更包括生物及非生物要素相互影响的历史。
换言之,自然环境史研究对象有三个层面的内涵:研究非生物如常见的水、岩石、土壤、大气及气候、地质地貌、宇宙星系等非生物要素、类群发展变迁及其相互影响的历史;研究不同类型及区系的动物、植物、微生物等各生物要素、群落,以及不同生态链、食物链、生态系统发展变迁及其相互影响的历史;研究生物界与非生物界两大自然系统相互影响、作用、发展变迁的历史。这是环境史最基础的内涵及组成部分,是其研究对象中内容最丰富、庞杂的部分,也是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及成果最多、难度最大、最难驾驭及把握的部分。
二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史,包括环境的改造史和重构史。这个层面的环境史,就是国内外大部分学者从不同视角给予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定义的主要内涵。主要研究自然界中的非生物要素及类群以及生物要素及其群落、系统,与兼具自然特殊生物属性及社会属性的人类个体、群体及其社会相互影响、促变的历史。换言之,人与自然的关系史既包含自然界各要素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制约及影响,以及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冲击、破坏、恢复与重建的斗争史,也包含自然界与人类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和谐史。
从实质上说,这个部分也应该属于自然史的范畴,因为人是自然界的生物之一。但人作为特殊的生物个体,是生物界最具竞争力的种群,成为最具主导作用的动物,在与其他生物的竞争中逐渐弱化了自然属性,强化了社会属性并对自然界产生了日益强大的影响、冲击乃至破坏作用。近代化之前,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及作用大于人对环境的影响;近代化后,人类插上了科技的翅膀,在制度、文化及经济发展的促进下,迫使非生物界的很多构成要素及其类群、系统发生了从量到质的巨变,生物个体及其种群、生态系统不断突变乃至灭绝,自然环境的构成、发展方向随之改变并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这成为自然中心主义产生的根源。对人类而言,这个层面的环境史内容最为丰富、生动,传承及记载也最多,在以人类为主导的研究及书写语境中,可以独成一域。
环境及其要素、类群与系统的重构,是人类社会科技及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活动导致自然环境变迁后果的综合结果。这类人为重塑或按人的引导进行的环境重构现象贯穿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其数量、分布范围不断增加及扩大,逐渐形成了一些既具自然属性又有人为特性的另类生态系统。如历代进行的人工植树或造林、近现代出于经济或其他目的改造或铲除原有生态系统,引进非本土的物种并建构新生态系统等,这对自然界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导致本土生态的灾难,成为人与自然关系史中不可忽视的内容。
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互影响、作用的历史是个动态、复杂的过程,各时期、各地区环境变迁的路径、方式及特点千差万别,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史成为环境史研究中最具魅力的部分。
三是环境变迁的因果史及规律史,这是被赋予当代属性及未来意义的环境史。这个层面的环境史及其内容,在严格的意义上虽然可以并入上面两个部分的内容中,但环境史学科的现实属性及未来使命使其研究显得极为重要。如若附属到上述相应的内容中,其重要性、专门性及系统性得不到应有凸显,研究的深入性也会受到限制。因此,环境变迁的动因、特点(规律)、影响(后果)及其对自然界其他因素反作用的历史,就成为环境史研究对象中需要独立出来并使其富有自然及人文色彩的重要内容。
无论何时何地的环境变迁,有其深刻动因,既具单一性又具多元性,有时是单因引发多因、有时是多因归于单因。探究不同类型的动因,寻求其间的规律性及其经验教训,在历史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循环发展特点的背景下,充分发挥对现实的巨大资鉴作用。
任何环境变迁都会引发不同的结果,进而引发自然界(人类及生物界、非生物界)更深刻的变迁,进而引发自然界其他可预知或不可预知的变化。人类及其他生物要更好地在非生物、生物环境的支持下持续生存、发展,就要深入、系统地探讨环境变迁的趋势、特点及规律,探究环境变迁的各类后果,适时总结人类在不同区域、时间段上适应环境变迁的经验教训,总结其他生物及非生物要素适应环境变化而发展变迁的规律及特点,进一步揭示表象背后的因果关系。从历史的趋势及特点中预见未来,不断修正人类发展的模式、矫正人类与环境各要素发生关系的方式,减少甚至避免环境灾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持续发展。这正是环境史最具现实及未来意义的内涵。
在此基础上,广义、宏观层面上的环境史定义可表述为:环境史是一门研究自然界非生物及生物各要素产生、发展、变迁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重点关注人与自然界各生物及非生物要素相互依赖、影响与塑造的关系及其变迁史,以探究自然界及其环境状态发展变迁的动因、特点、规律及其后果的历史学分支学科。
狭义、具体层面上的环境史定义,应根据不同区域的地理位置、生物类型、非生物构成等要素进行界定,具有鲜明的地理区位尤其是海陆位置、气候带及生物分布的影响等特点。对中国环境史而言,主要是研究中国境内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等不同气候带环境中的河流、湖泊、海洋、大气、岩石、土壤、矿藏等非生物,以及陆生生物及环太平洋区域的海洋生物各个体、类群、系统等产生、发展、变迁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探究中国境内各环境要素及其类群、系统变迁的自然与人为原因、变迁规律、特点及其对人类社会及自然界的影响与后果,总结其间的经验教训,为中国环境的保护、恢复、重建及其良性、持续发展,为现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资鉴。
二、从传统到现代:环境史视域中“灾害”定义的新诠释
明晰了环境史的研究对象及定义,再审视传统学科中相关学科的相关定义,其内涵及表述就有了完善及修改的必要性。一些传统学科及其专有名词的定义应该随时代的发展及其内涵的拓展,进行相应完善并推陈出新,以使其在通俗及学术层面更能涵盖其客观含义,适应学科的新发展。与环境变迁关系密切的灾害、灾荒定义就是典型的例子。
1.灾害、灾荒的传统定义
传统“灾害”与“灾荒”的定义以人类为影响主体,“害”或“荒”的承载体都以人为核心,充斥着不自觉的浓厚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随着生态及环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作用及价值的凸显,灾害、灾荒的传统概念逐渐凸显出单一性及狭隘性,其实际内涵的改变使定义名实不符。
灾害的传统定义是针对人类而言的祸害,是指人力不可抗拒、难以控制地给人类造成众多伤亡及大量财产损失等祸事和危害的自然或人为事件,是天灾人祸导致的对人类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害。①灾害的传统定义各不相同,此定义乃综合各学者的相关阐述而成。故“地球上的自然异变对人类的负面影响超过一定程度时被称为灾害”②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中国自然灾害灾情分析与减灾对策》,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VII页。的定义,得到了传统学界及世俗的认同及沿用。
一些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了相似的界定。李永善认为人类最初把各类交换过程给群体或个人带来的伤亡和损失称为灾害,专指对人类与社会、国家与民族、地区与单位、家庭与个人的伤亡与损失而言,离开人类将无灾害可言;③李永善:《灾害系统与灾害学探讨》,《灾害学》1986年第1期。李英奎、倪晋仁及申曙光等均认为,灾害是指自然发生的或人为产生的对人类和人类社会产生危害性后果的事件。④李英奎、倪晋仁:《泥沙灾害与泥沙灾害链的分类分级》,《自然灾害学报》2005年第1期;申曙光、黄小舟《灾害与社会及社会发展》,《社会科学研究》1993年第6期。美国灾害社会科学先行者Fritz的定义影响较大,他认为灾害是对社会或社会其他分支造成威胁与实质损失,造成社会结构失序、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支持系统的功能中断的具有时空特征的事件;⑤陶鹏、童星:《灾害概念的再认识——兼论灾害社会科学研究流派及整合趋势》,《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2年第2期。汤爱平等认为灾害最主要和普遍的特点是给人类带来损失,给人类社会内部组织带来破坏或使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功能失效;⑥汤爱平、等:《自然灾害的概念、等级》,《自然灾害学报》1999年第3期。陈玉琼、黄崇福的定义也类似。
灾荒的传统定义也以人为承载体,是指自然灾害造成的饥馑等对人带来的损害,多指荒年。荒乃形声字,从“艹”从“巟”,表示长满野草的沼泽地,指田地无人耕种而荒芜,引申指收成不好,“四谷不升谓之荒”。《管子·五辅》曰:“天时不祥,则有水旱;地道不宜,则有饥馑;人道不顺,则有祸乱。”从这一层面而言,灾荒即“因灾而荒”,灾害使人食不果腹、居无定所,是谓“灾荒”。学界的定义大致类似,邓云特认为,灾荒是以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之失调为基调,引起人对自然条件控制失败所招致的物质生活上之损害与破坏;⑦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5页。夏明方认为灾荒是灾与荒的合称,灾即灾害,荒即饥荒,是天灾人祸后因物质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短缺造成的疾疫流行、人口死亡逃亡、生产停滞衰退、社会动荡不宁等社会现象;⑧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5页;李亚光《战国时期荒政的特征》,《淮海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3期。孙语圣、徐元德认为,灾荒总是与人类的生产生活相联系,使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时刻面临着威胁;⑨孙语圣、徐元德:《中国近代灾荒史理论探析》,《灾害学》2011年第2期。张建民、祁磊等均认为灾是指任何一种超出社会正常承受能力、作用于人类生态的破坏,荒指饥荒,主要是对人造成伤害;⑩张建民、宋俭:《灾害历史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祁磊:《〈周礼〉”灾荒”概念释义》,《社会科学》2011年第11期。孟昭华认为,灾是自然破坏力给人类社会生活或生产造成的祸害,荒是由自然灾害而致的土地荒芜与谷蔬瓜果失收减收的民不聊生状态⑪孟昭华:《中国灾荒史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页、第14页。;陆永昌认为,灾是指自然界的破坏力对人类社会造成的损害,荒是灾的延续,给人类带来生产、生活困难。在此不一一枚举。
2.灾害与灾荒内涵在生态及环境层面的拓展
因学科、文化背景、研究取向、定义方式等存在的差异,灾害、灾荒定义及具体解释虽各有不同,但都把因灾而致的害、荒与人类社会必然地联系到了一起。但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密切及自然对人类社会影响及其自身作用的凸显,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人与生物界、非生物界的关联性正从不同侧面凸显,对人类为承载主体的灾害、灾荒的传统定义及内涵产生疑问,并引发相关思考就成为必然,即灾害、灾荒的主体和承载体难道还应该只局限于人类吗?显然,灾害、灾荒发生后,受影响、冲击及破坏的主体绝不仅仅只有人!
因此,部分学者以灾害定义的诠释和辨析为目的展开论述,力图在灾害、灾荒的界定上有所突破及创新。如陶鹏、童星以“危险源—关系链—结果”为逻辑架构结构化灾害概念,①陶鹏、童星:《灾害概念的再认识——兼论灾害社会科学研究流派及整合趋势》,《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2年第2期。李永祥对灾害定义所经历的曲折发展过程进行了论述,②李永祥:《什么是灾害?——灾害的人类学研究核心概念辨析定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1年第11期。最终虽未给出明确定义,却反映出传统灾害、灾荒定义已显示出了其不适合时代发展及其内涵逐渐扩大的特质。
由于环境作用的凸显,与时俱进的网络对灾害、灾荒的定义进行了拓展,百度及维基百科将灾的影响主体延伸到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灾害是指给人类和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造成破坏性影响的事物总称”。部分学者也做了类似的、看起来较全面的定义,孙语圣、徐元德认为,灾荒是由于自然变异、人为因素或自然变异与人为因素相结合的原因引发的对人类生命和财产及人类生存发展环境造成破坏损失的现象;③孙语圣、徐元德:《中国近代灾荒史理论探析》,《灾害学》2011年第2期。李永善认为给人们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事件是狭义层面的灾害,广义层面的灾害是一切对人类繁衍生息的生态环境、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与发展,尤其是生命财产等造成或带来较大(甚至灭绝性)危害的天然和社会事件。④李永善:《灾害系统与灾害学探讨》,《灾害学》1986年第1期。
但很多观点常常是混合的,且“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是个宽泛的概念,其涵盖范围是有限的,没有脱离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很多灾害影响的主体,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要素外,还有与人类过去或目前的生存不一定有密切联系、在未来是否发生联系或联系时间尚未可知的要素,即灾害绝对会冲击、影响到那些与人类无直接、必然联系的环境要素。故灾害、灾荒的定义就有了重新界定的必要。
3.灾害、灾荒的新定义及当代学术价值
在人类对环境的改造作用加大、自然对人类生存发展的限制作用日益明显的现当代,灾害、灾荒定义的外延或内涵,都应该在传统基础上拓展及深化。尤其是近现代世界范围内影响巨大的各类灾害,使环境灾害(灾难)、生态灾害(灾难)等概念日渐深入人心,生态、环境因子及生物、非生物要素的致灾及受灾性能更加显而易见。将自然环境中能受到灾害冲击的一切生物及非生物个体(无论是否与人类生存发展有关)都纳入考量范畴,就成为新时期灾害、灾荒定义最基本的前提。作为事件或现象的定义,以简单明了、不琐碎繁复为要旨。
笔者认为,“灾害”是指给人类及其他生物、非生物体个体及其环境,以及各类个体构成的组织或繁殖、发展系统造成破坏性影响,或导致悲剧性后果的自然或人为事件;“灾荒”是指给人类及灾害环境内各生物、非生物要素及维持这些要素生存及持续发展的机制造成破坏、损害,导致其在数量与质量上发生改变并带来悲剧性影响的现象。
灾害及灾荒除了对人及其社会造成影响外,还影响到自然界里的每个生物个体。此外,地球上还有众多的非生物,并在事实上与人类及其他生物的生存及发展有着(或将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密切联系,无数的非生物个体在灾害中也会受到冲击及破坏,在质与量上都会蒙受极大损失。故灾害影响及冲击的主体包括人及动植物、微生物等生物和非生物要素及其系统。
与传统定义相比较,新定义有3个特点:一是在致灾原因及后果上对传统定义的继承。即致灾原因依然是有自然及人为的层面,任何灾都能带来破坏性及悲剧性后果。二是对传统定义的延伸,即对灾害、灾荒影响要素的范围作了扩展,影响主体由原先单纯的“人”及稍宽泛但还是凸显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的“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扩大到了灾害及灾荒区域内整个的环境要素及各要素存在、发展及繁殖的系统,其中不仅包括人,各类动植物、微生物等生物体及其系统,还包括各类可用或暂不可用(未来也不一定可用)的固体、气体、液体等非生物体及其系统。三是对传统定义的深化,传统定义只强调灾带来损失、破坏及短期内的损害、危害,新定义则在此基础上凸显灾害环境内各要素、各系统承受的长期及持续性的影响与破坏而致的悲剧性后果。
从这个层面上说,灾害、灾荒定义的革新,将带来学术研究及世俗认知的巨大改变。
首先是学术研究视野、研究范围的拓展及深化。新定义使灾害、灾荒及灾害史、灾荒史乃至环境史的研究视域得到拓展,研究主题更加深化,研究范围从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及精神文明扩大到自然界中的每个要素、类群及其系统,从而促动、丰富其他学科的研究及其发展。
其次,学科交叉将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体现。新定义使学术研究面临新的难度及更高的要求,在灾害、灾荒及其历史的研究中,客观、全面、科学的研究结论的得出,使多学科交叉、跨学科研究不仅成为必须的研究手段,而且必将在更大、更宽的层面上展开学科的交叉及合作,才能避免因研究方法单一、研究内容片面孤立而导致研究结论具有主观性及浅狭性的弊端。而灾荒、灾害研究的新结论,将对其他学科相近领域的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三,世俗认知层面的变革。新定义将使普通民众对灾害及灾荒原因、影响、结果等有更深入的理解,从另一个层面推动民众进行环境保护的自觉性及自律性,推动政府防灾减灾及其政策法规在生物、非生物等环境层面进行有针对性的补充、完善及深化,促进民间防灾救灾组织在未来的实践中,增加一些对生物及非生物环境进行积极的救治及保护的措施。
三、定义探讨及推广之案例——环境史专栏
有关环境史定义及其研究对象的探讨,以及从环境史视域对传统学科名词的重新界定及其内涵的拓展研究,是近年来史学研究中的重要突破及创新。除了研究者个人在相关的论著中涉及外,学界关注环境史研究的突出表现,就是很多刊物创设了“环境史专栏”,集中刊出在观点、视域、研究方法及范式等方面极具创新性的环境史新作,其中大部分论文均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环境史名称的界定及其学科属性等问题的探讨,将环境史定义及研究对象等问题的探讨推向深入,以一种全新的学术表达方式,推进了环境史研究系统、广泛的开展。
1.环境史研究专栏的创设
环境史作为历史学新兴的分支学科,因其研究对象及内涵、研究方法及路径迥异于传统史学,从环境史视角对很多重要历史问题进行的研究及结论,正在改变或改写着历史,很多已成过往、几成定论的历史更趋客观,传统的历史面貌及历史走向在一扇新打开的门里陡然丰富多彩、气象万千起来。在环境危机日益严重、学科分野及交集日益复杂并趋多元化发展的今天,具有了更广泛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这使环境及其历史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成为当今最热门的话题及视点,引领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推动着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决策走向,环境史学科已然形成。在这种局势下,发掘出更贴近现实的环境史研究素材及选题,刊载见解独到、立论精辟的环境史论文,成为国际史学权威学术杂志拓展学术阵营、创新学术品牌、提升栏目品质的标识之一;创办专门性的环境史学术刊物也成为国际学术刊物发展的新态势。
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如火如荼地展开并渐趋繁荣,不同视域、不同区域及时段的环境史论文一如雨后之春笋,欣欣而向荣,有关环境史研究的笔谈、专栏不仅成为学术刊物办刊选材的创新点受到重视,也成为引领研究方向、吸引学术眼球的亮点受到推重。如《中国社会科学报》的“历史学”栏目以简明扼要、新颖独特的选题及史料,以持续性刊文为特点,在环境史栏目研究中脱颖而出,成为慧眼独具、推动及引领环境史研究的阵地。该报自2011年9月1日开始至2014年3月26日共12期的“历史学”专栏里,刊载了一批国内外环境史名家的论文,在发掘、开拓环境史研究的新方向、新领域,推动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及向交叉学科研究方向展开起到显著作用。
与其他环境史专栏类似,该专栏有一批地域广泛的作者群,既有美洲著名的环境史学者唐纳德·沃斯特,R·马立博,欧洲环境史学会主席克里斯托弗·毛赫、简·卡卢瑟斯,也有中国环境史学者如王建革、谢丽、李玉尚、陈业新、朱浒、刘祥学、张箭、戴建兵等从不同视角、领域出发撰写的论文。涵盖了城市化及环境危机、水资源及水环境、环境史的理论与方法、环境意识、气候变化与环境变迁、海洋环境史、民族环境史、粮食作物与水生生物、绿洲-沙漠环境、水利工程与环境变迁、资源控制与区域环境、中国环境变迁史、灾害与环境、环境疾病、非洲环境史、抗生素与环境史研究等当代环境史研究领域最热门的领域、最典型的问题,涉及到6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研究者的观点及思想倡导、引领着世界及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新领域、新方向。如李玉尚《被遗忘的海疆:中国海洋环境史研究》以简明扼要的笔法,在更大程度及层面上介绍了中国环境史的新领域——海洋环境史研究的价值及意义,在中国海洋环境史研究中无疑起到积极的倡始、推介之功。
二是老题新做而出现的具有新意、深意的成果。如陈业新《中国环境史中的儒家生态意识》、孙群郎《技术进步、大都市区蔓延与环境危机》、朱浒《小冰期降临:1791-1850年中国环境恶化趋势与应对》、张箭《甘薯的世界传播史》等,从环境史的视角阐述了儒家文化、城市化、气候史的另一侧面,展现了环境及生态在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特点。
三是从环境变迁史视角展现社会最关注的现实问题,如水资源、水环境、灌溉方式等的变迁。如王建革《人水关系:古代江南水生植物历史变迁》、谢丽《以水为中心的人地关系:塔里木盆地南缘绿洲文明探微》等文,展现了自江南水乡到西北绿洲生态的变迁节点及不同区域水生环境的变迁表现及变迁趋向。
四是从灾害、疾病及其治疗等视角论述环境变迁的结果及其特殊表现方式,以及抗生素使用引发对人体环境及宏观环境的关注等,如戴建兵《逝彼百泉:近代华北的凿泉灌溉业》、施雱《抗生素引发的新环境史研究》、张箭《被“疟疾”改写的人类历史》等。
五是探讨了民俗形成的环境因素,如刘祥学《瑶族社会历史上男女平等现象的环境根源》、彭丽华《葬之以礼:环境、伦理与古代丧葬》等,把环境史研究的触角扩展到了社会风俗层面。
六是欧美环境史学家对环境史理论及方法的探讨,其中涉及到了对中国环境史研究路径的倡导。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生态史观》、克里斯托弗·毛赫《人与自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马立博《从史前到现代:讲述中国环境故事》、简·卡卢瑟斯《南非历史上的环境不公与资源控制》等成果,是在作者早期研究基础上,对环境史研究方法、现实意义及其资鉴作用的阐述,对中国环境史研究的理论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2.环境史研究专栏的展望
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生物种群,既受自然环境限制,又利用其社会性、技术及文化改造着自然环境,并与之密不可分。环境史的研究对象及内容广泛而深刻、宽泛而细致,宏观中包含着微观,这就决定了环境史必然是一个视域广阔、内涵宏富的学科。
虽然目前环境史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其中既有早期历史地理等人文社会学者研究的成果,如对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古代都城与生态环境,动植物变迁与区域沙漠化,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灾害、疾疫与生态环境变迁,气候、区域生态环境史和生态环境保护思想、水环境、水资源开发与生态变迁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也有自然科学如动植物学、微生物学、生态学、资源环境、地理学、气候学、医学等与环境史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近年来环境史学者在环境史的理论及方法、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方面的研究,推动了中国环境史的整体发展。
但相对于环境史研究的宏阔内容,相对于漫长历史时期的环境变迁及环境变迁的各侧面而言,目前的环境史研究及其成果,仅只是环境史这座庞大冰山的一角。在未来研究中,中国环境史学及相关专栏应在以下方面继续拓展新领域:
一是中国环境史理论及方法的继续探讨及研究。目前虽然有学者对中国环境史的理论及方法进行了研讨,但迄今尚无学者做出一部既有世界环境史视域,又有本土环境史研究情怀的中国环境史理论的专著,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环境史学科的深入发展。
二是从整体史观的视角对中国整体环境史进行研究。目前中国环境史研究成果较多的是断代环境史、区域环境史、环境变迁史及早期环境思想史,但迄今尚无一本完整的中国环境史专著出现,亦无一本环境史教材供给高校环境史学科的人才培养专业使用。
三是对一些已开始但还处于起步阶段的领域,如海洋环境史、疾病环境史、山地环境史、环境制度史、环境法制史等进行拓展及深入。对一些已有初步成果的农业及工矿业生态环境史、生物及其环境变迁史、灾害与环境史、环境思想史、环境保护史等问题的研究,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拓展及深化。
四是开拓一些目前几乎没有进行的诸如水生生物环境史、水域环境史、大气环境变迁史、冰川环境变迁史、民族环境变迁史、边疆环境史、环境口述史、中外环境变迁比较史、中国的世界环境史研究等领域。
目前,环境史研究栏目不断出现,专栏成果能够以更集中、更新颖、更有质量的研究成果,培养、推出一批环境史学新秀,成为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主要阵地之一,不仅进一步深化环境史理论、方法及具体问题的研究,也提升中国乃至世界环境史的研究水平及其成果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