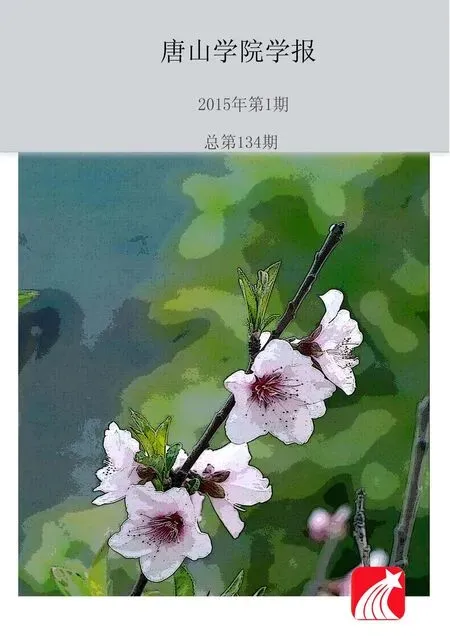《日本灵异记》中的中国儒学典故
刘九令
(渤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
《日本灵异记》中的中国儒学典故
刘九令
(渤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
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佛教说话集《日本灵异记》中引用了许多有别于佛教题材的中国儒学典故,这些典故的运用在一定意义上增强了作品的文学表现力,使其更具文学韵味。此外,这些典故对于作者研究、中日文学文献交流研究以及《日本灵异记》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互补互证研究都有重要的价值。
日本灵异记;中国儒学典故;文学性
一、引言
《日本灵异记》是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佛教说话集,大致成书于公元822年前后,作者为奈良药师寺的僧人景戒。作者景戒一方面将书的全名定为《日本国现报善恶灵异记》(研究界通常简称《日本灵异记》),凸显其对抗中国的日本国属性,另一方面在编撰该书时,却受到了中国先行说话集,如《冥报记》《金刚般若经集验记》的启发。在写作过程中也大量借用中国故事题材、故事类型,模仿中国文学的表现手法等,这些方面已有学者做了深入的论考。其实,《日本灵异记》中还多处引用了中国儒学典故,这些典故在性质上有别于佛教题材,在佛教说话集中却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而这一点似乎并没有引起先学们的注意和重视。本文拟以《日本灵异记》中的儒学典故为考察中心,揭示其对中国文学吸收和借鉴的情况。
二、《日本灵异记》对中国儒学典故的运用
日本学者出云路修在新大系本中指出了《日本灵异记》所引中国儒学典故的某些出典,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本文利用这些研究成果,将研究再向前推进一步。我国学者钟涛在《六朝骈文形式及其文化意蕴》一书中给用典作了分类,并对这种分类作了详细的阐释:“六朝骈文中数典用事的方式,事实上包括了造语与用事两方面。造语是依据古典的言辞,用事则是依据故事的话题。……在造语或用事中又可具体分为截取旧典只言片语和概括整个故事的主题两种方法。前者是从语句、辞句等方面从外形上对旧典加以运用,后者则从内容方面对故事加以概括运用。”[1]本文拟参照上述分类,对《日本灵异记》中的中国儒学典故分别进行论述。
(一)造语类
《日本灵异记》中以造语方式出现的中国儒学典故至少有三处,分布在上卷序文和中卷序文中。
1.上卷序文用典
上卷序文用典如下:
然景戒,秉性不儒,浊意难澄。坎井之识,久迷大方。能功所雕,浅工加刀,恐寒心恉,患于伤手,此亦崐山之一砾。但以口说不详,忘遗多矣,不胜贪善之至,慓示滥竽之业,后生贤者,幸勿咳嗤焉。祈览奇记者,却邪入正,诸恶莫作,诸善奉行[2]202。
这段文字中共有两处用典,分别为“坎井之识”和“慓示滥竽之业”。这里的“坎井之识”指井底之蛙,有见识狭浅之意。新大系本解释了“坎井之识”的含义,并指出“坎井之识”与《荀子·正论》的关系。《荀子·正论》中有关于“坎井之蛙”的文句:
彼楚越者,且时享、岁贡,终王之属也,必齐之日祭、月祀之属,然后曰受制邪?是规磨之说也。沟中之瘠也,则未足与及王者之制也。语曰:“浅不足与测深,愚不足与谋智,坎井之蛙,不可与语东海之乐。”此之谓也[3]。
然而早于《荀子》的《庄子·秋水》中已有“埳井之蛙”字样,原文如下:
公子牟隐几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独不闻夫埳井之蛙乎?”谓东海之鳖曰:‘吾乐与!吾出跳梁乎井干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则接腋持颐,蹶泥则没足灭跗。还虷蟹与蝌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乐,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时来入观乎?’东海之鳖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絷矣。于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极其深。禹之时,十年九潦,而水弗为加益;汤之时,八年七旱,而崖不为加损。夫不为顷久推移,不以多少进退者,此亦东海之大乐也。’于是埳井之蛙闻之,适适然惊,规规然自失也[4]。
由此可见,新大系本中出云路修虽指出了该典故与《荀子·正论》的关系,却没有看到该文句出现的最早文献。《荀子·正论》中有“语曰”字样,其语当为引用而来,所以据此判断“坎井”最早应出现在《庄子·秋水》。出云路修还提到寺川真知夫的考证,其考证认为“坎井之识,久迷太方”语出《高僧传》的“以为坎井之识,久迷大方”一句,笔者虽然没有看到这篇论文,但是从文句的相似度或重叠度来看,比较赞同寺川真知夫的观点。这里考察的目的并不在于指出确切出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校注本,出云路修应该在注释中将文句出处上溯到最早的《庄子·秋水》。
而“慓示滥竽之业”,是我们当代汉语的“滥竽充数”之意,出自《韩非子·内诸说上》,原文如下:
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悦之,廪食以数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听之,处士逃[5]。
上述两个典故,在现代汉语成语中多写作“井底之蛙”“井蛙之见”“滥竽充数”等。而“埳井”中的“埳”通“坎”,与《荀子·正论》中“坎井之蛙”的“坎”相同,是塌陷之意。因此《日本灵异记》中截取了“坎井”(或者说‘坎井之识’)这一语句,造语成典。同样,“慓示滥竽之业”则取原文中“竽”,造语成典。此处,景戒借用此典故以自喻知识浅薄、不自量力,意在表示自谦。需要强调的是,这两个典故均出自中国的儒学典籍,本身没有任何佛教意义,经僧人景戒在佛教说话集序文中加以借用,使这些典故的文化与文学语境发生了很大变异。
2.中卷序文用典
中卷序文用典如下:
然景戒,秉性不聪,啖口不利,神迟钝同于刀。连居字不华,情惷戆同于刻船,编造文乱句[2]251-252。
其中“情惷戆同于刻船”指的是成语“刻舟求剑”,出自《吕氏春秋·察今》,原文如下: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以故法为其国与此同,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6]!
文中“契”同“锲”,意为“刻”。《日本灵异记》将“契其舟”化作“刻船”,造语成典。这里用典的意义同前文大体相同,用以自喻愚钝。
上述三个典故的特点是,截取故事中的某些关键词,或者化用其中某个语句,指代事件,借以自喻。这体现了作者对于中国儒学典故内涵的理解深度,也侧面反映了其驾驭文字的功力和技巧。从文学意义上看,由于用典,使得作者想表达的自谦之意显得“意婉而尽”,“藻丽而富”。
(二)用事类
与造语类不同,用事类要大体概括其事件或事件主题,借以表达思想。
1.上卷17借用“丁兰木母”的典故
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个人被派遣参加解救百济国的战斗,后被唐军所俘虏。这个人与同被俘虏的其他八个人用松木刻了一尊观音像,虔诚礼拜,最终得以逃脱。文末写道:
丁兰木母,犹现生相。僧感画女,尚应哀形,何况是菩萨而不应乎[2]214-215?
“丁兰木母”的故事最早出自刘向的《孝子传》。这里引自《法苑珠林》第四十九卷丁兰条:
丁兰,河内野王人也,年十五丧母,刻木作母事之,供养如生。兰妻夜火灼母面,母面发疮。经二日,妻头发自落。如刀锯截,然后谢过。兰移母大道,使妻从服三年拜伏。一夜忽如风雨,而母自还。邻人所假借,母颜和则即与,不和则不与。郑缉之孝子传曰:“兰妻误烧母面,即梦见母痛。人有求索,许不,先白母。邻人曰:‘枯木何知’,遂用刀斫木母,流血。兰还悲号,造服行丧。廷尉以木减死,宣帝嘉之,拜太中大夫者也。”[7]1487-1488
《日本灵异记》中刻松木观音像有感应,《孝子传》中丁兰刻木为母亦有感应,在这一点上二者有相通之处。《法苑珠林》另有记载:
丁兰温清竭诚,木母以之变色。鲁阳回戈而日转,杞妇下泪而城崩。斯皆隐恻入其性情,故使征祥照乎耳目。是知道藉人弘,神由物感,岂曰虚哉!是以祭神如神在,则神道交亦;敬像如敬佛,则法身应矣[7]1034。
由引文所见,“丁兰木母”事最终归结到“敬像如敬佛,则法身应矣”的佛教道理上。《日本灵异记》中的礼观音像得以逃脱兵难,是观音救济中的常见内容之一,此处又借用“丁兰木母”来佐证应验不虚的佛理。丁兰的故事在中国儒家文学中表现了“孝”的思想,而这里景戒将丁兰故事概括为“丁兰木母”,用此典故来证明观音菩萨应验的真实性,实现了典故意义由儒学向佛教的转换,由此为其宣扬佛教教义增加了感染力。
2.中卷序中的五个典故
〔好恶〕之者,铁杖加身。好善之者,金珠装体。譬如押之向依,牵之避斥,加也损减,除也满益。流头食糠,朱明舍宝,许由洗耳,巣父引牛,岂异此意欤?死还三界如车轮,生廻六道似萍移。此死彼生,具受万苦。恶因连辔趍苦处,善业攀缘引安堺。赖颐慈而膝前怀虎,由生爱以顶上栖羽。孟尝之七善,鲁恭之三异,盖斯意之矣[2]227。
序文中共引用了“朱明舍宝”“许由洗耳”“巣父引牛”“孟尝之七善”“鲁恭之三异”五个中国儒学典故。其中“朱明舍宝”的故事在中国的多部《孝子传》中都已不见,这里转引黑田彰论文《阳明本孝子传的成立》:
朱明者,东都人也。有兄弟二人。父母既没,不久财产各得百万。其弟骄奢,用财物尽,更就兄求分。兄恒与之。如是非一。嫂便忿怨,打骂小郎。明闻之,曰:汝,他姓之子,欲离我骨肉耶?四海女子,皆可为妇。若欲求亲者,终不可得。即便遣妻也[8]。
而“许由洗耳”“巣父引牛”的故事则出自晋代皇甫谧撰《高士传》的“许由条”,故事原文如下:
许由,字武仲,阳城槐里人也。为人据义覆方,邪席不坐,邪膳不食,后隐于沛泽之中。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而治矣,而我犹代子,吾将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巣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齧缺遇许由,曰:“子将奚之?”曰“奚谓邪?”曰“夫尧知贤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贼天下也。夫唯外乎贤者知之矣。”由于是遁耕于中岳颍水之阳,箕山之下,终身无经天下色。尧又召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颍水滨。时其友巣父牵犊欲饮之,见许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巣父曰:“自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誉。污吾犊口。”牵犊上流饮之[9]。
前面“朱明舍宝”中,朱明把财富多次分给挥霍无度的弟弟,后将不满此事的老婆休掉。“许由洗耳”和“巣父引牛”实际上是同一个故事。尧欲将帝位让给许由,遭到拒绝,后来又要给他个“九州长”的职务,同样遭到拒绝。许由认为尧的话语玷污了自己的耳朵,便在河边洗耳。而在河边饮牛犊的好友巣父听到许由述说,认为许由并非真心拒绝,否则为何不躲到更为偏远的地方,于是赶紧将牛牵到河的上游,以免许由洗耳的水污染牛嘴。这三个典故均以人物事件的形式呈现,朱明舍财,许由、巢父弃权。景戒将这些典故一起使用,表达了舍弃财物和名利、远离贪欲的主旨。中国文学语境中的这些儒家典故,表现的是淡泊名利的思想,而在《日本灵异记》的佛教文学语境中却被改造成了佛教的清心寡欲。
另外还有“孟尝七善”和“鲁恭三异”。“孟尝七善”中的“七善”意义不明。据新大系本《日本灵异记》的注释:“‘孟尝还珠’(蒙求)的故事很著名。‘七善’不详。或许和杨喬上书七表孟尝的行为有关,从文脉推测,或许和鸟兽有关。”[2]58事实上,“孟尝七善”应取自《后汉书·循吏传》,“七善”是指“尝安仁弘义”“耽乐道德”“清行出俗”“能干绝群”“为妇申冤”“革除前弊”“单身谢病”。关于这一点,笔者已经另行撰文进行详细考证。
而“鲁恭三异”,出自《后汉书》,内容如下:
憙复举恭直言,待诏公车,拜中牟令。恭专以德化为理,不任刑罚。讼人许伯等争田,累守令不能决,恭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责,辍耕相让。亭长从人借牛而不肯还之,牛主讼於恭。恭召亭长,劝令归牛者再三,犹不从。恭叹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绶去。掾史泣涕共留之,亭长乃忏悔,还牛,诣狱受罪,恭贳不问。于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国螟伤稼,犬牙缘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闻之,疑其不实,使仁恕掾肥亲往廉之。恭随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过,止其傍。傍有童儿,亲曰:“儿何不捕之?”儿言:“雉方将雏。”亲瞿然而起,与恭然决曰:“所以来者,欲察君之政迹也。今虫不犯境,此以一异也;化及鸟兽,此二异也;竖子有仁心,此三异也。久留,徒扰贤者耳。”还府,具以状白安。是岁,嘉禾生恭便坐廷中,安因上书言状,帝异之。曾诏百官举贤良方正,恭荐中牟名士王方,帝即征方诣公车,礼之与公卿举同,方致位侍中。恭在事三年,州举尤异,会遭母丧去官,吏人思之[10]。
所谓“鲁恭三异”是指在鲁恭的治理下,某地方“虫不犯境”“化及鸟兽”“竖子有仁心”这三异。孟尝和鲁恭在故事中都是清官贤吏的形象,不过在原文的语境下是强调两个人的“仁慈”“慈爱”的一面,因为在“孟尝七善”和“鲁恭三异”的前面有“赖颐慈而膝前怀虎,由生爱以顶上栖羽”的文句,与“慈”“爱”等关键词相呼应。加之,鲁恭对待百姓也是“专以德化为理,不任刑法”,也是强调“非刑”而用“仁慈”。在佛教看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此主张以慈悲为怀。儒家中的官吏慈爱惜民的思想,与佛教的慈悲观念有很多类似之处,故被景戒加以比附。另外,“赖颐慈而膝前怀虎,由生爱以顶上栖羽”是两个佛教典故,前者指“慧越伏虎”一事,后者指“螺髻仙人宿禽于顶上”。将两个儒家典故与佛教典故放在一起,使儒典佛典化,以儒说佛。这两个典故用带有人物和数字的文句,表达了作者宣扬佛教的虔诚。从艺术效果看,使得要表达的宣佛主旨更加形象生动。
三、所引中国儒学典故的意义
《日本灵异记》中所引用的中国典故不止上述这些,有些典故以造语的方式散见于文本的各个角落,由于造语与中国原故事有很大的差异,或是变形程度很大,难以辨认,因此,考证出隐藏其间的典故是今后《日本灵异记》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那么,研究其中的中国儒学典故究竟有何意义和价值呢?笔者认为,至少有四点。
首先,挖掘作品的文学价值。关于《日本灵异记》的文学性问题,笔者已经另撰文讨论,在此简略提及。作为说教文本的《日本灵异记》的编撰固然以宣教为最终目的,而不是为了文学创作,但是换角度看,要让读者或信众接受教理、教义,若不辅之以文学手段能够顺利达到其最终目的吗?可以说,在文本中使用文学手段是编撰该书必然要做的事情。文本故事中除了采用拟人、夸张、譬喻等文学手法之外,用典也是重要表现之一。作品中,以典喻理、以典说事、以典自喻的手法,起到“意婉而尽”“藻丽而富”“气畅而凝”的艺术效果。用典同拟人、夸张、譬喻等文学手法共同支撑起《日本灵异记》的文学性的大厦。对于那些对《日本灵异记》文学性研究采取无视、忽视、轻视态度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个有益的补充和有力的反驳。
其次,对关于作者景戒的研究大有助益。作品由作者创作产生,因此当研究某一作品时往往也要将作者的研究纳入其中,而作者本人所阅读的书籍及其本人的文学、文化素养是考察的重点之一。在景戒研究方面已有诸如柳田国男、米村静枝、鹿苑大慈、志田谆一、黑沢幸三、大谷义博等学者考察其出身问题,包括出生地和所处阶层。这些学者大多将着眼点集中在个别故事以及相关的历史事件的相互印证上,而关于景戒学养的考察并不多,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其中所引典故来推察景戒本人所读书目,揣测其具有的文学素养,也为景戒的“归化人”说提供可参考的证据。除了以此考察学养之外,还可以由此窥测作者所读书目之巨以及对内典、外典广泛涉猎的开放态度,并以此为基点促进作为佛教说话集的《日本灵异记》的非佛教研究。
再次,对于研究中日文学文献交流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文学文献很早就传到日本,对日本文化、文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书早于《日本灵异记》的《古事记》《日本书纪》《风土记》《万叶集》等也或多或少受到中国文学的影响,但这些文本中所体现的中国文学元素却大多比较隐蔽,不易发现,学者们只能通过其中的细部考察方能发现其中的蛛丝马迹。而《日本灵异记》则不同,景戒直接借用典故,研究者可以按图索骥,追溯其出处或有转载记录的书籍,并由此判断在该书成书之前中国文学文献在日本流布的情况。
最后,对《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有互补互证的价值。《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是日本最早的记录当时流传于日本的汉籍文献目录,学术价值极高。然而,其中所录汉籍书目有所限制。875年,由于皇室藏书库——冷然院遭遇火灾,其中的藏书大部分被焚毁。后来,五位下大臣藤原佐世奉敕编撰了这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但是,其中收录只是火灾中所幸残存书籍以及当时借出未还和藏于其他皇族贵族、寺院的书籍。可见,其中所辑录的书目不可能是当时汉籍的全部,必然会有所遗漏,因此通过《日本灵异记》中所引的典故典籍出处,可以弥补《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之所遗漏。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某些典故往往在中国文学文献中多次重复应用,往往很难确定究竟出自哪里,如果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与之互相比照,可以进一步缩小出典的考查范围,甚至可以确定出典。
四、结语
《日本灵异记》作为佛教说话集,受中国佛教文学影响很大。作者景戒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怀,将大量的中国外典融入其中,使这部佛教书呈现出一些非佛教的性征,丰富了这部作品的价值。儒学典故不同于佛教,但是却存在某些可以比附的地方,景戒恰恰是利用了这一点,用儒学解释佛教,证明佛教存在的合理性。前文对《日本灵异记》中的典故作了考察分析,并由此揭示其具有的四个方面的价值和意义。从该书用典的情形来看,其中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序文中,具体到正文故事中却极少。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这是因为相对来说,用典较为艰深晦涩,其背后蕴含深厚的文化背景。可以说,所用典故对于当时缺乏一定汉文修养的下层民众来说,不会像情节性较强的具体小故事那样好理解,尤其序文中多议论、说理内容,用语生僻,逻辑性强,较为抽象。因此,可以说序文和正文故事具有不同性质和意义:序文主要写给具有一定知识和文化素养的读者阅读,体现一种书面性质,而故事则是提供给普通民众阅读或是宣讲的,更具有讲唱的性征。
[1] 钟涛.六朝骈文形式及其文化意蕴[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142-143.
[2] 景戒.日本灵异记[M].出云路修,校注.东京:岩波书店,1996.
[3] 叶绍钧.荀子[M].北京: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36年:92.
[4] 黄永年.老子·孙子·庄子·吴子[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61.
[5] 钦定四库全书·韩非子:第729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690.
[6] 吕氏春秋[M].庄适,选注.北京: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36年:69.
[7] 释道世.法苑珠林[M].周叔迦,苏晋仁,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
[8] 黑田彰.阳明本孝子传的成立[J].京都语文(第14号),平成19年:90.
[9] 皇甫谧.高士传[M].刘晓东,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6.
[10]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874-875.
(责任编校:白丽娟)
Chinese Allusions inNihonRyoiki
LIU Jiu-li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Bohai University,Jinzhou 121013, China)
NihonRyoikiis the first collection of Buddhist stories in Japan. Lots of Chinese Confucian allusions are cited in this book and these allusions are essentially different from the Buddhist subject matters. To some extent, the use of these allusions strengthens its literay effect and makes the book more impressive Besides, the allusions are complementary to the study of the author, Sino-Japan literal exchange,NihonRyoiki,andRibenguoJianzaiShumulu.
NihonRyoiki;Chinese Confucian allusions; literature
I313.299
A
1672-349X(2015)01-0075-04
10.16160/j.cnki.tsxyxb.2015.0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