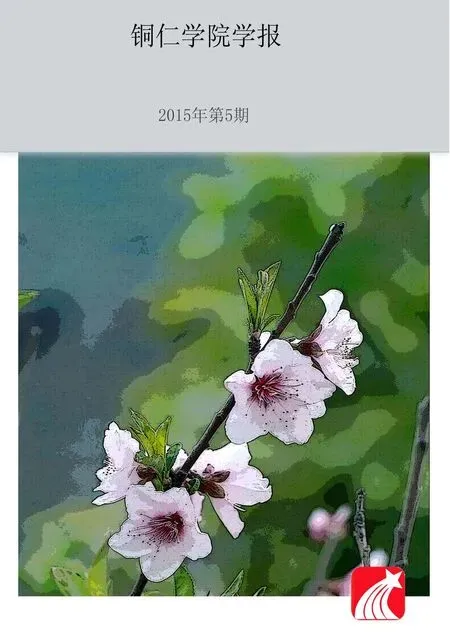城镇化进程中湘西苗族婚恋习俗的变迁及社会影响
——基于勾良村的田野调查
吴金庭
( 铜仁学院 武陵民族文化研究中心,贵州 铜仁 554300 )
城镇化进程中湘西苗族婚恋习俗的变迁及社会影响
——基于勾良村的田野调查
吴金庭
( 铜仁学院 武陵民族文化研究中心,贵州 铜仁 554300 )
勾良村历史悠久,民俗风情浓郁,灿烂多彩、特色明显的婚恋习俗文化在这里得以延续和发扬。在城镇化背景下,勾良苗寨的婚姻习俗进行了现代化的整合,发生了很大的变迁,既保留了自身文化的主体性、独立性,又融入了现代化的因素。在变迁中,产生的一些社会新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和探求解决途径,这将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湘西苗族; 婚恋习俗; 变迁; 社会影响
湘西苗族历史悠久,在长期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丰富多彩、民族特色明显的众多婚恋习俗。例如,“唱苗歌”、“赶边边场”、“奔婚”、“吃排家饭”、“开娘钱”、“卵卜鸡卜”等。湘西苗族热情好客,崇尚爱情婚姻自由。新中国成立后,传统的婚姻习俗仍然影响了好几代人。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现代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湘西苗族婚恋习俗遭到了极大的冲击,有了很大的变迁,对社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勾良村的历史文化概况
勾良村位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落潮井乡境内,该村是一个苗族聚居村寨,全村 8个村民小组,376户,2280多口人。勾良苗寨建寨于唐垂拱三年(679),至今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素有“苗疆第一寨”之称。该村西距贵州大兴机场 6公里,距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凤凰县城25公里,其地理位置正处于湘黔结合部位上,中原汉文化与西南楚巫苗文化在这里碰撞整合,形成了特色明显、内容丰富的苗族文化。苗族传统节日“六月六”苗歌节每年就是在勾良村的凤凰山下举行。
勾良村村民平时生产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为苗语,中老年人大都着苗服。村民中主要有吴、龙、麻、伍四大姓,其中,吴姓人口占 50%以上。勾良村主要过春节、清明节、重阳节,其他节日不重视,宗教信仰主要是信仰原始宗教和祖先崇拜,逢年过节除祭祀祖先外,还祭拜土地庙、飞山庙等。
二、勾良村婚恋习俗的变迁
进入20世纪90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勾良村民不断地走出寨门,在现代文化与传统民族文化的碰撞中,勾良村苗族婚恋习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恋爱场所和恋爱方式的变化
历史上,勾良村的苗族男女青年婚姻缔结方式往往是通过“赶边边场”、田间劳作或节庆、仪式活动中相互认识,以歌传情,以物为媒,私定终身。“赶边边场”是最为普遍的一种方式,因为赶集之日,附近苗寨的男女青年都会前来,此时是男女苗族青年认识的最好时机,亦是恋爱的最好场所。苗族男女青年在圩场附近的树荫下、田坎间、山道上,三五成群,以歌传情,从中寻找自己中意的情人。这也决定了苗族男女青年从小就要学会唱苗歌,不然就难以博取对方的爱意。“后生不学唱,找不到对象”,生性木讷不会唱歌的男青年往往要依靠父母去求媒人说媒才能成家。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勾良村村民外出务工的人员不断增多。很多苗族青年初中毕业后就选择外出打工,留在村里劳动的极少。他们大多在打工中与外乡外村的青年相识、相爱、结婚,也有很多是在外求学中认识,然后恋爱结婚的。现在,勾良村传统的恋爱方式几乎已经消失,若是有人还按照传统的方式去找结婚伴侣,必然会被别人笑话。
(二)结婚方式——“奔婚”的消失
改革开放后,勾良村苗族青年除了极少数是尊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之外,绝大多数是自由恋爱结婚,采取的方式往往是“奔婚”。“当男女双方恋爱程度,各达沸点,愿意缔结婚约,如父母不赞同,加以反对,碍难成功,遂不遵父母命。易采取‘奔婚主义’也。”[1]181勾良村的“奔婚”有着自己的独特方式。男女双方“奔婚”时,往往提前约好时间,然后男方邀约几个玩得好的伙伴深夜赶到女方村寨附近等候,女方也会邀上几个女伴,在家人全部酣睡之时偷偷溜出家门前往村外与男方会合,然后一起奔往男方家中。到了男方家后,男女青年会坐到一起唱苗歌、打牌、宵夜,天亮后,男方父母就会请本族两个能说会道的年长者挑起酒肉、烟糖赶往女方家中报信。等到女方生小孩举办“三朝”酒时,女方父母才会送来嫁妆及婴儿所用物品,这种形式被称为“双喜临门”。
进入21世纪,在外来文化和现代经济的不断冲击下,勾良村“奔婚”形式已不复存在。现今,该村苗族青年男女基本上都是自由恋爱到达谈婚论嫁之时,双方主动告知自己的父母,同意后就会定下日期,然后由男方的父母、叔伯等人挑起酒肉、烟糖、爆竹到女方家中提亲,提亲其实也就是订婚仪式。待到一定时候,才正式举办结婚仪式,宴请亲朋好友。
(三)通婚圈的扩大
勾良村苗族只在本民族内通婚。青年男女交往结识的对象,一般只局限于本乡本土附近的几个苗族村寨,鲜有和汉族通婚的惯例。村民历来奉行“同姓不婚”、“姨表不婚”的古老原则。“苗族的祖先祝融是第一个严禁内婚的。苗族的《古老话》中说,若同姓结婚,就要用火烧死。”[2]
近几年,“外出务工/经商农村女性的通婚范围扩大,有流动经历的女性中,15.7%的配偶是在外结识的异乡人”[3]。男性的比例比女性更高,而且在与同姓结婚方面,男青年更多。据笔者统计,和外村同姓女青年结婚的有8对。勾良村苗族青年男女与其他民族通婚的也比较多见,省内有之,省外亦有之。笔者2015年春节到勾良村调研时就遇到第3村民小组有 2对年轻家庭是与外省结婚的,一个是与四川绵阳的女青年在打工时相识然后结婚的,另一个是在乡村游做导游时与内蒙古一女游客认识恋爱、结婚。
(四)早婚习俗的变化
苗族历来有早婚习惯,这和苗族为了抵抗外来压迫剥削、快速繁衍后代有一定的关系。“苗民结婚早,女子年龄普通由十六岁至十八岁或二十岁;男子普通由十八岁至二十岁或二十四岁。”[1]181勾良村苗族青年早婚现象逐渐严重,很多都是先结婚生孩子再去政府补办结婚证。在苗族自由恋爱风尚影响下,加上家长对教育的不重视,学生小学或初中毕业后就辍学在家,恋爱从十一、二岁就开始,在十五、六岁就结婚,有“十七、八岁做父亲,三十六岁当爷爷”的说法。父母对此亦不多加阻拦,认为早结婚早当家,“早生贵子,早来福”,可以为家庭多增加劳动力。
步入20世纪90年代,勾良村村民清醒地认识到贫穷的根源就是因为没有知识,所以村民都积极送子女上学,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逐渐增多。很多青年都是在中学(专)毕业后才出门打工,挣了钱之后首先就是回家建新房子,改善居住条件,然后再积攒结婚资金。如此一来,很多男青年都是在二十六、七岁,甚至更大一点才成家。苗族女青年恋爱对象也不奉守从一而终的老传统,选择的范围较广,因而结婚年龄也渐趋偏大。
(五)婚姻习俗呈现传统与现代并存、苗族习俗与汉族习俗融合的趋势
“未来的文化不仅融入了强烈的民族性特征,也融入了鲜明的时代性特征,形成民族传统与时代精神的互补和并存的文化新格局。这并不意味着出现一个文化大杂烩的时代,而是一个文化多质、同质和异质被重新整合的时代。”[4]19420世纪90年代以来,勾良村婚俗习惯呈现出传统与现代、苗族习俗与汉族习俗的融合并存的趋势。例如,女方的嫁妆由柜子、箱子、桌椅、自行车、缝纫机等变为彩电、冰箱、摩托车、小汽车等;男方婚宴时间由三天两夜改为一天,苗家“排家饭”已不复存在;客人的贺礼由实物(米、鸡蛋、布)变为礼金;很多年轻人都是先登记结婚,再择日举行婚礼;拍婚纱照、迎亲花车、录制婚礼场面成为一种时尚;等等。在这些习惯的变化中,既有传统的因素在里面,又有现代的因子,是民族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结合。
三、勾良村婚恋习俗变迁的原因
(一)国家政策法规的不断完善和强力执行
1982年9月新《婚姻法》实施,党的十二大确定“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同年12月,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这确立了计划生育的法律地位,使之走上了依法行政的道路。2001年 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并于2002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1992年10 月 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是我国第一部以妇女为主体、以全面保护妇女合法权益为主要内容的基本法。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对妇女政治权利的保障性规定更加具体。各级各类政府部门坚决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勾良村村民法律意识不断提高,晚婚晚育、优生优育为越来越多的勾良村村民所认同。
(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冲击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社会转型带动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勾良村和全国各地农村一样,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这批苗族青年大多接受过中学教育,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基础,易于接受现代化文明的洗礼,促使其人生观、价值观、婚恋观与过去人产生不同。市场经济的发展让这些人看到了个人价值在社会中的体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勾良村当地传统文化的一个冲击和挑战,两者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博弈,并在抗衡中寻找新的适应方式,既有突破创新又有对传统习俗的保留。这样,勾良村的婚恋习俗呈现多样化。
(三)女性婚姻自主程度的提高
农村女性的初次婚姻“由本人决定”和“本人决定,征求父母意见”的比例为56.2%,其中有外出务工经历的比例为68.8%。青年妇女的婚姻自主程度更高,35岁以下的为75%。完全由“父母决定”的比例,不论城乡、男女,都比10年前下降了很多。相对而言,农村比城镇下降明显,女性比男性下降更多[5]。妇女参政权、就业权、受教育权、婚姻自主权在社会生活工作中得到更大程度的体现,女性社会地位得到提高,传统的“父权”“夫权”家庭体制受到冲击。
(四)现代生境中苗族文化自我积极的整合
“民族社会结合时代特征和现实需要,对自身文化进行重新阐释和现代整合,重塑适应时代需求的新文化,实现了民族文化的现代性变迁。”[6]随着以网络信息为主的现代大众传媒的盛行,勾良村村民通过电视、报刊杂志、手机、网络获得了更多的外界信息;年轻人外出求学和打工,将外面新鲜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带回了村寨;城乡差距缩小,勾良村的婚恋习俗也在潜移默化中进行自我整合,传统中融入了很多现代的汉族文化因子,喜闻乐见、积极健康的习俗得以传承下来,一些不利于社会主义法制、道德建设的不合理习俗逐渐地被抛弃。
四、勾良村婚恋习俗变迁产生的社会影响
(一)攀比之风日盛,结婚开支快速增长
经济发展为婚礼消费提供了资金保障,男女青年受到现代思想的冲击,结婚攀比之风盛行。结婚仪式讲究排场,女方派发的彩礼数目不断增加,酒宴的标准也不断提高,造成家庭经济负担沉重。20世纪90年代,勾良村男青年结婚开支大约为6000元,主要是花费在聘礼、置办酒席上。近几年,结婚开支一般在6~8万元,大部分是花费在聘礼、置办结婚所用物品、酒席上,几乎相当于一个家庭年收入的2~3倍。借钱结婚现象非常普遍,有的因为花费大,婚后一直在还债,又会陷入到贫困的境地。同时,巨大的经济压力反过来还会影响着婚姻的稳定。
(二)已婚男女独立性增强,离婚率快速增长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城乡差别缩小,生活、工作环境等的改变,男女青年性别观念和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调查显示:59.5%的人认为目前中国男女两性的社会地位差不多;女性具有较强的自信心和独立意识,86.6%“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88.9%“在生活中主要靠自己,很少依赖他人”;男性的相应比例为92.2%和95.2%[3]。已婚男女在外出务工时,独立性强,受外界现代开放思想的影响较大,特别是女性在家庭中拥有更多的婚姻自主权,在遇到家暴、婚外情时往往不征求父母意见就采取离婚的方式解决。近十年,勾良村已婚男女离婚率不断提高,对后代产生了不良的影响,给家庭、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不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五、结束语
在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湘西苗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广泛、频繁。随着本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湘西苗族的一些民族特征也在发生新的变化。从勾良苗寨婚恋习俗的变迁中,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国家正在实行文化策略的调整、自下而上对民族文化实施“变迁”;另一方面,湘西苗族并不是完全被动地在被引导着变迁,而是积极响应,对自身的民族文化进行现代整合。在此过程中,政府职能部门应主导话语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让苗族文化保持鲜明的文化主体性和独立性,才能有效地将苗族优秀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从而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1]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2]石邦明,龙炳文.湘西苗族婚姻习俗[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2).
[3]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J].妇女研究论丛,2011,(6).
[4]张文勋,施惟达,张胜冰,等.民族文化学[M].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1998.
[5]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报告[J].妇女研究论丛,2001,(5).
[6]崔榕.湘西苗族婚姻文化的百年变迁[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1).
Changes and Social Impacts of Marriage Customs of Miao People in Western Huna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A Study Based on Fieldwork in Gouliang Village
WU Jinting
( Wuling Ethnic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Tongren University, Tongren, Guizhou 554300 ,China )
In Gouliang, a village with a long history and rich customs, bright, colorful and particular marriage culture continues and develops. In the context of urbanization, marriage customs of Miao People in this village undergo a process of modern integration and great change, with a subjectivity and independence of its culture being kept and some modern factors being absorbed. Some new social problems occurred in this process deserve our thinking and their solutions should be procured, which will benefit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
Miao People in Western Hunan, marriage customs, changes and social impacts
G127
A
1673-9639 (2015) 05-0060-04
(责任编辑 黎 帅)(责任校对 郭玲珍)(英文编辑 谢国先)
2015-04-23
吴金庭(1969-),男,湖南凤凰人,苗族,铜仁学院武陵民族文化研究中心讲师,研究方向:民族文化与民族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