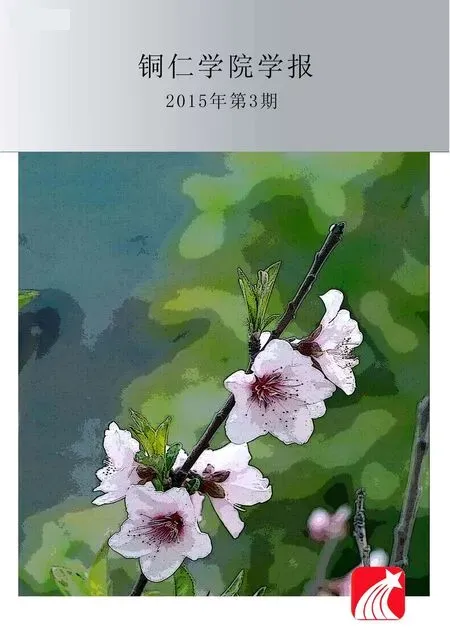暮年浮海的澄明之境:苏东坡流寓雷州诗文的情感世界
张学松,彭洁莹
( 广东海洋大学 文学院,广东 湛江 524025 )
暮年浮海的澄明之境:苏东坡流寓雷州诗文的情感世界
张学松,彭洁莹
( 广东海洋大学 文学院,广东 湛江 524025 )
苏东坡流寓雷州的诗文是他人生最后一次沉浮起落的记载,表现了其流落感、忧惧心,以“鲁叟”、“箕子”自喻和“人生如寄”、“岭海亦闲游”的思想。
苏东坡; 流寓; 雷州; 诗文
苏东坡绍圣四年(1097)五月十一日与胞弟苏辙相遇于藤州,六月五日同行至雷州,六月十一日渡海到海南;元符三年(1100)获赦北归,六月二十日渡海到雷州,七月四日到廉州。其流寓雷州半岛的时间不足一个月。其间所作诗文不多。诗只有 4首:《和陶止酒并引》、《六月二十日渡海》、《自雷适廉,宿于兴廉村净行院》、《雨夜宿净行院》。文只有2篇:《伏波将军庙碑》、《书合浦舟行》。另有与范冲、秦观、林济甫、史氏太君嫂等信札若干。各类文体加起来不过10余篇。不过,绍圣四年(1097)作于梧州的《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过海即作的《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户酣笙钟。觉而又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次韵寄子由》、《和陶还旧居》、《到昌化军谢表》,元符三年(1100)渡海北归时所作《别海南黎民表》、《汲江煎茶》、《澄迈驿通潮阁二首》,渡海后作于廉州的《移廉州谢表》等,皆与流寓雷州紧密相连,故可一并考论。苏东坡流寓雷州时期所作诗文虽然不多,却是他人生最后一次沉浮起落的倾情书写,表现了丰富复杂的思想情感,凝聚了他深沉而深刻的人生思考,对于认知东坡晚年思想情感、人生境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择要论其三端,以切入这一重要的问题。
一、“寄命一叶万仞中”:流落与忧惧
东坡在惠州三年心情渐趋平静,已在白鹤峰买地筑屋作终老计:“已买白鹤峰,规作终老计。”[1]499此次再贬海南,心中陡起波澜,流落漂泊之感、忧愁畏惧之心难以自抑。《与王敏仲十八首》之十六:“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庶几延陵季子嬴博之义,父既可施之子,子独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家,死不抚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1]1846《到昌化军谢表》言其渡海辞别家人时,“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言其南迁途程:“并鬼门而东骛,死瘴海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责。”[1]1119-1120《和陶止酒并引》:“与子各意行,同落百蛮里。萧然两别驾,各携一稚子。”[4]510流落中带有凄凉感。《伏波将军庙碑》:“自徐闻渡海,适朱崖,南望连山,若有若无,杳杳一发耳。艤舟将济,眩栗丧魄。”其铭曰:“寄命一叶万仞中!”[5]986把生命寄托在在万仞深海中漂泊的一叶小船之上,其漂泊感、恐惧心溢于言表。《雨夜宿净行院》“一叶轻舟寄淼茫”与此仿佛。《书合浦舟行》:“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疏星满天。起坐四顾叹息:吾何数乘此险也!已济徐闻,复厄于此乎?”真实地记载了其漂泊大海的忧惧之心。东坡兄弟在雷州时,雷守张逢颇为关照,到海南后东坡给张逢写信:“某启:兄弟流落,同造治下,蒙不鄙遗,眷待有加。感服高义,悚息不已。”[1]1896在感念中流露出“流落”之感。即使有吉庆之事也深感“流落”,《与史太君嫂一首》:“某谪海南,狼狈广州,知时侄及第,流落中尤以为幸。”[1]1944这种流落感、忧惧心在其与范冲的信中反复述及:
流离僵仆,九死之余,又闻淳夫先公倾逝,痛毒之深,不可云喻。久欲奉疏,不遇便人,又举动艰碍,忧畏日深……(《与范元长十三首》之二)[1]1680
先公已矣,惟望昆仲自立,不坠门户,千万留意其大者远者……此非苟相劝勉而已,切深体此意。余不敢进言。(《与范元长十三首》之三)[1]1680
先公论往古事著述多矣,想一一宝秘,此岂复待鄙言耶?某当遣人致奠,海外困苦,不能如意,又不敢作奠文,想蒙哀恕也。归葬未知得请,苦痛之极,惟千万宽中顺便。此中百事,远不及雷,然百优所集,亦强自遣也。(《与范元长十三首》之四)[1]1680
孙行者至,得书,承孝履如宜,阖宅皆安,感慰之极……九死之余,忧畏百端,想蒙矜察……(《与范元长十三首》之六)[1]1681
毒暑,远惟孝履如宜。海外粗闻近事,南来诸人,恐有北辕之渐,而吾友翰林公,独隔幽显,言之痛裂忘生……某深欲一见左右,赴合浦,不惜数舍之迂,但再三思虑,不敢尔,必深察……(《与范元长十三首》之八)[1]1681
到雷获所留书,承车从盘桓此邦,以须一见,而某滞留不时至,遂尔远别,且不获一恸几筵之前者,非爱数舍之劳也,困危多畏故尔。此老谬之罪,想矜察……(《与范元长十三首》之九)[1]1681
某如闻有移黄之命,若果儿,当自梧至广,须惠州骨肉同往。计公昆仲抚护舟行当过黄,又恐公在淮南路行,不由江西,即不过黄,又不知某能及公之前到黄乎?飘零江海,身非己有,未知归宿之地,其敢必会见之日耶?惟昆仲金石乃心,困而不折,庶几先公之风没而不亡也。临纸哽塞,言不尽意。(《与范元长十三首》之十)[1]1682
范元长即范冲(元长乃其字),是范祖禹的长子。范祖禹是东坡的好友,元符元年(1098)卒于化州贬所。东坡在海南闻其卒理应撰奠文以祭,但未撰,北归到雷州后理应到灵前“恸哭”致祭,但未去,非东坡不念旧情,东坡“海外粗闻近事,南来诸人,恐有北辕之渐,而吾友翰林公,独隔幽显,言之痛裂忘生”,可见二人情谊笃厚,此皆其“飘零江海,身非己有”,又“困危多畏故尔”。
东坡之流落感、忧惧心并非始于贬谪海南。青年时所作那首《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应似飞鸿踏雪泥”[1]20的比喻,即已深寓人生流落漂泊感。“乌台诗案”发生时他欲投水自尽,贬居黄州五年,元丰七年(1804)由黄州团练副使量移汝州团练副使,他在《量移汝州表》中说:“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1]1085贬惠途中,上皇帝《赴英州乞舟行状》曰:“自闻命已来,忧悸成疾……道尽途穷,譬如中流失舟,抱一浮木,恃此为命,而木将沉,臣之衰危亦云极矣。”[1]1356在惠州给其表兄兼姐夫程正辅信中言:“某再启:窜逐海上,渴况可知。闻老兄来,颇有佳思……某获谴至重,自到此,旬日外,便杜门自屏,虽本郡守,也不往拜其辱,良以近臣得罪,省躬念咎,不得不尔。老兄到此,恐亦不敢出迎。”[1]1776
经历黄州、惠州两次重大贬谪后,面对人生挫折,毫无疑问,苏东坡当显得更为从容和淡定(详后),但他是人而非神,无论如何随缘自适,内心深层的“流落”与“忧惧”也自所难免。这种流落与忧惧不惟在诗歌中更多地在与亲友的信中表露,大概书信更能表露真情实感。
东坡流寓雷州的流落感、忧惧心源于三种因素:一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岭南古为蛮荒之地。民谚曰:“春、循、梅、新,与死为邻;高、窦、雷、化,说着也怕。”①见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二引《道护录》,《四部丛刊》本。八州皆在今广东境内:春州,今阳春;循州,今龙川;梅州,今梅县;新州,今新兴;高州,今高州;窦州,今信宜;雷州,今雷州半岛;化州,今化州。海南的自然环境更为恶劣。东坡在《与程秀才三首》中言:“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1]1801宋代祖训不杀言官文臣,贬到岭南即等于赐死,再贬到海南,哪还有生还之望?“问翁大庾岭上住,曾见南迁几个回?”[1]552此外,东坡流寓雷州,无论南迁还是北返都要渡过大海,而所乘又是木帆船或渔民打鱼的船(蜑船),波涛汹涌万丈深渊,真是“寄命一叶万仞中”!凶险恶劣的自然环境,对任何人的心灵都是一种威慑和震撼。二是政敌的迫害。元祐大臣再次遭贬,惟有苏东坡一人到海南,可见政敌对他怨恨之大。其弟苏辙被贬雷州与其隔海相望,应是政敌有意的戏弄。据说苏轼贬儋州,苏辙贬雷州,皆取其字之偏旁,这岂不是游戏人命?兄弟二人在雷州受到雷守张逢的礼遇,政敌章惇得知后,派酷吏湖南提举常平官董必察访岭南,张逢被勒停职,苏辙再贬循州。苏轼在海南受到儋守张中礼遇,张中也遭罢黜。“苏门四学士”皆受牵连而被贬。苏轼所说的“困危多畏”概缘于此。他并不仅仅是怕自己再遭打击,而更多的是怕连累朋友。三是疾病的缠绕。苏轼贬海南已是62岁,北返已是65岁,年衰多病。六月十一日夜渡海作《和陶止酒并引》即因痔疮病发而呻吟不止。
二、“天未丧斯文”:“鲁叟”与“箕子”
孔子的一生漂泊,曾自称为“东西南北之人也”(《礼记·檀弓上》),东坡与他颇为相似。东坡《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诗曰:“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1]541《千秋岁·次韵少游》:“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2]740《舆地纪胜》卷一百二十五《昌化军》:“轼初与弟辙相别渡海,既登舟,笑谓曰:‘其所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者耶!’”[3]946上皆用《论语》典。《论语·公冶长》:“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4]43又《书合浦舟行》言其由雷州往廉州途遇大雨,“碇宿大海中……所撰《易》《书》《论语》皆以自随,世未有本。抚之而叹曰:‘天未丧斯文,吾辈必济!’已而果然。”此也用《论语》典。《论语·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4]88显然 ,东坡是以“鲁叟”即孔子自喻。同时,东坡又以殷箕子自喻。《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箕子乃殷朝之贤臣。《史记·殷本纪》:殷纣暴虐,箕子谏不听,“乃佯狂为奴,纣又囚之。”武王伐纣,“乃释箕子之囚”。[5]79《后汉书·东夷列传》:“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以礼仪田蚕,又制八条之教。”[6]1901《易经·彖辞下·明夷卦》:“‘利难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7] 461意思是说:“‘宜于牢记艰难,持守正道’,是由于遭遇危难时能隐晦自身的锋芒,即使蒙受自己人加给的灾难也能持守光明正大的心志,箕子就是用这种方法固守正道的。”“天其以我为箕子”是说上天大概要让我做箕子吧。这是东坡以箕子自喻。
东坡以鲁叟与箕子自喻,有以下四层含义:第一,批判现实。孔子之所以欲乘木筏到海外去,是因为现实社会黑暗混乱,其政治主张不被施行,箕子被囚是因为殷纣王暴虐。东坡正道直行,却被一贬再贬,此次贬海南,真是“乘桴浮于海”了。两典的运用,恰如其分,隐喻了宋王朝现实社会的黑暗。第二,“舍之则藏”。孔子与箕子都是大智慧的人,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与反抗不是硬碰硬,而是注意韬光养晦,讲究策略。孔子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4]68“乘桴浮于海”就是“藏”,“藏”不是逃避而是韬光养晦,是一种斗争策略。箕子被殷纣王囚禁,“晦其明”,佯狂自保,也是“藏”的策略。“藏”大概就是鲁迅所说的“迂回”战术吧。东坡被贬海南虽是无奈,不是主动“乘桴浮于海”,也非“晦其明”佯狂自保,但,他身蹈死地,“九死南荒吾不恨”,也有“藏”的意味。第三,传播文明。这是东坡诗用两典的核心含义。箕子被武王封到朝鲜,把中华文明带到那儿,使其地得到开化。孔子是中华文化与文明的符号,“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他自觉而又自信地担负起传承文化与文明的历史重任。“天其以我为箕子”,“天未丧斯文”云云,苏东坡也是自觉而又自信地担负起传承与传播文化、文明的重任。海南时为蛮荒之地,与中原文明相去甚远,所谓“蛮夷之邦”。在海南,他看到当地多荒田,人们不重视农业,不得温饱,作《和陶劝农六首并引》“以告其有知者”[1]513,鼓励黎人从事农耕;看到海南人信巫,“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他“书柳子厚《牛赋》以遗琼州僧道赟,使以晓谕其乡人之有知者”[1]2092,告喻乡人重惜耕牛;看到当地风俗男守门户女出外劳作,他书杜子美诗“以喻父老”[1]2130;到儋东学舍访问,发现那里寂寥无声,他“永愧虞仲翔,弦歌沧海滨”[1]513,为不能像三国时的虞翻那样,虽处罪放之地而讲学不倦教化斯民,深感愧疚;听到邻家小儿诵书之声,他无比欣慰:“跫然已可喜,况闻弦诵音。儿声自圆美,谁家两青衿”,甚而由此想象此蛮荒之地或可出现像张九龄、姜公辅那样的大文人:“九龄起韶石,姜子家日南”[1]527;当他“半醉半醒”遍访黎民朋友,途遇儿童吹葱叶迎送时,顿感黎民知礼民风淳厚,欣然有孔子率弟子暮春而游的乐天遂志,优游放旷,不以天涯万里漂泊为意了:“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1]530。第四,坚守正道。箕子“晦其明”,孔子“舍之则藏”,都是一种政治策略,目的是“正其志”守其“道”。东坡一生坚持原则不随波逐流,不为自身利益而改变政治主张,王安石变法,他因反对“新法”而被贬,司马光上台“新法尽废”,他因在地方官任上看到新法的可取之处又反对司马光。在海南,他修订了在黄州作的《易传》、《论语说》,又以主要精力撰成《书传》,且打算写一部史评著作《志林》[1]1833。其目的,一是为传承中华文化与文明,自不待言;二是为弥合“日愈”“破碎”“分裂”的“大道”,探索真理宣扬真理,“我如终不言,谁悟角与羁”[1]520;三是“犹当距杨墨,稍欲惩荆舒”[1]521,坚守政治与学术正道。《孟子·滕文公下》:“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王安石初封荆国公,后封舒王。“荆舒”暗指王安石,“惩荆舒”即暗喻反对王安石的所谓“新学”。这就是东坡的“正其志”守其“道”。
三、“吾生如寄耳,岭海亦闲游”:“寄寓”与“闲游”
东坡刚到海南作《和陶还旧居》曰:“生世本暂寓,此身念念非。”[1]511在海南接到秦观告知将有移廉之命的信札复信曰:“廉州若得安居,取小子一房来,终焉可也。生如暂寓,亦何所择?”[1]1738《伏波将军庙碑》“寄命一叶万仞中”,《雨夜宿净行院》“一叶轻舟寄淼茫”皆含有“寄寓”思想。《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九死南荒吾不恨,此游奇绝冠平生。”把贬谪海南视为“奇绝冠平生”的“游”。《别海南黎民表》:“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1]540把“跨海去”比作“远游”。北归至江西作《郁孤台》:“吾生如寄耳,岭海亦闲游。”[1]553把连同贬惠在内的七年的岭海贬谪生涯视为“闲游”。“寄寓”是东坡人生观中非常重要的一面,“闲游”则是对“寄寓”思想的深化与升华,是东坡晚年重要的人生观。“吾生如寄耳,岭海亦闲游”,是东坡生命即将终结时对其人生观的形象而简洁的总结概括。
“吾生如寄”是东坡诗文中反复咏叹的主题,拙文《苏东坡雷州行迹考辨》一文考辨《题那梅溪》诗之真伪时已述及[8]。正因为“人生如寄”,所以要诗意地栖居。这是苏东坡善处逆境,随缘自适,始终保持乐观旷达的思想根源。东坡并非没有乡情之人,他有着浓郁的乡情,但,由于他认为“人生如寄”,所以他往往把贬所视为自己的故乡。在惠州作《丙子重九二首》曰:“三年瘴海上,越峤真我家。”[1]502《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别海南黎民表》:“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把海南作为故乡,而自己真正的故乡“西蜀州”反而成为“寄生”之地了。量移廉州时他又拟在廉州安居。这种随遇而安、反把他乡作故乡的思想行为皆源于东坡的“寄寓”人生观。
何谓“闲游”?《汉语大词典》释“闲(閒)”第(3)意为“安静”,第(4)意为“悠闲”。[9]74释“游(遊)”第(2)意为“遨游;游览”,第(3)意为“游憩;游玩”,第(4)意为“优游;逍遥”。[9]1497释“闲游”为“闲暇时到外面随便游玩;闲逛。”[9]87所谓“闲游”即安静地、悠然自得地游览、游玩。“闲游”在东坡作于江西的《虔守霍大夫监郡许朝奉见和复次前韵》再次出现:“大邦安静治,小院得闲游。”[1]554在《次韵阳行先》中“闲游”又作“天游”:“室空有法喜,心定有天游。”[1]554“天游”见于《庄子·外物》:“胞有重阆,心有天游。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心无天游,则六鑿相攘。”“心有天游”即心与自然共游。[2] 5259与自然共游即“天人合一”、“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之意,也即庄子的“无功”、“无名”、“无己”、“物我两忘”的“逍遥游”。“逍遥游”指人的精神由“必然王国”进入到“自由王国”。东坡《郁孤台》、《虔守霍大夫监郡许朝奉见和复次前韵》、《次韵阳行先》三诗用同韵,作于同一时地。“闲游”、“天游”与“逍遥游”同一含义,是东坡即将走向生命终点时对人生的深入思考和概括。流寓雷州的《六月二十日夜渡海》“此游奇绝冠平生”的“游”也是“闲游”、“天游”。“岭海亦闲游”指岭海七年的贬谪生涯如同“闲游”,“此游奇绝冠平生”指海南三年的贬谪生涯如同“闲游”,而且是东坡一生中最为“奇绝”之“游”。《自题金山画像》曰:“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2]5573“三州”代指东坡一生三次重大的贬谪,而儋州则是其人生最后一次贬谪,这次贬得最远,环境最恶劣,而东坡却把这次贬谪生涯视为“奇绝冠平生”的“闲游”,恶劣的自然环境、物质的匮乏、政敌的一再迫害,在其北归的途中统统化为乌有!说明东坡晚年的人生境界已进入到“物我两忘”的自由王国。这种“闲游”的人生境界其实也是《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所描绘的境界,东坡的心胸此时真如皓月朗照的大海一样宽广而又澄明!
一件事情可以佐证东坡此时所达到的人生思想境界的高度。众所周知,东坡由定州南迁途中“五改谪命”,再由惠州远贬海南,皆政敌章惇所为。东坡北归时章惇则被贬为雷州司户,本州安置。当时天下舆情以为东坡有望回朝主政,执掌宰柄。章惇之子章子平担心东坡“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给东坡写了一封示好的信(见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九),东坡即复信:
某顿首:某自仪真得暑毒,困卧如昏睡中。到京口,自太守以下,皆不能见,茫然不知致平在此。得书,乃渐醒悟。伏读来教,感叹不已。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益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鱼所知。建中靖国之意,可恃以安。又海康风土不甚恶,寒热皆适中。舶到时,四方物多有,若昆仲先于闽客、广舟准备,备家常要用药百千去,自治之余,亦可以及邻里乡党。又丞相知养内丹久矣,所以未成者,正坐大用故也。今兹闲放,正宜成此。然只可自内养丹。切不可服外物也。舒州李惟熙丹,化铁成金,可谓至矣,服之皆生胎发。然卒为痈疽大患,皆耳目所接,戒之!戒之!某在海外,曾作《续养生论》一首,甚欲写寄,病困未能。到毗陵,定叠检获,当录呈也。所云穆卜,反复究绎,必是误听。纷纷见及已多矣,安得此行,为幸!为幸!更徐听其审。又见今病状,死生未可必。自半月来,日食米不半合,见食却饱,今且速归毗陵,聊自憩。此我里,庶几且少休,不即死。书至此,困惫放笔,太息而已。[1]1811
东坡青年时与章惇是好友,后来交恶。信中,东坡对二人四十年来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只以“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益也”一句淡淡带过。然后对章惇“高年”(按,章时年67岁)“寄迹海隅”,先从精神上给予安慰,再非常仔细地叮嘱:“备家常要用药百千去”,“只可自内养丹”,并拟寄赠海南所作《续养生论》(后即寄)。凡了解苏章二人关系者读罢此信无不慨叹!说东坡“宅心仁厚”、“以德报怨”无不可,但这还不够,东坡之所为更主要的是他晚年“闲游”的人生思想境界所使然。
以上我们择要从三个方面谈了东坡流寓雷州半岛诗文的思想情感。被贬天涯,万里漂泊而生流落感、忧惧心乃人之常情、人之常性。以“鲁叟”、“箕子”自喻并躬身实践,第一,东坡是宋代的文化大师,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艺全才,切合他的身份与地位;第二,体现了他积极入世的儒家“事功”思想;第三,经历黄、惠之贬,东坡几起几落,由“庙堂”走向“江湖”,走向民间,与人民有了深入的接触和交流,也有了深厚的感情,传播文明“教化斯民”便成为他自觉的历史担当。“寄寓”思想自东坡青年时作《和子由渑池怀旧》就已初露端倪,自此贯穿其一生;“闲游”则是东坡晚年人生思考的结晶,是对“寄寓”思想的升华与超越,是其人生境界的巅峰。“寄寓”与“闲游”是佛老思想的濡染,是东坡“内修”与历练的结果。这些貌似矛盾的文化因子和谐地统一在这位文化巨人的身上,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晚年臻于澄明之境的超越万有回归大化的真实的苏东坡形象。他穿越了时而浑浊时而湛碧的历史长空,神采奕奕地向我们走来。
[1] (宋)苏轼.苏轼全集[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 (宋)苏轼,著.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卷二)[Z].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3]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
[4] 杨伯俊.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 (汉)司马迁.史记·殷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0.
[6]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东夷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0.
[7] 徐寒,主编.精注全译四书五经[Z].北京:线装书局,2006.
[8] 张学松.苏东坡雷州行迹考辨[J].文学遗产,2011,(4).
[9] 罗竹凤,主编.汉语大词典(第12卷)[Z].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
On the Emotional World of Su Dongpo's Poems and Articles Written in Leizhou, a Foreign Land: Clear Realm in his Late Years
ZHANG Xuesong, PENG Jieying
( Faculty of Arts,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Guangdong 524025,China )
Su Dongpo's poems and articles written in Leizhou are the recordation of his last ups and downs,which expresses his sense of driftage and apprehension, his personal comparison as “Confucius” and “Chi Tzu” as well as his thoughts that “Men's life is like boarding in this world.” and “Living in Mountainous areas is like traveling”.
Su Dongpo, foreign land, Leizhou, poems and articles
I206.6
A
1673-9639 (2015) 03-0031-06
(责任编辑 白俊骞)(责任校对 郭玲珍)(英文编辑 何历蓉)
2015-01-10
张学松(1955-),河南上蔡人,现为广东省雷州文化研究基地主任,教授。
彭洁莹(1972-),广东揭西人,现为广东省雷州文化研究基地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