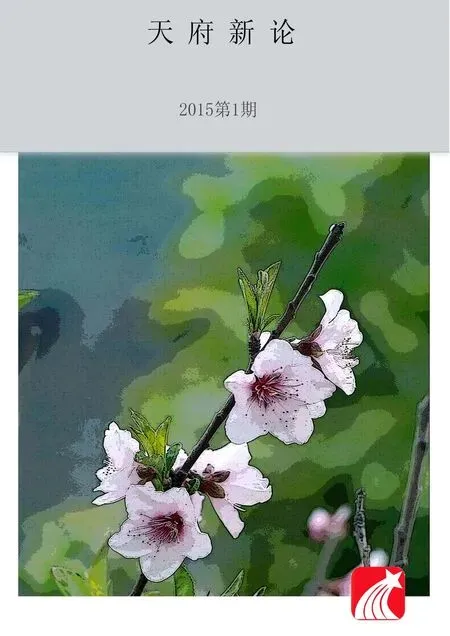政治现代化的范式:中共党史研究的新方法论
张 翔
一、导 言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主要革命党,以及1949年之后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集中反映中国政治现代化过程的许多典型特征。因此,对中共党史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总结中国共产党革命与执政的历史经验,更有利于更深层次地体认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逻辑理路。但近年来,中共党史研究开始逐渐陷入“内卷化”①美国人类学者克利福德·吉尔茨 (Clifford Geertz)用“内卷化”(Involutum)这一概念,形容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达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便停滞不前或难以提升至新的高级模式的状态,本文借用这一概念形容中共党史研究层次一直难以提升的研究格局。Clifford Greertz:Agriculture Involution: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rge in Indonesia,Berk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63,p.34.的困境中。许多研究课题不断地在重复相关的历史解读,或者在一定的时空范畴简单地挖掘史实细节。这些研究成果对于中共党史研究固然重要,也丰富了中共党史的内容体量,但客观而言,这些成果的理论层次主要还依赖于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学界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框架,缺乏理论层次的越迁,也就是所谓的“内卷化”困境。造成这种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论长期缺乏典型意义的突破,存在着一定的固化倾向,从而影响了学界从另一个理论层次或研究范式中分析与理解中共党史。
因此,在当前一个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全新历史时代中,从方法论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共党史研究已经成为一种研究必要,而且,这种重新审视的时机业已成熟。一方面,“内卷化”研究已经使理论层次的提升遭遇阻碍,从方法论角度转变研究视角与研究范式,从而提升中共党史的研究层次已经成为理论研究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中共党史研究中的理论成果为方法论转型积累了必要的理论素材。在这种背景下,深入地探讨与分析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论具有明显的理论意义。
二、典型的中共党史研究范式及原则
目前,无论是国内研究还是国外文献,中共党史研究大体遵循两种典型的研究范式:革命史研究范式与国家史研究范式。这两种范式遵循不同的原则,从不同的侧面反应了中共党史的面貌,但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现有研究中的局限以及理论的生长点。
革命史研究范式将中国近代史概括为“一条主线”,即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历史过程。如罗荣渠先生所言,“革命史框架下的中心问题是反帝反封建”〔1〕。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无疑承担了最为重要的历史角色,因此,革命史范式所关注是中国共产党在反帝反封建的进程中如何完成革命事业,并最终夺取国家政权。这种研究范式抓住了中国近代历史最为核心的特征—— “革命”,与“告别革命”〔2〕这一错误史观形成鲜明对立,从而成为中共党史研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范式,但同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局限性。一方面,过分地将研究中心聚焦于中国共产党本身。诚然,中国共产党是整个近代革命史的核心要素,但是,过分聚焦于中国共产党自身,则使相关研究对于整体性的政治、社会、经济要素缺乏全面的把握,对于中国共产党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缺乏宏观认识,也“疏于对中国总体发展的把握”〔3〕。另一方面,在革命史范式中,明确的伦理判断与意识形态话语过于明显。在以中国共产党作为核心研究对象的背景下,革命史范式的相关研究成果很自然地将国民党作为革命进程中一个对比的参照系。因此,“中国国民党为什么失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作为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梳理,这一议题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长期先入价值判断占据主流的研究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在革命进程中的角色“差异性”被强化。这种分析方式往往割裂了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的联接性,也忽视了双方在政治体制与政治发展上的延续性。
国家史研究范式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近代史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以“国家—社会”关系为轴心,研究这一轴心范畴内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结构与体制的变迁逻辑。这种研究方式聚集于近代以来“国家—社会”关系的变迁,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则成为贯穿于这一变迁中主要的线索之一。国家史研究范式突破了传统革命史简单地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的研究思路,开始着眼于中国共产党所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但是,国家史研究范式在事实上转移了中共党史研究的中心议题——中国共产党,在严格意上已经突破中共党史研究的学科界限,甚至还具有“把中国革命从历史舞台中心移开的倾向”〔4〕。因此,对于中共党史研究而言,国家史研究范式的缺憾在于,该范式模糊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学科规定性。
基于革命史研究范式与国家史研究范式在中共党史研究所面临的局限性,如何在明确中共党史学科规定性的基础上,避免中共党史研究过分地聚焦于中国共产党本身,已经成为理论界必须正视的一个关键问题。
三、政治现代化的范式:中共党史研究的新方法
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政治现代化的范式将试图破解上述的研究局限,从另一个视角开辟中共党史研究的新方法。政治现代化的范式以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定位与行为表现为研究轴心,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政治现代化的范式以中国共产党作为主要的研究议题。作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在传统政治模式向现代政治模式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政治现代化范式的首要内涵是确认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心议题的研究逻辑。另一方面,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政治现代化的进程紧密结合。以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心议题,并不意味着研究焦点单方面地集中于中国共产党本身。政治现代化范式是将中国共产党置于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着重关注中国共产党如何促进国家政权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这一核心问题。政治现代化的范式既着力扭转目前国家史研究中出现的“议题偏离”的趋势,也试图弥补传统革命史范式忽视政治生态与立足价值判断的不足。但需要指出的是,政治现代化的范式对于上述两种范式而言,并非一种“替代”,而是一种“平衡”。具体而言,这种“平衡”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历史”维度与“价值”维度相平衡
在当前国内,许多学者以先入的价值判断与伦理预设作为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前提,“大多数研究著作与文章都是从‘我党’、‘我们党’的立场出发,缺乏客观的第三者视角”〔5〕。这种研究方式可以称之为侧重“价值”维度的研究,虽然有助于学界总结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但过分以“价值”维度作为研究的前提,难免弱化中共党史的学术研究功能。其典型表现在,许多学者以“革命”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而历史层面的研究只是为论证“革命”服务,从而使“历史”维度成为“价值”维度的附属。正是基于此,著名中共党史学家张静如先生就曾提出要加强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以拓宽和加深中共党史研究。但是,随着各种近代专门史研究的拓展,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共党史研究中心议题的定位在一定程度上又被削弱。因此,在当前的中共党史学界,强化一种“历史”维度与“价值”维度相平衡的学术原则至关重要。这就要求当前的中共党史研究确立“两个坚持”:
一方面,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在近代历史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这个“坚持”是在宏观层面对“价值”维度的确认。当前的国家史研究虽然突破了“价值”维度的桎梏,但是又偏离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学科规定性。因此,作为一个专业学科,中共党史的深化研究首先要明确中国共产党在近代历史中的核心地位。这就要求确认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最革命的阶级,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进而取得全国政权。对这一事实的确认不仅是中共党史区别于其它史学研究的学科规定性,更是与西方国家中许多对中国共产党持负面态度的研究成果划清界限〔6〕。在“价值”维度上的明确是中共党史研究方法论转型的一个基本前提。
另一方面,要坚持对于“历史”维度与“价值”维度的“相对二分”。客观而言,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历史”维度与“价值”维度在本质上难以割裂,但两者可以做到一定程度的“相对二分”。在宏观层面要坚持“价值”维度,对于中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历史发展,则要坚持“历史”维度。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与国家政权、社会阶级之间呈现的动态关系,与前执政党国民党之间的政治关系等一系列中观层面以下的话题,应坚持“历史”维度,从而避免“价值”维度限制研究的深入。即使是一些早年已经做出“价值”判断的话题,例如知识分子是否应归属于“小资产阶级”等,都可以从“历史”的角度重新诠释与研究。这种“相对二分”不仅有助于中共党史研究立场的中立化与多样化,更能够促进中共党史研究新视角、新领域的开拓。
(二)“政治”维度与“伦理”维度相平衡
除了“价值”维度之外,传统的中共党史研究还特别有意识地建构中国共产党的“伦理”维度。这一维度的核心分为两个要点:第一,将中国共产党视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与革命史的主角;第二,以“革命”为内核,根据“革命”、“不革命”、“反革命”三个主要概念建构一个由肯定到否定的伦理谱系。“伦理”维度虽然对认识近代历史有助益,但是,简单地以“伦理”视角看待历史也无疑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无论是“革命”、“不革命”还是“反革命”,在历史上都各自具有不同的政治角色定位,有些甚至十分复杂。例如,国民党在早年是革命的,后期则演变为反革命;国民党右派相校于其它反革命是革命的,而相较于中国共产党则是反革命的;北洋政府相较于清王朝是革命的,相较于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则是反革命的。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因此,依赖“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等“概念标签”进行历史分析,是对近代史的一种高度简化,不利于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化。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不仅是革命的领导者与革命史的主角,而且是一个政党,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在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政党。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不仅具有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也具有一般政党所具备的典型特征。因此,从革命领导者的角度定位中国共产党则造成角色定位的单一化,局限了中共党史研究的视域与水平。
在这种背景下,中共党史研究不能仅仅在伦理上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史中的贡献做出相应的肯定,还需要从政治的角度,以一个典型政党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在近代历史中的角色。从中国的政治实践出发,中共党史研究应特别关注中国共产党作为政党的两大核心功能。
第一,政治整合功能。政治整合功能是一个政党的重要功能,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到执政的发展过程中,政治整合也是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的重要功能维度。作为一个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两个方面实现了政治整合。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政党的组织化网络整合全国政权。近代以来,在封建割据占主流的历史背景下,“国家政权的整合需要全社会以一致的力量向上运行才能完成”〔7〕,这就需要有统一的权威性力量。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自上而下严密的组织化网络形成一股“政治向心力”,完成了国家政权的整合,从而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地方割据与“统治分化”〔8〕。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沟通机制联接“国家—社会”关系。近代以来,在国家政权“碎化”的催化下, “国家—社会”关系处在“疏离”状态。国家政权无法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社会利益在政治过程中也难以得到有效的表达。正是因此,有学者把政治整合定位为“将国家与社会有机地连接起来,降低社会的政治离心力”〔9〕。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在政治层面表达社会民众,尤其是工人、农民的利益诉求,重新建构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政治沟通机制,从而形成“国家—社会”关系的耦合。作为政党功能,两个方面的作用事实上贯穿于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中,这应该是中共党史研究深化的一个重点领域。
第二,政治治理功能。在西方典型国家中,无论从何种角度理解政党功能,“竞选”都是政党功能的核心与落脚点。但在中国,基于近代以来“国家—社会”的“双弱”格局,中国共产党成为国家治理结构的中心,替代了国家政权履行治理功能。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严密的组织网络也为治理的实现提供了物质载体。由此可见,与西方典型国家以“竞选”为中心的功能维度不同,中国共产党的功能维度是以“治理”为中心。这种差异决定了中共党史需要在两个方面加强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治理功能的研究。
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在治理中的职责体系。在革命史的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在治理中的职责体系一直被忽略。加之,中国特殊的“党政关系”不断调整,中国共产党在实然层面承担什么样的具体职责,在应然层面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职责,理论界均未有明确的研究与定论。因此,中共党史学界立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与国家建设的历史范畴,归纳中国共产党在治理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职责体系。另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在治理中的运行机制。治理中国这样的一个历史复杂、构成多元的大国,需要执政党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在领导革命与国家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许多灵活的策略展开治理实践,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与社会反响。这些策略在很多地方已经形成一种特定的运行机制,联结中国特殊的“党政关系”。但在当前,对于这种运行机制在历史上如何形成、具体表现与未来的发展方向等诸多政治性问题,中共党史研究还无法做出回答。因此,加强对中国共产党在治理中的运行机制研究是中共党史研究深化值得考虑的一个课题。
(三)“现代化”维度与“革命史”维度相平衡
作为中共党史研究的主要范式,“革命史”范式重视政治现代化中的革命维度,将中共党史预置于“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过程中,而所有的史料搜集与分析都围绕这一斗争过程展开。事实上,作为一个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国共产党所内嵌的时代本质上是一个政治现代化的历史。可以说,政治现代化的历史是研究中共党史的一个轴心。脱离政治现代化这一宏观历史背景,中共党史的研究将陷于空洞化或边缘化。
由此可见,“革命史”范式不仅局限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时也使历史逻辑的叙述偏离了政治现代化这一主线。因此,中共党史研究需要超越“革命”与“反革命”的“二元结构”,并且重视“现代化”维度,从而实现二者之间的平衡。
一方面,从政治现代化的角度塑造基本概念。中共党史研究是一个政治学与史学交叉的学科领域,但在当前的研究视域中,史学概念占据中共党史研究的主流,而政治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则涉及很少。许多关于国家建设、政党发展、制度改革等基本的政治概念受限于固有的价值定位,尚未明确化与清晰化,甚至一部分研究还与国际学界存在着不必要的分歧。从这个角度上看,以下五个问题亟需在研究中加以重视:第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定位问题。第二,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权制度化过程中的功能问题。第三,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参与扩大的过程如何表达社会利益?第四,中国共产党如何建构合法性?第五,中国共产党如何组建现代政府,在技术性层面与传统政府又存在哪些区别?
另一方面,从比较现代化的角度审视中国共产党的角色定位。“现代化”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不同的国家有着具体且不同的表现形式。政治现代化受制于特定的政治传统、经济结构、文化观念等要素,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则更加明显,甚至还会在同样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出现异质性大于同质性的特点。作为一个后发的政治现代化国家,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除了立足于本身的革命性外,更要将其置于世界政治现代化的比较框架之中。
在西方典型国家中,多党制度贯穿于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因此,政党对于国家而言,是“多元整体的一部分”〔10〕。在中国,则不同。作为一个政党,中国共产党不是仅仅代表部分利益,而是在部分利益表达之中具有整体性的特点。因此,如费正清所言,中国共产党是典型的“国家主义政党”。作为国家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依赖自上而下的组织网络与严格纪律,具有较强的组织化力量,能够有效地动员与整合政治资源。对清末以来的“弱政府”而言,这些特点直接有利于政府能力的提升,并有利于抑制清末“割据化”的政治权力格局。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了“政党—政府”相统一的党政关系,这种党政关系既区别西方典型国家的“政党—政府”关系,也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之中。由此可见,从比较现代化的角度透视中共党史,将更有利于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关联,这对于中共党史的研究深化与议题扩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问题与讨论
除了上述的“三个平衡”外,中共党史研究在运用政治现代化范式的过程还存在若干问题需要讨论。
第一,政治现代化的范式是“政治学”与“历史学”的统一。中共党史是一个政治学与历史学交叉的学科,两个学科的协同作用是中共党史研究深化的一个契机。但长期以来,对中共党史的研究缺乏必要的政治学规范,造成了“政治学”与“历史学”的失衡。因此,政治现代化的范式并非排斥历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也并非对史实作任意式解读。而是,在历史学研究的基础上,注入政治学的基本概念与研究方法,使中共党史研究带有更加明显的政治学色彩,从而实现“政治学”与“历史学”的统一。
第二,政治现代化的范式是对传统研究范式的“扬弃”。中共党史是近代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涉及的历史主题是贯穿近代历史的“革命”进程。因此,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基于“革命”维度做出一定的价值判断是必要的。政治现代化的范式并非放弃传统中共党史研究范式中所包涵的“价值”判断,而是在明确基本“价值”维度的基础上强化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意义。毕竟,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中共党史研究不应拘泥于固定的价值判断,而应该从更广泛的视野中分析与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功能与意义。
第三,政治现代化的范式是要从政治生态系统的角度研究中共党史。无论是革命史范史,还是国家史范式,都忽略了中国共产党在近代历史中所处的政治生态系统。政治生态系统的角度意味着不能仅仅关注中国共产党,而要运用系统的方法将中国共产党置于整个社会系统中进行分析与考察,从中探讨影响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各种生态要素。任何政党都不可能脱离相应的政治生态系统而单独进行,而且,政治生态系统中的许多要素甚至是非政治性的。这就意味着,中共党史的研究需要在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议题的前提下,抓住“政党—国家”、“政党—社会”、“政党—政府”等诸多政治生态系统中的核心关系。政治现代化范式正是要从这若干主要关系的变迁中透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第四,政治现代化的范式还需要进一步地深化。研究范式是“一种观察与理解的基本框”〔11〕,在方法论结构中属于中观层次的方法。因此,在这一基本框架之下还有许多微观层次的具体方法需要进一步地探讨。客观而言,运用历史学范畴对中共党史进行研究,在方法论层次上已经趋于成熟,许多微观层面的方法都得到了良好的运用,并形成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政治现代化范式尚未成熟,如何运用政治科学的具体方法分析中国共产党,如何做到政治学与历史学在微观方法上的融合等问题都需要深入地分析与研究。
五、结 语
作为一次方法论的转型,政治现代化的范式对于中共党史研究具有明显的意义。首先,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系统性的政治逻辑。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近代的政治含义仅限于“革命”,而对于中国共产党整合政权、利益表达、统一国家、建设国家、制度改革等层面的政治逻辑则不够清晰。政治现代化的范式正是在“革命”逻辑基础上深化对其它政治逻辑的研究,从而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逻辑进行系统性的整合。其次,回应了西方主流学界对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的批评。长期以来,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西方学界难免片面地对中国共产党持负面论断。这种理解使西方政治学的典型范式在研究中国改革与发展的问题上屡遭困境,这不仅不利于中共党史的深入研究,也不利于中国政治研究的发展。政治现代化的范式不着意于引用经典的西方政治学范式,正是基于回应西方主流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的简单否定。第三,为比较政治研究提供了一个“对话”的方法论平台。传统的中共党史研究与国际主流的研究范式存在一定的出入,从而在中共党史领域,造成了国内研究与国外研究的“疏离”。政治现代化的范式本身就以比较研究作为基点,从方法论的角度为国内研究与国外研究搭建了一个“对话”的平台。
〔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商务印书馆,2006.48.
〔2〕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一世纪中国〔M〕.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1-5.
〔3〕〔美〕哈里·哈丁.美国当代中国学的演变与展望〔A〕.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C〕.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501.
〔4〕〔美〕周锡瑞.把社会、经济、政治放回二十世纪中国史〔A〕.中国学术 (第一辑) 〔C〕.商务印书馆,2000.201-204.
〔5〕杨凤城.中共党史研究的规范与方法〔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3).
〔6〕Kjeld Erik Brødsgaad & Zheng Yongnian,Bringing the Party Back In:How China is Governed,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2004,pp.4 -5,p.57;Roderick MacFarquhar,“The Anatomy of Collapse”,September 26,1991,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pp.5-9.
〔7〕张翔.以“组织化”抑制“割据化”:1911年-1949年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背景、范式与展望〔J〕.天府新论,2012,(3).
〔8〕桑玉成.政府间交易对政治整合的影响〔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1999,(9).
〔9〕谢岳.组织结构的制度化重建:开放社会的政治整合〔J〕.天津社会科学,2002,(2).
〔10〕〔意〕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M〕.王明进译.商务印书馆,2006.54-55.
〔11〕〔美〕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 (影印版)〔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32.